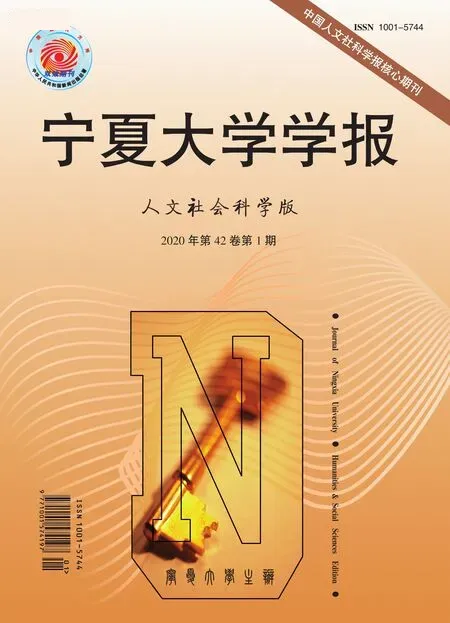清末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孙建伟
(陕西师范大学 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状态日趋显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仁人志士将变革的目光投向了语言文字, 认为汉字笔画繁多、形体复杂, 影响了时人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由此,不少热心人士主张改革汉字、减省形体。1895 年,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卷三下《〈汉书·艺文志〉辨伪》中指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 人事趋于巧变,此天理之自然也。 ”[1]这里康有为非常理性地思考了书体演变与文字繁简之关系,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了文字简易化的总趋势。 康有为对汉字形体繁难的认知,是其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由此引发了时人对汉字去留问题的思考。
总体来看,当今学者对于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研究,基本以介绍陆费逵、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的简化理论与实践,介绍《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发布与废止等情况为范式。 比较早期且较为全面介绍该时段汉字简化运动的是新加坡的谢世涯。 他在《新中日简体字研究》(1989)[2]中,针对这一时段汉字简化运动的发展,以“研究者”为线索,分别介绍了陆费逵、钱玄同、黎锦熙、陈光尧、胡怀琛、徐则敏、顾良杰、容庚等人的汉字简化理论与实践;他同时介绍了《第一批简体字表》。 从“学术史”视角考察该时期汉字简化问题的主要是凌远征。 他在《新语文建设史话》(1995)[3]中,重点介绍了陆费逵的《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钱玄同的《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等论著及“手头字”的推行、“简体字表”的公布等事件。 此外,苏培成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2001)[4]中,以“事件”为线索,分别介绍了陆费逵的汉字简化观、钱玄同对汉字简化的推进、胡适的“破体字”观、“手头字”的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发布与取消,同时还介绍了简体字相关的一些资料性著作和研究性著作。 另外,王凤阳的《汉字学》(1989)[5]、张书岩等编著的《简化字溯源》(1997)[6]、李宇明的《汉字规范》(2004)[7]、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2005)[7]等,对该时期汉字简化问题的探究与上面几位学者相似,此处不再赘述。
由上观之,尽管目前针对清末及民国时期汉字简化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但这类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对于这一时段汉字简化问题的关注点不够全面,对其发展脉络的梳理不够清晰,对一些重要节点或动向的把握不够细致,对该时段汉字简化发生、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的揭示不够精准。 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清末及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脉络,把握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为汉字规范史、汉字学史的撰写提供更多可参考的史料,为当今和未来的汉字规范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综合来看,我们可将其时汉字简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分为下面四个阶段。
一 解决字形繁难问题的摸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指清末兴起的“切音字”运动,集中发生在1892 年至1913 年间,典型地表现为一种被称作“简字”的拼音符号。 从该运动的发展来看,既涉及“简字”方案的制订和推行,也涉及其时学者对“简字”的推行理据、推行办法的争论等。
(一)“简字”方案的制订与推行
其时有不少学者在考察文字由繁至简这一演变总规律的基础上, 认为可以通过拼音的方式,消除汉字形体繁杂的问题。1892 年,卢赣章在《一目了然初阶》[9]中认为,记录汉语的文字较为繁难,故而主张采用拼音。 1896 年,蔡锡勇在《传音快字》[10]中指出,“从繁到简”是汉字发展的一种规律。 为普及教育,他在美国开始拟制汉语的拼音方案《传音快字》。 同样是在1896 年,沈学于《盛世元音》[11]中强调了文字的工具性,认为“古字寓形,今字寓音;欲利于记诵,笔愈省为愈便,音愈原为愈正”。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汉字的构件出发,实现拼音化。 1900年,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12]中认为,汉字的缺点在于形体繁难。 不过他反对单纯求简的速记式思想,认为“省手力而废脑力,书易就而读易讹”,因此主张用汉字偏旁作为字母。
多种类型“简字”的制定,使得用拼音替代汉字的“简字”之风愈来愈盛。 有的从理论上阐明推行“简字”之缘由。 1906 年,《竞业旬报》第5 期上刊发了《简字研究》[13]一文,认为我国识字的人少是由于汉字太难,于是出现了“简字”法则。 也有的从现实需求出发,指出推行“简字”之必要。 1910 年,《福建教育官报》第18 期上刊发了《论简字为识字捷法宜由军队试行》[14]一文,讨论了中国语言的南北地域之别。 该文认为中国文字太烦琐,主张以“简字为汉字之音符,汉字即京音之语号”;如此则“文字不相僢,语言可统一”,在军队中尤其便于推行,且是最有效果的。 文章还指出,军队的士兵来自各地,有的人不识字,再给他们教授汉字,便会非常困难;如果将他们迁移到他地,则困难更多,故而认为非常有必要给他们教授“简字”。
有的介绍了某地的“简字”课堂,指出“简字”推行之效果。1906 年,《竞业旬报》第6 期上刊发了《简字学堂》[15]一文。 文章指出,杭州行简字风气,杭州城内各营均已添加“简字”教科,其中以“旗营”办得最好。 到1909 年,《直隶教育官报》第18 期上刊发了《推广夜课简字学堂》[16]一文,主张推广夜课简字学堂。 有的介绍了一些有代表性的 “简字” 成果。1908 年,劳乃宣在《增订合声简字谱》[17]中认为,“语言画一”由“文字简易”始,故创制了《合声简字谱》,后又增订,故名为《增订合声简字谱》。 同年,《新朔望报》第4 期[18]、第6 期[19]上刊 发 了《简字谱》(1-2),介绍了劳乃宣的《增订简字谱》。
(二)对“简字”推行理据、推行办法的争论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学者针对“简字”应否推行、如何推行等,展开了剖析与辩驳。 典型表现为1910 年《宪志日刊》上刊发的《论简字与汉字汉语之关系因及其利害》(1-6)。 该文讨论了世人看待“简字”的正反两种态度。 并就汉字应否改从“简字”提出两条判别标准:其一,以是否适用于义务教育为准。 该文以《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数量为限,计算了每日学习汉字的数量,计算了学习全部汉字所需的时间。 由此认为,不改易无法实现教育之普及。 其二,以是否适应于“学战”为准。 该文指出,学汉字需五年、十年之功,认为它的繁难影响了学术之推广,致使中国之学术为少数人所掌握。 由此该文主张,应借“简字”切汉字之音。
二 字形系统简化思想的萌生阶段
虽然清末学者制订了多套“简字”方案,但由于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字形体繁难的问题。 故而其时学者逐渐对“简字”之路予以否定,又转回到汉字本身。 他们在考察汉字发展演变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将焦点对准了汉字中本有的减省形体,并归纳出了整理减省形体的方法。 同时,其时学者对清末及民国初期汉字改革、简化的种种做法也进行了思考与总结。 从相关成果的刊布时间来看,这一阶段集中在1908 年至1929 年间。
(一)否定“简字”之法,主张从汉字本身找出路
虽然“简字”之风曾颇为盛行,且有一定的推行效果。 但这种做法是否能够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能否实现古今文化之传承,能否切实减少汉字繁难的问题,颇为值得思考。 以吴稚晖、陆费逵、李思纯等为代表的学者,对“简字”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判,主张从汉字本身进行改良。
尽管其时学者总体上认为汉字“必然”会被废除,但它又不会立刻被废除。 故而学者们也在探索“过渡” 时期的办法, 或者认为可以对汉字进行简化, 或者认为可以采用社会上已经存在的减省形体。1908 年9 月,《通学报》第6 卷上刊发的《行用简字平议》综合评价了沈学、蔡锡勇、劳乃宣三人的简字之举,认为均不可取。 《行用简字平议》还认为,社会通行的汉字一年半时间即可学完,而且有自晋唐以来的行草字,简洁灵便。另外,1909 年4 月,《甘肃官报》第21 期上刊发的《推行简字之慎重》[20]认为,应慎重对待“简字”的推行。
主张放弃拼音文字采用汉字中已有减省形体的是陆费逵。1909 年1 月,陆费逵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21]中认为,汉字形体繁难,学习起来较为困难,不利于推行,并认为这是近人创制“简字”法的动因。 他进一步指出,近人创制的“简字”与旧有文字在形体上差异过大,不如推行俗体字。 其理由为俗体字是最便捷、最易推行的汉字形体。 陆氏的文章一经刊出,便有人发出了质疑。1909 年2 月,沈友卿在《论采用俗体字》[22]中,对陆费逵的俗字主张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可采用的俗体字数量有限,大量由这些俗体作为构件的字并没有相应的俗体可替代,从而无法推广,其作用极其有限。 针对沈友卿的质疑,1909 年3 月,陆费逵在《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字〉》[23]中进行了回应,并继续主张采用俗字。
认为其时应该“暂时”保留汉字的还有李思纯。1920 年,李思纯在《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24]中认为,汉字将来“必归废灭”,但其时只能逐渐补充,不能根本废弃。
(二)探索搜集已有减省形体的方法和步骤
尽管其时有很多人主张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但这种根本性质的转变非一时可成, 故而以钱玄同、陆费逵、陈光尧等为代表的学者,努力探索采录汉字中减省形体的方法及步骤。
1918 年,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25]中,反对改良汉字,反对推行“简字”,主张废除汉字,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语)。不过钱玄同又认为,改用拼音文字需要“十年”之久,并主张这十年时间内仍然使用汉字。 故而他于1920 年2 月,在《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26]中拟出了搜集固有形体的八种方法:其中“采旧”的有五类,即采取古字,采取俗字,采取草书,采取古书上的同音借字,采取流俗的同音借字;“新造”的有三类,即新拟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借义字,新拟的减省笔画字。
至1922 年8 月,钱玄同又在《汉字革命》[27]中指出,在汉字改为拼音字母的“筹备”期内,对于汉字的补救办法为:写“破体字”,即凡笔画简单的字,不论古体、别体、俗体,都可采用;写“白字”,国音同音的字少用几个, 选择笔画较简而较通行的字,去代替几个笔画较繁而较罕用的字。 同月,钱玄同还发表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28],转录了他此前归纳出的八种方法。
自钱玄同归纳出了搜采减省形体的八条规则之后,该时期的学者们大都转录或提出了相类似的整理办法,集中收录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29]中。 比如何仲英的《汉字改革的历史观》、凵//的《对于简笔字之我见》、 正厂的 《过渡时期中的汉字》、周起鹏的《汉字改革问题之研究》等。
(三)对清末及民国初期汉字改革思路的总结与思考
自国人创制的第一个“切音字”方案发布后的30 多年间,针对汉字的繁难问题,其时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 不过,这些方案是否能够既有效消除汉字的繁难问题,又能满足记录汉语的需求, 同时也不至于割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则需要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 对此类问题进行考察的主要有陈光尧、杨端六、陈登皞等。
1927 年,陈光尧在《中国文字趋简的历史观》[30]中认为,汉字的演变总体上趋向便利,并列表展示了各字体的基本情况,比如时代、笔画数、字数、创制者等。 他还梳理了“近代的简字”,主要有宋、元俗字,王照、劳乃宣的“简字”,国语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等。 此外,陈光尧在《〈简字举例〉答客难》[31]《〈简字问题〉答客难》[32]《发起简字运动临时宣言》[33]等文章中, 也讨论了清末及民国初期汉字改革、简化的发展进程等问题。
1928 年8 月,杨端六在《改革汉字的一个提议》[34]中主张改用“省笔字”,并将“省笔字”分为四类。 第一,省笔字;第二,俗字;第三,古字;第四,草书。1928 年9 月,陈登皞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具体方针》[35],其副标题为“反对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音”。 陈登皞指出,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总的趋势是“由繁而简”,只是这种趋势是渐进的,颇为迟缓。 他进一步认为,应大力提倡简字,认为其时流行的简字数目有限。 1930 年陈登皞在《中国字应怎样改良》[36]中也梳理了其时汉字改革、简化的种种做法,认为进行文字简化,是中国文字自身改良的一个好办法。
此外,该时段还有不少类似的成果,集中收录在1929 年9 月河南教育厅编辑的 《中国新文字问题讨论集》[37]中。 比如薇芬的《中国文字改革的管见》、企重的《我亦一谈改革中国文字》、李作人的《改革中国文字问题》、超的《论简字》、吴健民的《谈谈文字的改革》、刘仲昌的《民众教育与汉字革命》等。
三 字形简化成果的汇聚阶段
在经历了第二阶段的理论探究之后,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工作进入了更具实践特色的第三阶段,其时间区间集中在1930 年至1935 年。 一方面,学者们对识字教育该教授哪些汉字,教授多少汉字,从哪些汉字开始教起,如何教授等问题,进行了更为科学的测算和分析;另一方面,他们搜集整理出了多种简化字形表。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1930 年至1935 年间,其时学者们整理出的简化字表有12 种,且大都以“繁简字对照”的模式进行展示。
(一)对汉字形体难易度的量化分析
民国初期的学者们逐渐用实验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对识字教育中教授的具体字形、所教字量、教授步骤等进行了更为科学、深入的探究。 相关研究者主要有艾险舟、徐则敏等。
1930 年3 月,艾险舟的《识字教学之研究》[38]从识字教学的视角认为, 要想民众教育发展得快,便不能不采用简体字教学。 1930 年10 月, 徐则敏在《汉字难易分析的研究》[39]中认为,汉字的繁难影响了民众教育之推行,并引用了艾险舟《识字教学之研究》中的相关观点为佐证。 徐则敏还整理出了《历代汉字增加表》,认为要想求得普通所用的字,最好的办法就是 “统计法”, 将普通书报中的字加以统计,从而可了解每个字常用的价值。 在徐则敏之前,陈鹤琴、敖弘德、王文新三人已进行过相关统计,他又在上面三位的基础上抽取出常用字2400 个。
属同类的还有徐则敏的《汉字笔画统计报告》[40]、李步青的《拟选民众应识的字之标准及其方案》[41]、周先庚的《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42]、邹鸿操的《简字与原字书写速度之比较》[43]、章荣的《简字的价值及应用之试验研究》[44]等。
(二)“俗字”问题及“俗字集”
搜集并整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俗字”,是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具体表现之一,相关研究集中在1933 年至1934 年间。 学者们多是在分析“俗字”的特点、存留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搜集“俗字”的方法、步骤、原则,继而整理出“俗字”表。 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曲元、陈光尧、刘德瑞、徐则敏等。
1930 年,刘复、李家瑞编著的《宋元以来俗字谱》[45]在北京出版。 该书共搜集《古列女传》《全相三国志平话》等十二种书中的俗字1604 组,6240 个[46]。刘复认为,借此可观八九百年来俗字的演进和变化的轨迹。 从实际效果来看,本书虽为研究俗字而作,客观上却推动了简笔字运动。1933 年11 月,林语堂在《提倡俗字》[47]中对“别字”与“俗字”进行了区分,并明确提倡“俗字”。 1933 年12 月,曲元在《俗字方案》中搜集并列举了报纸、杂志上常见的俗字300组。 曲元赞成俗字,还主张创造俗字,提议向小市民搜集俗字,认为他们是俗字最广泛的使用者。 1934年2 月,陈光尧发表了《简字九百个》[48],他从《中华简字表》中摘录出了900 个简字,并给出必要注释。1934 年3 月,刘德瑞在《讲义上正俗字之商榷》[49]中考察了写讲义的人使用俗体字的原因,并将日常通用的俗写字搜集起来,连同正字按组排列,制成正俗字表,共计150 组。 1934 年7 月,徐则敏在《550俗字表》[50]中认为,俗字正合乎汉字简易化的进程。
关于“俗字”问题的讨论,还有滢的《提倡俗字》[51]、温锡田的《提倡“俗字”“别字”》[52]、杜子劲的《奉天承运的俗字》[53]、补庵的《说俗字》[54]等。
(三)“手头字”及“手头字”运动
“手头字”问题是该时期继“俗字”问题之后,学者们集中讨论的又一个热点。 他们在对“手头字”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梳理了“手头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整理出了“手头字”字集。 虽然“手头字”运动在1934 年8 月间便已发起,但大量的研究文献则集中出现于1935 年。 该论题的研究者主要有“手头字推行会”、张新夫、陈子展、胡行之等。
1935 年2 月15 日,张新夫在《民众读物应采用手头字的建议》[55]中认为,“手头字”指人们日常手头上写的便当字,与“简字”相近,但比“简字”更“自然”且“通行”。1935 年2 月25 日,陈子展在《关于手头字》[56]中指出,该年度中国文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手头字的推行,它是继“口头语”之后语言文字上的又一革新;他听闻“手头字推行会”大致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八九月间,《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不久将发表。 至1935 年3 月,《生活教育》杂志第2 卷第1 期上刊发了《推行手头字缘起》[57]。 该文指出,人们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便当”字,大家手头上都这样写,但书本上却不这样印,从而造成要认识两种字形的问题。 因此该文主张将“手头字”铸成铜模铅字,也用在印刷上。 “手头字推行会”选出了常用的300 个“手头字”作为第一期字汇;并计划之后再陆续增加,直到“手头字”和印刷体一样为止。1935 年5 月,胡行之在《关于手头字》[58]中认为,“手头字”的推行是必然趋势。 对于“手头字” 的数量, 胡行之认为除了各地通行的以外,还可以再行搜集,于是他列出了新整理的80 组“手头字”。
此外,该时期关于“手头字”的研究成果还有馥泉的《手头字运动》[59]、吕思勉的《反对推行手头字提倡制定草书》[60]、丰子恺的《我与手头字》[61]、坚壁的《关于手头字》[62]、杰的《为什么要提倡手头字》[63]等。
(四)“简体字”的甄选及推行
“简体字”又称作“简笔字”。 与“俗字”“手头字”两个论题相比,民国学者们对“简体字”的研究持续时间更长,相关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 从时段来看,集中在1934 年至1936 年间。 尽管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汉字最终将走向拼音化道路,不过更多是将目光投向如何系统提取出已有的减省形体以供社会使用。 此外,学者们还重点讨论了“简体字”或“简笔字”的推行范围及推行办法。 另外,在《第一批简体字表》发布前后,学者们整理出的以“简体字”或“简笔字”命名的“文字表”有12 种之多。
1934 年2 月,钱玄同在《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64]中认为,简体字不仅适用于平民教育,在小学、中学教育中也应推行。 他还指出,要普及简体字,首先需要规定简体字的写法,从而需要搜采故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作为素材; 有了标准体,就可以用其偏旁组织新的“配合”;如果还不够,便可用这些构件造新的简体字。 1934 年9 月,黎锦熙在《大众语文的工具——简体字》[65]中引用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搜采故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胡适的《用历史的眼光说明简笔字的价值》三篇文章,以阐明他对汉字改革、汉字简化的观点。黎锦熙赞成“简体字运动”,认为其时只需按“自然”的原则去做,而不可强定系统、臆造新体。 1934 年11 月,吴稚晖、曹聚仁在《谈简笔字》[66]中认为,应先采用“久已公认”的“简笔字”,不能创造得太“生疏”,那样跟“本字”成了两个字,读旧式书报又不认识了。 1934 年12 月,童仲赓在《简笔字的自然趋势》[67]中从汉字发展的历史审视简笔字的演进趋势,认为与其“改弦更张”,不若“因势利导”。1935 年2 月,钱玄同在《与黎锦熙汪怡论采选简体字书》[68]中详细说明了采选简体字的目的、原则、所据素材及应注意的问题等。
至1935 年8 月21 日,《“中央日报”》 刊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69],其中含有颁发文件:《部令第一一四〇〇号》《第一批简体字表》,字表“说明”,推行办法,选编经过。 自此之后,有非常多的学者针对该字表进行了多视角研究。 相关论题主要包括:《字表》所收的简体字合理与否,推行方法科学与否,简体字与识字教育、工作效能的关系,简体字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汉字简化及简体字的历史观等。
除上所述外,同类的还有钱玄同的《论简体字致黎锦熙汪怡书》[70]、黎锦熙的《关于简体字的各方意见的报告》[71]《简体字之原则及其推行办法》[72]、顾良杰的《吾人对于简体字表应有的认识》[73]、黎正甫的《简体字之推行与阻力》[74]等。
四 简化相关问题的总结与反思阶段
1936 年1 月,《第一批简体字表》(以下简称《字表》)被勒令停止推行。 虽然该《字表》从正式发布到被废止尚不足一年,但汉字简化运动和关于汉字简化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其时学者对汉字简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且深入的总结与反思。 这一时段跨度较长,从1936 年一直持续到1949 年。
(一)对汉字的前途和命运之讨论
在《字表》发布后,民国时期的学者们从汉字改革的各流派出发,重点围绕“简体字”是否是汉字改革的未来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论。 或者认为应该彻底走拼音化道路,或者认为“简体字”之路也行得通,或者认为应该“多路融合”。
其时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拼音化道路才是汉字改革的目标方向, 其典型代表有萧迪忱、 之光、达牛、邓渭华等。 这些学者或认为“简体字”之路是“换汤不换药”,或认为“简体字”破坏了汉字的系统性,或认为汉字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等。
1935 年9 月,萧迪忱在《汉字改革问题的回顾和展望》[75]中指出,汉字必须要改革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如何改。 对此他认为,限制字数、减少笔画、造新形声字、加注字音,都是“换汤不换药”,虽能降低难度,但不能成为便利文化的工具。 他最终认为,G.R.的“拼音法式”能够体现中国语言的特点。 1935年10 月,之光在《简体字在文字运动中的地位》[76]中认为,简体字只是写起来简便,在读音和记忆上是一样的;并且“简体字”是有限的,无法将所有的汉字都减省为两三笔,进而认为汉字早就应该简化为拼音文字了。 1936 年10 月,达牛在《从汉字改革运动说到中国的前途》[77]中认为,既然汉字已经失去了时代的需要, 则应爽快地推进 “拉丁化新文字”。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邓渭华,1937 年5 月,他在《汉字改革的途径》[78]中分析并总结了汉字改革的八种方法,认为只有“欧化”才是最终的唯一出路,即走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之路。 此外,王力的《汉字改革》[79]、陈耐烦的《中国文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80]等,也持类似观点。
与上面的看法不同, 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简体字”自有其历史渊源和推行价值,可以继续推行。 对于具体简化方法,学者们大都认为,应该以近代的俗体字为核心顺势而为,同时也可以适量采用行书、草书、古字的写法。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黎锦熙、陈光尧、张世禄、张公辉、曹伯韩等。
1936 年6 月,黎锦熙在《注音符号与简体字》[81]中简单梳理了甲骨文、钟鼎文、小篆中的简体字情况。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简体字之所以也有价值,是因为它是顺着汉字自然的趋势发展的。 1938 年11月,陈光尧在《简字运动概说》[82]中考察了历史上人们提倡简字的动机。 同年12 月,陈光尧又在《科学教育与简字》[83]中从推进科学教育的视角认为,汉字必须要进行改革,推行简字为重要的思路。 1946年4 月,张世禄在《汉字的特性与简化问题》[84]中讨论了汉字的改革,认为不应该把汉字的改革和废止混为一谈;并强调指出他所谈的“汉字改革”是在顺应汉字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对其加以调整。 另外,1948 年4 月,张世禄在《汉字的简化运动》[85]中亦为简体字的继续推行进行了辩护。 1946 年7 月,张公辉在《国字整理发扬的途径》[87]中主张选取常用的形体,消减罕用的样式,废除变体、繁体的歧异,寻求大写、小写、正书、草书的近似,以达到简便的目的。1946 年12 月,曹伯韩在《简体字的检讨》[88]中认为,简体字的结构也完全符合汉字的造字原则和演变规律。
也有学者从更为综合的视角出发,认为应该将标音符号运动、简体字运动等方法结合起来,为汉字的改革和简化探索新的方向。 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沈有乾。 1937 年5 月,沈有乾在《汉字的将来》[88]中主张“三路会师”。 即将标音符号运动、简体字运动、基本字运动这三种方法的好处发挥出来,从而可以产生“第四种”方法。
此外,相关讨论还有童振华的《中国文字的演变》[89]、史存直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过去和现在》[90]、吴一心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之史的综述》[91]等。
(二)对汉字繁简体的量化和质化研究
学者们除了从理论上考察简体字应否推行之外,也更注重从实验统计和数理分析的视角,考察繁简体字与学习效率的关系,还进一步上升到了认知心理的层面。
前文我们已提及,其时除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外,类似的简体字表有10 多种。 在《字表》被停止推行后, 有不少学者结合这类字表中收录的减省形体,对汉字繁简体的教学效度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实验研究,相关研究者主要有周学章、杨骏如、曹芷清、薛鸿志、李爱德等。 尽管一些人认为,简体字对于减少汉字的繁难问题作用有限,但学者们总体上认为,在认识、抄写、默写等方面,简体字都较繁体字有明显优势。
1936 年4 月,杨骏如、曹芷清在《估定简体字学习效率的比较实验报吿》[92]中,对已有的繁简体字实验进行了简要述评,主要涉及章荣的《简字的价值及应用之试验研究》、周学章的《繁简字体在学习效率上的实验》。 之后该文论述了其实验过程与结果。 由此他们认为,在认识、抄写、默写等方面,简体字都较繁体字有明显优势,并极力主张在各种教育中应采用简体字。1948 年1 月,刘公穆在《从工作效率观点提倡简字》[93]中认为,其时简体字已经普遍应用,通用的俗体字约为520 个字,简写字约为450个字。 其时的常用字有7000 多个,因此简体字约占常用字的1/7。
属同类的还有张定华的《简体字与行政效率》[94]、周学章的《繁简字体在学习效率上的实验》[95]、沈有乾的《简体字价值的估计方法》[96]、杨骏如的《简体字在国语教学上效率的实验》[97]、薛鸿志的《汉字简正写法之比较》[98]、周学章和李爱德的《繁简字体在学习效率上之再试》[99]等。
除采用实验分析和数理统计外,以艾伟为代表的学者,又将汉字难易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认知心理的层面,这是其时学者们考察汉字简化问题的又一个新视角。1936 年6 月,艾伟在《从汉字心理研究上讨论简体字》[100]中认为,“简字表”适合于一切大众和小学读物采用, 但不宜繁简二体同时并用,因为这是违反学习心理的。 至1947 年9 月, 艾伟在《汉字心理研究之总检讨》[101]中又指出,字形的问题重点涉及笔画数、字形组织、形与声、形与义的关系、字的认识和默写、字形的记忆与保持、字形观察的心理特征等。 他认为,字形学习的困难在于笔画数的增多和字形组织结构的复杂。
综上来看,我们将清末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解决字形繁难问题的摸索阶段,字形系统简化思想的萌生阶段,形体简化成果的汇聚阶段,字形简化相关问题的总结与反思阶段。 不过,上面的四个阶段在具体发展时,并非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突然结束,故而我们文中给出的时间节点存有交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