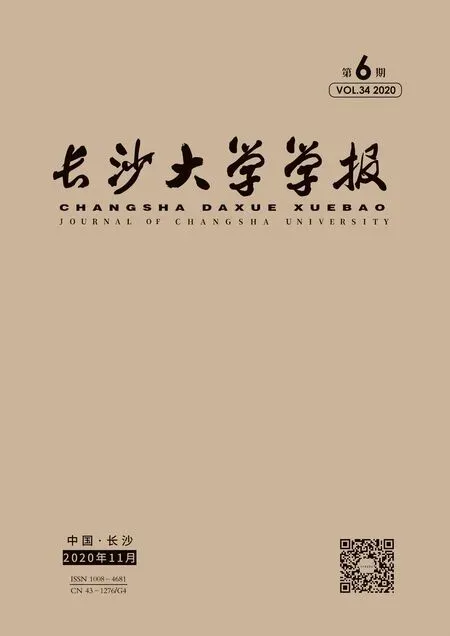看与被看:莫里森小说中的凝视机制研究
刘晓露
(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在《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2006)一书中,收录了“凝视”词条:“凝视”是指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式。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并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当今对凝视的批判已经成为文化批评主义者用来反抗视觉中心主义、父权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的有力武器[1]349。黑人批评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就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1952)中将凝视与种族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结合起来,阐述了黑人群体在不同境遇里遭遇的白人眼光。法农认为,白人凝视就如“一个不寻常的沉重包袱,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并最终导致黑人“对身体的认识是一个彻底否定性的活动”[2]84。作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的文学创作始终关注黑人主体是如何在以白人文化为主宰的美国文学中被构建起来的。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白人审美和文化话语中的黑人被塑造成无法言说的他者,这种意象在文学、电影及其他视觉形式中表现为黑人形象的客体化、简单化和模式化。在性别和种族交错的立场上,莫里森的艺术探索超越了女性客体化的界限,她早期的四部小说《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娃娃》(1981)可谓艺术性地再现白人凝视导致黑人主体心理创伤的力作。本文试图将其置于现代商品文化背景之下,探讨莫里森作品中关于“凝视”的不同机制,探究主导社会秩序的凝视是如何被她的黑人角色所内化,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通过主人的凝视构建自我、成为他者的。
一 《最蓝的眼睛》:影像凝视与自我否定
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揭示了西方社会将美的标准强加至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女性身上所带来的摧毁性。在小说的序言中,她批判性地指出,“身体美作为一种美德的概念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3]2。在她看来,黑人的贫困生活并不独特,独特的是把自己视为极度丑陋的这种自我感知。
当你注视他们时,你会纳闷他们为什么这么丑陋。你再仔细观察也找不出丑陋的根源,之后你意识到丑陋来自信念,他们对自身的信念。似乎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子给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而他们不加质疑便接受下来。主子说:“你们都是丑陋的人。”他们四下瞧瞧,找不到反驳此话的证据;相反,所有的广告牌、银幕以及众人的目光都为此提供了证据。“是这样”,他们对自己说:“这说的是实话。”他们把丑陋抓在手心里,穿戴在身上,去闯荡世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付它[3]24。
这个隐匿的神秘主子暗指西方社会白人主宰的意识形态霸权,它将凝视作为工具,剥夺了黑人的主体价值,强加给他们关于美的价值标准,给他们分配低微的社会位置。同时,莫里森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意识工具的普适性,当凝视聚焦在广告牌、银幕或其他媒介时,众人的目光皆被吸引,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小说中,佩科拉的母亲波莉从小在冷漠的环境中成长,缺乏家庭温暖,生理上的缺陷进一步造成她的自卑,而婚后的家庭生活并不如意,丈夫乔利的酗酒和暴力、巨大的经济压力,都让她对生活充满了抱怨。为了从日常的辛劳、贫穷和疏离中找寻某种意义,她跟随着数百万人逃离到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经典电影的梦幻中。波莉告诉读者:“他们会熄灭灯光,影院里一片漆黑,然后银幕亮了,我会立即进入影片情节。”[3]78在现代电影工业一系列的诱人操作下,波莉作为银幕的观者,她的自我意识被抹去,和其他观者一样,他们深深地沉浸在电影的真实中,在故事世界中与理想自我相认同。“看电影受教育之后,她会以绝代美女的尺度来衡量每一张她见到的脸,这个尺度是她从银幕上得到的最大收获。”[3]78美国学者罗伯特·雷(Robert Ray)在关于好莱坞电影研究的专著中指出,影视作品制作的痕迹会被一一抹去以建立现实的影像幻觉,观众被鼓励与大银幕上的角色建构认同[4]34。银幕上所展示的女性客体是为了满足男性凝视的愉悦性目的的,因此这种认同有着将女性置于自我否定深渊的危险,而波莉,作为一个热衷于观看白人电影并极力模仿电影中女明星妆容的黑人女性,势必承受着更为复杂的自我否定,因为她的同类是几乎不可能出现在银幕中的任何地方的。在白人电影的熏陶下,波莉开始把外貌美与道德美等同起来,并竭力把自己的黑人性剥离出去。她被迫将一个陌生的、完全不现实的女性美的标准适用于她自身,这种矛盾所带来的极度失望最终造成了她心理的扭曲,导致了她自我身份——女性、黑人、贫穷的三重贬值。
事实上,影像凝视的内化及其相应的好莱坞造星机制几乎扩展到小说中所有女性角色身上。黑人姐妹克劳迪娅和弗里达被父母的房客亨利先生比作白人女星葛丽泰·嘉宝和琴吉·罗杰斯。有着浅褐色皮肤的混血女孩莫丽恩告诉朋友们有个黑人女孩想要把她的头发做成女明星海蒂·拉玛尔那样的,而黑人女性内化的欲望和不可得之间的矛盾使这成为了一个笑话。佩科拉喜欢用印着白人童星秀兰·邓波儿头像的杯子喝牛奶,只为触摸和欣赏秀兰那张甜美的脸蛋,幻想自己神奇的转变。
小说中,波莉和乔利的女儿,12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是白人主宰的社会凝视机制下最大的牺牲品。她出生在下层阶级家庭,暴力和贫穷为女孩的成长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她从未得到过生活的馈赠,与生俱来的低等和丑陋使她试图通过得到一双白人那样的蓝眼睛来逃避凝视、减轻痛苦,但最终导致了混乱、失常,以及破碎的自我形象。在佩科拉身上,也曾经存在过发现自我的可能性,在去杂货店买糖果的路上,佩科拉试图解开一个永恒的审美悖论:蒲公英是野草还是美丽的花朵?在与自然的交流中,佩科拉与蒲公英产生了某种意象上的关联,她也在试图发现自己是一株野草还是一朵拥有某种价值或未被发现的美丽的花朵。佩科拉有着孩童看世界的坚定天真,她能注意到成人往往忽视的细节——人行道上的裂缝、地上的野草等等,她能不受阻碍地辨认事物的本质。然而,对佩科拉而言,这种孩童的天真和自我肯定的瞬间太短暂了,她走进杂货店买玛丽·珍糖,这种糖的包装纸上印着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玛丽·珍的小头像,“糖果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3]32。而店主雅克鲍斯基对佩科拉的漠视是小说关于凝视最细致的描述。
在视网膜与物体之间,在视觉与景物之间,他的目光犹犹豫豫,徘徊不定。在时空的某一固定点上他感觉没有必要浪费他的眼神。他并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看得见的东西。一个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小店老板,满嘴土豆、啤酒味,满脑圣母玛利亚,怎么会看得见一个黑人小女孩呢?他的全部生活经历告诉他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是不值得,也是不必要的[3]31。
莫里森在这里构建了主子/白人与他者/非白人之间的凝视关系循环。主子望向他者,看到了对方人性的缺失;反过来,他者望向主子,看到了主子的全能,并产生了自我否定。两者共同创造了凝视循环,肯定了对对方和对自我的非人性化评估[5]96。佩科拉意识到对许多人来说,她其实是不存在的。佩科拉的自我在与白人凝视相遇后分崩瓦解,她知道问题的核心在于她的黑皮肤,正是这一成不变的“黑皮肤引起了白人眼神里带有厌恶之感的空白”[3]31。佩科拉与白人凝视的对接以反射性的自我否定而结束,这个事件对佩科拉而言是心理上的转折点,她选择相信蒲公英是丑陋的杂草,自我憎恨植根入她的内心深处,佩科拉将一切不幸的根源归结于没有一双白人那样的蓝眼睛,她的自我被不断腐蚀直至陷入最后的疯狂。
二 《秀拉》:视觉伦理与镜像凝视
在第二部长篇小说《秀拉》中,莫里森把视觉关系的焦点转移到人物行为中看(see)与注视(watch)的伦理性区别。《秀拉》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也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峰期。小说以女主人公秀拉与朋友奈尔的成长及友谊为主线,描写了20世纪40、50年代俄亥俄州梅德林市一个富有传奇和魔幻色彩的黑人社区“底层”的生存境况和生活变迁。如果说《最蓝的眼睛》呈现了白人凝视及其构建的社会意识形态对黑人自我产生的毁灭性后果,那么《秀拉》中,成为共同体的黑人女性在自我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开始质疑这一模式。故事的两个女主人公,秀拉和好朋友奈尔,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密不可分、互为补充。童年时期的一次意外事件成为她俩共同的秘密,将彼此的人生捆绑在一起。
“她们在阳光下奔跑,耳边呼呼生风,这风把她们的衣裙紧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后来她们来到一处枝叶繁茂的四棵大树围成的四方形荫凉地方。”[6]54她们像进行某种仪式般在大树下挖了个洞,又一起把它埋上,两人结成了最亲密的同盟。然而,这种情感上的联结以一种意料之外、骇人的方式达到高潮——秀拉失手将黑人小孩“小鸡”甩入水中溺死。当地人并不知道小男孩溺水的真正原因,这个秘密永远埋藏在奈尔和秀拉之间,成为文本潜在、隐藏的叙事动力。多年后,在故事的结尾,秀拉的外祖母伊娃质问奈尔当年为什么要淹死“小鸡”,奈尔立刻否认了这个控诉,说是秀拉做的。
显然,伊娃知道两人对此事负有共同责任,也对这一事件中的视觉关系有着细致入微的伦理意义上的理解。她对奈尔说:“你也罢,秀拉也罢,又有什么区别?你当时在场,你眼瞅着(watch) 发生了那件事,对不对?要是我,我绝不会看(watch)一眼的。”[6]166之后,奈尔独自离开,回想着伊娃的控诉,长久以来困扰她的谜题解开了,那正是她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着的、必须为此事负责的内疚感。正是隐藏在童年时期的这些记忆碎片把她引向秀拉,她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当年作为旁观者的内心活动。
伊娃说“你眼瞅着”(watch)是什么意思?她怎么居然会看到呢?她是在当场。可伊娃没说“看见”(see),她说的是“眼瞅着”(watch),“我当时不是眼瞅着(watch)。我只是看见了(see)。”不过她反正在那儿,事情就是这样,那种旧日的感觉和旧日的问题又来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悄悄地为自己的平静感到骄傲。当时秀拉手足失措,她却仍能控制自己,她面对着秀拉那惊恐羞惭的眼睛深表同情。如今看来,她当时所想到的成熟、安详和同情,不过是随着一阵欢快的冲动之后而来的镇定。就像河水在“小鸡”身体溅出的漩涡上面平和地复原了一样,她的欢快为满足所冲刷掉了[6]167-168。
奈尔带有快意的旁观实质是一种偷窥欲的满足。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指出,“人是一个受本能愿望支配的低能弱智的生物”[7]87。偷窥其实来源于自我的压抑。被压抑的本我寻求释放,但是仍然要考虑法律和社会,于是压抑和欲望混合起来的冲动就表现在偷窥上。偷窥者主宰着整个局面,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与对方关系的主动权。行为主体相对行为客体而言,更自由,更有控制感,更安全。控制感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得到安全,通过控制来满足内心的安全感,使自己有所依靠。当秀拉看着小男孩挣扎直至最终死亡而惊慌失措,甚至哭出声来时,奈尔却冷静自若,在旁安慰。多年以后,奈尔终于意识到是偷窥癖的施虐倾向驱使自己目睹整个事件,这也加深了读者对奈尔和秀拉的认知,她们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显示出人性的复杂。同样,秀拉的外祖母伊娃很早就意识到秀拉也是一个施虐型偷窥者。秀拉的妈妈在一次意外中被火焚烧而死,秀拉躲在柱子后面,大家都以为她吓呆了,伊娃却坚持认为,“秀拉对起火的汉娜袖手旁观不是因为吓呆了,而是因为她深感有趣”[6]79。
在凝视机制的复杂性方面,莫里森无疑想要向读者展示更多。《秀拉》和《所罗门之歌》就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镜像凝视,表明了男性的自我肯定和女性的自我否定之间的性别差异。在两部小说中,不同的性别主体分别在凝视的反射层面上找到或失去了自我。
小说《秀拉》中,一战幸存老兵夏德拉克在底层居民眼中是一个精神受到创伤、行为疯狂的异类。战场上的炮火摧毁了所有的疆界,引发了人们的错置感。夏德拉克醒来后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他臆想自己的双手会像藤蔓一样蔓延,在医院他忘记了自己的面孔,丧失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出院后他无所适从,在大街上游荡,被警察关在监狱,他凝视着马桶里自己的倒影,重新发现了自己的黑面孔和他的自我。一旦确认自己黑皮肤的真实性,他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他的精神避难所。夏德拉克的狂躁症立刻缓和了,他心满意足地“睡了他新生命开始后的第一觉,这一觉比在医院里服了药片之后睡得还香,比果核还实在,比秃鹰的翅膀还稳定,比鸡蛋的外壳还安静”[3]17。
水中的倒影是一个拉康式的镜像,将碎片般的个人体验整合成统一的主体意识。这里的男性镜像凝视肯定并建立了夏德拉克的自我认同,他获得了新生。小说中,夏德拉克是当地黑人社区中谜一般的存在,他首创了“全国自杀节”,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每年的1月3日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夏德拉克首先在镜像中发现了自己的种族本质,然后开始积累起个体的自我感。他的故事出现在小说的开头,他把头发扎成黑人特有的脏辫,他的住所坐落在从祖父那儿继承过来的祖先的土地上,在形式上与黑人民族的原始时空相联结。夏德拉克用创造神话的力量创造了他自己的假日,使之成为了当地的日常行为和民间传说。夏德拉克、奈尔、伊娃经历了黑人社区的分崩离析,在小说结尾作为见证人进入19世纪60年代。
三 《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娃娃》:商品文化的欲望客体
与《秀拉》中的男性自我肯定相反,莫里森在下一部作品《所罗门之歌》中指出,在父权制社会价值体系中,女性凝望镜子强调了自我否定或缺失感。通过自我欣赏和商品化的展示性运作,镜像凝视使得女人们沦为了男性欲望的展示性客体。小说中,黑人女孩哈格尔不可自拔地爱上自己的表兄奶娃,她对自我的认知展示了白人关于美的标准对黑人女性施加的毁灭性伤害。哈格尔的狂热感情遭到了奶娃的拒绝,为了帮助她从绝望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祖母派拉特送给她一个小巧精致、镶着金边的粉盒,然而,这证明是一个危险的玩具。哈格尔看着粉盒中的小镜子,这个致命、诱人、自我反射性的凝视激发了关于美的陌生标准。她自欺欺人地认为奶娃之所以不爱她是因为她没有垂顺的长头发和蓝眼睛,而长头发和蓝眼睛是白人社会作为商品化标准为所有人构建的。小说中,哈格尔的祖母和母亲代表了自然,她们能够抵抗外在形象的诱惑和凝视的殖民化力量[8]9。哈格尔的祖母派拉特是自然之子、灵魂的治愈者,是带领人们超越外表进入本质的精神导师。她天生没有肚脐,被视为异类,受尽周围人的歧视与冷眼,因此她知道外表,即使是误导性的,对个人有多么重要。哈格尔幻想成为一个想象中的自己,一个让奶娃更期待的人,她也因此拒绝了真实的自我,那个被祖母和母亲用传统生活方式塑造的自我。
正是因为在消费文化中女性承受着更多欲望和性别上的剥削,哈格尔疯狂地列出要买的商品清单和护肤品,目的就是成为“值得”男性关注和青睐的对象。她买的许多东西是“一副‘倍得适’牌的橡皮吊袜带,‘伊·米勒’牌的无色长筒袜,‘水果织布机’牌的紧身短裤,两件有背带的尼龙长衬衫——一件白的,一件粉的——一双‘乔伊斯’牌的摩登皮鞋和一顶‘坎·布利欧’的帽子”[9]35。与夏德拉克在镜中获得重生和自我肯定相反,哈格尔失去了自我,也最终失去了生命,她名义上死于由发烧引起的感染,实质上是死于对自我的极度厌恶,以及无法完成商品所承诺的神奇转换而导致的终极绝望。
莫里森的第四部小说《柏油娃娃》则进一步探讨了消费社会商品文化下女性被彻底物化的过程。小说中,黑人女孩吉丁在退休了的美国富翁“糖果大王”的好心帮助下,前往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完成学业后,成为巴黎时装界的模特儿新秀。在一个类似镜像凝视的场景中,吉丁的黑人崇拜者桑盯着她在一本法国杂志上当时装模特的照片,展示了吉丁在接受男性凝视的玩味中被物化的过程,因为桑发现盯着杂志上她的时尚照片比注视站在他面前真实的吉丁更为简单。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物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它系统性地打破传统和自然的统一,打破社会形式、人际关系、文化事件甚至宗教体系,然后以一种新型的后自然进程或机制进行更有效的重构[10]62-63。在商品文化的压力下,吉丁的原有认知被打破,她被抽象成一系列的人体照,桑不但可以观看,而且与真人相比,他和照片上的吉丁产生了更简单更直接的关联,吉丁成为商品文化中男性消费欲望凝视的客体。同时,吉丁强烈的自恋情结和展示欲也在这里暴露无遗,她骄傲地向桑翻译文章中关于她的法语介绍,“展开有四页大”,她读简历时那种断断续续的方式强调了她彻底的物化,“柴尔兹小姐……毕业于索邦大学……一名艺术史的优秀学生……学位……旅居巴黎和罗马的美国人,她在这两座城市中经营着一家出色的小公司……”[11]140-141这段文字介绍的讽刺性在于,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在这本杂志的介绍中却没有哪一项成就是具有价值的,它们只是将限量商品,即在照片中被展示的吉丁精心包装好,使观者或买家对之产生更强烈的消费欲望。
吉丁生长在一个富有的白人家庭,完全孤立于黑人社区,显然,在莫里森所创作的人物群像中,她比其他角色更适合成为凝视的客体。吉丁个人化的意识形态和人生观,她作为模特的职业性的展示欲,标志着她的物化是由消费社会制造的各种情境、角色和态度所导致的。当代社会微妙的凝视,多为引诱而非暴力,当她成为男性欲望的完美客体,她也站在了几乎所有黑人女性的对立面,这一点颇值得玩味。《柏油娃娃》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孤岛上,一个昔日法兰西帝国统治的殖民前哨,这是有深意的,因为岛屿和吉丁的身体代表了在主体意识形态中同样具有异国情调、殖民化的幻想空间。这种隔绝和主宰的关系能延伸到所有女性身上,女性导演兼作家朱迪斯·威廉姆森(Judith Williamson)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同质性关系:“女人是一座孤岛,因为她是神秘的、遥远的,一个可以让人度假的地方,但同时,她也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内的岛——被包围、被隔绝,如同被殖民者统治的殖民地,在同一的海洋中作为他者而保持完整。”[12]107
四 结语
凝视总是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身份问题联系在一起,如西方对东方的凝视、白人对黑人的凝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富人对穷人的凝视。这是一种无声的目光暴力,却能对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13]。莫里森向读者揭示了隐藏在各种看似合理的凝视表象下的残忍、傲慢的本质,其中汹涌奔流着赤裸裸的暴力。她的系列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凝视的多重机制,揭示了凝视作为社会控制和种族压迫工具的复杂性,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女性施加的持续性伤害。长期以来,白人审美与文化话语居统治地位,黑人被塑造成无法言说的他者。同时,伴随着社会消费时代的到来,女性“身体”越来越成为父权制社会中被凝视的对象化客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视觉消费的对象。黑人女性对自身美的塑造是以白人/男性的评判作为价值标准的,观看是一种权力,黑人女性则被置于“被看”的生存境遇,体现出这种权力的隐性话语结构:白人/男性处于权力中心,而黑人女性始终处于被奴役、控制、边缘化的生存境地。小说中对凝视的不同运行机制的描述充分诠释了黑人主体是如何将“那种源自外在的凝视,认为存在固有的劣等性的观念进行内化的”,正如莫里森在1994年版《最蓝的眼睛》的后记中所阐述的那样:小说是对“那将她定罪的凝视”的审问和拷打[14]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