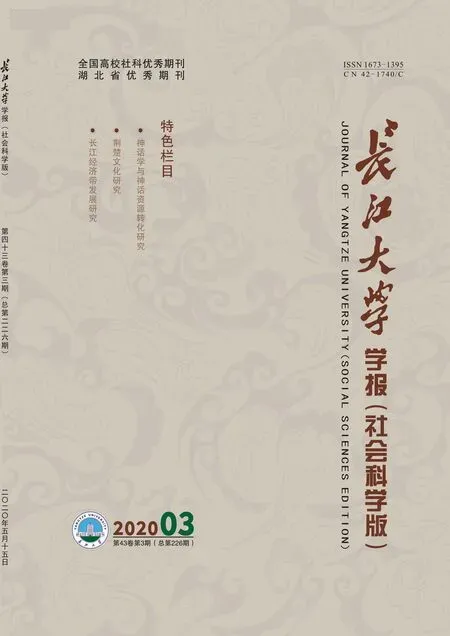中国古代图像群落中的神话编码
——兼论《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
李鹏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神话作为一种古老的叙事文体,记录着古代先民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忆,展示着与自然抗争的坚毅品质与高超智慧,蕴含着对天地山川、宇宙万物的哲学思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1]由于岁月的侵蚀和时代的更迭,远古先民保留在神话中的记忆和思考已经渐渐褪去,如何抽丝剥茧去还原和理解神话真正的叙事声音,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论证分析。将证据与神话相结合进行分析,是较为主流的一种认识,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古史辨派对神话“考古式”的去伪存真,从神话原型理论的兴起到叶舒宪提出四重证据法,这些都为神话学的客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第四重证据,叶舒宪认为,它“是指文字符号和语言符号之外的符号或符号物,包括图像、遗址、文物和其他一切承载着人类意义或文化意义的物证,如血型、肤色和基因”[2],由此开启了通过图像文物研究中国神话的广泛性思考。
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对于神话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引领意义,它把对神话的不可知论引入实证分析领域,其中,将出土图像与神话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早在上世纪上半叶便已有之。孙伟伟在对神话图像研究的梳理中指出,鲁迅、闻一多、孙作云等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神话研究与考古图像的结合,成果有《伏羲考》《饕餮考》《蚩尤考》等,到20世纪后半叶,更多学者致力于通过对石画像、崖刻、壁画等考古物的研究,来思索先民神话的精神内涵,以伏羲和女娲形象探究为主。[3]
中国古代的图像资源蕴含着先民的何种思维,这些图像所展示的神话编码又是为何,这里可以借助生物学的术语“群落”加以分析。生物学观点认为,有规律组合在一起的种群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群落。若将图像比拟为生物,则目前所出土的图像,大体可以分为太阳群落、月亮群落、昆仑群落、人祖群落、图腾群落、宗教群落等部分。21世纪以来的神话图像研究已朝综合系统化的方向推进,诸多学者在现有出土图像和前人研究论述的基础上,对不同图像群落的研究形成了体系化的论证,如刘惠萍《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王青《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王倩《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过文英《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等论著或博士论文,都形成了对神话图像研究的系统化思考。
图像文献的数量是有限的,但神话的研究范畴是宏大的,有限的图像文献无法涵盖所有神话类型的研究,这是目前神话图像研究的现状。如何打破此种瓶颈?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刘惠萍认为,“利用考古图像材料考察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内容,实具有补足或验证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价值与意义。”[4](P13)对于神话学研究而言,图像实证已经不单是对神话文本的一种辅证,“绝非是文本单向地决定图像,图像系统是和文献系统同样重要的神话载体”[5](P11)。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台湾东华大学刘惠萍教授《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将图像作为神话的独立主体进行研究,对图像中的日月神话的基本面貌、观念形态等方面作了系统思考,剖析了古代图像背后的神话内蕴。笔者以此书为例,对特定图像群落中所展现的神话编码进行解读。
一、太阳图像群落中的神话投射
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在《比较神话学》中提出,“神话的核心以及神的原初概念,归根到底总是太阳。”[6](P7)太阳中心说的神话观念影响了一代神话学者的研究。太阳和水作为原始先民真实可感的事物,影响着人们的早期生活和思维观念,太阳神话、洪水神话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的神话类型,它们反映出早期人类对太阳和水的敬畏和崇拜,这两种事物滋润着万物生灵,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先民自然而然会对它们的产生和特征作更为深入的思考,并赋予它们更为神奇的表征。
原始思维投射在神话中,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样式,诸如在中国各民族流传的太阳神话中,太阳产生的母题是比较普遍的,综合各个神话文本的表述能发现,太阳大体是由神、神性人物、人、动植物和无生命物通过创造、生育和变化而来的。对此类母题,王宪昭在《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W1550太阳的产生”中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如太阳是用何种材料创造而来的说法,就有水族用火,布依族用黄泥和红岩石,拉祜族和哈尼族用金子,彝族用眼睛,哈萨克族用光和热,畲族用松枝等来造太阳。[7](P322)这些神奇性的幻想成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对于太阳产生的独特思考,也展现出早期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思想观念。
关于太阳产生的神话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日中有乌”的说法,“三足乌”也历来被视为太阳的象征。实际上,在各民族的神话中,动物变成太阳的母题大概有如下几类:汉族讲乌鸦变成太阳,金翅鸟变成太阳,三足乌是太阳;壮族说公鸡变成太阳;毛南族认为龙变成太阳。[7](P325)这些神话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先民的共同认识,像乌鸦与太阳之间的联系,不仅在《山海经·海外东经》《山海经·大荒东经》等神话文本中有所记录,通过现有的考古出土文物中的图像也能进行验证和还原。如陕西华县柳枝镇泉护村出土的鸟纹彩陶盆的残片,距今已有近六千年的历史,残片之上是一只展翅腾空的飞鸟侧身像,飞鸟上方由半圆弧包围,半圆弧和飞鸟之间是太阳的图形,只是飞鸟下半身已是残片,很多学者据此残片基本都认定此图像应为“飞鸟负日”图纹。刘惠萍发现,在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的遗址中存在有“日载于乌”图像群,如河姆渡的双鸟太阳骨匕和蝶形象牙器、汝州的阳鸟负日、大汶口的日鸟纹等出土文物,上面所雕画的均为太阳与飞鸟合体的图纹。可见,神话未必是一种虚幻的反映,更多应是一种原始思维的折射,图像的表达更能证实先民对神话的确信,印证神话的叙事是神圣的。
图像上的图案所表现的内容有着较高的重复率。从刘惠萍所列的《汉代墓室所见日、月画像一览表》可见,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T形帛画,到新莽时期的陕西千阳壁画墓,再到东汉晚期的四川成都杨子山1号墓画像砖,历经三百年的传承,不论是长沙帛画、陕西壁画,还是四川墓画,尽管出土地域和图像类型不同,但“日中有阳乌”“伏羲身上刻日轮”“伏羲托日”的图形都共同存在。这些图像都被刻于墓室,作为丧葬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已经不是一种自由的创作或随机的装饰,而是一种特定的人生信仰、社会功能,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的,“如果不考虑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赋予视觉图像的不同功能,我们就不能写出艺术的历史。”[8](P12)神话在墓室的图像中所表达的意义已定型为一种社会文化功能,但这种文化现象根据时期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达。
第一,上古时期,太阳图形群落具有原始象征性。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在陶罐、陶盆等陪葬品或岩崖面上来刻画太阳的形状,如云南沧源岩画的太阳图像,就是一个手持弓箭的人在太阳里或太阳下的形状,广西花山的岩画描绘了一个人用手触摸太阳的景象。陶器作为早期人类的陪葬品,上面刻画了更多的太阳图像,如郑州大河村遗址中的彩陶就刻有太阳纹,即用圆圈和放射线组成了太阳的样态,再如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腹部有八角星图案,依然是太阳的图形。若非对太阳有着痴迷的崇拜,先民是不会在日常生活的器具上刻上太阳的,而且这种崇拜是跨越地域而存在的,通过宗教意义的层面来解读更为贴切,这种原始性的表达应更集中地表现为太阳神崇拜的观念。
第二,先秦时期,太阳图形群落的定向化表达已然存在。先秦时期出土的陶器、玉器、衣箱上所刻画的图案中已经出现了鸟与太阳相结合的形象,如凌家滩的玉鹰,“鹰首侧视”,“胸腹部饰以八角星为主体的纹饰”,“八角星纹饰,星内画一圆,象征太阳,代表太阳光芒四射”[9](P3)。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代的衣箱上有《后羿弋射图》《夸父逐日图》,这两幅图与太阳神话有密切联系。《夸父逐日图》中绘有两个兽形图案,一侧有腾空而飞的鸟,鸟的两侧有两个圆点,后有一人一手抓鸟尾,一手持武器作击打状,发掘者据此认为此图应为夸父逐日,但王青认为可以将邢义田对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10](P139~193)的认识运用于此图的解释,抓鸟尾意味着“得爵”,是祝福的图像,而非太阳神话[5](P37)。虽在学术上存在着争议,但鸟与太阳相结合的定向化表达,在先秦时代已然是存在的。
第三,两汉时期,太阳图形群落的功能固定化。两汉的太阳图像与前代相比,太阳的形状确定为三类:其一,三足乌置于圆轮之内以表征太阳;其二,阳乌背负圆轮呈飞翔状以示太阳;其三,伏羲捧日或人面鸟身的人格化太阳形象。此三类基本能够涵盖两汉时期太阳群落的太阳图像。刘惠萍对汉代墓室的画像做了重点解读,她认为,墓室中的太阳画像与天文历法和阴阳观念有直接关系,墓室中的天文景观是对死后小世界的再创造,是生命延续或永恒的寓意,较为符合早期人类模拟巫术的思维,随着神话观念的转变,象征天界太阳的形象已从动物渐变为人祖,及至东汉晚期,甚至已很少见日月画像所象征的天空图案,西王母、伏羲女娲等仙人、人祖出现的比重增多,即便有日月的图像,也多已散落在整幅画像的角落,仅有点缀的功能。
太阳图像群落的演变折射出三个神话现象:其一,太阳与鸟的结合观念。陈勤建认为,先民对太阳崇敬的“情感是在‘鸟田’稻作环境中滋生的”,“鸟类带来了稻种”,人们“便萌生了一种鸟化的感情”[11](P58),由于先民鸟信仰观念早已存在,如东夷部落对鸟的信仰,加之互渗律思想的作用,太阳鸟的形象便出现了。其二,太阳从活物化向人格化方向的转变。神话中的神灵从无形的神到实体神,再到之后被赋予更多的人性,这反映了人类在同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对自身的肯定,以神性人物或英雄为主体的神话表达出了这种人本思想——即便是神,也要为人类服务。其三,古老崇拜观念的留存。无论神话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原始先民固有的太阳崇拜观念是存在的,刘惠萍在书中列出了《汉画像“日中金乌、阳乌”分布一览表》,从中可看到社会群体的期待认识和原初的信仰观念。
二、月亮图像群落中的神话观念
相比太阳神话的璀璨夺目,月亮神话似乎没有那么耀眼,实则不然,它有着较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和信仰根基,有些学者认为月亮具有的力量能使种子发芽,植物生长,甚至影响女性产子,如美国历史人类学家M·艾瑟·哈婷认为,“在几乎还没有任何系统的或有组织的宗教信仰的部落中,把月亮作为丰收的施者或食物供给的保护神来崇拜或膜拜。”[12](P21)对于月亮的崇拜在不同民族神话中有所展现。王宪昭在《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W1580月亮的产生”中,对月亮源起的表述做了较为具体的梳理。以月亮的变化产生为例,有毛南族的熊变月亮,汉族的兔子变月亮,独龙族等14个民族的太阳变月亮(此类型之下有14个二级母题),羌族的灯变月亮,布朗族的火球变月亮,彝族的蛋壳变月亮,布依族的白元宝变月亮,水族的特定的洞变月亮等。[7](P330~331)这些不同的变化都有其内在根源,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月亮的独特认识。古代文献中对月亮神话的记载和描述主要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归藏》《淮南子·览冥训》《淮南子·精神训》,等等,而这些记录往往在出土的图像中也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例证。从图像学的视角来验证神话文本的合理性,首先需要对月亮图像群落的分布有一个认识。
太阳图像群落主要分布在墓室和岩崖,月亮在岩崖中的图像相对较少,它集中出现在日常生活器具和墓葬之中。中国墓室的建造融合了较为浓厚的阴阳理念,逝者魂魄需由男女两位神灵接引才能升天,这种思想符合早期的阴阳观念,因而除了太阳的图像之外,月亮在画像和墓室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它最常见的象征意象为蟾蜍、玉兔、桂树,与我们所熟知的神话中的意象相吻合,但月亮与这些意象之间关系的绑定应是先秦时代观念的反映。
在出土的上古时期的陶钵、陶盆、陶罐、口杯、象牙器等用具上,很多都刻有月亮形纹饰,如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而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片、何家湾遗址出土的平底陶盆上,都有蛙纹。与太阳图像不同,这些图像既不能说明早期蛙与月亮神话的关联,也不能说明早期先民就具有月亮崇拜的观念。先秦时期,蟾蜍和玉兔的意象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增高,但却未在相应的图像中有太多展现。到了两汉时期,它们或零散或综合地出现在图像中,从刘惠萍所列的两汉月亮画像中可见,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的帛画便是月中有蟾蜍和玉兔,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的壁画墓里的月中有蟾蜍和桂树,崇州东汉晚期画像砖墓中的女娲托月,月中有蟾蜍和桂树。基本上月亮图像群落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圆轮中的单一动物形象。古代出土文物中蟾蜍即月的表征较为普遍,这与先民对月亮意象的认知观念有重要关联,如河南南阳出土的月亮图、蟾蜍北斗图、日月同辉图,其内都刻有月轮,轮中就是蟾蜍,但这并不意味它是月亮唯一的象征物。如南阳白滩出土的牛郎织女图中,七星连成的圆形内是一只玉兔;山东梁山后银山壁画有金乌与玉兔的图案,象征着日月。
第二,圆轮中的动植物。根据刘惠萍在书中所列出的《汉画像“月中奔兔”分布一览表》,14个墓画中有蟾蜍和奔兔同时存在的情况,如南阳市卧龙区阮堂画像石中,东方苍龙星宿上侧的月轮中是蟾蜍和奔兔。同样的,在东汉中期之前的画像中,月轮中的兔子基本都是奔跑状,而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画像中则出现了捣药的玉兔,《汉魏晋南北朝画像“月中捣药兔”分布一览表》中列出,安徽淮北的孟大园画像、山东滕州官桥镇大康留庄出土画像等11处均为月中捣药兔的形象。
第三,月亮的人格化表达。与男性神伏羲相对的是女娲,她常伴随着月亮的形象出现在图像中,如河南洛阳出土的西汉后期卜千秋壁画墓中,女娲前面有月轮,内有蟾蜍和玉兔,再如四川崇州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砖墓里,女娲左手托月,月中有蟾蜍和桂树。有的图像则直接默认伏羲举日、女娲托月,如云南昭通的白泥井石棺画像中的女娲,其左手所托便被认为是月亮。这种定向化的表达与父系氏族社会话语权力的控制有一定关联。
蟾蜍、玉兔、桂树、女娲缘何都能与月亮产生必然的联系,又被根深蒂固地植入传统文化的语境?通过对比文献资料可知,其终极指向的内涵应为寄寓着先民对长生不老理想的追求和探索。如蟾蜍能够与月亮产生关联,大体可归因于三个方面:其一,在古代社会,蟾蜍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肚大浑圆如孕妇,繁殖能力较强,生殖崇拜的观念蕴含其中;其二,在汉代,蟾蜍(蛙)与求雨仪式相关,而“水气之精者为月”,故而蟾蜍与月在雨水层面能联系在一起;其三,蟾蜍被认为是古代的不死药,它“不仅源于古人的月神崇拜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更与蟾蜍自身的形态特点与生活习性有莫大的关联”[13]。用永生的观念来解释其他意象似乎更为合理,如《酉阳杂俎·天咫》中记载,桂树“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意即此树有长生不死之能,而“桂”确是道家求仙方士所认定的灵药,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产生了对长生的各种幻想追求。在中国各民族的月亮神话中,月亮因为服用长生水而具有不死的能力,也因此成为先民祈求长生的美好愿望的投射。
三、神话图像研究中的文化辐射
神话图像是一种较为独立的神话叙述语言,虽然与神话文本的表述形式不同,但却通过人们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影响着社会文化心理,图像表达所蕴含的文化信仰和价值取向已深深积淀在民族文化之中。它产生于神话思维出现的时代,是一种神圣性的表达,但其象征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需求。刘惠萍在书中的最后两章着重探讨了神话图像在魏晋以后墓室的发展、对佛教和粟特祆教的融合以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展示了神话图像研究对重大文化事象的辐射。神话图像所映射的文化会在传承中转化,在传播中交流,在时代中发展。
首先,中国的神话图像文明会在传承中有所转化。汉墓中的日月图像的数量和规模是可观的,它们基本上都是先民定向化的表达,其文化意象和神话编码的含义也较为明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图像所表达的却更为贴近世俗生活。这与神话观念的淡漠和传说故事等民间文体形式的发展有一定联系。比如敦煌藏经洞内的一幅唐代的日曜菩萨的绢画,菩萨手捧日轮,轮中却是一只雄鸡。更有甚者,在福建将乐县出土的元代壁画墓中,月中绘有桂树和玉兔捣药,而圆日中竟是一只三足鸡。若说为画工的笔误,那在宋代以后的若干典籍和诗词中却都可见“日中有鸡”的说法,而且,从“阳精”“三十六禽”“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等角度都可对此进行解读。正如刘惠萍所言,“唐宋以后的人们以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与想象,完成了对古老日中有乌神话的重新阐释。”[4](P330)这种对神话图像的重述,虽然以变形化的方式传承,但终会因符合时代和生活的需求而被广泛传播。
其次,中国神话图像文明在传播交流中会与不同宗教和文明相互融合。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几百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宗教形式。中国神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是人类童稚期的产物,但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异,这就决定了神话有活态传承的属性。佛教与中国神话的融合通过图像的方式最直观地呈现出来,如敦煌莫高窟第35窟是十一面观音图,八臂观音右上方第一只手托着的圆轮内有金乌,而左上方第一只手托着的圆轮内有桂树、蟾蜍和捣药玉兔。圆轮内的这些事物是中国固有的神话意象,佛教显然是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用传统图像来表现外来文化或宗教主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较为常见的现象,有利于借助本土化的理解来宣传宗教的教义和信仰,更好地吸纳大众参与宗教生活。
最后,中国神话图像文明会在时代中发展。神话图像作为一种实物性证据,零散地分布于岩崖、墓穴、寺庙等各处,即便同一神话图像群落,它们的分布也并不集中。对于如何行之有效地对纷繁复杂的图像群落进行研究,王宪昭认为,“通过有效的神话数据建设促进优秀传统神话的保护传承和相关文化产业开发,将是充分发挥神话社会文化功能的有力保证。”[14]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建设神话图像的数据库势在必行,它适应了中国神话图像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符合神话图像研究的趋势。建设信息数据库,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研究分析,利用信息化技术,按地域、时代、用途、特定意象进行筛选,更便捷地找到自己所要研究的方向,节约成本的同时也保障了准确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出土的图像资料,文物在出土之后会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将其进行信息化存档,能更为持久地保护珍贵的文物资源,进行可持续的利用和开发。
四重证据法对神话学研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对证据的关注,将神话的研究引向可知论。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法所关注的一个侧面,注定会成为神话学研究的重点。很多学者都对神话文本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通过解读出土的神话图像资源则能够打消这种质疑。刘惠萍《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通过对两汉墓室中的日月图像的形象研究,系统探究了其思想背景、观念形态、神话因子、传承发展和文化交流,用更为直观的图形,呈现并还原了神话较为真实的面貌,揭示了先民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和社会认知。对神话研究而言,图像学视角并不是万能的存在,它所涵盖的神话类型是有限的,不足以揭示神话的全貌,它所展现的图形面貌是直观的,有时未能呈现文献出土的时间和地域,那么就需要更为客观准确的理解和基础扎实的专业判断,这也就加大了对图像原初意义分析的难度。虽如此,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方兴未艾,它定然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