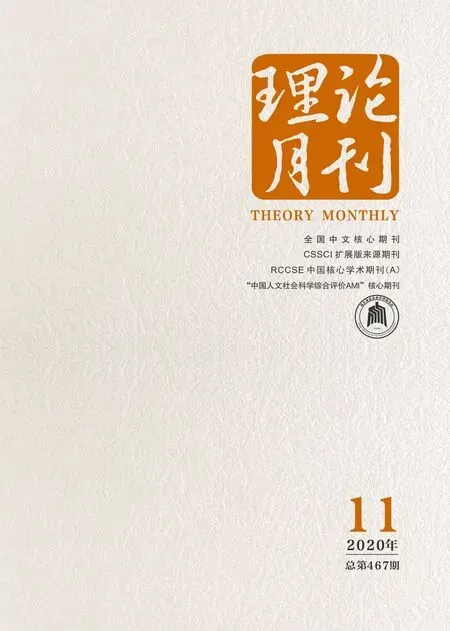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概念的理论探源及其存在论革命意蕴
□何晓亮,刘秀萍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4)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是关乎马克思哲学根基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一个基本概念,即“感性—对象性”概念的深入考察。而对这一概念进行具有存在论革命高度的领会,需要深入与马克思同时代并对马克思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们的具体研究当中,从而展示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革命的逻辑生成历程。
一、黑格尔对“感性—对象性”概念的抽象化理解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一开始就对感性进行了抽象化的理解,他把感性理解为精神现象中最直接呈现的意识现象,用以区分“我”和对象。“我”有感性,说明“我”有意识,“我”通过感觉知道:“我”不是对象,对象不是“我”,而是被“我”感觉到的。所以,“我”和对象最直接的区分就是感性。但是感性“对于它所知道的仅仅说出了这么多:它存在着”[1](p63),“而这个纯粹的存在或者这个单纯的直接性便构成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性”[1](p64),但是“一个现实的感性确定性不仅仅是这种纯粹的直接性,而乃是这种直接性的一个例子”[1](p64)。所以,在把“我”和对象区分开来以后,还要分别把两者统一起来,在意识范围内寻求“我”和对象各自确定性的统一性。于是,这种感性确定性的存有立刻就分裂为两个“这一个”:“作为自我的这一个和作为对象的这一个。”[1](p64)但是,黑格尔认为,感性本身是很难确定的,他分别用“这一个”的双重形式“这时”和“这里”举例,并最终确认感性的确定性只能是某种一瞬的“定在”,凡是超出了这一瞬的“定在”,“我”的“意谓”便失去了确定的对象。所以,感性的确定性最终只能返回到语词的共相,即“这一个”。万物所指皆可用“这”“这一个”来替代。而这其中就有一个矛盾,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当人们这样做时,就“恰好说出了和他们所意谓的直接相反对的东西”[1](p72)。当“我”要追求感性确定性的时候,“我”用“这一个”来表示,但是它是最不确定的,因为万物都可以用它来表示;但是当它最不确定的时候,“我”却用了一个最确定的词将它表述出来。
所以,黑格尔不承认感性具有任何真理性,他声称,这是整个自然界都在宣扬的公开的秘密。“因为动物并不把感官事物当作自在的存在,对它们抱静止不动的态度,而是对它们的实在性感到绝望,有充分信心把它们消灭”[1](p72),当一条狗把食物这样的感性存在吃掉的时候,感官事物的真理性也就消失了。所以,真正留存下来的感性所确认的东西乃是作为普遍共相的“这一个”的抽象存在,感性在黑格尔那里完全陷入了抽象化的认识当中。
至于对象性(活动),黑格尔更多把它理解为与真正的感性活动绝无任何相关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活动和外化活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2](p203)活动。黑格尔对对象性(活动)的理解包含两层意思:
一方面,对象性(活动)本身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外化活动。黑格尔所理解的对象性(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意识自身设定自身的异化、外化活动。从逻辑出发点来讲,“黑格尔从异化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说得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2](p200),说得再直接一些就是从“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对象本身,即财富、国家权力乃至全部外化的历史,“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思维的生产史”[2](p203)。这个对象性活动产生的外化物、异化物本身并不是什么现实的存在物,而是自我意识自身所设定的“物性”。它以为自己是现实的存在物,实际上不过是“抽象物”“抽象的物”,是外化的自我意识本身。因此,这里所说的这种对象性活动本身,指的不过就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2](p203)运动。
另一方面,对象性(活动)本身还包含另外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外化活动所生成的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2](p206),但他又认为,“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正像抽象的意识本身——对象就被看成这样的意识——仅仅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差别环节一样,这一运动的结果也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2](p204)。所以,对象被黑格尔看成是需要被克服的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2](p206)。这就涉及对对象本身,即对象化的自我意识本身的扬弃。但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2](p206)。黑格尔的这种关于在抽象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异化的理论就是非要逼迫人们把“扬弃异化”和“扬弃对象性”一并进行,这样就把“小孩和洗脚水一块倒掉”了。正如马克思所言,“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p210),如果把对象性本身也扬弃掉了,黑格尔所指示的人显然就只能“被看成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2](p206),是绝对(无对象)意义上的存在物。
然而,自我意识的这种“对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的对象性活动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其“仍然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2](p213),“因为对象对思维来说现在已成为一个思维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作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2](p216)。因此,虽然黑格尔唯一知道和承认的对象性活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这种对象对主体本身存在的确证必然也陷入抽象化的理解当中,但他毕竟以抽象的方式为马克思理解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哲学前提。
二、费尔巴哈对“感性—对象性”概念的直观化理解
在黑格尔那里,“感性—对象性活动”局限在抽象的自我意识本身的范围内而不停旋转。这种限于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之核心——“意识内在性”——的理解,怎么也逃不脱主体性哲学的范畴。然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的提出,试图打破这种意识之自闭性,或曰击穿意识的内在性,从而把整个哲学的基点落到现实的感性之上。
首先,费尔巴哈提出的“感性原则”直指黑格尔的“绝对实体”。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讲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时指出,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感性事物)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绝对精神)对立起来。与西方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不同,费尔巴哈反对把超感性的形而上的绝对精神当作绝对实体,并以之作为万物存在的本质和根据。相反,万物自身的存在应当基于自身,并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而获得肯定,而不是依附于他物,再通过某种间接的方式返回到自身来得到确证。费尔巴哈说,“只有那种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东西,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明确的东西,直接根据自身而肯定自己,绝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但是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对明确的……直接认识的秘密就是感性”[3](p170)。由此,费尔巴哈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超感性的绝对精神世界决然对立的感性世界,并主张一切事物的现实性、真理首先在于它是感性的,凡是感性的事物都是现实的,非感性的事物都是非现实的。“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3](p68),所以,感性才是现实性的根据,是现实性本身。
配方施肥区:测土配方复合肥(20-10-10)40 kg/亩。配方施肥无氮:过磷酸钙33.33 kg/亩,氯化钾6.66 kg/亩。配方施肥无磷:尿素17.39 kg/亩,氯化钾6.66 kg/亩。配方施肥无钾:尿素17.39 kg/亩,过磷酸钙33.33 kg/亩。
其次,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直指黑格尔的“绝对主体”:
第一,主体如果“ 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4](p29)。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就阐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绝对即主体的概念”,也就是把绝对的实体同时理解为主体。既然这个实体是绝对者、上帝,那么,这个主体也就是“绝对主体”。“绝对”的意思就是“无对”,即没有对象,在它的上面、下面、左面或右面,决然没有可以与之相匹配的对象,因为它是“一”“一切”“大全”。“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2](p210)所以,这样的绝对者主体必然是无对象的存在物,只能孤零零地存在着。因此,费尔巴哈在这里首先针对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也包括黑格尔哲学的那些变相形式。后来,这一命题被马克思直接表述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p210)。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2](p210)所以,只要是现实的存在物必然是有对象的存在物,否则它就只能是“无”。
第二,“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4](p29)。如果说第一个命题是从否定方面来讲,那么,第二个命题是从肯定方面来讲。费尔巴哈指出了与现实的主体本质相关的三个对象:一是自然界。现实的人以自然界作为对象,意味着自然界是人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所以,自然界的本质是人。费尔巴哈甚至说,人吃喝的东西是“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3](p530)。二是他人。“我”是一个主体,“我”以另一个人作为对象,那么他人就是“我”的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如果没有他人,那么“我”就是无。因此,“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所以,费尔巴哈说人是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三是上帝。上帝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形式,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没有超出人的上帝。
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确不满意黑格尔的抽象思维,而“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这种哲学基点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启了存在论革命的契机。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费尔巴哈把感性仅仅理解为感性直观,而没有理解为感性的活动。这与他始终采取具有感觉论色彩的朴素直观的人本主义哲学态度直接相关。在他看来,感性就是感觉的直观,这种感觉的直观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人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感官的直观认识而达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感性的直观才是真理的标准。所以,费尔巴哈实际上仍旧采用一种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态度去静观事物本身,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2](p499)。于是,感性的客体被当成一种凝固化的、始终如一的、自在的存在物。这样一种“无人身的感性”的思维方式,本质上使得客体依旧是客体,主体依旧是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全然分裂的状态,至多在其对象性原理的帮助下,才达到一种具有感觉论色彩的直观的对象性同一关系。因此,费尔巴哈本来想借对象性原理来消除主体和客体之间这种感性的界限、分离和对立,但是这种建立在单纯的直观基础上的对象性不过“只是在表面上做出一个‘跃进’的姿态便立即折返自身”[5]。这使得主体根本无法贯穿对象(客体)的领域,于是,“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2](p528),去弥合那种仅仅看到“眼前”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之间、“现有”和“应有”之间的矛盾。而这种所谓的高级哲学直观,就是“本质直观”。这里似乎有了胡塞尔现象学的韵味,但由于费尔巴哈仅仅停留于单纯的“静观”而放弃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传承下来的“活动的原则”“建构的原则”,使得他又远没有达到现象学的要求(现象学的客体是由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建构起来的)。而这种所谓的高级哲学直观,也就是关于人的抽象化的“类意识”,包括理性、意志和爱等等,后来被费尔巴哈用来解释人与人的一切社会普遍关系。这不过是用意识的唯心主义来看待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活动,于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又在某种程度上退回到形而上学中去了。
三、马克思对“感性—对象性”概念的实践化理解
如果说黑格尔对于“感性—对象性”概念的理解陷入了一种“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思辨当中,那么,费尔巴哈则陷入了一种“无人身的感性”的抽象实在当中,二者都把这一概念抽象化了。这种离开“人身”的抽象化,这种远离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范畴体系,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往往会陷入传统哲学的理性本体论、自然本体论等实体形而上学或实体本体论的误区,成为海德格尔所批评的“无根的本体论”。马克思则在人的实践的基础之上把“感性—对象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性活动”,进而建构起扎根于人的生存实践的新哲学。
(一)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感性概念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把整个哲学始终建立在现实的感性基础之上。马克思在《手稿》里明确提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2](p194)。在感性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因此,感性始终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基点。但这里所指的感性既不是纯粹意识、想象中的超感之物,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中的抽象实在,而是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感性活动,即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的来说,马克思对“感性”本身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人的感性能力来讲,把感性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就现实的物来讲,把感性理解为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生动的人的感性活动。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当我们一般地讨论人的感性能力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人的官能。这种能力包括人的外感官能力(人的五官感知能力)和人的内感官能力(人内在的全面生命情感体验)。无论是外感官能力还是内感官能力,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对人而言,它们都是一种真实的感性存在。因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2](p191)。所以,一个对象要作为人的现实对象而真实存在,这不仅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或者说更主要地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而且,“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2](p191)。因此,眼睛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的感觉,眼睛的对象也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所以,人的感性的能力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规定着人的对象的现实存在,是人的现实对象存在的依据和界限。同时,马克思又指出,人恰恰又是“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由此,马克思进一步从感性的立场提出了对人的主观感性之外的客观世界的本体论证明。在他看来,人的感性是对于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的肯定,因而感性不仅是对于人自身的肯定,也是对于自然对象的肯定。
马克思说:“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地得到肯定,那么不言而喻:(1)对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的、它们的生命的特殊性……(2)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式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么这就是对对象的肯定……”[2](p242)所以,人的感性的无限丰富性必然导致他对对象的肯定方式的无限多样性,而对象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就是感性本身的特殊存在方式。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的人的本质规定角度来理解“人的感觉、激情等等”,而且还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完成了对人自身和对象的本体论的双重证明。然而,感性如何能够真正确认对象的真实存在呢?第二点给了我们直接的提示。通过直接的否定对象的活动,我们就直接肯定了对象本身的存在,而这样的活动也是可以被人的感觉所直观的。所以,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2](p197)。在这里,通过对人的劳动,即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诞生”和“形成过程”的考察,我们就找到了理解人、自然界和全部世界历史的钥匙。
事实上,马克思通过对感性实践活动的考察不仅找到了人的感性能力得以不断丰富和提升的原因所在,而且找到了人的感性异化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 ,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p191)。实际上,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感觉的完善性都是在人的现实的活生生的感性实践的活动中不断得到发展,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但当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生产关系来考察人的感性时,他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的感性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劳动中只有压抑感、剥削感、奴役感、异化感,在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残。然而,异化的扬弃与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人的感性异化的解决还是要回到现实的感性活动中才能找到出路。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马克思并没有把人自身的感性和感性能力当作单个人所固有的、始终如一的抽象物来理解,而是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方面来历史地考察人的感性能力的发展、完善和异化,而这一点在对物的感性生成的考察当中得到了更系统的阐述。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当我们说某个事物是“感性的”,这通常指的是某个在人之外的事物是能为人的感觉官能所感知的,是可以通过人的感觉经验直接观察到的。如果对感性事物的认识就到此为止,那这不过是又退回到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视域,把物本身当成与人无涉的“感性对象”。这样的物,不过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在之物,并不在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之内。由这样的物所组成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p530)。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2](p527-528)。所以,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道:“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2](p531)因此,当马克思在分析一切人类生存和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事实” 和“第三种关系”时,他的理论的立足点始终是基于人的生存的感性实践活动,他把它明确地归结为人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2](p532)。可见,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感性活动,而且“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p525)。全部历史不过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生成史及其产物。
(二)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对象性概念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原则,继而提出了自己的对象性原理,即“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2](p210),反过来说,现实的感性存在物必定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也就是说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是说它是受动的”[2](p211)。所以,凡是现实感性的存在物必定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既指其自身是有对象的存在物,又指其自身是受外在于自身的对象所规定并确证其自身存在的“受动的”存在物。所以,感性存在物本身的所有内容都由其对象物所规定,理解感性必须以对象性为基点。
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由于费尔巴哈对感性始终采取一种直观化的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实质上依旧处于一种二分的状态,而他引入对象性原则就是想通过主客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来使主体能够始终贯穿客体,以克服这种二分状态。但由于陷入对象性的直观,这种所谓的克服最终是不可能的。但马克思的对象性原理克服了费尔巴哈式的直观化理解,同时也就克服了这种主客二分的状态,从而使整个哲学的基点真正落到了感性之上。马克思对象性原理的全部要义集中在这段话上:
“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p209)
这里我们依旧看到黑格尔式的表达方式——人通过自己的外化去设定,但这里的“人”不再是黑格尔的“意识”或“意识的存在物”,也不是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某种始终如一的自在存在物,而是立足于人的感性实践基础上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所以,这种“设定”不是意识(“纯粹的活动”)的创造对象的活动,也不是费尔巴哈式的对象性直观活动,而是体现为“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活动”。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如前所述,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是有对象的存在物,是由在主体之外的对象设定并确证自身存在的受动的存在物。所谓“有对象的存在物”是指这些对象是主体所欲望、所需要的对象,一旦脱离了对对象的这种需要,他会发现自身“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活动”[2](p211),他自身便成了抽象的东西。所谓“由在主体之外的对象设定并确证自身存在的受动的存在物”是指对象不依赖于主体而确实在主体之外存在;这个在主体之外存在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2](p209)。因此,这里所说的“外化”以及外化之对象物,并不是指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人自身创造了一个对象(因为对象本身一直在人之外已然存在),毋宁说,被对象所设定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在对象身上实现了自身的真实存在,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的存在,人本身要存在起来,就是把他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不断实现出来,实现自己的对象性生活,“所谓实现对象性的生活即是要求在确实在外的真实的对象身上表现和确证自己的生命”[6]。然而,虽说对象确实是在人之外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对象与人之间就处于断然分裂和隔绝的二分状态,人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对象性的活动,是因为他是被对象设定的,“如果他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由此,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的人进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的前提便是人内在地包含他的对象本身,也就是说,人本身已把他的外部对象世界(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作为自身内部一个不言而喻的环节包含于自身了。由此,主体与客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和自我确证之间的内在对立便消失了。由这种对象性活动所规定和揭示出来的主客体之间的一体化对象性关系蕴含了感性本身的全部内容和规定,因为恰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最初是处于一种“被抛”的状态,而事物首先是作为“上手”的东西向我们呈现的,所以,人要生存于世,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的“上手性”(实践性)的对象,他不得不“烦忙”于世,“烦神”于人。因此,作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的人的“感性确定性”(黑格尔用语)无非是人与其对象之间的一体化的对象性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这种“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就是整个马克思“新哲学”的“新基点”,由此,也开启了整个“新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新视域”,即“关系的原则代替了实体的原则”。当然,如果我们把问题更深推进一步,对这种“新哲学”的“新基点” 进行现象学还原,我们就会发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而这种对象性活动同时就是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由此,对整个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就再也不能局限在某种凝固化的、始终如一的抽象的或具象的“实体”之上,而是要回到这种“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之中。而这种“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并不是处于一种现成所予的、自在静止的状态之中,而是处于一种“生成状态”之中,处于一种不断“存在起来”的状态之中。因为人就是“对象性活动”或“感性实践活动”本身,他不是“being”,而是始终处于一种“to be”的生存论结构当中。由此,建立在人的生存实践基础之上的对象性概念被彻底揭示出来。
所以,对感性本身的理解要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一定是对对象的感性实践活动,也就是对象性活动。所以,一定意义上,对象性活动就是感性活动,同时也就是实践活动。“感性的实践活动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仅仅是利用自己的‘双重性质’而把已经分裂的人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媒介或桥梁;相反,它是包含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内的单一的(直接感性的)全体。”[7]由此,马克思就将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关联全部打通了。
四、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感性—对象性” 概念的存在论革命意蕴
首先,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概念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使哲学的基点从意识的内在性中挣脱出来,转向了基于人的生存实践的感性。因为“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8](p75)。马克思将哲学的基点落到现实的感性之上,并提示我们对感性的确证要返回到“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之中,由此,哲学本体论的革命悄然发生,建立在人的生存实践基础之上的“关系的原则代替了实体的原则”,因此,马克思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2](p209)。从主客一体化的对象性关系出发,“从某种与我思确实不同的东西出发”,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囿于意识内在性范围之内的整个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
其次,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概念开启了哲学的生存论路向,使哲学从知识论路向的存在论转向了生存论路向的存在论。“知识论路向的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而生存论路向的原则却要求自身达于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9]知识论的存在论境域,其前提就是要求主客二分,然后认识的主体越出自己的“内在范围”获得对客体的“超越”,达到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概念的、逻辑的或反思的现实切中和内在把握。生存论的存在论境域,则是要求回到那种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人与自然的原初对象性关联”,并从人的生存实践出发,不断进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在主客体之间确立起对象性关系,进而勾连起整个人类世界,由此达至一种体现人的此在性的生存论的存在论境域。所以,在生存论的视域下,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看成自己的对象,这种人的“自己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生活,就是“此在”。人在感性的对象性生活的“牵挂”或“操心”中不断领会存在本身。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基础上的感性实践生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