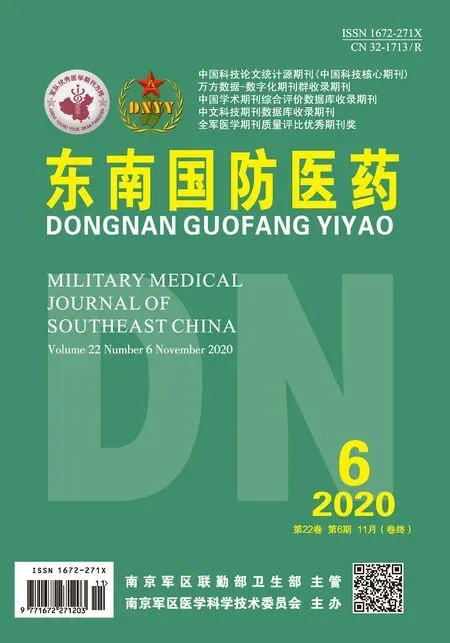补体受体1基因多态性与疾病相关性研究进展
唐 梦,朱明明综述,罗 伟审校
0 引 言
补体受体1(complement receptor 1,CR1)是血浆蛋白补体系统激活的主要调节因子。它是一种I型膜结合糖蛋白,分为胞外、跨膜、胞内三部分,缺乏胞内和跨膜部分的称为可溶性CR1,基因序列位于染色体1q32上。CR1表达于红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嗜酸粒细胞、T和B淋巴细胞以及树突状细胞表面。单个红细胞膜上的CR1受体密度仅为白细胞上的1/(10~50),由于红细胞数量巨大,因此体内约90%的CR1受体存在于红细胞膜上[1]。CR1的基因多态性包括3中,现已有较多研究证实其通过不同的基因多态性参与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如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氏病、疟疾、麻风、心血管疾病及肿瘤等。本文就CR1的基因多态性及参与疾病发生发展作一综述。
1 CR1及其多态性
CR1又称CD35,即I型跨膜糖蛋白,属于补体活性调节因子家族成员之一[1],在多种细胞上均有表达。其基因多态性包括:①导致CR1长度不同的基因多态性,②导致红细胞CR1密度差异的单核苷酸多态性,③产生Knops血型抗原的单核苷酸多态性[2]。
1.1 CR1长度多态性CR1的编码基因位于1q32,该基因存在4个不同大小的共显性等位基因,其变异是由遗传重复和缺失造成[3]。该等位基因编码不同的CR1亚型,其分子量大小从160 kda到250 kda不等,从小到大为CR1-C(F′)、CR1-A(F)、CR1-B(S)、CR1-D,其中以CR1-A(F等位基因型)和CR1-B(S等位基因型)最为常见。大量研究表明CR1-B(S)会增加AD的风险性[4]。
1.2 CR1密度多态性细胞膜上CR1的密度与常染色体共显性双等位基因系统遗传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也会改变细胞膜上CR1的表达量,其中Hind Ⅲ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与CR1基因内含子27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相对应,与细胞CR1表达相关。不同长度片段对应不同的基因,其中6.9 kb Hind Ⅲ基因组片段与低表达等位基因的纯合子相对应,表达200 kb以下的CR1,而7.4 kb Hind Ⅲ基因组片段对应高表达等位基因的纯合子,表达量则明显增高,而杂合子介于两者之间[3]。除Hind Ⅲ多态性外,细胞膜上CR1密度还与CR1基因中多种单核苷酸多态性相关,其中与疾病研究最多的有外显子33的Pro1827Arg多态性(C5507G)、外显子22的His1208Arg多态性(A3650G)。在白种人中,以上CR1多态性中的C、A等位基因都对应Hind Ⅲ RFLP的高表达等位基因,都与细胞膜上CR1的高表达相关[5]。由于85%的CR1表达在红细胞上,红细胞上的CR1通过与C3b、C4b结合,介导其调理的免疫复合物的清除。因此CR1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大部分都是通过改变红细胞CR1密度来影响疾病发展。
1.3 Knops血型抗原的多态性Knops血型基因型,由CR1第29外显子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产生。其血型抗原系统包括Knops抗原a和b(Kna和Knb)、Swain-Langley 1和2(Sl1和Sl2)、Sl3、Sl4、Sl5、McCoy a和b(McCa和McCb)、KAM+/KAM-以及Yka (York)抗原[6]。目前,该系统与疟疾等疾病的关系是研究的热点。
2 CR1与疾病
2.1 CR1与神经系统疾病
2.1.1 CR1与ADAD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主要是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其病理特征包括老年斑块和神经纤维缠结的形成,而老年斑块主要是由淀粉样蛋白β(amyloid-β, Aβ)聚集形成[7]。Lambert等[8]首次发现CR1基因位点的2个snp(rs6656401、rs3818361)与迟发性AD(late-onset Alzheimer’s disease,LOAD)的发病风险相关,并确定了编码CR1的基因是AD的易感基因。世界各地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确定了CR1基因与不同种族的AD均相关,包括欧洲、中国、美国等[9-11]。研究已经总结了CR1的多种单核苷酸多态性与AD相关,并且提示这种相关性具有地域差异[12]。在包含不同种族的人群中进行的meta分析发现CR1的rs6656401的A等位基因与所有样本中的LOAD的风险相关[13]。CR1在外周和大脑中均有表达,在美国的研究发现降低外周红细胞CR1和Aβ清除率的CR1多态性增加AD风险,而增加外周红细胞CR1(rs10127904)和Aβ清除率的CR1多态性降低AD风险[14]。上述研究表明CR1多态性对外周红细胞CR1表达的影响可能是CR1多态性与AD风险相关的基础。但也有研究发现小胶质细胞中高表达的CR1 rs3818361通过调节Aβ代谢和在白质中小胶质细胞活动来作为AD的调节剂[15]。不同风险位点与AD神经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不同,在芬兰老年人群的研究中发现,CR1 rs185310342与AD的脑淀粉样血管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16]。几乎所有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有神经纤维缠结,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发展为AD,在美国的研究发现CR1 rs6656401的次等位基因纯合子频率增高,可增加Aβ的沉积,导致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向AD进展[17]。既往也有研究提出CR1 rs4844609增加不同脑区Aβ沉积导致情节记忆下降[18],因此评估这些CR1基因多态性对轻度障碍发展到AD具有预测作用[19]。在中国,Zhu等[20]在青岛进行的研究发现CR1-SNP(rs12034383、rs3737002和rs6691117)与AD患者中颞叶体积的变化显著相关。同时他们还提出CR1-rs10779339的变异通过降低脑葡萄糖代谢率而增加AD的风险。总之CR1基因多态性从不同方面影响AD相关的特征,如记忆力下降、Aβ的清除以及大脑结构等。与AD发病相关的易感基因的多态性不仅影响疾病本身,还会影响患者对其他病原体的易感性,Harris等人[21]提出CR1基因多态性可能影响大脑对HSV-1的易感性。
研究已经明确指出AD与长CR1亚型相关[4]。在法国的研究发现CR1-B(S)中虽然存在额外的C3b/C4b结合位点,但其表达频率却明显低于其他CR1亚型,而这可能是由于其附加片段中基因位点的甲基化增加造成的,从而增加AD的风险性[22]。
2.1.2 CR1与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PD)PD的症状包括运动症状及非运动症状,认知障碍就是非运动症状之一,而AD是认知障碍最常见的表现形式。相似的病理及临床特征表明AD和PD可能有一些共同的遗传发病因素。在非西班牙裔白人、巴西人的研究中,未发现CR1的rs6656401与PD存在联系[23-24]。但最近在中国的研究发现,当CR1的rs3818361基因型为AA时,具有APOE的ε4等位基因的人群PD风险降低,而rs3818361基因型为GG时PD风险增加[25]。表明PD和AD可能通过基因-基因相互作用导致其相似性。
CR1基因作为参与AD的免疫反应的特异性基因,提示免疫炎症过程可能是AD发病的驱动因素。同时也增加了对PD的认识,可能成为治疗两种疾病的靶点,因此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2 CR1与疟疾恶性疟疾主要是疟原虫侵入红细胞的一种传染病,包括两种致死性的并发症,严重疟疾贫血(severe malaria anemia,SMA)和脑疟疾(cerebral malaria,CM)。CR1作为补体激活调节因子,存在于大多数血细胞表面(85%在红细胞),不管是感染恶性疟原虫的红细胞与未感染疟原虫的红细胞通过CR1形成玫瑰花环结,还是红细胞上CR1可调节间日疟原虫对网织红细胞的侵袭,均证明了这种分子在恶性疟疾的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26]。红细胞上CR1密度多态性对疟疾感染有影响,也具有地域差异。Cockburn等[27]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CR1外显子22 A3650G多态性的中等表达基因型(HL)与严重疟疾的保护有关。在印度的研究发现CR1内含子Hind III RFLP、CR1外显子22 A3650G多态性以及外显子33 C5507G多态性的高表达基因型与SMA、CM易感性增加相关[28]。这些研究提示高CR1的红细胞有可能堵塞脑毛细血管,导致严重疟疾。在泰国,Nagayasu等[29]发现Hind III RFLP的低表达基因型(LL)与CM易感性增加相关。在日本,CR1的rs9429942 高表达等位基因TT与CM的保护性相关联[30]。这些研究表明由红细胞上CR1(CR1/E)调节的循环免疫复合物的清除在脑疟疾的发病机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巴西,研究发现knb等位基因以及该等位基因与KAM+等位基因的结合会增加疟疾的易感性[31]。在非洲,Knops血型抗原系统多态性对疟疾的易感性有重大影响,研究结论却不统一。在西非研究发现McC血型抗原的McCa/b和McCb/b基因型可能分别与对严重疟疾的易感性增加和对严重疟疾的显著保护有关[32]。而近年在肯尼亚的研究中发现Knops Sl2多态性与脑疟疾和死亡显著降低有关,而Knops McCb多态性与脑疟疾发病几率增加有关[33]。同时还有重要发现,即上述保护作用只在正常α-珠蛋白基因型个体中可见,因为观察到Knops Sl2和α+地中海贫血基因型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而以上结果均表明CR1基因密度及Knop血型多态性都会影响疟疾的易感性,但是具有地域差异,这种多态性可能是由于基因的选择性保护。
2.3 CR1与心血管病风险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一种进行性疾病,其病理特征是脂质和纤维素在大动脉中积聚,也是一种多种基因相互作用的疾病[34-35]。CR1不仅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成分,还有研究表明其介导了动脉粥样硬化中低密度脂蛋白的清除[36]。因此分析CR1基因的多态性有助于了解心血管疾病(冠心病)的风险。首先是关于红细胞上CR1密度多态性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研究。在意大利和波兰人中均发现了CR1-Pro1827Arg多态性与冠心病相关。在意大利,研究发现伴有血脂异常的冠心病患者的CR1-Pro1827Arg多态性的低表达基因型(GG)明显降低。在波兰人中,有心血管病史的终末期肾病患者的CR1-C5507G基因多态性的低表达基因型(GG)明显增高,而且该基因型也与心肌梗死相关[37]。现在已经发现了多种CR1-snps参与心血管病的发病。de Vries等[38]通过调查发现有12个CR1-snps与冠心病相关,其中10个CR1-snp与冠心病风险降低有关,有2个CR1-snp与风险增加相关。而以上与冠心病风险相关的多态性位点还与冠心病的炎症指标(如CRP)及死亡率相关。以上研究都表明了CR1基因多态性在在冠心病中有重要作用,未来我们还要着重研究这些CR1-snp在心血管病中的功能,以利用这种多态性协助治疗。
2.4 CR1与麻风麻风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和麻风支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对麻风的易感性不同,研究者一直在寻找其中的原因。而众所周知,补体系统在多种疾病的感染中都有重要作用,也包括麻风。其中CR1可以表达在多种细胞上,当表达在吞噬细胞上时,CR1主要介导补体调理的病原体的粘附和吞噬。而麻风分枝杆菌就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巨噬细胞,因此推测CR1的多态性可能影响麻风分枝杆菌病的易感性。但既往对于CR1基因多态性与麻风的易感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却很少。最早是Fitness等[39]报道了马拉维农村地区麻风病与McCoyb等位基因的保护性关联。后来在中国也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但未发现麻风病与CR1多态性有关联[40]。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遗传背景的不同。最近Kretzschmar等[41]调查了巴西麻风患者的CR1多态性,并且利用SSP扩增得到的信息重建了18个单倍型,发现其中重组人*3B2B.3A2B.3B1单倍型会增加个体对麻风的易感性,且与年龄、性别和种族无关,最古老的单倍型rs12034383的GG等位基因也增加麻风的易感性。以上研究表明CR1多态性和单倍型可能通过增强寄生虫吞噬和炎症而增加麻风的易感性。但还需要在更大的研究中验证以上结论。
2.5 CR1与肿瘤肿瘤的发生发展涉及很多因素,有环境因素也有遗传因素。而Zhang等[42]总结了补体系统在癌症中有重要作用,包括调节基质细胞免疫、诱导肿瘤细胞增殖、逃避凋亡和免疫监视,促进肿瘤细胞迁移和增殖。而CR1作为补体级联反应的调节因子,其基因多态性在肿瘤的发病中也有重要作用。而临床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多种与CR1基因多态性相关的肿瘤。在胆囊癌中,Srivastava等[43]在北印度进行的研究,发现CR1外显子22的 A3650G 多态性的低表达基因型(GG)与胆囊癌风险增加相关。并且这种基因多态性现象在女性中更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红细胞CR1的低表达导致免疫清除功能受损所致,但是这种性别差异我们还需要在更大的实验中验证。在肝癌,首先是胡金川等[44]通过研究提出CR1基因SNP位点rs4844600 G>A 与肝癌相关,对应的基因型GG、CC携带者肝癌的易感性也增加,而对应的基因型GA、CT 携带者肝癌易感性降低。后来Luo等[45]研究了CR1基因多态性与广西人群HBV相关性肝病的相关性,发现CR1基因rs3811381、rs2274567多态性均与研究对象乙肝病毒相关性HCC易感性相关,特别是在男性、酗酒者和非吸烟者中。但前者主要在50岁以上老年人中,后者主要在50岁以下年轻人中。在胃癌中,胃癌是来自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目前其发生发展机制仍未明确,与多种因素有关[46]。Zhao等[47]调查了中国人群中13个CR1-snps与胃癌风险的关系,发现CR1 rs9429942 CT基因型及rs7525160 CG基因型与胃癌易感性降低相关,而且由于考虑到基因相互作用在复杂疾病发病机制中的普遍性,在他们的研究还发现rs75422544、rs10494885和rs7525160这些多态性位点在胃癌中存在相互作用。在肺癌中,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在肺癌中占比最高[48]。Yu等[49]在研究中发现rs7525160 G>C多态性与非小细胞肺癌易感性显著相关,而且重要的是他们首次发现了这种多态性与吸烟状态的潜在相互作用,提示基因-环境相互作用在肺癌易感性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Chaszczewska-Markowska等[50]在波兰人中却未发现CR1的 rs7525160多态性与NSCLC的关系。以上研究表明CR1基因多样态性影响着肿瘤的易感性。
3 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述,CR1基因多态性具有地区和种族性差异。近年来,多数研究明确了CR1基因的单核苷多态性与不同疾病易感性的关系,但是这种多态性是否有助于疾病的治疗,也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未来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探索CR1基因多态性在不同民族,不同疾病中明确的功能以及利用这种多态性协助疾病的治疗。
——“零疟疾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