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在粽叶上的母爱
●夏生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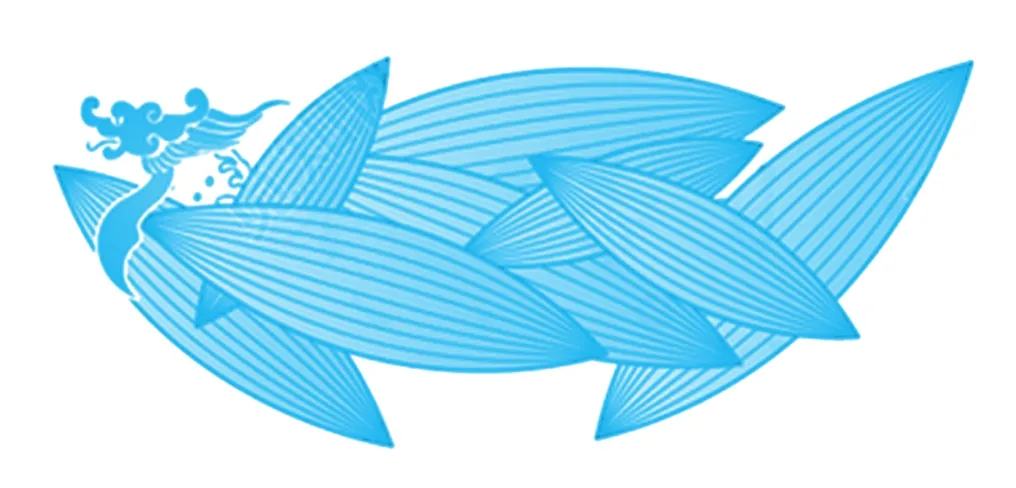
故乡有个传统,每逢端午、中秋和春节,俗称 “三大节”,都要吃粽子。此时,碧绿、轻盈、寂寂无闻的粽叶,就会派上大用场,它们是包裹粽子的最佳“外衣”。
我家屋后的黄土坡上,有一片粽叶林。一年四季都不用施肥浇水,却总能长出密密丛丛、异常茂盛的粽叶来。在母亲眼里,采摘下来后,它们片片都是宝。
粽叶采摘的最佳时间,是在农历的七八月份。时候一到,母亲每日便都要顶着似火的骄阳,去粽林中采摘粽叶。粽林又高又密,高得转眼间就将母亲淹没;密得连风都钻不进去,酷热难耐。可每每母亲进林,总要在里面待上大半天,双手不停地翻飞劳作,直到背后的竹筐被盛得满满。
每次出来,母亲都会浑身汗透,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可她顾不上休息,简单擦擦汗后,又要弯腰低头,用稻草将叠整齐的粽叶,一把把地捆扎起来,以便于放到太阳下晾晒,晒干后收起来待用。这个过程同样漫长而辛苦。
“三大节”前夕,母亲会将干粽叶拿出来一些,挑去附近的村庄叫卖。在乡下,干粽叶很廉价,一斤最多一块钱,可对母亲来说,已然十分满足和欣喜了。她总说:“这粽叶本来天生天长,也不需要本钱,卖一块就是赚一块,积少就能成多!”
卖过粽叶后,母亲还要去镇上集市卖自己包的粽子。包粽子,先是煮粽叶,干粽叶遇上沸水,如同茶叶遇见开水,瞬时便拾回了往昔粽林里的模样,碧绿、舒展、柔软,还多了一股不遗余力的清香。
母亲是包粽子的行家,煮好的粽叶经她双手一叠,便有了漂亮的尖角漏斗,舀入早早拌上花脸豆、红豆、枣子的糯米,压紧捏实,再取一根细麻线,一端用牙齿牢牢牵着,一端在粽身“打个滚”,一个棱角分明、修长、漂亮的粽子便利落地“结”在了麻线上,接下来,会结出第二个、第三个……成了一串。
母亲包的粽子特别紧实,煮熟捞起,剥去粽叶,插上筷子,就能举着吃,绝不会松散开。味道更是没得说:一口咬下去,劲道无比,香糯至极,若再沾上些细糖,则甜糯入喉进肺,口感更佳。冷吃或热吃,味道各有千秋。所以,母亲包的粽子从不愁卖。
到了“三大节”最为隆重的春节,家家都需要足够多的粽子,可镇上有不少商户不会包,还有的嫌烦,不愿去包。只想吃现成的他们,便会给钱请母亲帮着包,少的五六十个,多的几百个,糯米和馅料都是他们事先买好的,母亲等于是赚点包粽子的“手工费”。
由于订购量较大,母亲只好不分昼夜地包,尤其年关将近,我半夜起床小便,还能看到她弓着腰、低着头,在油灯下忙碌着。冬夜寒冷漫长,母亲脚边取暖的炭火盆早已熄灭,可她却浑然不知。母亲面前的糯米似乎永远都包不光,堆在桌上的粽子,如同一座座“粽山”,将她压得一刻也抬不起头来。
母亲采摘过多少片粽叶,包过多少个粽子,已无法计算。我只知道,她的双手因多次采摘粽叶,包裹粽子而结出一层层厚厚的、粗糙的老茧,牙齿也因咬过太多根捆粽子的细麻绳而时常酸痛、松动。
直到年纪大了,视力模糊不清了,牙齿也快掉光了,母亲才不再给人包粽子。但她依然坚持给儿女们包,每年我们兄妹三人回去过年,离家时,她都要给每家准备一大篮子粽子,这些粽子跟随着我们,从故乡走向不同的城市。
我们都有一个遗憾,谁也没能学来母亲的本领,包出来的粽子,无论外形、味道,都远不及母亲的。有时,小妹还怪她当年没好好教会我们,母亲则说:“会这个,算什么本事呀,你们把书上的知识学好,那才叫真本事。”
我们三人没有辜负母亲,都算把书读好了,离开了乡村,在城市里安身立业。但仔细一想,在过去那艰苦的岁月里,父亲过早离世,若没有母亲的辛勤无怨付出,边务农耕种,边琢磨出一条粽叶“致富经”来供养我们,我们又怎能按时交上学费,顺利读上书,从而能有今天呢?母亲才是那个有真本事的人呀!
年复一年,老家屋后的粽林总是郁郁葱葱,一坡碧绿,那永不凋敝的颜色,是故乡的底色,更是母爱的底色。母亲不就是那一片片粽叶吗?一生无求,寻常无奇,但却总能用爱紧紧包裹我们,想方设法地为儿女们撑起一片远航的风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