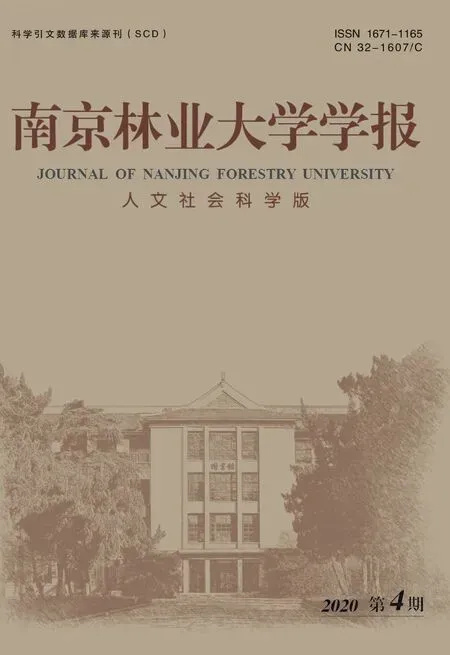从城市生态批评视角论城市怪象
唐建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一、城市生态批评:从缺席到在场
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开端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推动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催生了大量代表性城市文学作品。相比而言,西方城市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萌芽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主要关注城市对文学的影响,聚焦城市地形学、城市文学地图的描绘和城市文学史的建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成为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随着空间理论的兴起,城市文学研究转向具体城市空间的象征意义与叙说功能,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城市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城市空间的权力话语关系等得到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城市环境书写的研究长期以来都不尽如人意,人们更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将城市视为黑暗罪恶的温床、错位迷失的精神危机根源,将荒野和田园视为拯救人类的伊甸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领域城市生态研究得益于城市生态批评的发展,该理论萌芽于生态批评的土壤,经历了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1]
自1978年威廉·吕克特提出“生态批评”一词以来,该理论积极回应全球生态危机,在世界各领域学者的努力下,呈现出四大浪潮的发展局面。第一波浪潮中,荒野文学成为研究主题,研究对象聚焦于以诗歌为主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以梭罗为典范的美国自然写作作家的非小说作品。第二波浪潮指出了荒野研究中城市的盲点,学者们认为城市和乡村田野一样也应该纳入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代表性作品有社会生态学奠基人墨里·布克金的专著《无城市的城市化:市民权的兴衰》(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The Rise and Fall of Citizenship,1992)和迈克尔·贝内特和大卫·W.缇格主编的论文集《城市自然: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The Nature of Cities: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1999)。后者尤其强调了建构城市生态批评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需要重新认知城市化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以及城市的生态属性,旨在剖析城市生态社会问题的同时探讨城市栖居的可能性,为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指导,促进城市生态意识的培养。但是,处于摸索期的城市生态批评由于理论探索不足,经历了昙花一现后很快被转向全球性问题思考的第三波浪潮淹没。在第四波浪潮中,物质生态批评致力于糅合新物质主义与环境美学,以此推动环境人文学的发展,它将物质定义为物质化的过程,为重新审视城市的物质性与生态属性提供了可能。比如克里斯托弗·史莱菲克借用物质生态批评的观点出版了《城市生态:当代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物质施事与环境政治》(Urban Ecologies:City Space,Material Agency,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2014),指出重新解读城市的物质有利于消除城市与自然断层的偏见。这一时期的其他城市生态批评代表性作品有艾什顿·尼克尔斯的《超越浪漫生态批评:城市自然栖居》(Beyond Romantic Ecocriticism:Toward Urbanatural Roosting,2011),罗宾·墨里和约瑟夫·休曼的《城市生态电影》(Ecocinema in the City,2018)等。
不可否认,在世界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生态批评顺应了缓解全球性生态社会危机的时代需要,得到了全球学者的积极响应,从而推动了理论思潮在跨国性、跨学科性上的飞速发展。可是,当21世纪拉开世界城市人口超越农村人口的帷幕时,生态批评的城市维度即使经历了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但是至今其研究状态与世界城市的飞速发展及环境改善的时代要求极不相符。生态批评的一大谬误是“对乡村、西部和荒野空间的盲目崇拜”[2],导致城市研究成为荒野情结和田园书写主流下的暗流,或沦为生态批评“理论的边缘”。[3]xiii鉴于此,将城市纳入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考察其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互动关系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亟须深思植根于自然与城市二元对立关系的反城市偏见,揭示城市本身空间的发展不平衡,并为消解这两种怪象,有必要重新认识城市的生态属性,伸张城市环境正义,使城市生态社区的建设成为可能。
二、城市怪象的解读:反城市倾向与空间发展不平衡
凯斯琳·华莱士曾借用黑人女同性恋作家奥德莉·劳德的诗句“自然怪象”,分析劳德作为纽约市民所遭遇的种种怪象,“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与环境恶化怪象显得如此自然”[4]。在一定意义上,国际都市纽约所呈现的怪象也是全球城市的缩影,而解读这些怪象是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重要部分。
怪象之一是城市环境恶化表象后面所隐藏的反城市偏见。布克金指出,对城市的抨击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至今未曾偃旗息鼓: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就是文化与自然的对立,相比代表美好纯洁的乡村,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根源、丑陋的化身,而现代无序的城市更是“导致变态、恐惧、自私与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根源”[5]xiii。这种城市反生态的理念和反城市倾向同样渗透于早期的生态批评。在第一波浪潮中,深层生态学在责问人类中心主义时,所构建的生态中心主义却主张离开导致生态精神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来到荒无人烟的“真正”自然——荒野。对这些学者而言,经过人类加工的城市是非自然的,它侵占了大量山野田地与河流森林,密集的人群与高科技工业产品释放大量的垃圾废物,而远离栖居自然梦想、居住在水泥森林中的人们更容易出现精神危机。这种反城市的偏见是城市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内在原因,乡野变为自然的代名词,而城市成为见证人类文明衰落的场所。这种偏见也反映在很多城市文学作品中。舍伍德·安德森在其作品《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中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讲述了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的没落与大城市涌现对小镇的冲击,书中主人公乔治·威拉德乘坐火车离开家乡的背影也叙说着奔向城市的孤独与迷茫。伊迪丝·华顿笔下的莉莉在纽约的闹市期盼着“更安静的地方”,华顿与同时代作家亨利·詹姆斯、西奥多·德莱塞等一样继承了对美国田园乡村浪漫化的气质,在讴歌乡村的安谧环境与朴实灵魂的同时,表达了“对城市的批判”[6]。同样,诗人卡尔·桑伯格在其成名作《芝加哥》中也揭露了城市“不加理性控制、无限吞噬自然资源以求发展”的阴暗面,在他笔下,城市是“狂暴、庞大、喧嚣”的代名词。[7]
为了“拯救”城市,让自然回归城市,修建公园和广场成为重要任务。对于内战后重建的美国,欧洲城市成为其城市化的模板,人们认为绿化有利于遮掩城市的粗糙,培养市民的温文尔雅之风,从而降低城市的犯罪率。可是,这种将城市绿化视为营造优良道德氛围的做法无法根除反城市的偏见,反而更加凸显了城市是非生态的怪象,就像《纽约兄弟》中的霍默,面对高楼大厦围建的中央公园,他感叹的是自然的“终结”。[8]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城市反自然的偏见也助长了反城市的气焰,20世纪初城市的扩张让位于该世纪70年代城市的逃离,“狂野自然的美化牺牲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城市投资大幅度缩水,政府将投资大力转向郊区居民区的建造,以迎合民众远离城市、走近乡村的栖居需要。[9]173尽管郊区成为美国民众的新田园,其扩建却是“地理和生态意义上的失误”[10]164。一方面,郊区建设导致城市杂乱无序扩张,成为一个缺乏中心的庞然大物:大量土地被征用,大量植物被连根拔起,大量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在城市与郊区之间的交通消耗大量的能源,分散的人群也势必扩大污染的环境;另一方面,奔波于不同地点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给予郊区市民所期待的诗意栖居,新田园的梦想被现实的无根感粉碎。
城市的另一怪象是空间在种族和阶级维度上的发展不平衡。毋庸置疑,无论在城市或乡村,种族主义与阶级不平等是美国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可是,在工业革命中扩张并弥漫着浓厚商业气息的城市,种族与阶级的维度却有着欲盖弥彰的特点,即炫目的商业化看似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减小各种社会差异,有利于掩盖种族主义与阶级不平等;但是,从环境非正义的视角来看,这些社会问题却愈加凸显。楼区林立、车来车往的城市日趋成为有色人种和下层阶级的聚居地,而绿树环绕、鸟语花香的郊区则是更多白人中产阶级的选择。20世纪上半叶大量美国南方农村人口向北方城市迁徙,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郊区迁徙实质上是“白人的逃离”,大部分迁居郊区的市民是中产阶级白人,这样他们可以远离聚集于城市的贫困人口与少数族裔,避免其子女与这些“肮脏卑劣”人群的后代为伍,从而保证其人种的纯洁与高贵。[10]166如果说美国内战后从法律上宣告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合法,那么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实质上导致“居住隔离”在种族和阶级维度上的合法化,而“这种美国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致使城市贫穷延续,成为美国种族不平等的主要原因”[9]180。安德鲁·莱特从认知角度重新解读了“荒野”一词,“荒野”不再指代远离尘嚣的自然世界,而是指代“野性自然中居住人群的野性”,即人们内心世界的野性,对很多白人而言,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族裔并没有被城市文明所征服,他们内心的狂野导致城市从文明之都沦落为野蛮荒原,因此,“这种对城市居民与城市空间的诋毁无异于过去对原住民与自然空间的妖魔化”[11]。贝内特在揭露城市贫民窟形成的历史原因时,指出政府巨幅削减贫穷人口聚居的城市房屋建设经费,而大量投资于郊区中产阶级房屋的建设,这种劫贫济富的方式体现了严重的环境非正义,即严重损害了所有人口享受安全清洁自然资源的平等权。[9]179这种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怪象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索尔·贝娄笔下的芝加哥拥有着“厚实的墙壁,黑人住的贫民窟里散发着臭气”[12]334,主人公赫索格只有远离喧嚣污染的城市,在田园般的路德村才能享受到“宁静的真情”[12]376。美国城市自然写作的代表作家查尔斯·西贝特也在悲叹纽约这座“曾经伟大的城市”随着白人向郊区的迁移正经受着“可悲的衰落”,这里大部分市民是黑人和拉美裔移民,人们仿佛已经“遗忘”了他们的存在,政府很少投资城市的基础设施,路面经年未修,到处一片颓败。[13]
面对两大怪象——植根于自然与城市二元对立关系的反城市偏见与城市空间在种族与阶级维度上的发展不平衡,生态批评学者并没有提出毁灭城市、回归田园的建议,相反,他们提出应该将城市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认同其生态属性,伸张城市环境正义,而这也是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另一重点。
三、城市怪象的消解:认同城市生态属性与伸张城市环境正义
针对城市非自然的偏见,有必要重新解读城市内在的生态属性,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消解这一偏见的良方。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城市为生态社区、城市为自然文化结合体、城市为物质化过程。
在专著《无城市的城市化》中,布克金强调城市的最佳状态是生态社区。对布克金而言,城市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进程。盲目的城市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地球的人口分布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城市化还是人类自身导致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消除城市,完全抹杀城市化,而是从生态系统的整体主义和发展思维的角度将城市视为生态社区,鼓励市民通过互动建构城市的“第二自然”,即“与自然环境共存的人为自然”[5]ix-x。在一定意义上,布克金所提出的城市生态社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也是消除城市怪象的一大手段。
另外,城市被视为自然文化的结合体。如果说“荒野像城市一样由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话语塑造”,那么城市也像荒野一样由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因素合成。[2]与荒野不同的是,城市留下了更多人类打造的烙印,这就是城市被布克金称之为“第二自然”的原因,但这也无法否认城市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和荒野一样需要水、空气和土壤。在这里,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也相互依存、互惠互利,不同的是,人们无法更直接地了解所建桥梁房屋和所造汽车电器等消耗的各种自然资源,而在城市中栖息的动物和生长的植物往往在种类特性上与荒野中的很不相同。而从开放渗透的角度考察空间,城市不仅包括桥梁房屋、公园街道等物质环境,还包括使城市充满活力的人群、社区和机构,城市居民和乡村居住者一样,通过在城市空间中与其他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互动培养地方归属感,以此构成城市的自然文化结合体。劳伦斯·布尔在其专著《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2001)中,将“环境”定义为“感知世界中‘自然的’和‘人造的’两个维度”,而城市和乡村同样都是物质的集合与想象的对象。[14]6鉴于城市居住是我们未来的指向,布尔提出我们不能逃离城市,而应该“重新栖居城市”,不仅城市规划者与建设者担当着促进“重新栖居”的使命,而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需要投入到“重新想象工业城市对自然景观的改变以及重新想象自然环境的构成性影响”的双重任务中。[14]86在一定程度上,将城市视为自然文化结合体颠覆了自然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关系,艾什顿·尼克尔斯将这种结合体直接称为“城市自然”(urbannature),其核心观念就是“人类从未因为人类文化而脱离野性自然”[15]。
消解反城市偏见的第三种观念就是解读城市为物质化的过程。史莱菲克融合物质生态批评、文化生态与城市生态的观点,建立了“城市文化生态”的范式,探察城市中自然环境与文化元素之间互相影响而形成的“多重复杂的物质互动联系”[3]xii。从新物质主义角度来看,城市是“包含有机物/无机物和自然物/人造物等物质最密集的地方,也是人类与其他物质主体互动最复杂最纠缠不清的地方”[3]xxix。所有物质之间的互动过程组成了城市的能量流动与生态足迹,比如城市运转过程中会产生工业污染物、农药、垃圾等,它们是生产保证人类生存的其他物质时留下的有毒物质,严重危害人类自身的健康。从社会意义来看,城市物质生态批评是一种环境伦理,雾霾、毒气等污染物作为物质主体会作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机生命,人们应该关注并积极应对这种危害健康的物质化过程。可以看出,从物质的角度解读城市空间再次证明城市是自然文化的组合体或生态社区,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任何时候都进行互动,这些互动在公众话语与文化想象中又不断被再加工,从而形成了创造发展城市的物质化过程,而这也构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将城市视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城市生态观有力反驳了城市非自然的错误理念,作为一种“生态伦理,它关注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如何经营运转,考察运转中的各种弊端,提供让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建议”[3]xvi。
针对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另一怪象,伸张城市环境正义是重要途径。史莱菲克认为“城市是日渐扩大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典型社会环境”[3]xxxv。城市规划作为环境政治的重要内容,涉及工厂、医院、下水道、垃圾回收处等的位置规划。由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分配不平衡,白人上层/中产阶级成为主导社会话语的群体,他们成为决策城市规划的主体,当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将工业污染区、垃圾处理厂等建立在边缘群体社区时,这些消声的有色人种或贫困人群的健康将直接受到威胁,而这也直接践踏了所有人拥有健康环境的平等权利,换而言之,这就是环境非正义的表现,“社会正义与环境保护应该齐头并进,缺乏环境保护,物质环境将不宜居住;缺乏正义,社会环境也同样不利于人类生存”[3]xxxvi。史莱菲克用多部文学作品分析证明,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政治规划导致了当今的城市环境恶化,比如垃圾堆积与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也带来了环境非正义,不仅危害本地市民尤其是边缘群体,而当地的环境污染也会导致全球环境恶化。但是,史莱菲克也指出,环境政治不仅包括由主导群体或利益集团上传下达的城市规划决策,而且也涵盖草根民众对这些决策的反馈影响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环境正义诉求,很多社会媒介其实就是这种诉求在想象空间的再现,而文学作品是社会媒介中的重要部分。比如英德拉·辛哈的代表作《据说我曾经是人类》揭露了化工厂毒气泄漏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曾经可以站立行走的主人公在这场灾难后沦落为四肢行走的怪物,他的创伤经历传达了作者对边缘群体的同情,也是作者作为普通市民对城市环境非正义的控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想象空间的艺术产物再次证明了城市作为生态社区的复杂性:人类与非人类物质的互动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危及环境健康的灾难;城市决策者在环境问题上的短视或者对边缘群体利益的无视将导致环境恶化,而包括边缘群体在内的普通市民也可以通过发声伸张环境正义。比如朱恩·德怀尔以美籍墨西哥裔女诗人桑德拉·希斯内罗丝为例,探讨少数族裔在房屋建设中的创造性表达不仅挑战了白人对整齐划一社区的标准,也抒发了个人传达本族文化元素、树立民族归属感的情怀。希斯内罗丝曾将自己的房屋粉刷成墨西哥祖先欣赏的紫色,却因为违背了白人中产阶级要求社区整齐划一的标准,被城市设计审查委员会告至法庭。希斯内罗丝并没有向西方主流话语妥协,她坚持少数族裔在历史进程中参与了生存空间的创建,并且事实证明他们能够改善居住环境,以此驳斥了西方有关少数族裔是导致城市贫困罪恶的不良分子的论断。希斯内罗丝的观点也反映在她的小说《芒果街的小屋》中,她在想象空间中再次证明房屋的主人可以通过反抗城市规划中的主流话语实现自我建构,反过来,这种自我表达又可以为社区带来“创新与活力”,“使贫民窟变得典雅,为郊区增添情趣”[16]。
综上所述,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消除城市非自然的偏见,将城市视为生态社区、自然文化集合体或物质化的过程,有利于肯定城市的生态属性,从而纠正城市反生态的错误理念,扭转反城市倾向;针对城市空间在种族与阶级维度上的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认识到主导社会话语群体在导致该怪象中的负面角色,并发现城市边缘人群在反抗环境非正义、表达环境诉求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生态批评的疆界拓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根据联合国最新出版的《世界城市化展望》,全球城市化进程还在不断加速,本世纪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回避城市化问题已经绝不可能,而选择隐居乡野的做法无异于自欺欺人。根据生态世界主义观点,环境风险是超越本土界限的,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也已经是全球居民所要面对的问题。鉴于此,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继续推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背后是城市规划的诸多不平衡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环境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建设提供指导性建议,也体现了其社会价值。面对世界城市的飞速发展和环境改善的时代要求,城市生态批评的研究有必要发挥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消除反城市的偏见与空间发展不平衡,推动城市生态社区的建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