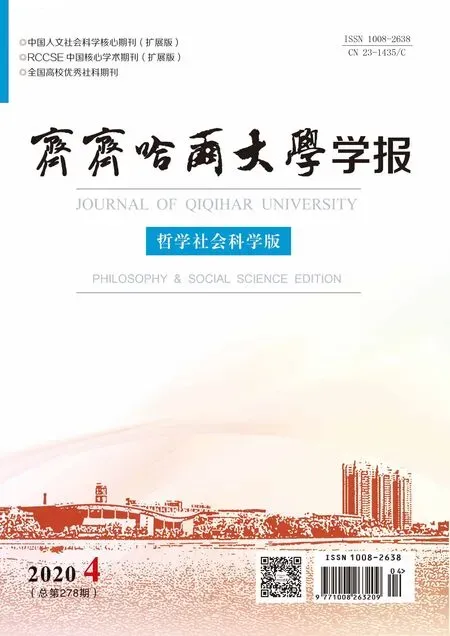孟子“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
李 炼,李 莹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孟子“仁政”学说的德治思想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同时是对孔子德治思想的超越。
“性善论”是孟子“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四心”,即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是人所特有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心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p59),同时,“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p200)孟子认为,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心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因此,仁义礼智也是每个人都有的,显然,孟子认为,人生而有“善端”,人的“四心”与“四德”是先天具有,并非外在所强加,也无关功名利禄,孟子发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思想,把人性与天性,人德与天德联系起来,认为仁、义、礼、智是先天存在于人内心之中的,是人所共有的内在本性,这种本性是纯善的,从这一前提出发,孟子认为,作为统治者与百姓一样,同样具有善良本性,只要在治理国家、管理政治中扩充这一本性,使其发扬光大,实行“仁政”,做到与民为乐,达到“以仁政得民心”,进行德治,保民而王。由此可见,孟子的德治思想强调“得民心”,“得民心”的手段即是行“仁政”。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私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2](p59)孟子表明,每个人皆有一种“同情心”,先王因为有同情、怜恤别人的心理,所以就有了怜恤别人的政治。凭借这种“同情心”来实施怜恤别人的政治,那么治理天下就如把玩手上的小物件一样简单。由此可见,孟子认为,实行“仁政”的前提是要有“仁心”,并加以扩充,通过仁政得到民心,实现德治。
一、 制民之产,安定民心
孟子虽没有明确提出人的需求理论,但是他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人要在解决温饱的现实问题之后,才会考虑教育及道德等精神上的需求。孟子提出了“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2](p89)“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分而定也。”[2](p89)孟子认为,要想得民心,首先要给予百姓一定的生存权利,才能安定民心,因此,孟子提出了“正经界”的土地改革,孟子认为,应对土地进行整理、界划、丈量,即“正经界”,“正经界”是井田制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而敢治私事”[2](p89)的理想社会,将土地以“井”字进行划分,中间的田地是公有田,大家共同耕种,周围的是私有田,先公后私,把公有田料理完毕,再去料理私人的田地。以此使百姓有“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2](p13)只有使百姓自身及其家庭拥有生存权,有一定的生活保障,能生存于世,而后才能教导百姓向善,安定民心,以此得民心,服从君王的统治,保持政治稳定。
为了能够“制民之产”,孟子认为不仅需要“正经界”,同时也需要“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即减轻税赋。当时的诸侯为了战争,对百姓实行三种赋税,这使百姓难以负担,甚至出现野有饿殍的惨状,此种环境之中,百姓不可能“有恒产”,因此,孟子认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2](p57)在某些方面免除百姓的税赋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之安心生产,满足自己生存的基本条件,百姓则会对君王产生感恩之心,同时,孟子还强调,对于鳏寡孤独这四种社会上无依无靠的人,应当首先考虑他们之生存状况。若最无依无靠的人可以存活于当时之社会,那么有依有靠之人应当是无忧于生存这一问题,正经界,免税赋,百姓安居乐业,民心安定,社会稳定,政权稳固。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p4)孟子认为,如果在自己一家人的宅院里,种植桑树,那么年岁大一点的人就可以穿丝袄了;家家有饲料去喂养鸡狗猪,那么也可以吃肉了,一家人划分的耕地,生产不被妨碍,一家人也能饱腹,尽心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的道理、敬爱兄长的道理去教导学生,大街上也不会出现背有重物的老人,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是不可能的事了。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即如此,孟子认为,温饱乃道德礼仪的基础,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百姓就无法生存,就无法谈及教育道德礼仪等问题,最基本的家庭单位无法生存,社会动荡,统治者无法统一天下,所以,孟子认为,应先“正经界”,再“置民以恒产”,安定民心,最后“保民而王”。
孟子强调要“制民之产”,强调“正经界”的土地改革,区分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同时,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在此基础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2](p4),种种措施皆是为了使民富之。再如“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对于刑法应当减免,赋税应当减轻,如此才能使百姓深耕细作,利于百姓生活。同时,在徭役方面,孟子主张统治者不能大修大建,一旦统治者大兴土木,就必然要使用劳动力,百姓就无法进行正常生产,耕作劳动力减少,不利于农业的生产,此后果必定是君独乐而民不乐。孟子认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统治者不能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对于百姓的剥削,不能毫无限制,需给予其一定的生存权,因此,孟子提出“以仁政得民心”之论断,通过“正经界”的土地改革,使民先富之,保障其生存权,同时为民谋利,与民同利,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得到百姓的信任与民心,安定百姓的生活,以此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与民同乐,收揽民心
孟子认为,想要实现“以仁政得民心”,进行德治,需要收揽民心。孟子十分重视“与民同乐”,认为君王应当“与民同乐”,才能收揽民心。孟子询问梁惠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梁惠王回答与人一同欣赏更加快乐,同样,比起少数人与多数人一起欣赏,梁惠王认为,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会更加快乐,因此,孟子对梁惠王说道:“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日:‘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日:‘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2](p20)孟子的意思很明确,他认为,君王的快乐并不只是君王的快乐,同样可以成为百姓的快乐,例如:君王爱音乐,百姓若是没有生活上的负担,也会眉开眼笑的和君王一起欣赏音乐,同君王一样心悦;若君王爱狩猎,只要不耽误农时,百姓也会为君王喜爱狩猎而开心。正如齐宣王的狩猎场“方四十里,民由以为大”,而周文王的狩猎场“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其原因就在于周文王“与民同之” ,而齐宣王则为己用之,百姓不能体会到狩猎的快乐,反而认为这是陷阱,自然就会失去民心,因此, 孟子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君王同百姓一同快乐,而不独享其乐,百姓便会心悦诚服,服从君王的统治。
孟子通过讲述周文王和夏桀的史事对梁惠王进行劝诫,《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2](p3)孟子认为,周文王兴建高台深池,虽然动用了百姓的力量,可是百姓毫无怨言,反而十分高兴,且取名“灵台”、“灵沼”,其原因就在于周文王能与百姓一同快乐,百姓快乐了,会认为这是一位好君王,自然就会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因此,君王和百姓都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与民同乐的同时收揽了民心。但是,夏桀与此相反,《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夏桀自比为太阳,百姓却怨恨他,要跟太阳一起死去,纵使有高台深池,却不能够独自享受,其原因在于夏桀只顾自己快乐,而忽视了百姓的感受,失了民心,孟子以此告诫梁惠王,作为君王,首先要成为有道德的君王,其次要学会与民同乐,快乐要分享才会实现真正的快乐,同时对于百姓而言,君王能够与民同乐,即肯定了百姓在君王心中的地位,百姓自然就会诚服于君王,如此也就收揽了民心。
再者,孟子认为,要做到与民同乐,收揽民心,反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也是十分必要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认为,兽类自相残杀,百姓都厌恶,作为君王,若是让百姓面露饥色自己厨房却有皮薄膘肥的肉,那便不能做百姓的父母官,不配当君王。孟子劝诫齐宣王实行“仁政”,齐宣王以喜爱钱财为由拒实行,孟子则以《诗经》里的公刘为例,认为君王若是喜欢钱财,也应当同百姓一起,尤其是社会上的鳏寡孤独四者,对于穷苦无依的人,更应该格外照顾,百姓同君王一起喜爱钱财,共同致富,百姓富足了,君王富足了,与民同乐就实现了。相反,如若不能和百姓同乐,得不了民心,百姓唉声载道,自然会犯上作乱,因此,作为君王,即使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对于百姓,仍然要做到与民同乐,百姓生活幸福了,怎么会想要去毁灭这种幸福呢,如此也就收揽了民心。
再者,在选拔人才方面,孟子认为也应讲究与民同乐,孟子对齐宣王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2](p30)孟子认为,选拔人才,当慎重。若是身边的亲近之人一致举荐某人,不能轻信,但是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也应当加以了解,若有真才实干再加以任用。孟子认为,选拔贤能,不应受身份的限制,同时,还要顺应百姓的意愿,满足百姓的需求,百姓则认为君王是为百姓着想的君王,百姓的自我存在感得到了满足,也就获得了民心,收揽了民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游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p24)如果君王能够顺应百姓,了解民心,并以此为乐,那么百姓也会顺应君王,把君王的快乐当做自己的快乐;如果君王能把百姓的忧苦当成自己的忧苦,那么百姓也会为君王的忧苦而忧苦。圣明的君王应当与自己的百姓同甘共苦,心中永存黎民百姓。如此,君王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成为英明君主。
三、谨庠序之教,规范民心
孟子认为,在安定民心、收揽民心之后仍然要规范民心。对于如何规范民心,孟子十分看重文化和教育的诱导和侵染作用,提出“谨庠序之教”来规范民心,通过仁义道德调节人伦关系,加强个体家庭的道德教化,对道德关系进行调节以此为“以仁政得民心”奠定文化基础实现德治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
孟子强调人性善,一方面认为凡人皆有“四心”由此发展出“四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p59)皆是上天的赋予。梁涛先生认为极可能是孟子与告子的人性之辩促使了孟子“四心”说的形成,由此孟子通过“四心”对性善进行了理论解释和说明。[3](p322)另一方面,梁涛先生认为孟子所举例孺子入井是为说明人皆有善性之存在,其表现出的善行也是出自其内在善性。“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是我本身就具有的,由于环境的侵染和自己主观的不努力、对人性本质的不探索导致人的善良本性的遮蔽。“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内在的德性是完全可求的,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通过四心表现出具体的善行,谓之善,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没有表现善的行为,其“性”仍为善,不过是遮蔽了人的善良本性而已。因此,并非人人都是尧舜,但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2](p147)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存在“四心”,蕴含道德心理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孟子认为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才能使四端之心生长扩充和实现,从内心按照仁义去行事才能体现人与禽兽的真正区别,使之向善实现人的善性。因此,在“四端”的基础上孟子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明人伦的道德教育以此维持并扩充人的善良本性。孟子十分重视教育,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教育主要通过兴办学校来进行。通过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等大道理来教导百姓,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教化,使得社会上各种等级的人可以遵循人伦规范的要求,形成人人互相亲近的和谐的社会风气。
在教育方面尤其要“明人伦”,孟子认为,人的社会关系主要由五组关系组成,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这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五种关系之中家庭关系包含三类:父子、夫妇、长幼;社会关系有两类:君臣和朋友,这五种关系共同组成了所有的社会伦理关系。维持这五种关系就要做到一条准则:“父子有亲、君臣有礼、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p94)“父子有亲”说的是父亲与儿子之间要有骨肉亲情;“君臣有礼”即是教导君与臣之间要持有礼仪,君臣之礼各不相同,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p142)也即臣待君如何,首先得看君待臣如何;“夫妇有别”教导夫妻之间挚爱但是有内外之别,在家庭中妻子应当是顺从于丈夫不违背丈夫,如此家庭关系才能和谐;“长幼有序”讲的是应尊敬老人、爱护幼小,有尊卑,幼服从长,弟弟服从兄长,如:“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朋友有信”教导朋友之间要有诚信,即以诚待人,若无诚信人与人之间将无信任可言,没有信任朋友之间也就不叫朋友了。孟子提出这五种人伦关系,就是要教导人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必然关系,并遵循相对应的行为准则。首先以家庭为基础促进家庭和谐,每一个家庭共同组成社会,以家庭之和谐促进社会之和谐做到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2](p89),孟子认为只要上层阶级明确了人伦关系,下层民众也会相互亲近,即是起到一种“上行下效”的作用,就算是圣王来了,也会来讨教的,孟子认为,这是得民心之后规范民心的方法。
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吃穿住行,缺乏内在的教化,这就与禽兽没有什么差别了。又如“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认为,君王要对百姓进行教化,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姓明察人伦关系,所以,他要求在实现“制民之产”,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后,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而教育的内容也就是“明人伦”,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孟子认为,君臣同样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但是孟子所主张的爱既不是杨朱的自私之爱,也不是墨子的兼爱,而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等级之爱。因为等级分明,所以即是间接的要求百姓服从君王的统治,同时,在教育过程中,君王要以身作则,时刻关注百姓的需求,时刻分享自己的快乐与忧愁,如此,百姓从内心也能够时刻牵挂君王的快乐与忧愁,君王心系百姓,通过种种手段保障百姓的生存,满足其需求,随后进行道德教化,百姓就会“感恩”于君,形成“忠诚于君”的心理条件,最终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因此,孟子的“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理想便实现了,通过对民心的收揽、安定和规范,最终实现“仁者无敌”,统一天下的目的。
四、保民而王,利用民心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p128)在孟子看来,政权的转移、得天下的根本即是能否“得民心”。那么,对于如何得民心,孟子认为,得民心之根本在于实行德政,仁爱民众,即通过三条路径:制民之产,安定民心;与民同乐,收揽民心;谨庠序之教,规范民心,通过这三条路径使百姓获得实际利益,百姓一旦获得实际利益,则会安定生活,对君王充满感恩之情,于是“中心悦而诚服”,最后实现其政治目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只有品德高尚的君王才能实行仁政,推行德治,无德之王是不能推行仁政的,因为无德之王本身不具有德性,更无法推行德性,无法实施仁政,所以,才会有百姓推翻暴君的暴政,更不要说用“仁政”去赢得“民心”,从而“王天下”了。
孟子之所以提出“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是因为孟子认为,仁与不仁是统治者能否“保民而王”的关键,而统治者推行“仁政”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2](p59)。统治者通过施行“仁政”,如“制民之产”、“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等具体措施,给人民以实际利益。[4](p82)孟子认为君王给百姓以实际利益,实则是想利用百姓的“感恩之心”,认为君王施恩于民,民受恩则感恩于君,对于统治者的统治,百姓就会乐于接受并服从统治,统治者通过施行“仁政”,尊重百姓的意愿,为百姓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使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通过调节君与民之间的道德关系,赢得百姓的支持,实现“得民心”,最后得到百姓的臣服,由此统一天下,即是“保民而王,利用民心”了。孟子在与梁惠王的谈话中说道:“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刃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离子散。彼陷溺其民,王王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2](p8)孟子对梁惠王说这段话的意思是想劝诫梁惠王施行仁政,他举例到只有一百里的小国都可以通过仁政而使天下归服,不要说魏国这样一个大国,若向百姓实行仁政,百姓就可在闲暇时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如此,就算是木棒也可以抵挡拥有锐利刀剑的秦楚军队,魏国实行仁政,而秦楚不行仁政,那去讨伐秦楚两国,无人可与之抗衡,因此有仁德的人是天下无敌的了。而这就清楚的表明了孟子对“民心”的高度重视,认为只要统治者行“仁政”,得到人民的拥护,便能得到民心,利用民心维护自己的统治,“仁政”之所以能统治天下的根据就在于此。同时,孟子也从反面论证了不行“仁政”,不得“民心”之后果,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2](p128)也就是说,桀纣因为暴政,失去了民心,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因而失去了天下。孟子而后就提出了得天下的办法,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另一方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p258)也反映了孟子对“民心”的重视,得百姓欢心的便可以做天子,“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此孟子指出了得天下的一条规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2](p128)
孟子生活的年代多年战争,民不聊生,当时诸侯国的君主都关注的是如何用武力来征服别国,尤其是在《孟子》一书中,就有多个君主向孟子讨教“天下归一”之道,但是孟子反对用武力讨伐,主张“仁政”,认为君王应当“以仁政得民心”,“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2](p10)也就是说,当今没有一个君王是不爱杀人的君王,但凡有一个不爱好杀人的君主,那天下的老百姓都会日思夜盼希望得到他的解救。孟子深知战争之苦,认为,爱好杀戮的君主是不会长久统治国家的,也不会使民心归顺,但是实行“仁政”,进行“德治”却可以“得民心”,就是因为在德治这一大环境下,百姓能够满足自己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需求,甚至能够受到道德教化,家庭稳定,试问谁想成为无依无靠的人呢?因此,实行“仁政”,进行“德治”,保护百姓,得到支持,带来的则是天下归一,和谐安定。因此,孟子认为,通过实行“仁政”收揽民心、安定民心同时规范民心,通过种种措施,在经济上使百姓富起来,在文化上,使民教之,明白封建人伦关系,在政治上选拔贤能,在个人修养上,提高君主和百姓的道德修养,逐步得到百姓的尊重与信任,百姓生活富足了,以此便能“得民心”,“民心”得到了便可以加以利用了,利用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百姓努力耕种,敦促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统治者的统治自然而然也就稳固了。从根本上来说,孟子虽高度重视“民心”,肯定了人民在统一天下中的作用,但他并没有真正看到人民的重要性,仅仅是单纯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或是手段,而其“以仁政得民心”之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以此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孟子认为,唯有施行“仁政”,进行“德治”,得到百姓的支持,才有利于封建统治者进行长久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显示出其“民本”思想,以及“民”、“民心”的重要性,孟子的“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在客观上或多或少符合了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满足了百姓的需求,但其根本目的仍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孟子的“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其“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既是一种政治主张,同时又是社会道德理想,特别是对于“民心”的高度重视,表明其“仁政”是关于“民心”的一种德治方式,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确有借鉴意义。但是孟子的思想并不完美,尤其是对君王的要求,过于理想化,同时寄托了太多希望,且封建社会中,多数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依靠道德去解决的,由此导致其想法过于理想化,现实生活中难以实行。分析孟子“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一方面有其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有其过时性,但是对于当代社会仍具有部分现实意义需要去挖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应当客观的看待孟子的“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从其“得民心”的手段和过程过来说,对于当代社会确有启示。
就经济层面来看,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管做什么,经济基础都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与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略有相似,他们都看到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表明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体现了孟子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精神特征。在现代社会,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要求,这从根本上肯定了经济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同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龙头之首,其重中之重在于解决极端贫困人口。孟子在其“制民之产”中认为,对于鳏寡孤独者应尤为关注,也即是在强调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贫困人口应该尤其关注,此与现代社会强调经济建设是相通的。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目的是使人民都富起来,为和谐社会创造坚实的经济基础。
就社会层面来说,孟子讲求收揽民心,实则是看到了“民心”之重要性,孟子虽以人民为手段,但是其重视“民心”的思想,仍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一定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强调民生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这与孟子的与民同乐,收揽民心具有相通之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根本上肯定了人民是目的这一前提,做到发展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就文化层面来说,孟子坚持“性善论”,强调“善”乃人的天赋秉性,为了维持这一善良秉性,必须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强调仁义礼智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因此,加强教育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仍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学习儒家思想,尤其是要加强伦理知识教育,通过“明人伦”的教育,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思想,对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道德上的调节,发扬人性“善”的一面,并通过教育扩充“善”,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完善人格,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就政治层面来说,孟子的德治思想仍有现实意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仁者无敌”,通过行仁政得民心的方式治理国家,统治天下,而德法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不失为一种治国良策。我国坚持法制为主,德治为辅的治理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方面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另一方面离不开对百姓的道德教化,通过道德礼制来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听取民意,反映民心,通过制度建设把民之地位放在首要位置,无疑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此外,对于人才的选拔,孟子的观点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何谓人才,孟子认为应当是德才兼备,孟子强调统治者应当是有德之人,无德之人不能得民心,推广到现代社会这仍然可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由于环境的侵染,会造成人的善良本性的蒙蔽,出现“有才无德”或是“无才无德”之人,因此,对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确是一个评判标准,在人才的培养、教育、选拔过程中坚持这一标准,强调道德自律,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