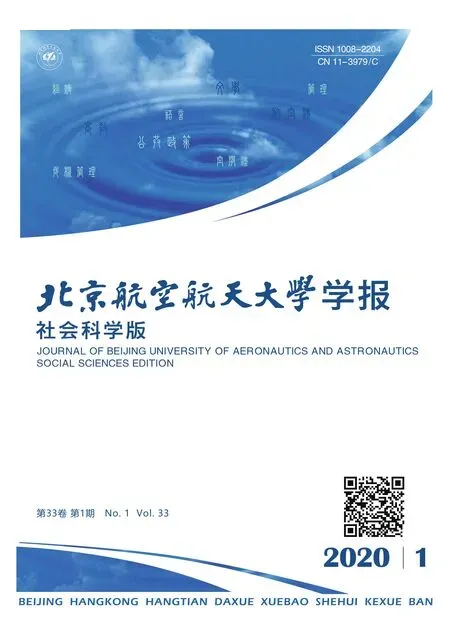航班放油备降的相关法律责任问题浅析
——以MU587和MU551航班为例
宋 刚, 耿绍杰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
近几年,新闻媒体时常报道旅客在航班上因身体不适出现各种危险症状需要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而导致航班改变飞行计划,被迫进行空中放油紧急备降附近机场的新闻。每次空中放油都会导致一系列的损失负担问题。笔者以航空运输性质的判定、航空承运人对旅客的救助义务、航油损失负担、旅客延误赔偿和旅客在航班上所受伤害的赔偿为顺序进行分析并给出一些建议。
二、案情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一)案情简介
2018年3月24日,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目的地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MU587航班从福州长乐机场起飞经停上海浦东机场,在飞行途中,一名中国旅客突然浑身抽搐、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救助这名旅客,MU587航班机组决定在空中放油并备降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①。
无独有偶,仅在一年之后,2019年3月27日,东航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前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MU551航班,在飞行途中,一名中国旅客突发不适,心跳加快、呕吐不止,MU551航班机组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决定在空中放油并备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②。
(二)问题的提出
这两次为了救助旅客,东航机组共在空中放油69吨,其中MU587航班放油30吨,MU551航班放油39吨。虽然东航损失了69吨航油,但是保证了两名旅客及时得到救治从而转危为安。毫无疑问,这两件事情经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然而其中却蕴含了诸多的法律问题,比如,东航每次为了安全降落被迫进行空中放油,损失的航油成本由谁承担?东航是否有救助旅客的义务?如果在飞机上旅客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东航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救人导致了航班延误,那么由此给其他旅客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谁负担?如果出现以上问题应该由什么法律文件来调整相关法律关系?虽然这两次没有法律纠纷,但是不代表以后出现类似事情依旧没有法律纠纷。无论是旅客还是航空承运人都要有“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的意识。
三、航空运输性质的判定
如果想要确定上述几个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定性两架航班的运输是不是符合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意义上的国际航空运输。一个航空运输被定性为非国际航空运输还是国际航空运输,其所适用的法律差别是非常巨大的[1]。
(一)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国际航空运输的认定标准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1款就开宗明义的规定了其适用范围,即“本公约适用于所有以航空器运送人员、行李或者货物而收取报酬的国际运输”。东航两架航班的运输目的明显属于为收取报酬而运送人员、行李或者货物,但是否属于该公约意义下的国际航空运输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根据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2款对“国际运输”③的定义可知,其将国际航班运输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国际直飞航空运输
国际直飞航空运输没有约定经停地点,只约定了其出发地点与目的地点,而且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当事国领土内。此种情况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短语,即“两个当事国领土内”,这个短语表明航空器起飞的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得在缔约国家境内,而且还得是不同的缔约国家,不能是同一个国家境内。以下举几个看似是国际航空运输,但其实不是国际航空运输的例子:①北京首都机场直飞平壤顺安机场;②北京首都机场直飞加德满都机场;③巴黎戴高乐机场直飞位于南美洲的卡宴罗尚博机场;④纽约肯尼迪机场直飞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前两者不是国际航空运输是因为,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虽然是分属于两个不同国家的领土,但是朝鲜和尼泊尔都不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家。后两者不是国际航空运输的原因在于,其出发地点至目的地点之间的飞行距离虽然很远且跨越了众多国家,但是该航班的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处于一个缔约国家的领土内(卡宴罗尚博国际机场位于法属圭亚那首都),所以也不是国际航空运输。
社会公众基本上会把以上4个例子认为是国际航空运输,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1944年《芝加哥公约》对“国际航班”的定义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国际航空运输”的定义。1944年《芝加哥公约》第96条第2款对“国际航班”的定义为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之上的空气间的航班。“国际航班”与“国际航空运输”这两个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2. 存在约定经停地点的国际航空运输
此种情况的航空运输并不要求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分别在两个不同的缔约国家,只要运输的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在同一当事国,并且在该当事国之外约定了经停地点,那么该运输就属于国际航空运输。此种情况的关键点在于“约定的经停地点”,而不管实际的经停地点,并且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明确规定不用考虑该经停国是否缔结了本公约。比如,航空运输合同约定的航程为北京经停平壤返回北京的航班,即使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都在一个国家领土内且朝鲜并非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家,但是这都不妨碍该趟运输属于国际航空运输。又比如,还是该趟航程,即使因为天气原因导致航班无法降落平壤顺安机场,直接返航了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属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2款所定义的国际航空运输。
(二)MU587和MU551两架航班运输性质的判定
因中国、英国与美国均属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家,所以出发地点为中国,目的地点为美国的MU587航班属于国际航空运输。在此需多提一句,一名旅客若购买的是MU587航班全程的机票,那么即使是在福州至上海的航段内,其也属于国际航空运输,在这一点的理解上可能会与社会公众的认识有所不同。同理,出发地点为中国,目的地点为英国的MU551航班也属于国际航空运输。故两架航班均为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所定义的国际航班运输。
四、航空承运人救助发病旅客的义务
将两架航班的运输定性为国际航空运输后,航空公司对旅客有没有救助义务就需要在国际航空法律渊源内寻找相关规定。
(一)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排他性适用
国际民用航空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多边国际公约、双边协定、各国国内法及法院判例、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和习惯国际法。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中,规定承运人对旅客责任的“华沙体系”下的各公约,均未明文规定承运人对旅途中发病旅客的救助义务。经查,《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中英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也未规定承运人对发病旅客的救助义务。
在各公约、条约未明文规定航空承运人负有救助旅客的义务的时候,就要利用“若未尽其义务则需承担法律责任,若已尽其义务则无责任之承担”的法理来进行判断航空公司是否具有此项义务。航空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应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没有法律义务,即无法律责任[2]。若航空公司在旅客发病时未救助旅客或救助不充分,造成旅客伤亡的情况下被法院判决需要因此承担赔偿责任,则说明其负有救助旅客的义务。反之,如果因航空公司未救助旅客,从而造成旅客伤亡但未被法院判决需要承担责任,则说明其不负有救助旅客的义务。
由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29条第1款的存在,旅客对航空承运人提起任何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只能根据该公约规定的条件和责任限额提起。航空承运人对旅客损害的赔偿制度只能优先并排他性的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就是为了禁止各国国内法在航空承运人对国际航空旅客、货物运输赔偿领域的适用,不管各国国内法对于赔偿制度如何规定,一律不予适用。这也就意味着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有关规定凌驾于任何国家相关的国内法律规定之上,只有在该公约没有规定相关责任情形(比如航空器空中相撞)或者明示适用各国国内法(比如谁能够提起诉讼)的前提下,方能适用各国国内法。虽然这个法条有一些“蛮横”和“独裁”,但是不得不说,正是由于此条款的存在,才保证了各国承运人赔偿制度的统一性。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EI AL Israel Airlines,Ltd. v. Tseng案确立的标准,如果该趟运输属于公约意义上的国际运输,则要么航空公司按照公约的责任规则对旅客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要么航空公司完全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一旦确定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意义上的国际运输,但根据公约第17条第1款④的规定,航空公司的行为不是第17条第1款的“事故”,则航空公司也不用基于其他法律被要求承担责任(即使根据其他法律,航空公司需要承担对旅客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29条的观点现已成为国际主流观点。基于此,不管世界各国国内法有没有规定承运人救助旅客的义务,只要航空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事故”,那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赔偿责任,也就意味着航空公司没有救助旅客的义务(未提供救助行为的情况下),或者已经尽到了救助旅客的义务(提供救助行为的情况下)。
(二)航空承运人救助旅客的义务
判断航空承运人有无救助发病旅客的义务的判断依据在于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而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直接决定因素在于是否构成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1款所规定的“事故”(关于“事故”的界定将在文末展开分析,在此只需要知道公约把是否构成“事故”的判断工作交给了各国国内法院,但是赔偿的制度还是要统一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
因美国法院对航空案件的判决往往形成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风向标,故参考美国法院对航空公司类似案件的判决进行分析,并将类似案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航空承运人未提供救助行为的案件;另一种为航空承运人提供救助行为的案件。
1. 航空承运人未提供救助行为的案件
McCaskey v. Continental Airlines案,旅客在航班飞行过程中突然中风但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因未给乘务员最基本的医疗培训,所以没有提供基本的医疗帮助也未备降机场,延误了治疗,法院认为航空公司没有救助行为,因此构成“事故”,航空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⑥。
Husain v. Olympic Airways案,因为旅客闻到烟味引发过敏,身体不适,乘务员没有尽力协助旅客帮助他更换座位导致旅客最后哮喘发病死亡,法院判定因乘务员的不作为行为构成“事故”,航空公司最后承担了赔偿责任⑦。
Seguritan v. Northwest Airlines案,旅客心脏病发作,乘务员未能提供医疗协助导致其病情加重,被判决未尽到相应救助义务,构成“事故”,需承担责任⑧。
Turturro v. Continental Airlines案,旅客第一次乘坐飞机,由于太过紧张,他在进入机舱内半分钟时在舱门入口处焦虑症复发,但是乘务员拒绝他下飞机,旅客因焦虑症过于严重而住院,法院认定乘务员拒绝他下飞机的行为属于未提供救助的行为,构成“事故”,航空公司需承担责任⑨。
2. 航空承运人提供救助行为的案件
McDowell v. Continental Airlines案,旅客心脏病发作,机组在用机上医疗箱为其进行紧急救助后未选择备降,而是直接飞往预定目的地。在航班飞行过程中,旅客心脏病加重,导致死亡。法院认定不构成“事故”,因为机组已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紧急救助。Krys v. Lufthansa German Airlines案同样也是如此。
Fulop v. Malev Hungarian Airlines案,旅客在航班飞行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匈牙利航空公司机组成员为其提供了的紧急医疗救助,并且广播寻找乘客中的医生帮助他,定时询问其身体状况。该旅客主动询问是否可以备降,但是机组并未同意备降。后来因为未及时备降进行手术而导致需要进行心脏支架手术。旅客以机组未备降使他没有得到及时手术为由要求赔偿,但是法院判决不构成“事故”,不承担责任。
Cheng v. United Airlines案,旅客在遇到较强气流导致的颠簸中受伤流血并且昏迷,机组人员虽然提供了一些救助,但是未能提供充分的紧急救助,被法院认定是公约项下的“事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通过上述两类案例可以发现,如果航空公司在旅客发病时,完全没有提供基本的医疗救助,没有任何基本的救助行为,肯定会被法院认定构成“事故”,需要承担责任;如果航空公司在旅客发病时,提供了一些救助,但是未达到充分的程度,也会被法院认定构成“事故”,需要承担责任;如果航空公司在旅客发病时,提供了充足的医疗救助,即使未备降,并且也未成功地避免旅客伤亡,法院也是不会认定其构成“事故”的,也就不用承担责任。此时结合“若未尽其义务则需承担法律责任,若已尽其义务则无责任之承担”的法理,可以推理得出最终的结论:在飞行过程中,如果旅客突发疾病,航空公司负有救助乘客的义务,且需提供充分的医疗救助。若航空公司在此情形下未救助旅客或者救助不充分,则会构成“事故”并因此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何谓“充分”,法院在判决中并未给出明确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充分”的评价标准不以飞机备降机场为必须。法律不要求机组在此种情况下必须备降有其合理性所在,一律要求备降不仅会大大降低飞行效率,而且进行备降的不确定性因素将会导致全飞机的乘客处于危险之中。机组对飞往备降机场的航线可能不熟悉、对备降机场所在国的飞行规则可能不熟悉,这都会导致危险的产生。
笔者认为“充分救助”的标准不能要求机组成员在飞机上对旅客的救助犹如医生在医院对患者进行救助一样,因为飞机上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医院,机组成员的医疗水平也无法跟医生相比,飞机上更不可能配备专门的医务室和医生。机组成员在上岗之前都会进行职业培训,而紧急救助是培训内容的一部分,各国民航主管部门都会对各航空公司的培训进行监督,所以,机组成员对旅客的救助只需要达到同行业的平均水平即可认为达到了“充分救助”的标准。
五、航油损失的负担
幸运的是,第二节两次案情中的旅客都因而得到了救治而转危为安,但是东航却因此而损失了航油。根据中航油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吨航油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约为7 300元,两次救助旅客仅仅因为空中放油就损失人民币约50万元,这还不包括后来又在备降机场补充燃油的费用和重新起降的费用。那么这笔数额不小的损失究竟应该由被救助旅客负担还是由东航自己承担?这也是备降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
(一)发病旅客负担航油损失
目前,中国民航界对此种情况的做法都是本着弘扬救人为本、人命至上的理念,航空公司放油损失都是独自承担,并没有让被救助旅客承担。笔者认为,航空公司没有找被救助旅客索赔的原因是主要出于建设企业形象。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主旨在于实现国际航空运输中的“某些”规则而非一切规则的统一化,在“某些”范围内公约规则具有一概排除国内法适用的效力,而在这“某些”范围以外,国内法规则自然是允许得到适用的[3]。旅客受伤、行李或货物受损、延误是属于“某些”范围以内,由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规则调整。但是其第29条的优先性、排他性条款的应用情形是旅客向承运人要求索赔。此时属于承运人向旅客要求索赔的情形,所以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此种情况下就无用武之地了。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法律渊源的适用规则,由于多边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均未规定相关的负担条例,所以此时应当适用各国国内法。准据法的选择应坚持航空器国籍国法原则的情况下,对于不同特殊情况兼顾考虑其他国家法律[4]。两案中航空承运人是中国法人、航空器登记国为中国、发病旅客具有中国国籍经常居住地为中国、订立运输合同地在中国,此时准据法应为中国法律。可以试着列举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
1.债法领域的救济可能性
(1)无因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301条规定了承运人负有尽力救助旅客的义务,虽然此时应该适用中国国内法,但是中国国内法对“尽力”一词的规定是非常模糊的,也未对航空承运人“尽力”救助旅客做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也没有相关判例。此时,借鉴国际上对航空承运人救助旅客的义务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第四节的分析,航空公司救助旅客的义务并不以备降为必须。东航两架航班放油备降救助旅客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在机上救助旅客,为旅客提供应急药品、将发病旅客转移到公务舱平躺休息等;第二层次是航班备降机场救助旅客。在第一层次内,航空公司救助旅客的行为都属于法律规定的义务,不满足无因管理中的构成要件,若想构成无因管理则不能负担相关管理性义务。据此,航空公司不能要求发病旅客给付应急药品和升舱的价款。第二层次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超出的范围可以成立无因管理之债。航空公司为救助旅客所损失航油、备降机场的相关费用可依无因管理之债要求发病旅客赔偿。
(2)见义勇为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83条赋予了航空公司争取适当补偿的依据,该法条又被称之为“见义勇为”法条。顾名思义,见义勇为是一种行为人无相应强制性义务的自发行为,其构成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要件与无因管理最基础的构成要件是一致的,即“行为人没有负担相关义务”。这就意味着,在第一层次内发生的相关费用,航空公司不能要求发病旅客支付,但是在第二层次内发生的费用及损失可要求发病旅客给予其适当补偿。
相比之下,《民法总则》第118条所规定的无因管理之债比其第183条更能使航空公司得到完全的偿付,因为第183条仅规定“可要求给予适当补偿”而不是“全额补偿”。
2.侵权责任法领域的救济可能性
(1)公平责任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公平责任原则可以为航空公司挽回一定损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必须得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才可适用。如果认为旅客侵害了航空公司的航油所有权,那么航空公司需要证明旅客存在侵权行为。程啸教授认为,“侵权行为必须受到意志的支配,即行为是在行为人的意识控制下、由其意愿所引导的,可以控制的人的行为。倘若某一行为不是在人的意思下的支配下进行的,而是被强制作出的身体的动作或者因外力的影响而产生的不自觉的反应,则不属于侵权法的行为。”[5]91根据此观点,则不能把旅客突发疾病、身体不适说成是一种侵权行为,因为旅客的意识并不能控制其是否发病。这样发病旅客就不是《侵权责任法》第24条所规定的侵权行为人,这就否定了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2)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一种三方构造,即导致险情发生的人或事物,紧急避险人和受损害的人。两案中,发病旅客是导致险情发生的人,紧急避险人和受损失的人都是东航。问题的关键是紧急避险定义“加害他人的行为”中的“他人”一词是否包括紧急避险人自己,也就是说,这就涉及到紧急避险是否适用于避险人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中国有法院认为“他人”一词包括了紧急避险人自己。同时理论界也有支持此种观点的[6]。但是程啸教授对此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作为免责事由的紧急避险仅适用于避险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不适用于给自己自身造成损害的情形。在紧急避险人因避险行为给自己造成损害时,不存在避险人对自己承担责任的问题,自然无需主张紧急避险而免责。”[5]325笔者认同程啸教授的观点,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受损失的人可以直接要求侵权行为人赔偿,而无需通过紧急避险要求赔偿。但是这样就又回到了上一点所讨论的问题,因不存在侵权行为,故航空公司也不能以此要求旅客赔偿航油损失。
(二)立法建议
虽然航空公司可以依据无因管理的法律规定要求旅客偿付相关备降的费用,但是航空公司往往都会弘扬人命至上,关怀旅客的企业文化而不会要求发病旅客赔偿,且即使要求赔偿,旅客也往往没有如此巨额的偿付能力。如果航空公司要求旅客赔偿备降费用,很可能既没要到钱,还有损企业形象。
长此以往,这样的结局就是航空承运人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放油救人造成极大损失的事件,而在旅客办理值机时就根据“国际客规”第29条第2款以旅客不健康为由而拒绝旅客登机。显然航空公司无法确认被拒绝的旅客都一定是不健康的,旅客还一定会因为对航空公司不满从而起诉索要赔偿。如此,只会使航空公司的承运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航空承运人有救助旅客的义务,在危急时刻如果具有备降条件应当备降,而且要确保承运人不因此而遭受损失。也就是说,因备降机场救助旅客而遭受的损失不应该由航空公司承担。但是笔者认为,将巨大的损失转移给旅客负担也是不合理的,这笔巨大的债务有可能使旅客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旅客是否会在航班上突然发病是一种不确定性因素,为了避免自己在航班上突发疾病导致的巨大债务,旅客很可能会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这样不仅会导致旅客出行效率的下降,还会导致航空运输业的发展停滞。
此时,最佳的方案是保险公司开发一种飞机上旅客突发疾病造成承运人损失的赔偿保险,然后立法者再通过立法规定旅客如若乘坐飞机就必须如同开汽车要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险一样,强制每名旅客购买此险。很多旅客在地面上即使身体状况良好,在高空中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突发疾病,而飞机上又不可能配备专门的医务室、医疗设备以及专职医护人员。虽然旅客突发急病的概率不高,但是一旦突发疾病造成飞机备降,就会造成一笔巨额的损失。如果法律强制旅客购买保险,那么当旅客在机上突发急病需要飞机紧急备降所造成的损失就会转移给保险公司承担了。故十分有必要强制旅客购买急病备降损失险。
六、旅客延误损失负担
东航两次放油救人都导致航班晚点了4个小时左右才到达目的地机场,因东航救助发病旅客给其他旅客带来的晚点损失应该由谁承担也成了一大问题。据东航工作人员介绍,有很多赶时间的旅客对飞机晚点表示理解。但是,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对潜在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航班延误的判定
首先需要确定晚点4个小时是否属于民航法律意义上的延误。航班晚于航班时刻表所公布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机场并不一定是延误。航班时刻非契约条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惯例[7]。因为客票本身不是合同,它所起到的只是一种证明运输合同存在的初步证据的作用[8]。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航空法研究所教授保罗·邓普西将航空法意义上的“延误”归纳为:延误是指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运输[9]。所以判断本案中两架航班是否属于延误需要确定东航完成该航班的时间有没有超过该航班以前执行同一航路所需要的平均时间,而不是看两架航班是否晚于航班时刻表所公布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机场。MU587航班从上海至纽约平均时间为14小时55分钟。MU551航班从上海至伦敦的平均时间是12小时20分钟。两架航班均晚点4小时左右,前者完成运输用了19小时12分钟,后者完成运输用了16小时30分钟,可以认定为明显超过了合理时间,构成延误。
(二)旅客延误损失的救济途径
确定了两架航班属于延误之后,就要确定延误造成的旅客损失的负担问题了。按照民法理论,此时因延误遭受损失的旅客存在两种可能的救济途径。
1.可能性途径一: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债务人的违约行为
第一种可能性的救济途径是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对于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的违约行为,究竟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制度还是严格责任制度目前理论界仍有争论。但是《合同法》第121条对此采纳了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为了体现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并且吸收了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上所说的“通常事变”情形亦有债务人负责的观点[10]。具体到两案中无论旅客有无过错,都需要先承担延误造成的损失,比如预定的接机专车、预定的酒店因航班延误而被取消预定的损失,然后旅客可以向东航追偿他们的损失。貌似这个途径是可行的,但是因为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29条的存在,使这个途径被堵死了。该公约第29条是索赔根据的强制性、排他性的规定,因该公约第19条已经规定了旅客延误遭受损失的责任制度,故延误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应当适用该公约第19条的规定,而不能适用《合同法》第121条有关第三人原因债务人违约的相关规定。通过该公约第19条可以看出,对于延误造成的旅客损失,航空公司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制度,如果航空公司证明了自己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就不用对延误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东航采取了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那么东航就可以不承担延误责任了。但是,何为“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何为“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
“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与英美法系“应有谨慎”原则存在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就是“应有谨慎”原则在民用航空法中的具体应用。如果认为“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这一短语不好理解,可以将其替换为“一切必要措施”,因为在英美法系中,这两个词只是同一法律概念的不同表述,就如同咱们日常生活中“出租车”与“的士”是一样的概念,并且作为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前身的《华沙公约》使用的就是“一切必要措施”这一短语。笔者认为二者除了用词不同,其本意并无实质性差异。《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该词是这样解释的:“期待于一个正常辨别力而谨慎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正常地应该采取的谨慎的、积极的或关怀照料的措施;它不是衡量事物的一个绝对标准,而是依具体有关事实情况而定的。”[11]可见,在过错责任制度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制度中,如果行为人尽到了“应有谨慎”的注意义务,采取了“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或称之为“一切必要措施”),那么行为人就不存在过错,自然也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在航空法司法实践中,世界各国对于“一切合理要求”这一标准的把握也是不同的。美国法院对“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的标准非常之高、非常严格,美国法院认为,如果航空公司在能力范围内有任何一件预防损害发生的措施能做到而没有做到,那么航空公司就需要为此损害承担责任,可参见1977年Hanover v. Alitalia案。在该案中,意大利航空公司意识到保险库中的物品极其贵重,故他对于自己保险库的看守采取了比其他航空公司更为严密的措施,但是仍没有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在庭审中,被告意大利航空公司主张其已经采取“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来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最后,法院判决意大利航空公司败诉,因为法院认为对该次不测事件,虽然意大利航空公司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防范,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本应要做或应该做到却未做到。被告未能采取保护贵重物品所应谨慎预见到的一切合理措施。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法院对“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的把握就没有那么严格。比如,英国法院的“Garein v. Imperial airways”案和法国的“Preyval v. Air France”案,这两个案件中法院均对于“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解释,两法院认为只要该航空承运人尽到了其他航空承运人同等的谨慎义务,采取了行业通用措施,那么就可以被认为采取了“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从而免责。
对“不能可采取此种措施”这一短语,笔者认为“不可能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就是对该短语最好的理解。如果是因为承运人以其能力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导致的延误,那么航空公司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两案中,东方航空公司选择了最合适的机场备降、在护送发病旅客下飞机的同时紧急联系地面后勤补加航油、加油完毕后又申请优先起飞等措施,可见航空公司为了使旅客尽量准时到达以避免因航班延误所造成损失,其已经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了最大努力。按照对于“一切合理要求的措施”的一般解释,东方航空公司在此种情况下,已经采取了与同行业承运人通常的措施。即使按照最为严格的美国法院对于“一切合理必要的措施”的判定标准,在此情况下,在其能力范围内已经尽到了一切的措施,所有措施均已采用也没有避免航班延误。同时,在此种情况下,东航也不可能安排机上旅客签转其他航班,如果签转其他航班,还要将签转旅客的行李重新分拣出来再运送至被签转航班,那么旅客延误的时间将会更久。所以可以认为,东航满足了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9条的规定,不用承担本次延误给旅客造成的损失。
2.可能性途径二:紧急避险的规定
在无法向承运人索赔的情况下,因延误遭受损失的旅客的可能索赔对象仅剩下发病旅客一个选项。此时,第二种索赔的可能途径是适用紧急避险的规定。在这里,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是发病旅客,紧急避险人是东航,受害人是延误的旅客。延误的旅客可以要求引起险情发生的发病旅客承担损失,笔者认为这是有法律根据的,即《民法总则》第182条紧急避险的规定。
七、发病旅客的医疗费用负担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1款明确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该公约第20条规定的免责条款也仅规定了因旅客过失而免除承运人相应责任的条款。可以说,旅客在飞行中受到伤害,要求航空公司承担严格的责任。
从表面看起来,发病乘客似乎可根据此严格责任条款的存在要求东航赔偿医疗费,但其实不然。可以肯定的是,两案中对于旅客遭受伤害的时候是处于在“航空器上”这一运输责任期间。但是并不是任何意外事件都可以称之为“事故”。20世纪80年代的赛科斯诉法兰西航空公司案,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华沙体系”下的“事故”一词并不等于《芝加哥公约》附件13中“事故调查”中的“事故”一词的含义,某个事件可能构成芝加哥公约意义上的“事故”,但可能不构成华沙体系下的“事故”。“华沙体系”中各公约均未给“事故”一词作出明确的定义,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依靠各国国内法院的法官依据其本国法进行判断。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Saks v. Ari France, DeMarines v. KLM Royal Dutch Arilines以及Warshaw v.Trans World Airlines案,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华沙体系”中“事故”一词的理解已基本趋于一致、形成通识。现“华沙体系”中各公约所写的“事故”一词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含义,它具体指的是不正常的、预料之外的、罕见的、人们不乐意它发生的事情,且该件事情必须与航空器飞行有关。如果完全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伤亡,不算事故。
文章第四节在讨论航空公司是否对旅客负有救助义务的时候提及了几个例子。
Husain v. Olympic Airways案中,旅客有哮喘病史,烟味可以引起他的急性哮喘,因身边旅客身上有烟味,这位有哮喘病史的旅客向乘务员提出要求更换座位,但是遭到了拒绝。后来,该名旅客死于烟味引发的哮喘。法院在该案中认为虽然旅客的死亡是因为其自身健康原因,但是乘务员在不会影响飞机飞行的情况下本来可以避免这种死亡的发生,但是她没有做到尽力救助旅客,在此类情况下,即使是由于旅客自身的健康造成的死亡,也构成事故。
笔者认为,根据美国法院对“事故”的认定,只要旅客所受伤害不是百分之百因其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即使旅客遭受损害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健康问题,但如果引起乘客损害的因果关系链条中存在一处是其自身健康之外的,对乘客而言是“无法预见、不可意料的意外事件”所导致的,那么就应当被认定为是“事故”。在Husain v. Olympic Airways案中,乘务员拒绝给他调换座位没有尽力协助他,就属于因果关系链条中“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
第四节中,另外两个未备降但是不构成“事故”的案例根据此种分析逻辑:虽然旅客遭受伤害是因其自身原因导致的,但是引起旅客损害的因果关系链条中不存在其自身健康之外的、对旅客而言不是“无法预见、不可意料的意外事件”所导致的。航班未备降对旅客而言是“可以预见”,而各公约、双边协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运输共同条件均未规定航空公司有备降的义务。航空公司的救助义务只需要达到充分即可。
按照法院对“事故”的理解,在MU551和MU587航班中发病旅客受到的损失完全是因其自身原因导致的,东航机组成员已经尽到了充分救助义务,引起旅客损害的因果关系链条中不存在其自身健康之外的、对旅客而言是“无法预见、不可意料的意外事件”所导致的,同时机组成员也无法避免此种损害的发生,所以不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1款规定的“事故”。两名发病旅客的医疗费用只能自己负担。
八、结语
综上所述,旅客如果在飞机上突发疾病,毋庸置疑的是航空公司有救助旅客的义务,如果不予救助,航空公司的不作为行为就会因其不作为行为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即使在此种情况下不备降,航空公司只要尽到了在航班上的救助义务也无需承担责任。在目前立法及相关种类的保险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航空公司为了救助旅客而造成的航油损失可以由发病旅客承担,但是为了便捷旅客的出行,减少旅客与航空公司因此而产生的负担,国家应立法推行“备降损失强制险”以尽量减少旅客和航空公司的损失。因航空公司救助旅客备降机场导致的其他旅客延误所造成的损失,受损失的旅客可以要求发病旅客赔偿损失。旅客须准确理解严格责任制度下航空领域“事故”的定义,发病旅客的医疗费用不能找航空公司索赔。
注释:
① 详见《乘客不适航班放油30吨备降救人 直接成本约50万》,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8_03_25_451477.shtml,访问日期为2019年4月20日。
② 详见东航新闻网《空中放油39吨 全航班一致支持 东航备降救治急病旅客》,http://www.ceair.com/about/dhxw/201904/t20190418_7312.html,访问日期为2019年4月20日。
③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2款:国际运输系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不论在运输中有无间断或者转运,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两个当事国的领土内,或者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有一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任何运输,即使该国为非当事国。就本公约而言,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两个地点之间的运输,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没有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不是国际运输。
④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1款: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
⑤ EI AL Israel Airlines, Ltd. v. Tseng, 525 U. S. 155(1998).
⑥ McCaskey v. Continental Airlines,159 F. Supp. 2d 562 (S. D. Tex. 2001).
⑦ Husain v. Olympic Airways, 116 F. Supp. 2d 1121 (N. D. Cal. 2000).
⑧ Seguritan v. Northwest Airlines, Inc., 446 N. Y. S. 2d 397(N. Y. A. D. 1st Dep't 1982).
⑨ Turturro v. Continental Airlines,Inc.,128 F. Supp. 2d 170(S. D. N. Y. 2001).
⑩ McDowell v. Continental Airlines,Inc., 54 F. Supp. 2d 1313, 1318—1320(S. D. Fla.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