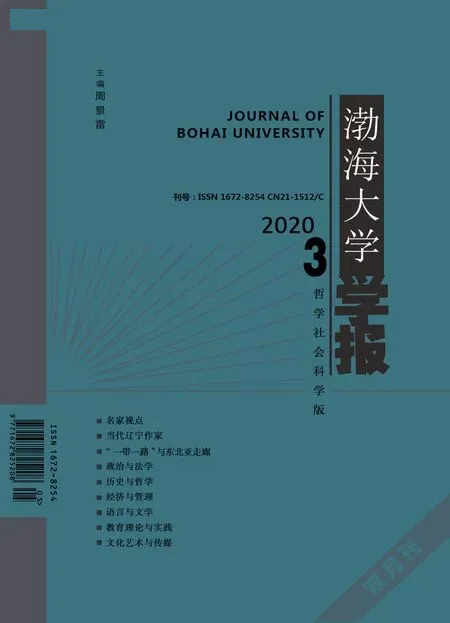构建新先锋的东北叙事模式
——与青年作家班宇的对话
林 喦 班 宇(.渤海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锦州03;.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 沈阳0000)
林 喦:班宇你好!近几年来,华语文坛出现“铁西三剑客”的名号,班宇、郑执、双雪涛三位来自辽宁沈阳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形成了比较突出的新时代新先锋的特征,获得了读者和学界的广泛认同,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大家也都欣喜地看到,在东北沈阳,在铁西区这块土地上成长出了这么优秀的作家。我想,“铁西三剑客”不是你们预期的,但有人愿意这样提及和归拢,势必有其合理性。从你个人的角度讲,这种效应也是你没有想到的吧?
班 宇:关于“铁西三剑客”,这个提法确实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估计其他两位也没有预想到。因为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会这样对自己进行要求,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写作。当然,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有自己比较明确的、清晰的内心表达,这是发自写作者个人内心的,也是来自于个人经验的。“铁西三剑客”的提法在我看来,可能是基于一个地理位置层面的概括而已,可能我们三个写作者有着比较相似的生活背景,有着相似的成长环境,有着似乎相似的阅读经验吧。
林 喦:在我看来,写小说是应该有天分的,也就是说,你具备了写小说的天分,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来。看到你的小说,我感觉,对于你而言,也是基于一种“心灵的自由”,而与反思一个时代其实并无关系。虽然很多评论家愿意把你的小说所投射的“时代大背景”看作“铁西区”,或者因为你少年时生活在铁西区。有资料说,1995年的沈阳,经济上出现了历史上最为萧条的时期,而那一年你才9 岁,你的童年记忆里深深埋下了“铁西区国企”转型的阵痛。根据你这样的童年记忆,评论家们便很“一厢情愿”地把你的作品(如你的小说《洪水之年》)归结为对“铁西区”一个时代的反思。我倒觉得,“铁西区”仅仅是作者为了叙事所表现的一个“环境”要素而已,也可以是“大东北”,是不是评论家想多了?你觉得呢?或者说,是你的小说作品再次唤醒了人们对“铁西区”(或者说东北地域)的回想呢?还是“铁西区”的过去给人们留下的印记太深刻了呢?
班 宇:觉得您说得很对。对于我的小说创作来说,“铁西区”首先是一个我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环境,毕竟我的个人记忆很多都是在铁西区完成的,包括童年和少年时期,还有一部分青年时期。我虽然没有以自己的身份经历过国企转型的变革,但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父母的朋友都是亲历者。所以,在我的作品里,或者说在我的所有小说里有一半都会涉及下岗或者铁西区这样的类似背景。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个人认为我的小说还是有一些自己在叙述层面上和技术层面上的探索。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太想将我的小说跟地域做成一个特别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我不想让大家仅仅从地域角度来对我的小说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解读。我认为,我个人的养分吸收,包括阅读和音乐,还有影像方面的这些影响可能是更重要的。讲一点阅读方面的收获,我觉得我受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比如余华老师、苏童老师、格非老师的影响非常大,我的小说技术和叙述模型以及叙述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向他们的一种模仿或者说是致敬。
当然不可避免地说,我也会回到东北和铁西,这个话题,我觉得确实是在近30年的过程中值得再去反思和探讨的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既然发生了,那么势必会对身在其中的人造成种种影响,这个影响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是一个人忽然丢了工作,或者是一个工厂忽然倒闭了,这就是一个事件,而影响却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随之展现出来的。比方说一个家庭受了什么样的影响?比方说一对情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怎么样的变化,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所有的这种事情、落在个人身上的这些故事,也许更值得关注,这个是所谓的影响之所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说铁西区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记,是一个类似于符号化的、类似于记忆经验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作为写作者,我是想从这些记忆经验上面重新梳理或者提升出来;从精神层面上讲,这种转变形成的问题思考算是我的小说想要探讨的命题之一。
林 喦:你觉得当时东北人面对下岗潮,面对生活的突然变故,面对变革时的生存态度和生存状态为什么能得到今天那么多人的共鸣?
班 宇:我觉得,我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不只是东北有这样的变革。据我了解,比如说武汉,比如说长沙,很多城市都面临着产业转型,国企改制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跟我的同龄者,或者说稍微比我小一点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记忆,所有人在那个时刻仿佛都处于某种不确定和动荡之中。这个现象,是我在小说里面所要讲述和阐述的内容之一,我觉得大家读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共鸣,就会激发出一些共通的时代记忆和情绪。这种情绪或者说共鸣,是时代的,不是地域的。
林 喦: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你的作品,是否也有“替父辈代言”的隐喻呢?
班 宇: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在我写作之前,我认为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面,上一代几乎是处于一种完全失语的状态,即他们在这种历史变革之中完全没有发出或者很少发出什么声音,我觉得这是我创作的一个动因。一个人如果身处在某个事件里面,他是很难说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的。比如说我们想叙述当下,想叙述现代,但是现在每天呈现给你纷繁的各种经验,各种信息太多,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对其进行或者做出一个很好的归纳和总结。
这样的话,你也很难选择一个角度来切入,进而理解你所身处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对于上一辈的人来说,可能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困惑,所以我的小说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是替父辈代言也好,替上一个时期做一个个人层面上的总结也罢,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的。我认为每一代人的声音都很珍贵并且值得去倾听,我觉得不能忽略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时代所应发出的这样的声音。
林 喦:当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们不能阻碍任何读者和评论家的“判断”,或者你自己没有这样想,但作品出来后所产生的这样的效果出来了,这也是作品的意义所在。我想,你之所以喜欢小说创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吧?或者说你是基于什么原因开始文学创作的呢?
班 宇:我个人的创作确实不是仅仅为了谋生,我最开始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写音乐、写乐评的。因为我当时是在读大学,那时候对音乐非常感兴趣,但是自己又不会什么乐器,只能以这种文字的方式来进行某种“曲线救国”,大概写了10年的乐评,几乎在所有的报章杂志上都发表过,包括《新京报》《通俗歌曲》《非音乐》《我爱摇滚乐》等这些杂志,还有《音乐天堂》《音乐时空》,等等。当写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整个媒体的格局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传统的纸媒日渐衰落。而新媒体又在这时刻开始诞生、开始发展,然后我对这个也进行了一些思考。我认为在资讯特别匮乏的时期,我像以前那样写作乐评是有意义的,那么在一个资讯非常丰富、非常丰满的时代里,仅仅是传递音乐资讯是不够的,我想有一些更多精神层面上对于自我的探讨。所以那个时候也恰逢豆瓣阅读举办了一个征文大赛,我在里面就投了一个稿子,写了工人村那一组作品,然后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反响,所以我更坚定了自己写作方面的信心,后来就一篇一篇的这样写了下去。
如果说是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还是对于个人困惑的一种疏解,或者说对于个体困境的一种描绘。我发现只有书写对我来说是最治愈最有效的。所以说,我需要书写,是我需要小说,而不是小说需要我。我觉得是这样。
林 喦:很多读者喜欢你的作品流畅的语言。既明白如话,又不像前辈那么欧化,既有东北方言的形象生动,又有古代白话的精髓。当然,你在语言上有自己的个性。你在写作的时候,有很强的针对性要表现所谓的这东北地域风格?或者说,这种语言风格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班 宇:关于语言的问题,我觉得必须重新发明,或者说是生成一种语言,才能描述好20世纪90年代千禧年时期以及当代东北。我的小说里面关于东北那些方言的使用,其实也是一种文学化的运用,我也不会每一个句子都是按照特别规范的方言词典上的一种表述去讲,而是尽量用一种日常的同时又稍微具有那么一点点文学性的语言来进行小说创作。
我觉得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复制或者还原出当时的东北,也能更好地展现出我所想要表达的作品的精神内核,所以我觉得这种语言风格算是一种改良。它最初的源头,比如说,我很喜欢老作家汪曾祺或者阿城,或者也有一些古文的编辑和阅读经验,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有一些影响;这对于我读过的那些欧美小说,整个的翻译文学的路径也有一方面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庞杂的一个影响。我可能从每一个点里面折取出来那么一点点,将自身作为一个过滤器——语言的过滤器,然后生成这种表现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我觉得我的小说里面的语言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有这种的也有完全比较西化的,比如《蚁人》等作品里面那样的表述。所以我认为每一篇小说都是不同的主题,每一个主题都有不同的可以去适配的一个语言风格,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要针对每一题、每一篇小说都进行一些语言上面的调整,以更接近自己想要描绘的精神核心。
林 喦:其实,我在与你交流,或者阅读你的小说之后,也不自主地陷入到了新先锋和“东北叙事”的“魔咒”里面。这说明,你的小说也确实有这样的特征了。所以,我设计我们对话的题目便成了《构建新先锋的东北叙事模式》。辽宁青年评论家周荣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班宇擅长运用意象和细节的力量,通过具有丰富象征和暗示意味的意象拓展文字之外的联想空间,达到言外之意画外之音的叙事效果”。看你的作品,如《海雾》《石牢》《空中道路》《逍遥游》《盘锦豹子》,等等。小说没有传统的情节“发生、高潮、结尾”式的小说模式,而是按照你自己的“意识”游走,并设置了很多带有荒诞和玄幻式的意境,可以视为游离于传统文化之外,不受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限制,比较在意念上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你的小说是符合这样的一种特征的。是这样吧?或者说,你在创作这种风格的小说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还是受到了某种小说风格的影响呢?
班 宇:我是这样觉得的,在我的文学系统里面,我认为小说跟故事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就是novel 和story 上面的区别。一个story 的话可以有开始可以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然后起因、高潮、经过、结尾,是这样的一个story 的故事的模式。
那么作为小说来说,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20世纪的布朗肖、卡夫卡、福克纳或者是贝克特,他们每个人的小说都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不同的表现手法。比如说福克纳那种强悍的、复杂的、缠绕着的句式;比如说布朗肖那种向内的、向自我的那种深入的挖掘和探索,就完全是在意识和头脑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游走和探寻。这都是小说的展现形式,所以我觉得,20世纪的现代派也好,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也好,这些文学遗产对我来说,我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小说,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卷本的一个大长篇,非常恢宏,非常浩瀚,里面有很多东方美学上面的东西,也有很多西式意识的影响。另一个是托马斯曼的《魔山》,阅读《魔山》的时候,本身就像是自己内心的一次永无止境的一次攀登。举这两个例子,意思是说,我觉得一个人的创作所受的影响,可能不单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作品,而是他所有阅读经验、人生经验以及他思考的一个总结,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产物。所以每个人在受了这些影响之后,比较关键的是要学到自己的语言和学会寻找到自己的这种创作方式或者说创作办法,这是一篇小说能成立的根基。
林 喦:你的小说反映出来你在小说细节上的用笔从来都是不吝啬笔墨的。举个例子,如《海雾》开篇就有这样的句子:“去野海要绕过那一趟狭长的铁栅,前几年是不必这样做的,低矮的树丛里有一道坦途,看海的人们从这条路上走过去,潮湿的尘土散落在脚踝上,再任由海水冲刷干净。那时每年虽然也有人溺亡,但没人将责任归咎于这片海”。作为一个读者而言,即使还没有读完小说,但开头这样的描述,就已经是让读者感觉到了这篇小说的“可读性”了,当然,也起到了未说下文之前,先设一个意境之谜的效果。
班 宇:这个是我个人对小说美学的一点粗浅的想法,我认为一篇小说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一个任务或者首先应该做到的一点应该是做到好读。这个好读,可能不只是在语言上要尽量完善,在相应的情节上面也要有所思考。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阅读取向是受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就是很多人不在纸质书上阅读,而是在选择屏幕阅读,包括电脑、手机、iPad,等等。
那么屏幕阅读最终的呈现方式跟纸质还是不一样,所以他们也会反馈到写作本身上来。我现在觉得所谓的21世纪或者说新时代的写作,一定要是讲一个比较俗的词语,就是有点扣人心弦的效果,让一个读者有往下继续阅读的动力,让一个写作者也有往下继续书写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这个我觉得是关键的。一篇好的小说应该像一个锁链一样,环环相扣,你读了第一句就想知道下一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并且这两句之间既有紧密的联接,然后其中也有句子与句子之间或者说段落与段落之间也有缝隙和诗意,这个是我的小说美学之一。
林 喦:比如《石牢》中“我虽十分疲乏,但睡得也不踏实,习惯颠簸之后,躺在这样平稳的床上,反倒不适应。我做了几个短暂混乱的梦,其中一个是在狭窄的山径上,雾气流滞,父亲走在前面,我默默跟在身后,他的步伐很快,我有点跟不上。我轻声喊他几句,也没有回应,只好向前疾跑几步,想要伸手抓住他的衣服,却不小心滑倒。地面湿润,遍布苔痕,我很着急,可怎么也爬不起来,双腿无力发颤,高声叫着父亲,他停在不远处,回头望向我,脸庞比从前更为瘦削,目光里全是恨意。我不敢与之对视,便低下头,将耳朵伏在泥里。我听见浓雾正簌簌落下,听见大地内部的声音,朝着远处波动,缓缓推进,又折射回来,仿佛装置着无数轨道,巨石在上面行进,相互碰撞后静止,堆砌成不规则的环形,也像一道垣墙,或者一座墓,将我环绕禁锢,困在此处,无人在外凿击,大地持续波动,天空如镜,浮云是它的倒影。”这种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充分展示你在小说创作技巧上的才华,既有暗示,也有隐喻,也集中表现了小说人物内心世界的无奈与迷惘,构成了你的小说的艺术特点。当然,这样的描写,也会让一般意义上的读者难以一下子明白作品,是吧?
班 宇:《石牢》小说是这样,最初是接到张悦然老师的约稿,是发表在他的《鲤》杂志上。这篇小说刊发是符合那期的一个主题——90年代。我认为我在接到命题的时候,我想我对于90年代的某种描述系里,我不想以一个切实的故事来描绘出我整体的一个对90年代的感受。所以我写了这样一个基于算是完全架空的这样一个故事,叫《石牢》。那么我觉得这篇小说可能会受余华初期作品的一点影响,它是完全架空的,每一个故事的背景是架空的,但是每一段每一句又都在写实,这是我对这篇小说的一点探讨。我觉得有一部分读者对这一作品的感受会跟《盘锦豹子》跟《逍遥游》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是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在可读性上来说肯定是比较高的,还是以叙述和讲故事为传统的。
而《石牢》这篇我只是觉得想要尽量完整的,尽量详尽地或者尽量准确地描述出来我对那一时代的感受,或许只有这种架空的形式更适合更适用,这种无限趋近于内心的这种形式,更让人觉得合适,所以我就选择了这种方式来完成这篇小说。还是我刚才说的那样,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实践语言,我觉得小说之间是有一个很大区分的。我觉得每一个作者在写完一篇作品,在开启另一篇新作品的时候,可能是所有的人都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面对的都是同一张白纸。
林 喦:坦率地说,看你的文学之路,和上几代人已经有很大不同。你走上文学之路有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文学评奖和新媒体的推广是不是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了呢?在今天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似乎每个人都可能要准备迎接新的职业和新的业态,你们会做一辈子小说家吗?
班 宇:我觉得我和同代写作者都不太会去思考我们做小说家的时间问题。我们写小说,大家更重要的是描述出此刻的一种感受,此刻的感受是对于追忆过往的一些感受,也可能是对于未来的展望,比如说一些科幻文学作品,也有可能是对于当下种种景观的一种分析和拆解,我也看见很多同辈写作者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新媒体和文学评奖机制一定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可以经由这两个途径,我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被更多的人所读到,然后产生一点点的影响,这对我来说还是未来的小说路径,我还是认为我想做到。
写一篇作品,我就认真对待,仔细的认真思考这一篇作品,不太会去想这篇作品出了之后之外的那些事情。我觉得无论是传播路径还是评奖方法,终归是对于作品的一种外界的宣传,或者奖励、激赏,而跟作品的内部对于自我的价值是还不是一个事情,我觉得小说最重要的是实现作者自己的某种理念,或者说是某种想法,描述出自己的那些内心的、那些暧昧的时刻。如果这点完成了,那么这篇小说也就完成了,其他也许都是附加品。
林 喦:在全国防疫的特殊时期,我们通过微信进行了交流。非常感谢,并祝你创作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