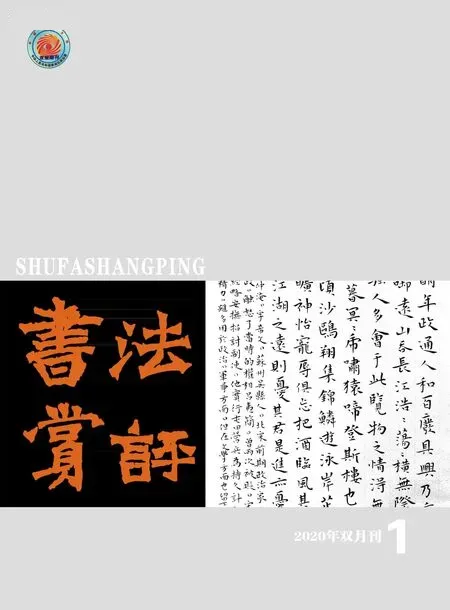两两素心存,终古照泉石
——陈奕禧与吴雯之交谊
葛曙明
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又字子文,号香泉,晚号葑叟。清代书法家,浙江海宁人,贡生。先后任职安邑县丞、深泽令、户部侍郎、石阡知府、南安知府。精于书法,后世称“香泉体”。所书《梦墨楼法帖》《予宁堂法帖》广为流传。著有《虞州集》《春霭堂集》等。
吴雯(1644—1704),字天章,号莲洋。清代布衣诗人,山西蒲州人,祖籍辽阳。早年以诗闻名,为王士祯、赵执信所赏识,应博学鸿词科荐举罢归,与傅山有“北傅南吴”或“二征君”之说,有《莲洋诗钞》。
一、陈奕禧与吴雯交往之起始时间
陈奕禧与吴雯应该是通过王士祯的圈子相识于京城。陈奕禧首次入京在1669年,《皇清诰封宜人先室沈宜人行述》:“己酉二月,予入成均,赴北试。”【1】但这年三月,王士祯前往淮安榷清江浦关,专司船厂。【2】陈奕禧并未在京城遇到王士祯,也没有证据能佐证他与吴雯相遇。而恰恰在这一年,吴雯随王士祯前往清江浦。【3】陈奕禧第二次入京在1677年,当时王士祯任职户部,诗名日盛。陈奕禧自农历1677年4月至1678年 12月在京,从诗文可以看出,离京前他已经投入王士祯门下。
吴雯首次见到王士祯是1668年,其年谱戊申条下有:“三月,始谒渔洋于京师。”【4】1677年吴雯至少有一段时间在京城,其年谱有:“汤西崖序云:丁巳识蒲州吴天章,慕其为人,与之交。天章方急归蒲州,未尝颂其诗。”【5】吴雯何时来京不得而知;从其诗句“鸿雁天边过,客子念远道”判断这次离京在秋冬间。1677年与陈奕禧有相遇的可能,但没有任何诗文记载可以证明。1678年冬,应博学鸿词科荐举,吴雯再次抵京。王士祯《吴征君天章墓志铭》载:“君在举中顾,独眈寂守。”【6】看来吴雯当时交往不广。但从陈奕禧对吴雯的悼诗可知,陈离京前正是两人相识的时间。陈有句云:“昔爱君诗会燕市,恰值中条就卑仕。君方奏赋明光宫,圣人抽落命数穷。”【7】证明相识地点是京城,相识时间就在前往安邑前。“恰值”一词说明当时相识不久。再者,如果相识已久,同时期文人诗文中就往往会留有痕迹。陈奕禧获得安邑丞任命后,吴雯也有长诗《送陈子文之安邑丞》相送。有句:“高才坐凭几,口占百函书。赠我数尺牍,藏弆等瑶瑜……索米向京洛,归梦无时无。谁知中条山,赞府先我趋。”【8】可知当时吴雯尚留京城备考,而陈奕禧已经先他赴山西任职了。因而可以确定他们的交往始于陈奕禧离开京城前的1678年冬。
二、陈奕禧与吴雯之交往状况
在陈奕禧一生的朋友中,除本邑的几位外,吴雯是十分重要的一位。王士祯《分甘余话》载:“门人陈子文奕禧以诗歌、书法著名……生平与蒲坂吴天章最善。”【9】两人接触时间主要是陈奕禧在安邑丞任上和深泽令任上时。两人时常往来并探讨点校古籍,题诗作书。两人相交至深,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失意之时见真情
1679年3月,吴雯失意京华,以荐举罢归蒲州,随后家事连连不顺。这一期间吴足不出户,情绪十分低落。此时陈奕禧与吴雯的往来,给予了他面对现实面对生活的勇气。
吴雯少而失怙,下有弟妹五人,生活艰难。其年谱载:“有母年五十,有弟三人、妹二人,婚嫁皆仰雯。”【10】早年他以诗文谒父执辈,因诗而名,年仅35 岁即与傅山、朱彝尊等当时令其仰望的学界前辈同获博学鸿词科荐举,虽不能说是春风得意,在京这半年,确也感受到了希望,而一旦放还,心理落差可想而知。离京时京城名流以诗相送表达种种惋惜之情,更令吴雯感到沮丧。1679年秋,陈奕禧亦有诗《奉和吴天章见寄绝句,时天章以荐举罢归》记述当时情境:“玉溪山人何日来,秋来念尔更悲哉。燕归气象何萧瑟,几得愁言把酒开。”【11】屋漏偏逢雨,在吴雯归居中条山这段时间,养家糊口的压力以及回乡后家里发生变故,令其更为消沉。他在《罗萝村诗序》中说:“家居数当骨肉之变,忧伤荼苦,转以疾困,足不出户限者且一年。”【12】当是他儿子、妻子相继去世之事,再加之自己也生病,1679年3月后有一年多时间,几乎足不出户,直到1680年夏才稍有好转。其诗《安昌绝句》有注云:“庚申夏仲,余方抱安仁之痛,更涉奉倩之疾,薄游安昌……”【13】
此时故友的相伴十分重要。除了谈诗论书,偶尔还作近郊之游,或相互留宿,彻夜长谈。乃至讨论未来是否作计然之策,终为二人所弃。陈奕禧有诗:“同向孟庄秋看菊,山外柿林红满麓。醉吟自合麋鹿群,纸窗灯火留君宿。忽然思效计然谋,赐不受命巨贾筹。书生落拓岂其辈,萧条底事成东流。”【14】读书人骨子里一股“贫贱不能移”的傲气,跃然纸上。另有《赠天章》:“欲从窥众妙,河曲访茅庵。自有今生愿,能忘永夕谈。檠花弹小烬,香醑鼓余甘,不省西窗外,埘禽叫竞三。”【15】诗中所述两人通宵达旦的夜谈,鸡叫三遍,意味尚浓。而有时干脆留宿茅屋,抵足而眠。如陈奕禧有《答天章书》:
宿君河上居,抵足半夜,醒复起。醉多抑塞语,触绪增感。别好友,翻觉宽释,然不愿乐时胜愁时也……知君有同恨,天既以此情畀此人,又使天下人无知之者……时二首记宿时语,削之,具问。【16】
而若短暂分离,又若三秋之久。陈奕禧有一封信写得十分诙谐而生动,真实反映了当时两者交往之密切:
日日思作天章书邀天章来,日日不得作书。忽天章书来,许吾来,然天章犹未来。却得作天章书,虽不快亦一快也。日日不得作天章书,非忙也,懒也。却日日看曩者天章书,非懒也,忙也。所选《今文海》,已得二千页,恨天章所作少,不过三数首,尚不快。能遂将新篇悉寄我,使一快耶?花残矣,春归矣,意绪殊恶,须天章来面谈……天章来读吾《今文海》,当知两眉颦蹙可借以暂开……邺架今人文,且望多搜速惠,我事济矣。日内视此如衣物,勿谓徒以冷语相答也。【17】
陈氏作为世家,有刊刻今古文选、书法的传统。当时陈奕禧编选了《今文海》,期盼吴雯能提供宏文,能一睹自己的编辑成果,提出相关的删选意见。
除了诗书交流之外,陈奕禧在物质上对吴雯也有所接济。吴雯有句:“三尺鹅溪罢剪裁,处膏不润亦奇哉。从来安邑多相累,翻向先生索袜材。”“大道无多说,微言惜强分。相怜转相勉,莫只绚声闻。”【18】陈奕禧与吴雯的密切交往,从同情相怜到鼓舞勉励,让吴雯从博学鸿词科落榜及家庭变故的阴影中逐渐走了出来。在这偏僻小县与中条山下,两人多少还可以谈诗校文,论书品画。而此后,吴雯先后在河南、湖南、北京、天津、陕西等地游幕,但只要回到山西,就会与陈奕禧联系。
(二)教读宗岱倍加亲
吴雯隐居读书中条山,陈奕禧邀其教读子陈世泰(宗岱),虽贫贱之交,修脯不足以解决生计,但总算在失意归乡之时,还有故友可以相知相交。在陈奕禧悼吴雯诗句中有:“翻然归走王官谷,念我娇儿亲教读。贫交不屑计修脯,寄兴无言对松竹。”【19】1679年陈宗岱尚只有八虚岁,作为名声极高的吴雯能够教读,关键主要是与陈奕禧意气相投。另一方面,陈奕禧有意接济吴雯,又恐伤及自尊,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从吴雯后面的诗也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师生缘是认同的。大约1693年前后,吴雯诗《别陈宗岱》字里行间,充满着恩师对弟子的高度评价、殷切期望与谆谆教诲之语,可见两人感情颇深。如:“吾子英异姿,雄文奋神虬。本自瑚琏器,伫为天庙求。所期慎操履,黾勉敦前修。富贵何足言,考德戒愆尤。忝窃纪群交,岂敢匿良谋。”【20】另有《鹿城官舍赠宗岱》则同样对弟子书法文采予以高度评价,并对他的未来前程充满期待。“……昨日来香泉,官阁拥孤吟。老凤排天阊,衮衮荣朝簪。公子复清华,学书比来禽。对此冰玉姿,慰我离索心。他时过郑谷,相候柴门深。”【21】就陈奕禧而言,儿子陈世泰能够获得吴雯这样的大儒亲授,也是十分感激。与吴雯在至真好友的基础上又添一层感情。
(三)昆仲之间增友情
陈奕禧大兄陈奕培时至安邑署中,因而与吴雯亦有往来。除了在安邑,他们在京城亦属于同一个朋友圈。比如与洪升、查慎行的交往。在陈奕培离开安邑赴京时,吴雯曾有诗相赠:“意气纵横上国游,岩廊犹有白云求。遭逢便奏甘泉赋,岂但才名动五侯。”(《送陈子厚之燕》)【22】对陈奕培的才情亦相当肯定。
而吴霞(天绮)也因兄长吴雯的关系,与陈奕禧多有往来。陈奕禧有写给吴霞的诗,如《吴子天绮自永乐至,步其见怀韵值雪中并怀令兄天章客汳(汴)》:“聚散缘何事,悠悠心所牵。人归天柱后,梦落大河边。日月驰驹隙,生涯费砚田。一囊春雪里,更值草堂年。(天绮自去秋一别至是始晤)。”【23】诗中对友人聚少离多颇为叹息,对远在汴京谋生的吴天章表达了牵挂思念之情。吴霞写诗不多,仅存一百多首,其《晴莲阁诗》却有诗《与子文同途至晋祠却送入秦》,从侧面可见陈奕禧在他们兄弟心中的重要位置。
(四)生活细节见至情
吴雯归居蒲州时,两人相距较近,往来频繁,时而论书,时而论文,时而饮酒。两人是可以秉烛夜谈的密友,是可以一榻同卧的知己。两人的深厚友谊在日常细节中更可见一斑。陈奕禧诗《天章送笋晚食成诗》十分特别:“日日怀君隔远喦,忽传书到急开函。兼将数亩贻溪竹,饱我清贫满腹馋。(贻溪在王官谷,近天章所居)”【24】友人来信并兼带送来新鲜春笋,丰富了诗人的晚餐,想来一边吃笋一边似乎看到了竹林中友人清瘦的形象。此诗按《虞州集》诗的前后排序初步可推断为1681年初春,此时天章应该就在王官谷,后因生活所迫,游幕潇湘。
在吴雯写给陈奕禧的诗文中从不避讳家事,包括妻子病重这样的事。1680年《庚申仲春寄子文赞府》:“疑义何人可较量,风灯薄醉静琴张。病妻却上平原帖,鹿脯端能远寄将。(时妇病甚)”【25】描述了自己在永乐的状况,尤其在诗后还加注说明了其妻病重的情况。吴雯当时的生活状况极其艰难,其妻就是在这样的困苦中离世的,但吴雯依旧耽于诗书。在他1681年《寄阮亭先生书》中向王士祯告知了种种艰难困苦:“别慈颜久矣,依依左右,无日不然。家居备极苦趣,已屡陈于老伯之前,无烦更道矣!中州皇皇年馀,实图一劳永逸。而究事愿多违……归而病困,且婚丧并举,所费不赀。”【26】文人总是十分顾及颜面,这样的窘困,除了在老师王士祯面前可以陈述,唯一可以倾诉的只有陈奕禧这样的好友。而在其妻祁氏过世后,陈奕禧以诗《为天章悼亡》吊之,还把吴天章与曾隐居玉溪并亦有丧偶之痛的李商隐相比。
(五)一生牵挂如亲情
相对于吴雯而言,不论是在安邑还是在深泽,陈奕禧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很好,但已十分幸运安定。而吴雯四处游走,始终未改其落拓书生的命运,也让陈奕禧十分挂念。
吴雯在1679年之后,至少还有一次参加科考,但这次考试也以失败告终。陈奕禧有诗《吴天章自省试归后别者将半载,怜其夙昔被征,今又不售,奉怀之作凡十二韵》:“尚复赴秋试,归来杂众人。骏淹千里足,鹏塌九霄身……”【27】通常,省试是指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一省之试则称乡试。题目中有“自省试归后”字眼,但诗中“尚复赴秋试”明确是秋试,而吴雯仅是生员,并无功名,一生以布衣之身份终老。严格讲他是不太可能赴京参加礼部的省试(会试)的。且按这首诗在《虞州集》排列顺序,疑是在辛酉冬,那么,吴雯当时参加的应该是1681年辛酉年的乡试。像吴雯这样有才华的学子,却在科举中屡屡受挫,可以想见科举之残酷。而除却科举一道,想要经世致用并不容易。
在后来吴雯的诗文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在贫病交加、科举失意的境况之下,吴雯对自己的未来似乎有所预感。《晋祠别陈子文》:“……东西各分手,彼此是离居。病后仍携药,愁多莫著书。茂陵前路在,久已弃相如。”【28】似乎是对老友牵念的一种无奈告白。作为同门弟子,陈奕禧对吴雯牵挂至深,令人唏嘘。他一直担心吴雯的身体,《赠天章》有句“最怜消渴疾,未合出关歌”,可知吴雯患有严重消渴症(即糖尿病),至于无法外出谋生。他在《寄国子祭酒王阮亭夫子书》中写道:“前日往蒲,宿于天章,篝灯夜语,卧而复起,醉而相泣。虽申燕尔之咏,惨遭鹡鸰之悲。既伤心于棣萼,欲寄情于沟水。失路惋抑,触境莫遣。审其萧飒之象,噫嘻,此子恐亦不能永年。海内真性情人,屈指无几,乃寥落飘离,偏至吾侪而极。兴言及此,真可痛也……”【29】尤其当我们读到“审其萧飒之象,噫嘻,此子恐亦不能永年”之句,令人动容。陈奕禧对吴雯的担心,已经完全超越了同门的情谊,更近乎兄弟之情谊。
他们的交往,无论是同处一地,朝夕相处,还是重山远隔,千里遥望,始终保持一种真挚的情感,毫无距离。在陈奕禧致谢方山信中有:“所叹同志散落四方,如天章之再客天津、西厓之远斥岭外、昉思久滞于都下……”【30】首先想到的就是挚友吴雯。陈奕禧远走益州之前,特意过蒲州看望吴氏兄弟,陈奕禧在深泽令任上时,吴雯前来小住两月。他们的情谊若素心相照,其境界不是一般世俗情谊能达到的。正如吴雯有句:“大道本无负,交臂岂创护。两两素心存,终古照泉石。”【31】
三、陈奕禧与吴雯之书法交流
陈奕禧与吴雯性情相近,虽则境遇不同,对于书法却有更多的共同观点与话语。
(一)基于时代风气
陈奕禧与吴雯的书法交流是基于清初时代风气的。随着康熙王朝日渐走上正轨,文化大环境与政策逐步改变,部分遗民接受了博学鸿词科的选用,即使有参与编修而不受清朝俸禄的,也至少可以看出思想领域一些矛盾缓和的迹象。遗民们对故国的感念,找到了修史、访碑这样的落脚点。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之中,通过吊古考释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大兴,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32】清代统治者以怀柔的心态乐见这一新气象,同时还对汉族文化尤其是书法表示出高度的认同与推崇,甚至不少文人学者以书法出色备受重用。这也带动了文人墨客关注学习金石文字之学与书法艺术,文人墨客交流少不了金石书画。
生于世家又具有先辈点拨或影响的陈奕禧,很自然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金石考据与书法学习上来,书法研究与金石考据成为陈奕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朋友眼里他是个“书法痴”。如查慎行有诗句:“吾党陈髯老可畏,书法纵横今米芾。平生致此盖有由,嗜古津津饫余味。南游北宦三十载,所至穷探自娱慰。尊彝款识拓商周,篆隶铭词藏汉魏……”【33】十分生动地描写了陈奕禧痴迷于金石书法的情况。正是这样的一次次交流探讨,奇书共赏的乐趣,驱使着陈奕禧无法停步,走在劈荆剔藓的访碑路上。
以傅山、戴廷栻等为首的一批山西志士,早年积极参加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在反清复明的实践无望之后,他们把精力转向治学,在金石与书法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恰好陈奕禧前往山西任职,于是与戴廷栻、范西彪等山西名士频频互动,而对于并未谋面的傅山,更是一种敬仰之情。与吴雯的交往,自然缺不了金石书法这一话题。
(二)书谊终生
陈奕禧与吴雯初次相见,便以书作相赠。陈奕禧与吴雯两人对于书法的探讨从未停息。
一是基于同门情谊。王士祯对门人陈奕禧特为推重,陈也受益匪浅,在诗书学习上受到王士祯的鼓励与鞭策。从现存书法作品可知,吴雯书法也具有很高的造诣,只是为其诗名所掩盖而已,同时代王戬等都有诗记述吴雯的书法。陈奕禧也有句赞他:“纷纷博学金门客,犹让莲洋笔势豪。”【34】因为同门,又都擅长书法,其交流便水到渠成。陈奕禧题《临褚河南枯树赋》云:“门弟子欲得先生书,辄假问学奏记,先生随意落札,便藏弆以为至宝……”【35】又如1680年夏,陈奕禧解馕入京,离京之前雨夜话别王士祯,有诗注云:“夫子作书,每不肯以己书赠人,天章吴子最爱其书,予此来得手笔极多。”【36】可见两人都十分崇拜王,以得王书为宝。常借问学之机获得王的书法并共同欣赏。
二是基于共同的审美观。吴雯的诗文中常可以看到他与陈奕禧对于金石和书法的讨论与欣赏。比如,在陈奕禧《益州行役记》与《皋兰载笔》未刊印之前,吴雯就已经有诗记述,估计先睹为快了,对其中涉及的访碑考释有很多的关注。《怀子文二首》有诗注:“子文《皋兰载笔》论王母宫碑刻最详。”【37】确实,借这两次公务远行,陈奕禧到达很多地方并对不少碑刻做了考证记载。这些记述为何先交由吴雯来阅读?我想主要是基于两人在对金石考据方面有共同的爱好,对待书法审美上有共同的观点。吴雯客深泽两月,两人日夜相聚,除了诗文,更多的还是对各类书法碑刻的考释题签等。吴雯有句:“清宵珠斗望阑干,对砚题签蜡炬残。应是渔阳千里雪,衙斋添做十分寒。”“……参差昙鹅群字,颠倒山阴薶骨方。拔镫微言宁石室,画沙真谛岂云阳。传疑传信须裁取,莫但随人筑道傍。”【38】从诗文中可以看到书法是他们二人自始至终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三)吴雯对陈奕禧影响
吴雯的书名不如陈奕禧,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书法审美观对陈奕禧的影响。
一是崇魏晋,尚碑学。吴雯书法虽不及诗名,然当时名流与其书法交流并不少。赵执信称其“作字用冯法”。【39】姜西溟曾经把自己宝藏有年的宋拓《乐毅论》赠送给吴雯,而王士祯认为是送对人了,正是吴雯对魏晋书法有独到的心得。【40】吴雯为人自然洒脱,颇得晋人神采却不拘一格,傲岸不屈。尤其是荐举放归后,落拓江湖却深得陈奕禧认同,引为知己。陈奕禧有诗述他们之间就书法、碑刻方面的学习交流活动。如:“下榻西堂赋别离,闲宵仍检汉唐碑。始辨冯生书判学,不如魏晋是良师。”【41】吴雯使他更坚定了崇魏晋尚碑学的信念,对他坚决地从董其昌书风中脱离出来有一定的影响。
二是对媚俗书法的否定。吴雯受傅山影响,而傅山是举起“四宁四勿”大旗的北方代表书家,也是陈奕禧所崇拜的偶像之一。吴雯早年曾多次拜访傅山,他与傅山心曲是相通的,从作品也可以看出吴雯的书风有傅山的影响。陈奕禧在众多题跋中推崇经学、注重考证、反对媚俗,如《临张猛龙碑》:“吾观赵吴兴能遍学群籍而不厌者,董华亭虽心知而力不副,且专以求媚,谁为号呼悲叹,使斯道嗣续不绝。”【42】他在题自书册题句里也写道:“余不作时派,妩媚、匀净。”【43】可见在审美观念上,陈奕禧与傅山、吴雯应当是有趋同的一面的。陈奕禧诗句“孟津骨朽松桥死,海内谁知所以然”,足证他深受傅山之影响及对傅山的高度认同与崇拜。而陈奕禧与傅山并未谋面,但我们也能看到陈奕禧某些作品中傅山的影子。除了从傅山流于世间的字迹以外,吴雯的影响一定存在。陈奕禧自述:“山书,今代之大家也,未尝渡江而南,故南人未知之也。唯余与蒲州吴天章深识其精奥处。”【44】很可能两人经常在一起欣赏研究傅山书法,因而在陈奕禧审美观念逐步形成过程中,很难说没有吴雯的影响。
注释
【1】陈奕禧:《春霭堂集》卷十四,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2】《王士禛志》第二章 生平,附:《王士禛大事年表》,《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编撰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版,110页。
【3】吴雯《喜晤王清远时余将还河中清远亦之官茌平五首》自注云:“阮翁以己酉使淮上,时与清远同获侍使院中。”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440页。
【4】【5】【10】翁方纲:《莲洋吴徵君年谱》,《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752页。
【6】王士祯撰:《吴征君天章墓志铭》,《吴雯莲洋集》乾隆十五年(1750年)刘组曾刻本。
【7】【14】【19】【34】【41】陈奕禧《春霭堂续集》卷二,康熙四十七年刻本,十六页。
【8】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119页。
【9】王士祯:《分甘余话》,张世林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61页。
【11】 陈奕禧:《虞州集》卷一,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12】吴雯:《罗萝村诗序》,《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737页。
【13】吴雯:《安昌绝句》诗注,《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14页。
【15】【27】陈奕禧:《虞州集》卷四,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16】【17】陈奕禧《答吴天章书》两通,《虞州集》卷九,康熙二十八年刻本。(各类介绍中均记录陈奕禧编撰《文海》,然从其书信文章,可知其所收集文章为1645年以后之文,故其自称《今文海》)。
【18】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324、352页。
【20】【21】【22】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427、430、401页。
【23】陈奕禧:《虞州集》卷三,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24】【36】陈奕禧:《虞州集》卷二,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25】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428页。
【26】吴雯:《致阮亭先生书》,《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729页。
【28】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352页。
【29】陈奕禧:《寄国子监祭酒王阮亭夫子书》,《虞州集》卷九,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30】陈奕禧:《与谢方山刑部》,《虞州集》卷九,康熙二十八年刻本。
【31】吴雯:《香泉》,《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432页。
【32】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3】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二十七《过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723页。
【35】陈奕禧:《春霭堂集》卷十六,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37】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353页。
【38】吴雯:《吴雯先生莲洋集》,三晋出版社,2010 版,429、434页。
【39】赵执信:《怀旧诗》(并诗前小传),《吴雯先生莲洋集》附录三,三晋出版社2010 版,772页。
【40】王士祯:《跋吴天章所藏宋拓乐毅论》云:“宋拓《乐毅论》如卫协、谢雉画列女,古意苍然不乏妩媚……西溟宝此有年,以遗天章,可谓具眼。”《蚕尾集》卷十,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42】陈奕禧《隐绿轩题识》,《丛书集成新编》 51 册,新文丰出版社编辑部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678页。
【43】陈奕禧:《春霭堂集》卷十七,《题自书册》,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44】陈玠:《书法偶集》,《明清书法论文选》上册,崔尔平选编点校,上海书店1994 版,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