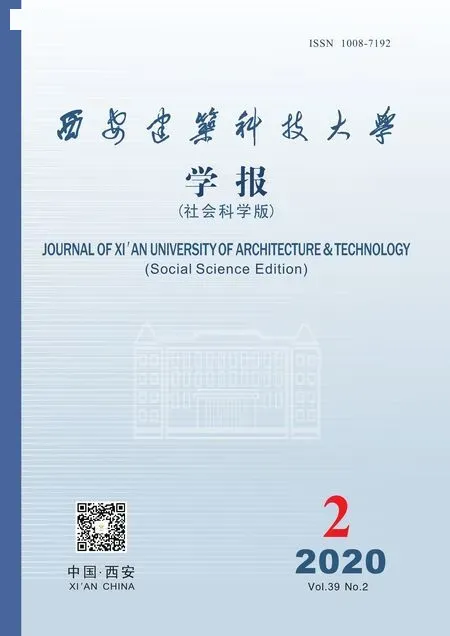历史合力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洞悉国内外局势、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发展总体向好,但全球性生态危机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局部冲突等政治冲突威胁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为应对各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一项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其中恩格斯的历史合力就潜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意蕴。但目前以历史合力论为角度,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章尚未引起学者关注。本文则以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为视角,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进行分析。
准确把握历史合力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探寻历史合力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之处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国内国际方面对这一思想从各个方面做出了阐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共谋发展必须“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2014年,国际社会联盟在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与发展项目”启动仪式的开幕词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最有同心力的集体,也是人类获得文明幸福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2]。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以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分析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的全球治理方案,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于一体的多因素的综合,这与与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的历史合力论有契合之处。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辩证统一关系的强调、对单个意志的力与合力的阐发、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强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历史合力论的实践方式。
一、单个意志的力与总的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处理各国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必然选择
恩格斯晚年提出了历史合力的思想,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领域的变革颇为关注,《自然辩证法》的撰写就是明证。通过考察《自然辨证法》,不难发现恩格斯对物理学知识颇为精通,在推进相关研究中,恩格斯将物理学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领域,促成了历史合力论的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回观历史合力思想,不难发现,要正确处理“单个意志的力”与“总的合力”的论断潜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在19世纪中叶,物理、数学等学科发展势头渐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以往哲学家对世界的认知。随着物理学的纵深发展,物理学的常用概念——“力”映入了哲学家的视野,成为解释世界的新向度。恩格斯晚年,就借用了物理学中“力”的概念,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思想。关于此,恩格斯在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做了经典论述,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3]605。这就意味着,每个力都有自己的意志,具有一定的方向和力度;而各个意志的力之间相互作用,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形成合力;合力与合力之间相互作用,汇聚成最终的历史合力。以此为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要达到的“历史合力”,是各国利益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而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殊性则是“单个意志的力”。与此契合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视了单个国家之“力”的冲突,明晰人类之“力”的融合,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拓展、加深了各国合作。
1.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正确处理各个国家单个意志的力
从历史合力论视角看,“许多个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这便是最终的历史发展结果。各个单个意志的力之间相互作用,最终按照平行四边形的原则形成了历史合力,每个单个意志的力都促成了历史合力的形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每个国家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殊性都充当了单个意志的力的角色。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尊重各国之间的差异,倡导“和而不同”。各国之间因文化、制度等差异,可视为不同方向的力,也正是这些不同才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必须强调的是,具有正向推动力作用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的,阻碍构建的反向作用力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斗争的。因为如果各个国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使得“单个的力量”朝向不同的方向,那对于全人类而言,“总的合力”的力量则会被削弱,长此以往,每个国家都会受损。
2.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个国家要趋向的“历史合力”
在力与力的相互作用中,力的大小和方向影响最终的历史合力,应用到历史领域,预测到某一历史趋势,为早日达成这一结果,每个力只要趋向历史合力的方向,并加大作用力,预期可早日成为现实。历史和实践均已证明,各国合作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着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工业革命后,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这一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促进各国为应对全球问题,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的方案,是“历史合力”总的趋向。“人类命运”是历史总的方向,“各国之间的利益”是要素和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符合历史趋势的,是不以单个国家利益为转移的,也是符合每个国家、每个民众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是一个长时工程,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规律,以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旨归。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大前提下,缩小国与国之间“力”的夹角,如此合力才会越大,促进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进程。
3.人类若想获得更高发展,就必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合力是无数单个意志的力相互作用而形成,其中每个意志的力都对历史有影响。如果某个意志的力太过强烈,根据物理学力学中平行四边形法则,会牵动其他单个意志的力的方向。国际交往同样如此,具有强大作用力的强国的决策会影响全球格局的变化。而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未来的命运,既源于两次世界发展的深刻教训,也源于当今某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打击别的国家的行为,更是对当今世界突出的全球危机的现实考量。从世界历史现状来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尤其是发展较快的国家与占优势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和经济打压行为时有发生。回顾世界历史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冲突带来的是世界性经济倒退,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当今世界,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提高,各国应该摒弃旧式的“零和”思维,走向“共赢”。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反对某些国家打着维护世界秩序的幌子刻意打压别国的行为。而且来自强国的打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旁观者”,因为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压的对象”,为了各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未来,世界各国应该携手共进,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做“历史合力”中的“反向作用力”。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道路曲折性与前途光明性的辩证统一
历史的发展融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之中,必然性表现为与物质生产结合的经济运动,而偶然性蕴藏于纷繁复杂的事件之中,而且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是综观整个历史而言,而绝不能割裂历史的延续性。如果单独考察某一个阶段的历史,片面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则是错误且荒谬的,恩格斯在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3]604。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是是物质生产、思想等各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的结果,如果忽略了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只谈物质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以此观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是符合历史的必然,但阻碍它的偶然性因素仍然存在,必须正确认识这条道路的曲折性与前途的光明性。
1.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具有历史必然性,要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前途的光明性
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程度更高,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关联程度也越高,除此之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问题也使得人类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生命体。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把握历史发展必然性,要充分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不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但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存在,应客观看待这种现象。不容忽略的是,某些国家片面强调国家利益最大化,枉顾世界潮流开展逆全球化经济现象仍然存在,局部冲突也偶有发生。基于历史必然性与客观偶然性的并行发生,为解决全球问题,为谋求人类利益共同福祉,习近平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在推动世界体系格局演化的同时,要求改变体系不平等状况,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自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构建了以“利润”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规则。殖民时期,资本逻辑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资本文明中,它在促进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血腥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不止殖民时期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方式由政治掠夺转变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兼并”和形式上的平等的经济交往。这一转变以更隐秘的方式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合理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为了改变这一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对此作出多番努力和尝试,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全球治理方案的一种现实形态。
2.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正确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的曲折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长时工程,它必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秩序,破除对自我利益的短暂而片面的追逐。但现有国际格局下,各国贸易壁垒高筑,逆全球化经济现象不断蔓延;局部冲突不断,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格局;难以逾越的文化、制度等鸿沟等都是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必须澄清的是,这些阻碍因素是偶然性因素,无法改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其中,必然性更多归属于历时态的时间过程,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展开形式,更多归属于共时态的空间领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符合历史规律的事物终会到来,不过其中偶然性的事情也不能忽略,尤其是偏离历史必然性趋势的偶然性运动[4]。我们应该认识到必然性作为事情发展过程总趋势和过程推移的联系之链,其作用是凝练性、规范性、约束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坚持共建共商共享,共同制定符合人类利益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并在规则制定后约束各国的行为。从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关系分析中可知,逆全球化、局部冲突等问题只是某些国家或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的有悖于历史发展趋势的行动。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合作才能共赢,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只会自食恶果,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将会危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夹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偏离。偶然性的偏离造成了必然性道路的曲折,只有在把握必然性这一趋势的基础上,正视道路的曲折性,才能破除现有迷障,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
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断细化地分工与全球危机的应对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必然会逐渐形成一种共同需要基础上的基本共识,一种建设性的共同价值作为共同的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5]。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平等公正的国际环境中“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但因新型的以全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会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国家倡导的国际关系,所以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存在。然历史发展的道路本就是曲折的,只有正确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的曲折性,才不会囿于偶然因素的偏离,而失去对光明前途的信心。
三、决定性与能动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物质生产与价值诉求的合理方案
唯物史观主张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合力论再次强调了这一辩证关系。遵循这一轨迹管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知,随着生产全球化,人与人转嫁在生产中的联系日趋密切,逐渐成为息息相关的整体。建立在共同生产之上,必然呼吁代表整体利益的价值观的出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顺应物质生产与价值诉求的合理方案。
值得指出的是,唯物史观自诞生以来因被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而饱受攻击,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再次澄清了这一问题。任何思想都产生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中,考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样不能忽略它产生的时代语境。不可否认,马克思的著作是充满批判性的,他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也是在批判黑格尔、施蒂纳、蒲鲁东等人的思想中建构的。但很多人忽略了马克思的批判目的,片面考察马克思阐发的思想,造成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误读。如果回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不难发现,在马克思之前,德国的古典哲学已经发展到顶峰,从康德到黑格尔,无不沉浸在思辨之中,黑格尔将一切事物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演绎,将思辨哲学推向顶峰。即使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对其体系的批判,但都无法站在思辨哲学之外进行科学的批判。为了将批判从“天国”降入“人间”,马克思从“现实的人”这一历史前提出发,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而随着物质上产的方式,人类产生了语言,进而产生了意识。简言之,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针对这一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把唯物史观简单化和庸俗化,将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显然是割裂了思想与现实的联系。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时,之所以强调经济因素作用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为了论战的需要——与唯心史观划清界限。所以这种带有论战性质的著作必然侧重驳斥对方的观点。但面对青年马克思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带来了部分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也持这种观点,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因素夸大为唯一决定历史作用的因素,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
对此,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604。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是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因素,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法律、观念等随之形成,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相互作用促成历史的发展。物质因素的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观念等其他因素与物质因素相互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就如恩格斯认为阐述唯物史观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一直强调那些萦绕在人民心目中对拿破仑一世的崇拜等观念因素,也是他们支持路易·波拿巴的因素之一。以此映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价值转向,可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必然性。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它主张以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来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这种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人类历史的方式是马克思与以往理论家的本质区别。从物质生产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知,随着生产全球化,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数次的经济危机一再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荡,都可能引发全世界的经济海啸,其根源就在于无法割裂各国之前的生产联系。为了稳固世界的发展,必然要构建全新的世界格局,促进各国共同的福祉,而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冾的,其中“一带一路”取得的成绩就是明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平等协作的机制平台,一带一路通过加强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想落到实处。何星亮曾到“一带一路”倡议经过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实地考察,调查显示中国企业与中亚企业合作开展基础社会建设,改善了当地的轻轨建设和城市供电系统;与中亚各国合作建设现代农牧业生产和加工体系,解决了融资难题;合作建设智能化、信息化的工业生产体系;为中亚地区培训技工,解决部分群众就业问题[6]。加入“一带一路”的倡议的国家,获得了切实利益,而“一带一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实践。
2.人类对共同命运的关注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
恩格斯在写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提到,“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3]604,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书信反复强调思想领域对物质存在方式的反作用,有效密弥补了马克思在论战中阐述的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在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其中“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598。社会意识有能动性,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以此管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对共同命运的关注必然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也都将成为受害者。比如2019年亚马逊森林、澳大利亚森林失火,为何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关注。其根源就是人们认识到一旦亚马逊森林、澳大利亚森林被毁,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必然接踵而来,最终损害每个人的生存环境。还有人类历史上的传染性疾病,比如艾滋病、埃博拉和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推动了人类对共同命运的关注:只有团结协作,才能维护全人类共同福祉。而维护全人类共同福祉,就必须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2014年国际社会联盟在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与发展项目启动仪式的开幕词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最有同心力的集体,也是人类获得文明幸福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回应了人类对共同命运的关切。
四、结 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外交的重要表达,它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是为谋求全人类共同福祉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唤醒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意识觉醒,进而团结全人类的力量,以应对世界性问题,推动人类走向真正的联合体。以历史合力为视角管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旨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重重阻碍,但它顺应了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回应了全人类的关切,是正确处理国际利益的必然选择。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世界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