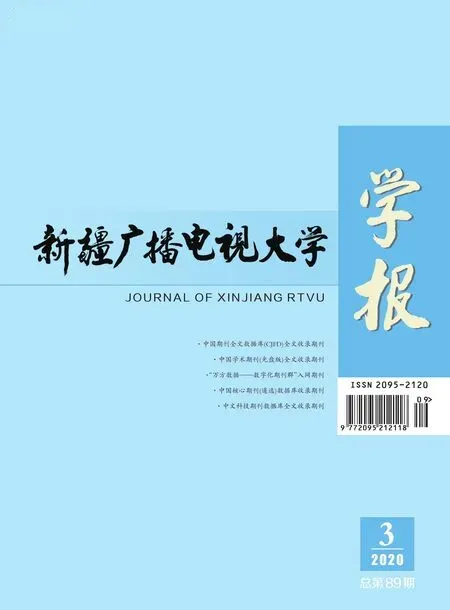电视剧《胡杨女人》中的胡杨意象解读*
杨月梅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2010年10月,由西安曲江影视和内蒙古电视台联合出品,张晓春导演的蒙古族题材电视连续剧《胡杨女人》在央视八套首播,一经播出便受到广泛好评,创下民族题材影视剧热播的新高。2011年8月,该剧荣获第2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提名荣誉奖”。该剧主要讲述了有着胡杨般坚韧意志的主人公斯琴替父还债的诚信故事,塑造了一位美丽善良、阳光乐观、坚毅果敢、一诺千金的当代完美女性形象。地方自然风光的唯美拍摄;地域民俗景观的音画再现;蕴藉悠扬的蒙古长调回响;浪漫理想的主旋律情节安排,使该剧获得观众普遍认可。其中额济纳胡杨林是该剧倾力推出的核心景观,胡杨在剧中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风物,亦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底色,而是作为重要的叙事要素参与到剧情的主题呈现、人物形象塑造和理想人格建构中。具体说来,该剧通过多层次、多角度摄影镜头的唯美捕捉,形塑如诗如画的胡杨风景,感发人们对自然胡杨意象的美感体验;运用蒙古族关于神树崇拜的地方性知识,赋予胡杨意象神格化色彩,再现民间胡杨意象的神话记忆;运用“君子比德”的儒家传统思维,以胡杨喻人,在将胡杨意象人格化的同时完成理想人格的建构。
一、如诗如画的胡杨风景形塑
风景美是《胡杨女人》的一大看点,蓝天白云、草原沙海、壮阔胡杨林、潺潺流淌的额济纳河令观众流连忘返于天地自然之大美妙境。胡杨是其中极具特色与新意的风景意象,以往内蒙古题材影视剧制作中,风景镜头多聚焦于草原景观,该剧以“俯仰观宇宙”的宏大视野,将草原、戈壁、荒漠等不同类型地理景观囊括其中,以浓墨重彩绘制如诗如画的胡杨景观,使人们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传统草原景观审美体验之外,获得别样崭新的审美感受。
“风景”并不等同于纯粹客观的自然,而是一个文化学概念。“风景作为话语形式、现实的再现以及实存的现实,渗透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中”[1]。按照美国学者W.J.T.米歇尔的观点“风景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动词”[2]。文艺作品中的“风景”,一方面来源于客观自然之物质实体,另一方面,又是创作主体表达特定意识和价值的文化实践,是创作主体建构、想象、生产、形塑的产物。《胡杨女人》中的胡杨风景意象首先是市场经济语境下地方文化和旅游文化实践下的消费性风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旅游与影视的跨界融合,尤其是以影视助推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趋势。影视作品的外景地拍摄、影视文化节、首映式等活动的开展,常常成为宣传地方旅游文化的强有力平台。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将如月与飞雪的生死绝杀安置在满目金黄的额济纳胡杨林中,两位红衣女子衣袂飘飘、剑拔弩张,静与动、刚与柔完美融合,如梦如幻,给人以超强的视觉震撼。在《英雄》强大影响力的助推下,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景区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和观赏。
《胡杨女人》主要外景地为内蒙古额济纳和锡林郭勒大草原,两地相隔千里,故事中人在其间穿梭往复。该剧编剧在谈到选景时指出“选景时才发现情况根本不同,因为胡杨林附近都是沙漠,很难把胡杨林和草原很好地衔接在一起”[3]。显然,草原景观和沙漠景观的拼接剪辑,画境般的拍摄手法,胡杨风景意象的高频特写,均显示出该剧创作在输出诚信价值观的同时,宣传地方旅游资源,助推胡杨风景区旅游事业发展的商业动机。
立足于带动商业旅游消费的隐性动机,该剧着意捕捉、剪辑自然胡杨中那些在形态、色泽上能够“悦目”的部分,以刺激观众的视觉,感发人们对胡杨之美的认同。一方面,该剧尽可能地将额济纳最富代表性的胡杨景观“一网打尽”,胡杨林、怪树林、神树,不同空间的自然胡杨景观被剪辑、组接,观众在观剧的同时,也对当地地标性胡杨旅游景观一览无遗。另一方面,该剧主要择选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畅神怡情的胡杨风光入境,以可视性、观赏性为前提,捕捉剪辑适宜入画的部分,并以明亮、绚烂的光影晕染出诗意氛围,使观者在观看剧情的同时获得诗画般的审美体验。以往影视作品中的胡杨意象常常与沙漠、戈壁意象同时出现,荒芜萧疏、缺乏生命气息的瀚海戈壁意象常常被着力表现,以此强调胡杨生存境遇之艰、凸显胡杨品格之韧。如2000年戈日泰导演的塔里木石油勘探题材电影《胡杨》,大量镜头投射在浩瀚无垠的沙漠、肆虐的风沙、有毒的河水等反映恶劣生存条件的地理自然景观上,在此背景中,沙漠腹地中那片神秘的胡杨林和胡杨林中埋葬的早期石油勘探者异质同构,成为不畏艰险、坚韧不拔、攻坚克难、战胜自然的精神主体。不同于以往胡杨意象在沙漠戈壁意象映衬下的粗粝沧桑之壮美,《胡杨女人》的镜头较少聚焦于令人感到逼仄荒芜的沙漠戈壁意象,而是在繁茂绚烂胡杨林和蓝天草原的周流往复中,让人体悟令人赏心悦目、怡情畅神之优美。该剧7月底开拍,正值胡杨树叶由绿转黄的季节,绿色到黄色的过渡在适宜的光影调度中,丝毫没有萧瑟凄凉的悲秋之感,而是让人在诗意的氛围中感受胡杨之生机灵动和绚烂辉煌。蓝天白云、晴空碧日、郁郁葱葱的胡杨林、古树护佑的蒙古包、神树上迎风飘扬的彩色布幡、蒙古包前卧倒的胡杨横木、栅栏、羊群、骆驼、马头琴、生活于胡杨林中的牧民等意象,组合成一幅幅极富诗情画意又充满生活气息的风景美卷、风俗画卷。
二、贯通天地的神圣空间
《胡杨女人》中的那棵被人顶礼膜拜的神树,是全剧胡杨林景观中最为特别的存在,与之有关的场景在该剧中反复出现,“特殊场景的重复再现,展现了文本中相关场景的特殊意义”[4]。神树位于胡杨林中,是周边最大的一棵,根底盘魄、主干斜生臃肿、枝干分散盘曲、树冠高大、枝繁叶茂。树上挂满了人们用于祈福的各色彩带,微风吹拂,五彩布幡和金黄的树叶交相辉映在晴空碧日下,摇曳多姿、神圣壮观。这棵神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庄子》中那棵能荫蔽数千牛、“絜之百围”的栎社树,看上去虬曲交错、不中绳墨,被匠人视为无用之材,但正因此而免受砍伐而长成一棵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参天神树。《胡杨女人》中的这棵胡杨树正是牧民们心目中的神树、是贯通天地、沟通人神、护佑良善的神圣空间。
现实中每每不如意时,牧民便来到这棵胡杨树下,向神树倾诉内心的秘密和诉求。剧中神树下祈福的场景有十多场,这些重复场景“不断刺激读者神经,作者将自己所希望表达的意图源源不断地传递给读者,由重复现象所衍生出来的意义也就变得更加明朗”[5]。每一次祈福者都以虔诚的姿态、凝心聚神,以宗教般的神圣仪式面向神树。神树在牧民心中是富有灵性的神圣空间,剧作通过不同的拍摄手法,暗示神树的这种神圣性:自上而下的慢镜头意蕴着神树俯视苍生的神性视角;自下而上的移动镜头暗示普罗民众对神树的仰望、崇敬与膜拜;自远及近从全景到特写的切换则突出了神树与众不同的伟岸。
神树是剧中不可或缺的神性依托,是能够俯视苍生、读懂人间善恶、护佑善良与正义的载体。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在神树下祈福的情节,但神树只护佑那些富有善良、正义、诚信品质的正面人物。136万的巨额债务,最终因斯琴奇遇葡萄玛瑙紫珠巨石而轻易化解;已经被医学判定生命晚期的斯琴,竟因为吃了毒草“慢放血”而奇迹般地痊愈了;口蹄疫使奶牛场面临破产的窘境,但红旗奶牛场的出现有如神助般从天而降,让斯琴因祸得福。剧中的反面人物,牧仁和白洁,不仅“行恶”时的祈福无法获得神树的护佑,在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后亦无法摆脱悲惨命运。薄情寡义、见利忘义的牧仁,不仅不能获得梦想的财富,即使是在最终悔心改过后,也难逃被狼咬死的厄运;婚内出轨、自私懦弱的白洁最终只落得被亲生儿子惊吓而死的悲惨结局。在爱情的天平上,胡杨神树同样不是一视同仁。神性的眷顾只青睐于善良正直之人的两情相悦,而不符合剧中伦理价值标准的负面形象牧仁、白洁、乌林汗,在爱情的世界中同样只能以失败作结。
正如有人对《胡杨女人》的评论:“这是一个真实的梦,一个写给成人的童话。它构建了一个人们求而不得的美好世界”。[6]神树景观为这部电视剧涂抹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也为该剧离奇的人物情节设置提供了艺术真实的合理阐释。人们对极富梦幻童话色彩的故事情节的接受与认同,既来源于内蒙古当地有关神树的地方性知识,更来源于人类对树木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和对草木自然的普适性共情能力。蒙古族自古就有着树木崇拜的传统,这体现在早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英雄史诗中,也体现在依然留存至今的民俗仪式中。根据《巴图尔·乌巴什·图们著四卫拉特史》的记载,早期的绰罗斯、准噶尔部落的祖先是一位以树为母的孤儿[7]。在布里亚特蒙古的神话中,树是萨满巫师是否具有神性的转换器,在神与人之间发挥着通灵作用[8]。这与《山海经》中记载的供众天帝“上下于天”的天梯建木具有同样的功能,均反映了早期人类天地、神人尚未分离的原始观念。神树崇拜思想至今依然留存于内蒙古民俗中,额济纳旗苏泊淖尔南岸有一棵树龄600年左右的胡杨神树,被视为神灵,牧民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以祈求神树保佑人畜平安。对树木的崇拜是人类各个民族早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对树木的亲近感亦是人类各民族共有的情感质素。《胡杨女人》通过对胡杨神树这一带有人类原型意象的着力描绘,不仅再现了当地蒙古族的民俗仪式,亦唤起了观众潜意识中对树木、对生命、对自然的感悟与敬畏。
三、坚韧顽强的人格表征
草木比德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树木意象常常用以表征君子品格。古代文人墨客从树木中体悟出“天然”品格,进而以木寓情、以树托志,在建构理想君子人格品性的同时,也赋予不同树木以不同的文化品格。如松柏的凌寒不凋、坚韧顽强;竹的孤直脱俗、虚怀若谷;梧桐的高洁自守、空谷幽怀;柳树的孤高幽洁,超然物外等。胡杨是我国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古代社会由于交通不便和地域、民族文化的区隔,胡杨意象没有像松柏、杨柳等树木意象那样广泛进入文人雅士的视野范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屯垦戍边、西部建设和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大发展,中部与西部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西部风景得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作为西部地标性景观的胡杨,一经发现,便引起高度注目。近20多年来,胡杨意象在文学、绘画、影视、舞台剧、摄影等不同艺术门类中大量出现,并被赋予极富时代性的多重文化内涵:如生生不息、奋发向上的生命力;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意志;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西部精神;淡泊隐忍、孤独守望的人生态度等。在当代胡杨意象的多重文化赋值中,不畏艰险、逆境求生的坚韧顽强品质是其最普遍的表征含义,电视剧《胡杨女人》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以树喻人,人树合一,在建构理想品格的同时,使胡杨意象的文化内涵具体化、人格化。
主人公斯琴被称之为“胡杨女人”,即胡杨般坚韧顽强的女性。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境况中,斯琴要还清136万巨额债务必须要有矢志不移的信念和坚韧执着的意志。在一诺千金,替父还债的故事中,斯琴像一棵矗立大漠的普通胡杨,积极向上、排除万难、逆境求生,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同与赞誉。同时,斯琴似乎亦是那棵无所不能的神树胡杨的化身,具有圣人般的胸怀,令人敬仰。胡杨树下“指血盟誓”的情节以有意味的拍摄形式隐喻斯琴与神树的同构关系。父亲去世之后,斯琴在胡杨神树下,主动召集牧民们弄清具体债务人和债款数额。当牧民一方面敬佩斯琴替父还债的义举,另一方面也质疑斯琴的还款能力时,斯琴以坚定的口吻向大家表示还款的决心。此时,音乐响起,镜头先是几次切换,在众人敬仰的目光、乌林汉怦然心动的深情、奶奶欣慰的赞赏和阿蓉惊奇的注视下,斯琴咬破指头,以指血签名。接着镜头给了斯琴一个特写,斯琴走到布满彩色布幡的胡杨神树下向苍天神树盟誓,神树下的斯琴在音乐背景的烘托下,在众人敬佩的瞩目下,俨然被染上了圣女的光晕。斯琴充满仪式感地向神树盟誓的场景与牧民们以敬仰的神情注目斯琴的场景巧妙地形成同构关系,视胡杨神树为圣树的斯琴,此时此刻俨然被摄影镜头神圣化,成为了神树胡杨的化身,由此,胡杨意象被人格化,主人公斯琴被神化。在这之后的剧情从各个层面凸显了斯琴圣母般的慈悲、善良、坚韧、勇敢和顽强。如背负一身债务,但却抚养着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以强大的包容之心原谅并且帮助曾经背叛自己的牧仁和阿蓉;感化自私懦弱的白洁为大志作证;说服抛弃幼女的王芳芳与阿蓉相认;解决额济纳河断水断流的困境等等。
对远离沙漠的他者来讲,沙漠被视为生命禁地,常常与残酷、恐惧、死亡、孤独等心理体验相联系。而胡杨是沙漠中唯一可以成林的树种,也是沙漠中最大的乔木。一望无际的瀚海映现出人类自身的渺小无奈和对生命的焦虑恐惧,而在这样的境遇中能扎根成林的胡杨显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之美”、一种在“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9]中积累而来的坚韧之美、崇高之美。因为生存境遇之坚,胡杨自然成为坚韧品性的最好代言。《胡杨女人》以胡杨指称主人公斯琴,赋予斯琴胡杨般的坚韧品质,又通过故事情节的推进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同时,赋予胡杨具体的文化内涵,从而完成胡杨意象的人格化表征。
结语
当代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疏离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图像成为人们了解关注自然的重要平台。电视剧《胡杨女人》对胡杨意象的风景呈现,使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西部地标性自然景观,获得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同时胡杨神树地方性神话记忆的再现和草木比德思维的复现运用,丰富了胡杨意象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可以说,胡杨意象在该剧中的呈现在同类影视剧中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为讲好“一带一路”上的景观故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