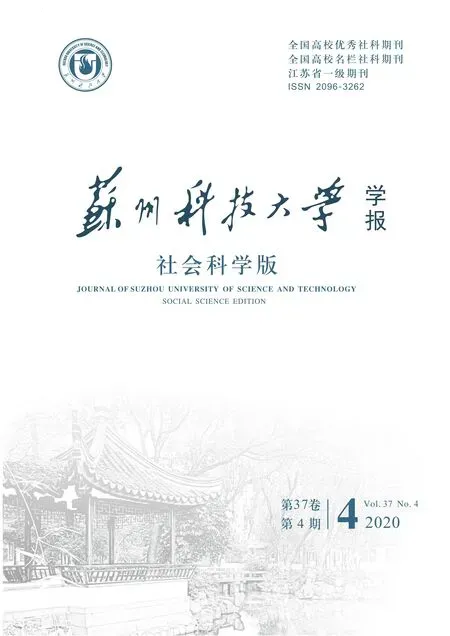母亲的塑像*
——丁玲《母亲》与张爱玲《易经》之比较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丁玲和张爱玲(简称“二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们的身世、经历及创作早已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1)相关研究成果有:彭漱芬《论“丁玲现象”》,《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第1~7页;万莲子《论“丁玲现象”》,《学海》2001年第1期第166~170页;朱郁文《“另类”,还是被“另类”:“丁玲现象”再思考》,《丁玲与中国当代文学——第十一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版第399~406页;刘海滨《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10~113页;邢向楠《张爱玲现象:从热到冷》,《文艺评论》2015年第3期第104~107页;刘绍铭《爱玲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版第3~12页。。由于俩人的没落世家出身、单亲家庭成长、有个追求独立自由的母亲等方面的相似性,她们的创作不时被学界拿来作比较研究,且这些比较大多集中于单篇作品、女性意识、个性风格及发展趋向等方面(2)如钱荫愉《丁玲与张爱玲:一个时代的升腾飞扬与苍凉坠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25~33页)、吴晖湘《激越的与苍凉的——丁玲、张爱玲创作文本的歧异》(《齐鲁学刊》2000年第3期第63~65页)、陈理慧《革命中的女性角色——〈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色·戒〉比较》(《理论月刊》2007年第1期第134~136页)、郜元宝《都是辩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第134~140页)等。,而在阐述俩人创作异同成因时,又主要强调社会环境、个人性情或生活经历等。当然,强调家庭身世方面影响的也有,但大多侧重于家庭生活的残缺或伤害。实际上,在家庭生活方面,对她们构成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母亲的生活经历、性情志趣及社会交往等不仅决定着她们的性格心理、价值观念,也深刻影响到她们日后的婚姻情感、人生命运、创作的题材选择和风格趋向等。
众所周知,“二玲”的母亲都是中国早期追求独立、自由的职业女性(丁玲母亲是自由职业者,张爱玲母亲也从事过经商、教书等多种职业)。“二玲”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因为丧父或父母离异一度生活在母亲身边,母亲为她们提供主要经济来源,也是她们的情感精神支撑及日后人生仿效或抗拒与逃离的对象。波伏娃指出,女孩童年时代最初“认为母亲比父亲更有权威。她认为这个世界是母权的世界,她模仿母亲,用她来确认自己”[1]。张爱玲小时候看到母亲对镜别翡翠胸针,就说出“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2]66等急切盼望长大、以便能像母亲那样打扮自己的话语。丁玲更是多次谈到母亲对于自己的教育和影响(3)详见丁玲的《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7》,第14页)、《我母亲的生平》(《丁玲全集:6》,第63页)两篇文章。。两位母亲的影响和“二玲”对于这种影响的认同或抗拒,不仅体现在她们早期作品中那些孤傲、倔强和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身上,更在她们笔下的母亲形象身上得到印证。这里,笔者拟以丁玲《母亲》和张爱玲《易经》(包括《雷峰塔》(4)张爱玲在1963年6月23日给邝文美夫妇的信中说,《易经》因篇幅过长,分为上下两部,上半部叫《雷峰塔》,下半部叫《易经》。)为考察中心,探析“二玲”对于母亲形象的塑造,以窥探她们创作风格的不同及其所开启的中国女性写作两种不同趋向的真正原因。
一、相似的成长历程:脱去少奶奶袍褂的新女性形象
丁玲《母亲》创作于1932年,是以作者母亲余曼贞为原型创作的一部传记性小说。原计划创作三部,后因作者被捕而被迫中断,只创作了八万多字的第一部,但一位生动、饱满的母亲形象已从这八万多字中立起来了。张爱玲《易经》创作于1957年至1964年,主要回顾作者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琐事,属于自传性小说。《易经》不像《母亲》那样以刻画母亲形象为重点,但母亲也是作品书写的重要对象之一,是作者追忆和刻画的重要人物。
两位母亲一位丧夫新寡,一位留学回来不久离异,但她们没有沦为传统悲切切的怨妇形象,而成为反叛传统、走出婚姻家庭悲剧阴影、倔强自立的新女性。她们走在时代前列,具有异乎传统女性的新思想和新追求。
首先,她们孤傲自立、倔强坚韧,没有一般旧式女子的懦弱和依附性。《母亲》中,曼贞三十岁丧夫,不仅负债累累,还有嗷嗷待哺的幼儿。但她没有被困难击倒,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哭天抢地,而是以柔弱之躯坚强地担负一切,甚至准备与奶妈们一起养猪种菜,操持和繁盛家业。正是这种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精神和自立自强的决心意志,使得她最终抓住机会,进入女学堂,成为一名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易经》中,母亲杨露同样不甘心命运摆布,她不满丈夫吸鸦片、养外室和无所事事的遗少习气,在劝说无效情况下,勇敢反叛传统的夫权统治和女性规范,与小姑珊瑚一起出国留学,开启属于女性自我的真正人生。可见她们没有依附丈夫或家人,没有满足于旧式少奶奶优裕的寄生生活,而是努力与时俱进,开创一种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新生活。
其次,她们都重视教育,意识到知识的获取对于女性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西方女权主义者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为女性争取平等受教育和受平等教育的权利,足见教育之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意义。曼贞或许还未能从女性解放的高度认识到教育对于女性自由解放的意义,但她从自己生活经历中感觉到,女性要“自立不求人”,一定得“多读点书”。她羡慕那些能外出读书做事的女性。丈夫去世后,曼贞决心“要替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她要不管一切的讥笑和反对,她不愿再受人管辖,而要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3]167,最终她进入新式学堂,实现平生夙愿。杨露也重视教育。如果说初次出国有赌气和陪小姑的成分,缺乏明确目的,那么再次去国则有明确的强己目的。她学习英文、画画和游泳等,即使要“自己刷地煮饭”,也觉得“年青自由”。同时,她为子女教育不惜与前夫闹僵,教育女儿琵琶“要锐意图强,免得将来后悔”[4]116。可见,渴望知识、追求自由的时代思潮在这两位母亲身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记。
此外,俩人都具有鲜明的反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制的女性意识。曼贞羡慕外国女人读书、参政,反观自身处境,慨叹“规矩苦死人,越有钱的人家,做女人越苦”[3]148。特别是与娘家兄弟的对比更使她痛感自己的性别劣势:弟弟因为是男性,可以读书闯世界,所以长成聪明能干、为人称道的男子,拥有丰富的产业;而她因为是弱女子,就该卖田还债,“只能在屏门后羡慕他的荣耀”[3]151,就该“连同大伯子都不准见面,把脚缠得粽子似的小”[3]152。因此,她要读书,要反抗这种受拘囿和压制的性别境状。在学堂里,她与姐妹们志同道合,“愿意在社会上,在事业上永久团结成一体,共同努力”[3]206;乃至愿意为了孩子们能“生长在一个光明的世界里”[3]204而去刺杀皇帝。《易经》中,杨露不时提及的她们姐弟惊险恐怖的出生情景及其“女人到底是好欺负的,不管有多凶”[4]111的慨叹,也是对封建男权意识压制和迫害女性的无情控诉,而她自身及家族其他女眷的不堪婚姻生活和情感遭遇,更是封建男权意识和性别歧视导致的后果。因此,杨露坚持出国留学,坚决让女儿读书,强调“坐在家里一事无成的时代过去了,人人都需要有职业,女孩男孩都一样。现在男女平等了”[4]116。某种意义上,她对女儿教育倾注过多关注,离异后接纳逃离父门的女儿而不愿意接纳同样想逃离父门的儿子,虽不排除经济原因,但也是其反叛和抗拒传统男权思想的一种潜在表征。
总之,身处革命思想或启蒙意识激烈震荡的过渡时期,传统思想观念分崩离析,西方现代意识涌入国门,两位母亲不可避免地受到彼时激进思想影响;同时她们又都出身官宦世家,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追求独立自强,勇于接受新思想,因而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
二、迥异的人生追求:社会解放与个人自由
《母亲》中,于曼贞生活的辛亥革命前后,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反对传统“贤妻良母”、力倡“女国民”时期。吕碧城于1904年指出:“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义务。……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5]478-479而要培养“女国民”,关键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不但可奠定女子自立的基础,而且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女子的爱国主义、独立意识和女权观念”[6]。于曼贞能进入女学堂就是得益于这种兴女学、培养“女国民”的思潮,其思想观念自然深受“女国民”思想影响。而杨露生活的五四时期,正是思想解放、个性解放风起云涌时,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成为时代号角,而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又是个性解放的重要内容。当时社会上也上演着许多知识者抛弃旧式婚姻中的包办妻子、追求自由爱情的悲剧。某种意义上,杨露婚姻的破裂与个性解放思潮影响有很大关系。两位母亲所处时代背景、家庭氛围及性格心理不同,其社会交往、为人处事及性别意识内涵自然也不相同。
首先是生活圈子和社会交往的不同。如果说曼贞更多是面向社会,融入集体生活,关注和追求社会解放;那么杨露则倾向于个人自由,疏离社会集体,走的是个人主义道路。《母亲》中,曼贞深受其弟思想影响。他在男学堂教书,“并不教人做文章,只教学生们怎样把国家弄好,说什么民权,什么共和,全是些新奇的东西”[3]155。曼贞就读女学堂后,很快融入集体生活,与同学们志同道合,平时谈论的都是学问、“读书求自立”、革命及“挽救中国”或者报纸上的国事。她们义结金兰,团结互助,以秋瑾和罗兰夫人为楷模,希望加入革命党,为国尽力。可见,曼贞真正地由闺阁少奶奶转变成倾向革命、投身社会解放的新式女性,她的追求不再局限于个人解放,而是整个社会的解放,向往一个能让孩子们快乐生活、不做亡国奴的“光明的世界”,其反封建反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昭然可见。相反,《易经》中杨露的思想始终停留在追求个人独立、自由的个性解放阶段。她生活于五四运动前后,受时代思潮,特别是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影响,追求个人自由。她教育琵琶,“不要太依赖别人”,要“为自己着想,当个新女性”[4]116。作者虽然没具体叙述杨露的国外留学生活,但从她回国后的人际交往,与珊瑚、雪渔太太及琵琶等人的谈话不难看出,她始终关注的是爱情婚姻话题,追求个人自由独立。当然,《易经》中更多的是她对儿女的理性教育乃至冷漠训斥,亲情淡漠疏远,甚至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只有在接听异国男性电话或者在给异国男友写信时,才能见到她少有的温柔。她为了追求自由独立而离异,但其实内心并未真正独立起来,无论在国内国外,她都没有固定职业,没有从经济上真正独立,仍依靠嫁妆过活。鲁迅曾指出:“倘若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则一切好名目都是空的。”[7]要经济独立,只有融入社会,参加社会工作,使个性解放汇入社会解放大潮,女性的自由解放才能真正实现。这可以说是《母亲》和《易经》揭示的共同主题,也是两位母亲的不同人生经历和追求给予当代女性解放的启示意义。
其次是为人处事风格的不同。当遇到困难时,曼贞勇敢面对,寻求解决;杨露则冷漠逃避,明哲自保。比如在处理与家庭和子女关系时,曼贞虽然遭遇丧夫之痛,家业亟待打理和重整,且还要面对气势汹汹的逼债族人;但她于悲痛中振作,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为了孩子们的生长,她可以捐弃她自己的一切,命运派定她该经过多少磨难,她就无畏的走去。”[3]143她重视子女教育,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把他们带在身边,不仅从生活和情感方面倾注母爱,悉心照看和呵护,而且亲自教他们读书识字。困难击不垮她,反而激起她心中潜隐的母性,中国传统女性为了子女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牺牲精神在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而杨露遭遇家庭问题时,采取出国逃避方法。儿女嗷嗷待哺时,她把他们扔给奶妈或其他亲人,远渡重洋。儿女读书成长阶段,她又吵架离异,远在异国他乡。即使短暂的回国相聚,不是理性教训和营养学灌输,就是责备、辱骂和怨恨,缺乏耐心的爱的教育和情感抚慰。特别是面对因离异及女儿投靠而可能出现的经济困境,她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冷漠叱责和诅咒女儿,甚至当着女儿的面,说出自己内心隐秘的怨愤和失望情绪。如琵琶患伤寒发高烧,躺在沙发床上,她不仅没有给予爱的抚慰与呵护,反而失声喊道:“你真是麻烦死了。你活着就会害人。我现在怕了你了,我是真怕了你了。……像你这样的人,就该让你自生自灭。”[4]64一个冷漠、自私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击碎了琵琶内心曾编织过多少次的母爱梦!可见,作为母亲的曼贞与杨露虽然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处理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态度与方式却截然不同。竟其原因,除了上述时代背景不同,与她们性格的不同也有很大关系。曼贞性格开朗豪爽,待字闺中便结拜姊妹,常与闺中女伴们聚会,谈谈小说,做做针线,下棋吃酒。丈夫去世后,忍痛接管家事,与仆人们一起面对困难,规划未来。入女学堂,也是与同学们团结互助,谈论时事,热情参与社会活动。而杨露则性格冷漠、孤傲,由于是遗腹子,生母又是侧室,嫡母严厉,母爱淡薄,孤儿寡母倍受族人欺凌,形成她敏感孤冷的性格。婚后对充满遗少习气丈夫的失望;多年旅居欧洲,西方独立、自由及个人主义思想,都进一步影响其孤冷的性格。
另外,两位母亲虽然都有反传统、追求自由平等的女性意识,但她们的女性意识内涵有本质的不同。女性意识指女性“为女”和“为人”的双重觉醒,借用庐隐的话来说,女性“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8]。然而,传统女性只有“为女”意识,即在家做父亲的女儿,出嫁做丈夫的妻子,有了孩子做母亲,却没有独立的思想人格,更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大潮唤醒了许多女性。她们追求独立自由,但大多停留于对个体的自由和平等追求阶段。文学作品中涌现许多反叛封建包办婚姻、追求自由爱情的“娜拉”形象,但她们极少能跳出个人主义的拘囿、关注社会解放,特别是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这类形象要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庐隐、茅盾、丁玲、巴金等人作品中出现。《母亲》中的曼贞是其中之一,这是丁玲探索女性解放道路问题的一个结晶。如果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从女性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层面探索女性解放出路,梦珂、莎菲属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但她们不是以沉沦就是以消极抗拒宣告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最终走投无路的惨败;那么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韦护》《母亲》等作品,则开始跳出个性解放的拘囿,尝试从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方面探索女性解放出路。曼贞已脱去少奶奶的袍褂,融入新的集体生活,过去“她一个人在孤单里向前奋斗,她不敢希望有朋友,然而现在她却有了这么多的朋友,至少她们都了解她,同情她,愿意帮助她,同时也要她的帮助”[3]206。她们“愿意在社会上,在事业上永久团结成一体”[3]206,愿意到社会上,为国家尽一份力,甚至希望加入革命党,为了孩子们将来能生活在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里。显然,曼贞已突破个人的狭隘情感,上升到整个社会的光明和解放层面,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如果说曼贞是将女性解放融入社会解放,走集体主义的革命道路;那么杨露的女性解放追求则更多停留于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平等阶段,她的女性意识也显得模糊暧昧,既追求现代独立,又保守落后、不无依附性。特别是在贞洁观念和自由恋爱方面存在复杂矛盾心态,正如张爱玲从电车上两个女人的窃窃私语中悟到的,“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9]。杨露念叨和做的事情多与恋爱、婚姻有关,所谈论的是国外发生的杀妻悲剧、大爷偷养外室及弟弟家女儿的婚事,所做的是与雪渔太太扮演外国爱情剧、离异后的交友恋爱等。她没有固定职业,除了约会、访友,就是看电影和打麻将。她没有固定收入,离异后主要依靠嫁妆生活,第二次回国就是因珊瑚挪用她的资金导致没法继续留学。可见,她不满和反叛包办婚姻,却又依赖旧式家庭给予她的嫁妆生活,并未在经济上真正独立。她追求独立平等,向往自由恋爱,却给女儿灌输陈腐的贞洁思想,如“处女‘冰清玉洁’,大家对一辈子保持完璧的女人敬佩得很”[4]138,“只要不越界,尽管去恋爱,可是一旦发生了肉体关系,那就全完了”[10]4。特别是对琵琶获得历史老师八百元奖金的怀疑,使她突然闯入浴室检视正在洗澡的女儿是否为处女之身。一个追求独立人格和尊严的母亲却把女儿的纯洁心灵、尊严践踏在地,这是杨露这位半新半旧母亲的可悲之处。她追求独立自由,也努力培养女儿的独立自由,却恰恰又是她在利用传统思想观念肆意蹂躏和摧残女儿内心刚刚萌生的独立、自由之花。
三、同中有异的理想化塑造:革命女性与温情母亲
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11]事实上,《母亲》和《易经》对母亲形象的塑造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理想化。丁玲曾说:“《母亲》是真人真事,但写成文学作品还需要提炼,要写出特点来,才能生动。”[12]《母亲》中的母亲形象明显要比《丁母回忆录》中的丁母自画像理想,对比两作,前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母亲形象进行了加工和提炼。
首先,删去了母亲头脑中的某些封建落后意识。《丁母回忆录》中丁母有一定的重男轻女和悲观厌世思想。她生活于封建社会末期,父亲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把成名继业希望寄望于儿子身上,让他们就读于自己门生之下,管束甚严;对女儿则放弃管束,“视之若幼婴,以娱晚境”[13]236。这种传统思想自然潜在地影响丁母思想。当她生下第一个女儿时,“伤心到极点,竟嘤嘤的哭泣”[13]256。特别是丈夫去世后,悲痛欲绝,慨叹“人生太无味”[13]267,决定如若遗腹子是女儿,就从夫于地下。后来生的是儿子,她才“向死中求活”[13]268。《母亲》则把这些封建落后思想删去了,只突出母亲的坚强、自立。其次,对母亲思想意识的提纯。《丁母回忆录》用了许多篇幅写丁母后来思想悲观、消沉,转而在宗教会社寻求慰藉和解脱。《母亲》对于母亲信教一事根本没有提及(5)第三部提纲中也未提及,而是把这些消极的宗教思想置放于另一个女性形象杜鉴秋身上,以之衬托母亲形象。,更多突出母亲融于集体,与众姐妹义结金兰,“对革命心向往之”[14]。最后,对母亲革命思想的凸显。《丁母回忆录》叙述与丁母交往最多的一位女性是琳,就是母亲实际生活中的女友蒋毅仁[14]。这是一位热心于妇女解放、教育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女性,与余曼贞是至交好友,两人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共同奋进。《母亲》叙述与于曼贞交往最多的一位女性则是夏真仁——原型是向警予。这是一位革命女性,她不断帮助和鼓励曼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督促曼贞思想进步。正是在她“要救中国,一定先要有学问,还要有一般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启发和鼓励下,曼贞不断克服少奶奶脾气,忍痛放足,战胜自我,成为一名独立自强的新女性。
不可否认,《丁母回忆录》中的余曼贞确实是一位勇敢、独立、自强、追求自由民主的新女性,但其思想比较复杂甚至有些消沉、厌世。显然,《母亲》中的于曼贞比《丁母回忆录》中的余曼贞要理想化。如前所言,《母亲》创作于1932年,正是作者创作发生转变时期,即由前期《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等书写现代知识女性恋爱情感和精神苦闷,转向30年代初《水》《田家冲》《多事之秋》等描写工农革命运动。但作者对自己这一创作转变并不满意,因为它们不是“潦草的完结”,就是“宏愿的失败”,于是决定“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15]4。换言之,《母亲》创作于作者既不满意早期恋爱题材又不愿写自己不熟悉的工农题材时期,此时又是作者文艺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1931年胡也频牺牲,丁玲思想发生很大变化。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北斗》杂志,强调文艺“深入生活”“为大众”“为群众”。加之,当时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现实复杂的斗争形势也需要和呼唤描写革命的作品。尽管她不愿意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但并不意味着她放弃创作的大众化转向。于是,她把现实革命形势需要及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倡导等综合内化,提升出《母亲》的创作,既扩大了社会生活容量,又未脱离早期女性探索创作路数,同时为适应现实斗争需要对母亲形象做了一些适当的润饰和理想化,以体现当时“大众的向往”[16]6-9。
《易经》中对母亲杨露形象的塑造也存在一些理想化。如果说《母亲》对曼贞形象的理想化在于突出其思想的进步与革命,那么《易经》对杨露的理想化主要是写出了她作为母亲角色的情感温馨和母爱流露。这在张爱玲以往作品中比较少见,只要比较《易经》与《童言无忌》对某些生活片断的追述便鲜明可见。比如“过马路”情景,《童言无忌》写道:“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2]95简单冷静的叙述文字里没有温情,只有冷漠与生疏。《雷峰塔》则有一段较长的情感铺垫和心理描述:“从百货公司里出来,得穿越上海最宽敞最热闹的马路。‘过马路要当心,别跑,跟着我走。’露说。她打量着来来往往的汽车电车卡车,黄包车和送货的脚踏车钻进钻出。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几乎无声的啧了一声,抓住了琵琶的手,抓得太紧了点。倒像怕琵琶会挣脱。琵琶没想到她的手指这么瘦,像一把骨头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这是她母亲唯一牵她手的一次。感觉很异样,可也让她很欢喜。”[10]144在细心叮嘱、张望和舒缓的叙述节奏里,不难感受弥漫其中的温情和爱意。这段文字流露出一位母亲对于孩子的本能而又节制的爱意与呵护,母亲虽然很少对琵琶表示亲热,但仅有的这一次牵手也让她倍感温馨。而在1976年写成的《小团圆》中,对“过马路”的情景复现又回到了《童言无忌》那种冷漠和不适书写中,甚至有种生理上的恶心感。母女俩“站在街边等着过马路。蕊秋说‘跟着我走;要当心,两头都看了没车子——’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那一刹那的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17](此处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加着重号的文字显示出母亲蕊秋对女儿九莉的冷漠疏远,毫无温情,甚至有种生理上的排斥。这种情感自然被女儿感应到,以致觉得母亲的手像“细竹管”,拟物化修辞更凸显了母亲的冷漠与自私。
《易经》对母亲形象的塑造理想化的原因,一是因为作者母亲去世不久(张母1957年8月去世,小说写于该年9月),尽管母亲对自己有许多伤害甚至敌意,但当母亲去世消息传来,悲痛忧伤油然而生,不愉快的记忆也在悲伤中慢慢软化,成为温情回忆。二是张爱玲刚到美国不久(1955年到美国),生活和工作尚不安定,出于寻求安全感和情感慰藉的本能需要,由于时空距离,对母亲的回忆及其温情化也顺理成章,往昔那些并不美好的记忆也会因情感润泽而成为漂泊灵魂的抚慰剂。此外,也有张爱玲寻求闯入欧美文坛的创作路数的努力与尝试。张爱玲凭借叙写男女情爱故事的早期作品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等而享誉文坛,但后来受到傅雷的批评。张爱玲虽然不服气,但内心也在寻求创作突破。1953—1954年,张爱玲在香港创作了政治题材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虽然突破早期男女情爱题材,但她并不满意,且多次述说是“命题作文”,表示不再写作“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18]28。她试图用英文写作《粉泪》(据《金锁记》改,又名《怨女》《北地胭脂》),以期在西方文坛立足,数次修改均未成功。寻求突破、想要立足西方文坛的焦虑,韩素英《瑰宝》和凌叔华《古韵》等自传性小说在西方文坛畅销的刺激,促使张爱玲转向写自己的故事[18]51,即创作《易经》和《小团圆》等,情感基调不自觉地倾向温情怀旧。这样一来,既远离了意识形态,又呼应着早期对女性情感、命运的执著探索和人性书写,导致其对母亲形象塑造的温情化倾向。
四、结 语
《母亲》和《易经》中两位母亲塑像的异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两位母亲留给各自女儿的不同印象和影响,从情感、心理等境域揭示了“二玲”创作风格不同的原因。两位母亲塑像不同的原因既是两位现实母亲的个性气质、人生追求及价值观念的不同所致,也与“二玲”创作动机的不同有关。丁玲的创作动机主要是通过母亲由一位旧式家庭少奶奶成长为向往革命的新女性,反映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面貌以及现实社会中大众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母亲形象具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具有号召和引导当时民众向往和追求革命的现实政治效用。张爱玲的创作动机主要是由于作者刚到美国不久,异域生活、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存在隔膜;加之母亲新近去世,即出于个人情感精神抚慰的需要。张爱玲40年代便享誉文坛,而《易经》真正与中国读者见面则是文学创作多元化和个性化的21世纪初,因此读者更多是带着已有的阅读前见进入作品,渴望揭秘张氏独特个性风格及其天才创造的成因。可见,不同的创作动机和阅读效果也昭示着两位母亲形象的不同塑造。而两位母亲的不同塑像揭示了“二玲”创作风格的不同发展趋向(一个是开创和预示,一个是回望和承续):丁玲经过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创作转型,逐渐转向将关注女性情感和命运遭遇同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融为一体,即将女性解放同社会解放相结合,走向宏大社会历史叙事趋向;而张爱玲在50年代初经过不甚满意的社会政治题材创作探索与尝试后,依然转向她熟悉和沉迷的对男女情爱题材的创作与探索,始终执著于对人性、人心的发掘与呈现,形成其个人情感化的叙事倾向。“二玲”创作的两种不同趋向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写作发展的两种主要趋向。这已是另一个话题,留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