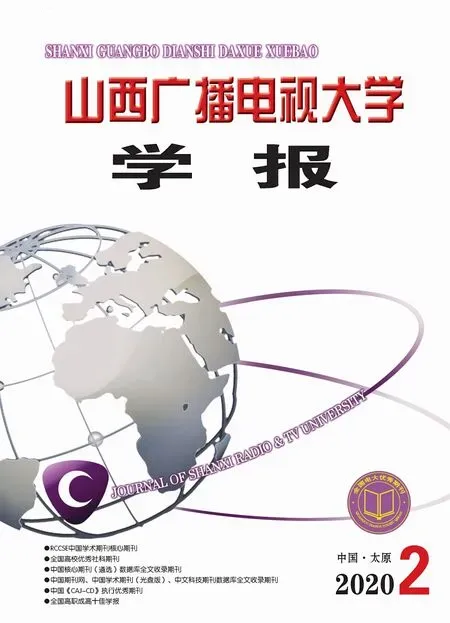嘉靖大同镇兵变问题浅析
□孙智勇 史 良
(山西大同大学 浑源师范分校,山西 浑源 037400)
明朝中后期,兵变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林延清先生统计:“从1509年到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规模较大的兵变就达六十余次”[1]368。对现存关于明代兵变问题的史料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在这些兵变中,其中嘉靖一朝就达19次,约占明代兵变总数的31.7%。而嘉靖朝的诸多兵变中,作为明代重要边防体系的九边重镇兵变高达12次,约占嘉靖朝全国兵变的63.2%,这其中,作为九边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京师屏障——大同镇的兵变竟有4次,约占嘉靖九边重镇兵变的33.3%。故对嘉靖大同镇兵变问题的反思与研究,是自明代以来就一直持续不绝的重要议题,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探析有着重要的历史与学术意义。
一、嘉靖大同镇兵变梳理
对目前所了解的史料进行梳理汇总,可知嘉靖朝的大同镇兵变主要有4次,纵贯嘉靖帝统治的各个时期,第1次和第4次兵变规模较小,故各类史书提及不多,但绝不能据此就否认其存在,第2次和第3次兵变则对明政府冲击最大,成为明中后期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具体如下表所示:
二、嘉靖大同镇兵变的主要特征
对嘉靖大同镇兵变进行历史的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其一些主要特征。
(一)兵变频发,持续影响
大同镇的兵变贯穿了嘉靖统治的全过程,且每次兵变又表现为分阶段地反复持续兵变。比如第二次兵变分为五个阶段,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大同军卒郭经等杀贾鉴兵变到被招抚为第一阶段,从被招抚军卒杀张锦文再次兵变到招抚为第二阶段,从招抚军卒杀王文昌再次兵变至招抚为第三阶段,从郭经等被捕杀,郭疤子等再次兵变至招抚为第四阶段,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郭疤子等再次兵变后被捕杀为第五阶段,反复持续不断。在同一地域兵变频繁发生,且还是在国家边防体系最严密,专制统治管控最严格的军事重镇发生,实属少见。另外,大同镇兵变持续时间较长,尤其以第二、三次兵变最为典型,都经年跨岁,分别为9个月和5个月。如果加上兵变后续问题的解决时间,则更加漫长,对嘉靖时期内政外交影响破坏是相当严重的。
(二)兵变与其他地区兵变密切联系
从相关史料来看,嘉靖大同镇这些兵变的发生不是孤立事件,既受全国其他地区兵变的影响,又影响了本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兵变的发生。比如第一次兵变是受同年发生的宣府镇兵乱的影响,第二次兵变则受到了甘州兵变的影响,“时重迁者效尤甘肃,遂杀鉴,鼓噪附虏。文锦招徕之,系官旗于狱,叛军复杀文锦”[2]267,第三次兵变则和第二次兵变紧密联系,“大同再变,以军骄不制,效尤往昔故也”[2]267,且很多兵变者本身就参加了第二次兵变,同时,在大同镇第三次兵变的影响下,第二年辽东镇也发生了持续性兵变,“乱卒于蛮儿、赵鼻儿谋俟林庭木昂至,胁赏如大同例。”[3]375
(三)参与人员广泛
《明代嘉靖时期大同镇兵变汇总表》中所统计的四次兵变,其参与群体较为广泛,不仅仅止于镇城内的一般军士戍卒。当然,也绝不是当时宣大总制都御史刘源清所说的:“城中衣冠之族悉以从贼”[4]751。其主要参与者除镇城军卒外,还有大量明政府在大同镇的部分高中低级军官及其亲眷,因为这些人都是兵变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比如第二次兵变时下级军官管队官关山、高级军官总兵朱振等,第三次兵变时,为兵变军士联络鞑靼的通事杨钺,被拥戴为头领的中军马升、把总杨林、黄镇,参将王安、郭全等。此外,还有大量被叛兵协迫的士民百姓。
(四)不以政治要求为目的
从上述4次兵变军士的诉求来看,与明代后期兵变主要以参加农民起义军队伍并推翻明政权的政治要求明显不同,这4次兵变主要是军士要求解决长年拖欠的粮饷、处罚贪赃枉法军官问题,或是要求减轻公私劳役,或是改善生存状况,或是拒绝换防等问题,正如赵立人先生所说:“只是为了反抗像贾鉴那样的个别将领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期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生存条件,并无任何明显的政治目的。”[5]
(五)均以失败而告终
从上表所载录史料来看,这4次兵变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兵变发生后,明政府就迅速派提督侍郎臧凤、巡按御史张钦进行镇压,对兵变领导人张的祥等5人加以杀害,其他参与者被调到极边哨所。第二次兵变发生后,明政府先后派遣军队进行镇压,主要领导人郭鉴等11人被斩首枭示,胡雄、郭疤子等4人被凌迟,其家属被连坐,财产被没入官,协助兵变的焦亚云等38人被刻榜枭示。第三次兵变的领导者王福胜等14人惨遭凌迟杀害,妻奴资产被没入官,父母祖孙兄弟都被牵连流徙,郭经、张玉等68人被处斩。而第四次兵变后,很快就被军官刘卿瓦解并招抚。
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缺乏斗争的政治纲领,无坚强的领导;二是不能团结更多的斗争力量,既未与其他反抗明政府的群众运动结合,还大肆劫掠杀害广大百姓,而失去民心;三是被明政府分化瓦解,先后被叛徒出卖,同时所依靠的蒙古势力北撤,使其失去支援。
三、大同镇兵变频发的原因分析
大同镇兵变频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府及各级官吏对军卒肆意压榨催生了大同镇兵变频发
明代中后期,封建皇权得到空前加强的同时,朝政更加腐败,贪官酷吏横行,军务堕废,经济上,皇帝、宗室及各级官吏、地主疯狂进行土地兼并,屯田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大同边镇军卒所受剥削严重,生活苦难,再加上政府及各级官吏经常以各种名义克扣士卒月粮军饷、扣减号衣布帛、私役买卖等,边卒往往饥寒交迫,无以为生。1497年(明弘治十年)兵科给事中吴世忠上疏备陈大同边备废弛,士卒困苦之状:“将官推举,多以贿通,一握兵权,如获私宝,既求偿债,又欲肥家,役军多至千人,侵屯动以万计,掊克赏赐,以赂权贵如此也。十月风霜,士甲无衤肖,妻居无煤,幼儿裸体。问其故,则曰:‘役繁粮薄,苦于奉将’。”[3]53迫于生计,士卒铤而走险发动兵变逐渐成为常态。1534年(嘉靖十三年)明隰川王孙朱成钜给嘉靖帝上书:“云中叛卒之变幸获销弭。究其衅端,实贪酷官吏激成之。臣虑天下之祸隐于民心,异日不独云中而已。”[6]
(二)大同镇兵变频发是嘉靖时期明军务管理的表现
大同镇兵变频发不是偶然性事件,而是明朝政府内外交困,国力日渐衰弱,社会矛盾激化的集中反映。嘉靖时,经过“大礼议”和“壬寅宫变”,加速内耗,明政府不断洗牌,朝政混乱,财政匮乏,大同边镇军粮长年拖欠,“据巡抚都御史刘麟言,大同等卫军士自正德七年以逸于嘉靖四年月粮俱未支给,十三年不发月粮。”[1]376外部环境也不乐观,沿海各地倭寇时常侵扰掠夺,北部蒙古诸部在小王子、吉囊、俺答带领下持续南下攻掠,如果不算小规模袭扰,“保守估计,在嘉靖一朝(1521-1566年),大同镇被侵扰次数大约有60余次,”[7]17而面对蒙古的进攻,明军又败多胜少,士气极其低迷,畏战、避战和逃军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还有边境军官士卒与蒙古诸部私下联络勾结。“士卒与蒙古部众私下的接触互动,为大同军兵举乱前后寻求外援和避难之所提供了现实可能。”[7]18从上文梳理的大同镇四次兵变情况来看,除第一次外,其余3次都与蒙古势力有关,据此,我们对明政府的边境的控制力可见一斑。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大同镇兵变频发的一个重要诱因。
(三)大同镇兵变频发与大同镇军纪败坏、兵将骄犷难治有关
大同镇兵变多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笔者认为这也与当地民风彪悍、素有反抗传统及军政败坏有关。历史上大同镇一直就是边关要镇或为京畿重地,自古就重兵尚武,且多次兵变叛乱。嘉靖时期边政败坏,大同镇军纪松弛、兵将骄犷难治情况更加严重。方孔炤《全边略记》中记载:“大同兵素犷悍,自江彬擅调后,益恣肆”,[3]58韩奇邦在《大同纪事》中也说:“三堂麾下官军素骄逸。”[8]263可见,大同镇军卒的骄犷难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有其传统的,而这也为兵变频发提供了可能性。且兵变发生后,新任军政人员害怕引起激变又往往对军卒放任,军纪更加败坏松弛,从而为新的兵变埋下了更大隐患。
(四)被投机者利用也是大同镇兵变频发的重要因素
从大同镇兵变的有关史料来看,其频发与投机者的利用不无关系,特别是第二、三次兵变时,表现更为明显。甚至一些中高级军官为达私利,也活跃其间,对兵变从发生到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第二、三次兵变时被拥戴的旧总兵朱振就是其中最为得利的投机者。嘉靖三年,当兵变发生后,因贪腐问题被告免职的朱振被叛兵推举为主,他就在明政府与叛卒中博弈,时而向朝廷表示忠心,抓捕杀害兵变士兵,时而又与叛军约法三章,为叛兵出谋划策,为他们向朝廷乞请宽恕,并放纵叛兵杀害官民,“时振以赃系狱,怨望喜祸,阴为郭鉴等策划。”[9]也正是他的投机表演,获得了实惠——贪赃之罪不予以追究,并重新担任了总兵。《殊域周咨》载记:“尹耕曰,朱振为乱兵所迫,然乎?曰非也。振自失职以来,心怀悒怏,貌著倔强,羁栖镇城,起衅,乐因变自利,其宿心也哉。”[10]442嘉靖十三年,久在大同镇城寓住的朱振,与新任总兵李瑾关系不睦,更是时时挑动镇兵发泄不满,以期再次获利,“伍中及墩卒时出怨言,振因以微言动之。诸来役者泣诉法太严,则曰:‘李瑾生长右卫小城,无长人度。彼习知伊小城中军伍易制也,岂知镇城多杰者邪?’又曰:‘往年张文锦之变,军人岂独于总兵官不敢发邪?’于是旧杀文锦脱漏未诛如王福胜辈咸愤曰:‘必杀之’。”[11]288之后,大同镇再次兵变,叛军再次推拥朱振为主,代行指挥。这就坐实了其参与兵变与平定兵变的政治投机性。
四、嘉靖大同镇兵变的影响
频繁发生的大同镇兵变对嘉靖时期的社会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打击明政府统治秩序,破坏了明政府在大同的经济社会及边防系统,还对明蒙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嘉靖政府调整了军队管理政策
面对大同镇兵变嘉靖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多为被动的临时性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无法从根本消除兵变频发的根源。
1.诛杀首谋者提高震慑。大同镇兵变直接危及嘉靖政府的统治,但全部诛杀又不现实,甚至还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比如在第三次兵变后,总制刘源清就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将参与者全部诛杀,希望借此震摄兵变军兵,从而顺利平息兵变。结果事与愿违,使形势更加严峻,大同军卒出于自身安危纷纷加入兵变,迫使嘉靖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加以应对。在4次兵变中,嘉靖政府对兵变参与者采取最多的主要是诛杀首谋者的策略,这样做一方面对参与者与未参与者进行震慑和警示,另一方面还可以展现统治者的“仁政”,同时还有利于对兵变者进行分化瓦解。这样做显然对迅速平定兵变是有一定效果的。比如在大同第二次兵变第四、第五阶段中,当兵变领导者郭经、郭疤子等再次倡导兵变之际,巡抚蔡天祐则对大同镇兵进行劝诫:“兵来惟诛首恶,胁从不问也,汝辈勿助恶即为良民,无事矣。”“以是首恶者煽惑,众多不从。”[12]878从而将兵变队伍瓦解,领导者郭经、郭疤子等51人被出卖捕杀。
2.调整具体措施。在高压征剿的同时,嘉靖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诸如招抚、封官赏赐、惩处贪酷官吏、减轻压榨等方式,以此来缓和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如对造成第三次兵变扩大化且对官兵“厚为掊克,赃贿不赀”[4]763的总制刘源清、都督郤永等予以革职拿办,以消除兵军卒的怒气;对兵变领导者中的指挥马升、千户杨林给以招抚封赏,用以瓦解兵变队伍。对边镇军兵也通过诸如大同总兵桂勇建议的:“帮军余丁及换哨守城者皆已占役,勿令种纳屯粮,苦以他摇,军士冬衣布花宜责所司,刻期征解,以八月内放给。”[4]706以及宣大总制张瓒建议的:“大同近罹兵变,调发征需之苦大同最甚,而宣府次之,乞将二镇是年应徵粮革除,奉诏蠲免五分外,其余悉行免征,以苏困苦。”[4]759使边镇军卒减轻了所受的剥削,生存状况略有改善。对胁从人员处罚政策也十分宽松,嘉靖皇帝下旨,直接规定:“大同乱军虽凶愫,实皆良民,朝庭不得以用兵,止除首恶及行刃重犯,余皆不问。”[4]709甚至还让兵部召集廷臣就大同兵变事宜讨论后,作出“胁从无罪者,事平亦各给银三两”[4]709的赏赐决定。这种方式的最大隐患就是实际上起到了变向鼓励兵变的作用,大同镇及其他地区的兵变的高频发生,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二)大同镇经济社会及边防系统遭到破坏
4次兵变给大同镇带来破坏性冲击,社会秩序动荡,兵变军士乘乱劫掠居民,杀人放火,大同镇城一片废墟,“日劫掠诸富家,搜杀诸定变有功者,一言不相入及素睚眦者,咸灭族矣。”[10]456礼部侍郎黄绾在向嘉靖汇报第三次兵变的奏章中说:“是役也,杀游击曹安、千户张钦等数人,士女千八百人被虏,及惊失者千余人,其余擅杀埋掩者不可胜数,毁室庐以万计,财货刍粮称是,民不堪命矣”[4]763。平乱过程中,明军也乘机杀掠大同镇城内外百姓、军兵,“大肆杀掠,城外横尸枕藉。”[12]880“杀戮之惨不足言也。”[8]267兵变也“造成大同‘墩营间有毁坏’,‘府库空虚,行伍离散’”,直接导致其军事防御能力大为减弱,”[7]38兵变后,军纪更加败坏,士卒更加骄横难治,“于是乎大同纪纲废坠,不可收拾矣”[8]267,边防系统遭受严重破坏。至嘉靖前期,募兵制度被迫开始全面推行,嘉靖十三年二月,“兵部以大同乱卒未平,又有虏警,请差给事中六人、兵部司官六人分诣各边,召募勇敢,以壮军实”[4]755。到嘉靖二十八年,“九边”军466895名(兵部咨送为452028名),募兵约占20%”[13],明政府兵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军士素质也因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之辈而大大下降。
(三)明蒙互动联系加强
如前文所述,叛军与蒙古势力互动频繁,4次兵变中有3次都有蒙古势力的影子。他们相互勾结,互相配合,严重地破坏了明朝的边境地区。比如嘉靖十二年:“叛兵勾虏入寇。初变,诸叛即使人以金币啖北虏,有刑通事者,数盗马塞外,颇知虏驻牧所,率数人往。虏初疑之,即知戕总兵事实,虏酋打来孙、吉囊、俺答、兀慎等以五万骑至。”[11]456这些蒙古势力与叛兵结盟后,迅速进入大同地区共同对抗明政府的镇压,同时乘机四处杀戮抢夺:“小王子留精兵相持,余众分掠浑、应、朔、怀诸郡邑,数月乃去。”[12]882使大同边民饱受苦难。另外,兵变军卒大量投靠蒙古势力,“自虏引退,大同叛卒有随虏北者”[4]756,这些人随着蒙古势力在边境长期屯驻,伺机入侵虏掠边境。他们常常充当向导、间谍,为蒙古势力侦查军情、渗透劝诱明朝军民叛乱,成为明边境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当然,另一方面,随着大量投奔军卒以及其他移民的北移,也给蒙古地区带去了先进的耕种及其他技术,客观上推动了蒙古腹地的开发和明蒙间的交流。
五、结语
嘉靖大同镇兵变只是明王朝众多兵变中的一部分,它的发生是明朝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的剧烈的、集中的体现,频繁的兵变使得明王朝的统治链条出现了裂痕,使明王朝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也使明王朝的国力受到不断消耗,更加剧了其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