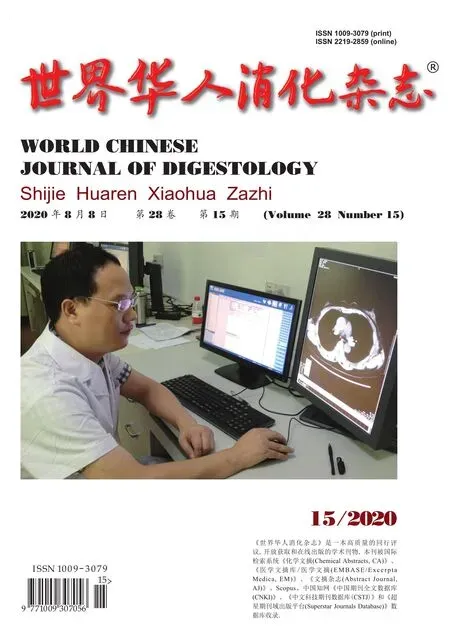强化克罗恩病监测和优化患者管理
王静静,范一宏,黄 蓉
王静静,范一宏,黄蓉,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6
0 引言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一种以复发和缓解为病程特点的肠道慢性免疫失调性疾病,可引起胃肠道任何部分的炎症,出现肠狭窄、瘘管或脓肿等并发症[1].疾病治疗通常采用药物治疗,主要的治疗药物是氨基水杨酸、激素、硫嘌呤类、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及生物制剂[2].目前CD的常规药物治疗可能不能充分控制潜在的炎症.长期使用激素,也可能使患者面临依赖和感染等风险.此外,患者症状严重程度与CD患者的内镜状态不一定一致.目前CD的治疗目标不仅仅是控制症状,而是达到临床和内镜缓解.为达到目标,治疗过程中,监测疾病活动度、内镜及影像学检查、炎症标志物水平有助于及时调整CD患者治疗方案,优化治疗.近年来,治疗性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在硫嘌呤、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中的运用已经有了很大进展,通过TDM可以优化和监测CD患者的治疗[2].大多数患者最终将需要手术治疗,在手术后疾病复发的患者需要持续的治疗,所以加强术后患者疾病的监测,对于预防复发和优化治疗非常重要[3-5].本文主要综述了CD患者治疗过程中炎症标志物的监测、药物监测及术后患者的监测,进而优化患者管理,使更多的患者达到治疗目标,指出了CD患者密切监测的重要性.
1 炎症标志物
临床实践中,由于成本和/或操作的侵入性,重复频繁的内窥镜或横断面成像检查是不可行的.因此,炎症的替代生物标志物,包括粪钙卫蛋白(fecal calcitonin,FC)和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在CD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FC在评估肠道炎症和治疗反应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准确性,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标记物.FC有助于识别内镜下复发或术后复发的高危患者,可能是CD患者“以治疗为目标”管理策略的基石[6].高水平血清CRP提示疾病活动,是指导治疗及疗效随访的重要指标[5].STRIDE一致建议CD的治疗目标为达到临床和内镜缓解,组织学愈合是否应该是一个最终的治疗目标是有争议的.如果内镜检查不能进行,则应在治疗开始后6-9 mo进行横断面成像评估.目前认为,FC或CRP,可能有助于检测残留的肠道炎症,并可能有助于患者监测.然而,这些炎症标志物的持续升高不应单独用于调整治疗[7].对于炎症标志物与抗肿瘤坏死因子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维持治疗期间,FC的水平和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IFX)的谷浓度相结合可以指导剂量调整,增加内镜反应和缓解的机会[8].一项回顾性研究[9]显示基线CRP水平和CRP下降率可作为CD患者抗肿瘤坏死因子原发性无反应和继发性无反应的临床预测指标,并可指导CD患者的治疗.CALM研究[10]是一项针对CD患者的3期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了炎症标志物与临床指标结合的方式监测炎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能否优化生物制剂治疗、改善治疗结局.事后分析表明FC和CRP正常化与CD内镜下黏膜改善/愈合显著相关.且FC正常化与CD内镜下黏膜愈合的相关性高于CRP.通过密切监测,阿达木单抗(adalizumab,ADA)优化治疗CD使近8成患者达到了严格的监测目标.这项研究首次表明,在早期CD患者中,根据临床症状和炎症标志物及时增加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比单纯根据症状做出决定,能获得更好的临床和内镜治疗效果.密切监测可以快速优化治疗.然而炎症标志物水平并不是目标,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建议仅使用炎症标志物进行治疗优化.炎症标志物可能反映残留的肠道炎症,但内镜和/或磁共振成像应该在优化治疗之前进行.因此,炎症标志物促进了对患者的监测,而不是治疗本身的目标.FC和CRP是辅助监测措施,不管症状如何,炎症标志物如果不能正常化,应进一步进行内镜或放射学评估.
2 药物监测
TDM被认为是个性化或个体化治疗策略的一种很有前途的工具,并作为改进现有治疗策略的一种新手段而受到欢迎,尤其适用于疗效或毒性治疗窗口较窄的药物.TDM是个人剂量的有价值的工具,有助于个性化或定制药物的概念[11].传统上,TDM包括测量药物浓度,调整进一步的药物剂量,以便将血浆或血液药物浓度维持在最佳的靶向治疗窗口内.主要需要TDM的药物包括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目前批准的生物制剂疗法包括抗肿瘤坏死因子疗法、抗整合素疗法和抗IL12/23疗法[2-4].相当大比例的患者将经历生物制剂治疗的原发性无应答或继发性丧失应答.仅靠症状评估指导的治疗决策不太可能达到最佳结果.TDM已成为最大限度提高CD治疗反应的一种有前途的策略[12].
2.1 免疫抑制剂 常规的硫嘌呤和巯基嘌呤是CD患者的一线免疫抑制疗法.此外,可以将硫嘌呤与抗肿瘤坏死因子联合治疗,以降低免疫原性,改善或维持临床反应.硫嘌呤不良反应常见,且可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应在严密监测下应用[5].硫嘌呤的代谢过程中产生药理上有效的核苷酸6-硫代鸟嘌呤核苷酸(thioguanine nucleotide,TGN),同时产生潜在的毒性代谢产物,如6-甲基巯基嘌呤(methylmercaptopurine,MMP).代谢物6-TGN和6-MMP在治疗至少4 wk后在红细胞(red blood cells,RBC)中的浓度被测定.6-TGN浓度高于235 pmol/8×108RBC与治疗效果相关.骨髓抑制与6-TGN浓度高于450 pmol/8×108RBC有关.6-MMP浓度高于5700 pmol/8×108RBC与不良事件有关,特别是肝功能异常,而极高浓度则可能导致骨髓抑制[2].在6-TGN和6-MMP的低浓度的患者中,可以增加硫嘌呤/巯基嘌呤的剂量,以达到治疗的最佳6-TGN浓度(235 pmol/8×108RBC以上).如果6-TGN和6-MMP的浓度都高于推荐的限度,或者6-TGN的浓度被认为是“治疗性的”,那么硫嘌呤治疗不太可能有效地维持临床缓解,应考虑改变治疗策略.除测定6-TGN和6-MMP外,还可检测硫嘌呤S-甲基转移酶(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ase,TPMT)多态性.TPMT酶活性低或缺乏的患者有过度产生药物衍生TGN代谢物的风险,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骨髓抑制,建议在开始接受硫嘌呤治疗的患者中进行TPMT检测,以指导硫嘌呤的剂量[11,12].此外,NUDT15 基因多态性检测对预测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人群出现骨髓抑制的灵敏性与特异性高,可以在使用硫嘌呤前检测.治疗过程中应根据疗效、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和 6-TGN 进行剂量调整,用药期间应严密监测不良反应.巯基嘌呤监测注意事项与硫嘌呤相同[5].
单一疗法MTX可以与硫嘌呤衍生物类似的方式使用,或者在硫嘌呤治疗失败的患者中作为二线免疫抑制剂使用,可作为维持缓解治疗的选择.MTX转化为甲氨蝶呤聚谷氨酸(methotrexate polyglutamate,MTXGlu),阻断二氢叶酸还原酶和嘌呤的合成,起到抗炎和促凋亡作用[11].在CD患者中,通过测量RBC内MTXGlu浓度来测定TDM的研究并不广泛.Fischer等[13]探讨了RBC中总的或个别的MTXGlu水平是否与克罗恩病的疾病活动性和不良事件相关.对12名患者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每周稳定剂量为25 mg MTX (口服或皮下注射).结果显示未观察到单个RBC或总MTXGlu浓度与临床疾病活动性(Harvey-Bradshaw指数评分)、炎症标志物或不良事件之间的关系.提示虽然CD缓解期患者的RBC总长链MTX (MTXGlu3+4+5)浓度普遍高于活动期患者,但其与临床疾病活动性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其他据报道,RBCMTXGlu3+4+5浓度与CD的疗效成反比,在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浓度更高[11].因此,RBCMTXGlu3+4+5浓度与临床疾病活动性之间没有确定的联系.
以上研究表明,监测6-TGN和6-MMP浓度、TPMT多态性,可以指导硫嘌呤的剂量.NUDT15基因多态性可在使用硫嘌呤前检测,预测骨髓抑制.CD缓解期通过测量RBC中MTXGlu浓度来测定TDM的研究并不广泛,目前研究表明患者的RBC总长链MTX (MTXGlu3+4+5)浓度普遍高于活动期患者,但其与临床疾病活动性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目前对MTX中的TDM的作用是有限的.
2.2 生物制剂 生物制剂正在取代传统的激素,成为更安全、可能更有效的药物,用于中度到重度活动性CD的患者,特别是那些已经用过激素的患者,或者患有肛周疾病的患者[14].尽管如此,许多患者对治疗没有足够的反应,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疗效.标准剂量的血清药物浓度的个体间差异很大,以及抗药抗体的产生被认为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15].对于生物制剂,TDM是一种基于药物浓度和抗药物抗体评估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是优化治疗的重要工具,从临床和经济的角度来看,TDM似乎都是合理的[16].
2.2.1 抗肿瘤坏死因子:被批准用于治疗克罗恩病的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包括IFX、ADA和塞托利单抗.其中,在开始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之前,应检查患者是否有潜伏/活动性结核和乙型肝炎感染[14,17].抗肿瘤坏死因子由大的蛋白质分子组成,既具有非人类的抗原,因此具有抗原性,又由于分子的大小而具有固有的抗原性.抗药物抗体的产生是一种临床上相关的现象,在不同的化合物中发生的频率不同[11].证据表明,接受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的患者治疗效果丧失和药物不良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抗药物抗体形成的结果,所有这些药物的治疗过程都可能会产生抗药物抗体,比例最高的是那些接受IFX治疗的患者[2].
在存在抗药物抗体的情况下,无论是临床缓解期的患者还是活动期的患者,最受欢迎的治疗策略是联合免疫抑制剂,这符合美国胃肠病学会(american gas association,AGA)指南,而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发布的指南也提到了支持这一方法的研究[18].免疫抑制剂能有效降低免疫原性,提高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水平[14].全剂量硫嘌呤疗法与IFX有协同作用,对于防止抗药物抗体的形成而言,6-TGN浓度在105-125 pmol/8×108RBC之间可能足以防止免疫原性.对于ADA,也有类似的协同作用.这再次暗示了6-TGN对抗药物抗体形成的保护作用,建议的6-TGN至少为223 pmol/8×108RBC[11].关于是否联合免疫抑制剂,不同的生物制剂研究结果不同.一项观察性队列研究中比较了IFX与ADA在临床上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价联合免疫调节剂治疗的价值.结果表明IFX和ADA具有相似的反应特征.然而,IFX需要联用免疫调节剂才能达到与ADA治疗相当[19].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20]研究了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临床和药代动力学因素,结果显示,在多变量分析中,唯一与原发性无反应独立相关的因素是第14周的低药物浓度[IFX:优势比0.35 (95%CI:0.20-0.62),P=0.00038; ADA:0.13 (0.06-0.28),P<0.0001],第14周与缓解相关的最佳药物浓度分别为IFX 7 mg/L和ADA 12 mg/L.同样,第14周的药物浓度也与第54周的不缓解独立相关[IFX为0.29 (0.16-0.52); ADA为0.03 (0.01-0.12); 两者均P<0.0001].IFX产生抗药物抗体的比例为62.8% (95%CI:59.0-66.3),ADA为28.5% (24.0-32.7).联合免疫调节剂治疗降低了发生抗药物抗体的风险[IFX的危险比为0.39 (95%CI:0.32-0.46); ADA为0.44 (0.31-0.64); 两者均P<0.0001].对于IFX,免疫调节剂的使用和第14周的药物和抗药物抗体浓度的多变量分析显示,免疫调节剂的使用对第54周的未缓解有独立的影响[优势比0.56 (95%CI:0.38-0.83),P=0.004],结果表明对于IFX和ADA,第14周的药物浓度预测了免疫原性,而抗药物抗体的发展预测了随后的低药物浓度.IFX产生抗药物抗体的比例大于ADA.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降低了它们发生抗药物抗体的风险.在PAILOT试验(评价ADA治疗CD儿童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治疗药物监测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这一特殊分析中,在ADA诱导后72 wk评估ADA联合治疗与单一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联合组与单用组在持续无激素临床缓解率(25/34,73%vs28/44,63%;P=0.35)或持续综合临床缓解率(CRP≤0.5 mg/dL,FC≤15.0 µg/g,10/34,29%vs14/44,32%;P=0.77)方面无显著性差异.临床和生物学结果在联合治疗组和单一治疗组中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监测亚组之间没有差异.ADA谷值和免疫原性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在两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提示,ADA联合免疫调节剂治疗儿童CD的疗效并不比单用ADA好[21].
目前临床上,为了优化疗效,临床医生经常通过增加IFX剂量或缩短输注间隔来强化IFX治疗.研究显示,经验剂量增加在高药物水平或抗药物抗体患者中的效用可能是最小的,这解释了关于其有效性的相互矛盾的结果[15].在IFX维持治疗期间,抗药物抗体的发展增加了活动性疾病的可能性,即使在低浓度和存在治疗性浓度的药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需要评估预防IFX抗体形成的策略,包括IFX剂量强化的治疗药物监测[22].尽管IFX的确切治疗窗口尚未明确,但维持治疗期间的低谷水平>3 μg/mL和诱导期的低谷水平>20 μg/mL与不同疾病的临床研究和后期的临床结果的改善有关.一项针对活动期CD患者的前瞻性随机探索性试验[23]探讨了将IFX水平维持在3 μg/mL以上的治疗药物监测是否比仅根据症状调整剂量产生更高的临床和内镜缓解率.结果提示与仅根据症状增加剂量相比,根据症状、生物标志物和血清药物浓度增加IFX剂量并不能在更大比例的患者中达到无激素药物的临床缓解.此外,最新的评估新西兰全国范围内抗肿瘤坏死因子和TDM在IBD治疗中的应用的研究中[18],在完成调查的人中,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将TDM作为IBD患者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治疗的一部分.大多数人认为测量水平和抗药物抗体的合适时间点是在下一次注射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之前的24 h内(ADA为92%,IFX为82%),这与AGA的建议相一致.调查参与者主要只在反应丧失或原发无反应的情况下应用TDM.虽然这与目前的一些指南建议仅在活动性疾病中实施TDM相一致,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主动TDM的益处.对于主动性监测,一项TAXIT试验[24](低谷水平的适应IFX治疗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主动药物监测的患者继续使用IFX剂量调整的治疗可能性更大,特别是对于IFX浓度<5 μg/mL的患者.IFX目标浓度为3-7 μg/mL,对于初始谷值小于3-7 μg/mL的CD患者,将谷值优化为3-7 μg/mL可使临床缓解率由65.1%提高到88.4%,并降低平均CRP值.然而,在最初的优化阶段之后,与基于临床的剂量调整组相比,基于谷浓度的剂量调整组没有看到额外的益处.还有研究发现IFX低谷水平在3-7 mg/L之间的治疗窗口.但主动的TDM并没有改善腔内CD.然而,主动性TDM组有较低的CRP水平和较少的患者需要抢救治疗[11].所以主动性TDM对疗效有提示作用.如果将基于患者治疗反应的被动性监测与基于谷浓度的主动监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被动性TDM策略相比,用于IFX的主动TDM略微具有成本效益.随着IFX成本的降低,主动监测策略更具成本效益[25].一项临床实践的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首次证明,与标准治疗相比,ADA的主动TDM可能与IBD患者治疗失败的风险较低有关[26].一项回顾性研究探究[27]了IFX暴露与儿童长期缓解的关系,纳入了接受维持性IFX治疗的CD和溃疡性结肠炎儿童.结果显示,通过在儿童中使用主动性监测,接受IFX治疗的儿童在维持治疗期间临床和/或内镜缓解较高.在一项儿童CD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28]中,研究发现主动监测ADA谷浓度,调整剂量和间隔,使无激素临床缓解率明显高于被动监测.
以上研究表明,对于IFX和ADA,尽管联合免疫抑制剂后降低抗药物抗体的程度不同,可能对于IFX而言,联合免疫抑制剂疗效更佳,ADA联合免疫抑制剂与单一治疗的疗效相比仍有争议.目前的建议,对于IFX和ADA,联合硫嘌呤或MTX,6-TGN对抗药物抗体形成的保护作用,6-TGN至少为223 pmol/8×108RBC.对临床反应/缓解患者将药物滴定至目标谷浓度,可以提高抗肿瘤坏死因子的疗效,且被动性TDM与经验性剂量增加相比更具成本效益.但一些研究发现在最初的优化阶段之后,基于谷浓度的剂量调整的临床缓解并不优于基于临床的剂量调整.此外,与被动性TDM相比,用于IFX和ADA的主动TDM是有益的,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基于TDM的治疗策略可以通过降低患者联合治疗的剂量、增加时间间隔和/或停止免疫调节剂,对药物浓度高于治疗浓度的患者实施降级策略,从而提高生物治疗的成本效益和安全性,此外,TDM还可以帮助治疗失败的患者选择下一种药物.目前的建议[2]是为了提高临床实用性,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的监测可以从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包括在比低谷水平更早的时间点评估药物浓度,以便在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期间或之后立即调整治疗.对于抗药物抗体而言,应进行更有效的抗药物抗体检测,克服仅在抗肿瘤坏死因子浓度较低或不存在时检测抗药物抗体的局限性:甚至在临床相关的抗肿瘤坏死因子浓度下降之前尽早检测抗药物抗体产生.
2.2.2 抗整合素和抗IL12/23制剂:α4β7整合素拮抗剂维得利珠单抗(vedolizumab,VED)可抑制肠道特异的白细胞转运,可作为中到重度克罗恩病患者的一线治疗,或用于其他治疗失败的患者.在目前可用的生物疗法中,它的全身副作用最少.一项队列研究显示,有黏膜愈合的患者第6周的VED谷值中位数为26.8 mg/mL,未愈合的患者的中位数为15.1 mg/mL.由于免疫原性低,通常不会联合使用免疫调节剂,还可以考虑用于对不同生物疗法产生抗体的患者[14].较高的VED血清浓度与较高的缓解率相关,这种关系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包括以前是否使用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还需要进行前瞻性研究来评估VED剂量的个体化和最优化[29,30].乌司他库单抗(ustekinumab,UST)同时抑制IL-12和IL-23.尽管尚未建立最佳的UST血清谷水平,但较高的血清UST谷水平与较高的临床应答率相关.有研究显示,UST谷浓度>4.5 μg/mL与炎症标志物减少(血清CRP水平或FC水平)和较高的内镜反应率相关[14,31].一项回顾性研究[32]显示用诱导后8 wk UST谷值预测16 wk临床疗效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中等,使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TDM可通过识别可能受益于剂量增加的亚治疗浓度的个体,证明对CD患者的个体化UST治疗是有益的.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33]中调查了CD患者在治疗前2 wk内的血清UST浓度与内镜和生化缓解的关系.结果显示,静脉滴注后1 h的血清UST浓度可用于确定CD患者最有可能在内镜下获得缓解.这一早期测量可用于优化CD的治疗.以上研究证明监测UST药物浓度可以预测疗效和优化治疗.与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相比,UST和VED的免疫原性低,安全性好[12,34].具体来说,对于VED很少观察到抗药抗体的形成,而在0.7%的UST研究患者中出现了抗药抗体.目前尚不清楚被动性或主动性TDM是否能改善治疗效果[11].以上研究表明,监测非抗肿瘤坏死因子生物制剂药物浓度可以优化治疗,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以进一步确定最佳药物浓度和抗药物抗体阈值.
3 术后管理与监测
尽管CD的药物治疗取得了医学上的进步,但大约71%的患者在确诊后10年内需要手术切除.50%的患者可能需要第二次侵入性手术[5].CD患者术后处理面临多重挑战.目前在这种情况下的适应症药物包括:抗生素、氨基水杨酸盐、免疫调节剂和生物制剂[35].每种药物都有固有的风险和益处,最佳方案仍不清楚[36].为了降低术后复发的风险和严重程度而开始或继续进行药物治疗称为“预防”.使用预防性治疗的决定和这种治疗的选择,应该以患者早期CD复发的风险为指导.高危患者包括穿透性疾病患者、既往两次或两次以上手术、主动吸烟、从诊断到手术之间的时间不到10年、确诊时年龄较小、广泛的肠道受累以及先前免疫调节剂或生物制剂治疗失败.所有吸烟的患者都应该被强烈建议戒烟[14,37].研究指出,高危患者需要强有力的免疫抑制治疗,应在手术后、复发疾病活动开始时立即开始治疗.在预防和改善CD术后内镜复发方面,硫嘌呤的疗效高于美沙拉嗪或咪唑类抗生素,但抗肿瘤坏死因子越来越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药物[38].与对照组相比,IFX预防CD术后复发是有效的[39].IFX减少临床和内窥镜疾病的活跃度.IFX预防性给药可以降低回结肠切除后血清学、内窥镜和组织学复发的风险.与硫嘌呤相比,IFX在有复发风险的高危患者中,回结肠切除后的组织复发率显著降低.高危CD患者应考虑在术后即刻进行IFX,还有研究指出,对于高危患者,最好在术后4 wk内开始生物制剂治疗.为了防止复发和维持内镜缓解,需要进行长期的维持治疗.ADA在减少高危CD患者的内镜检查和临床术后复发方面是安全有效的.在降低高危CD患者切除后内镜和临床复发风险方面,预防性ADA治疗优于硫嘌呤和美沙拉嗪.当ADA与IFX进行比较时,组织学、内窥镜和临床复发的风险相等[14,35,40].研究表明,对于术前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失败的患者,术后重新开始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的疗效有限,应考虑不同的生物制剂治疗[14].Candia等[41]评估术后处理是否应该基于单独的生物制剂治疗或联合硫嘌呤,以及治疗是否应该在手术后立即开始,或者在内镜或临床复发的指导下进行.结果显示,对于复发风险较高的克罗恩病患者,术后立即应用硫嘌呤,并在内镜下复发的指导下加用生物制剂是最佳的术后处理策略.术后2-4 wk使用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似乎是安全的,但2 wk内使用的安全性尚不清楚.Christine等[42]评估了CD患者腹部手术后2 wk内开始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的效果.对术后2 wk内或2-4 wk内接受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的患者与未接受抗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的患者的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并发症进行χ2和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腹部手术后2 wk内或2-4 wk内早期应用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不会增加CD患者术后感染的风险.
虽然生物制剂是最有效的,但也有许多潜在和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将其推荐为所有患者的术后治疗可能并不合适.以预防性方式开始治疗,还是先用最有效的药物治疗,还是升级治疗,这都是有争议的.但患者风险分层和通过预定的回结肠镜进行定期监测是最佳术后复发管理的基石[43].目前建议是对有术后早期复发高危因素的患者宜尽早(术后2 wk)积极干预; 术后半年、1年以及之后定期行结肠镜复查,根据内镜复发与否及其程度给予或调整药物治疗[5,35,44].治疗指南指出所有患者,无论其复发风险如何,内镜检查是诊断术后复发的金标准.这些发现定义了病变的严重程度,并有助于预测临床病程.建议在术后6-12 mo进行内镜评估,以帮助指导治疗决策[45].对于术后监测结肠镜检查无复发的患者(Rutgeerts评分为i0或i1,即手术部位回肠或结肠小糜烂少于5个)应继续定期结肠镜监测.复发性疾病(Rutgeerts’s评分i2或更高)的患者应该开始进行有效的治疗或优化目前的治疗方案[14].此外,超声可评估CD病变并发症、术后复发情况.CT小肠造影和磁共振小肠造影是诊断CD复发的有效方法,并与内镜评分相一致.这些技术对预测术后CD的临床病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46-48].FC在评估肠道炎症和治疗反应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准确性,有助于识别内镜下复发或术后复发的高危患者,有助于监测疾病活动性,并预测CD手术后的未来临床进程[6].有研究表明[49],FC可以预测CD术后内镜复发,但并不优于CRP联合Harvey-Bradshaw指数.
以上研究表明,抗肿瘤坏死因子被认为是手术高危患者最有效的药物,其他生物制剂的有效性还需研究.目前高危CD患者应考虑尽早在术后进行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但是否预防性给药,以及何时使用仍存在争议.手术后早期应用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不会增加CD患者术后感染的风险.术后6-12 mo以及之后定期行结肠镜复查.炎症标志物、超声,CT小肠造影和磁共振小肠造影等检查对预测术后CD的临床病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结论
近几十年来,CD的治疗目标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从关注临床反应转向黏膜愈合.在这种情况下,CD的管理是一个挑战,加强CD患者的监测显得格外重要.在早期CD患者中,根据临床症状和炎症标志物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比单纯根据症状做出决定,有助于对患者进行监测,能获得更好的临床和内镜治疗效果.但内窥镜检查和影像学成像应在优化治疗前进行.组织学缓解并不是临床的目标.结肠镜检查评估黏膜炎症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然而,当无法通过结肠镜检查评估黏膜炎症时,影像学检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推荐仅考虑炎症标志物的治疗优化方案.对于药物监测,TDM已被用于改善硫嘌呤的治疗,对MTX中的TDM的作用仍是有限的.与被动性TDM相比,用于IFX和ADA主动的TDM可以提高生物治疗的成本效益和安全性.目前的建议是抗肿瘤坏死因子药物的监测应从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从而提高临床实用性.被动性TDM适用于所有药物,但主动的TDM对于优化非抗肿瘤坏死因子生物制剂的效用仍有待描述.对CD的术后管理而言,炎症标志物对预测术后CD的临床病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术后6-12 mo以及之后定期行结肠镜复查.高危CD患者应考虑尽早在术后进行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但非抗肿瘤坏死因子生物制剂在术后预防性给药中的作用还需研究,抗肿瘤坏死因子预防性给药的最佳时间尚无统一意见,且预防性给药与术后复发采取早期治疗的有效性比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CD患者的治疗目标是实现临床/症状缓解和内镜缓解,在治疗前对患者进行疾病评估和风险分层设定治疗目标,在治疗后1-3 mo对临床症状、炎症标志物及药物浓度进行监测;在治疗3-9 mo后进行内镜复查,根据内镜结果判断是否已达黏膜愈合.治疗中通过设定严格的治疗目标,按设定的时间密切监测目标是否实现,调整治疗方案以实现目标.达标者予药物维持或降级治疗,未达标者继续调整方案监测病情变化至达标,对疾病进行长程管理、降低并发症、改变自然病程.然而,CD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可能需要根据疾病类型设定不同程度的治疗目标.要认识到,在某些类型的患者中,目标本身可能无法实现.此外,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需让患者相信实现特定目标的益处,并鼓励坚持强化治疗和监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