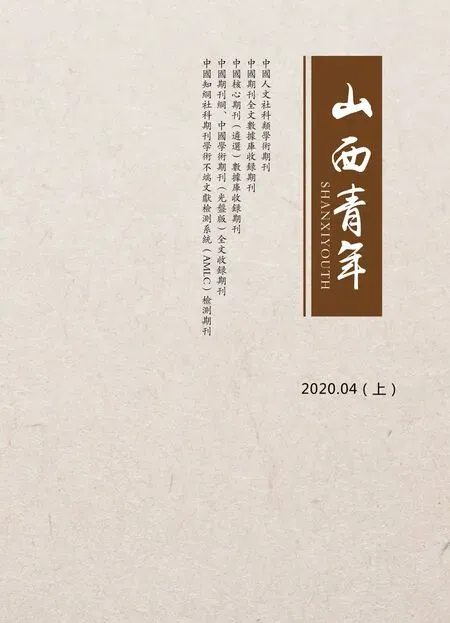从男权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看池莉作品中的爱情观
——以池莉爱情三部曲为例
王景然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1
从古至今,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追求的理想性平等中,有关于女性平等的问题一直是被极度关注的话题。从追求男女平等到认为男女的确有别到男女不用等同的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在显著提高。尤其在当下社会,女性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可女性仍因传统话语模式下根深蒂固的性属弱势,无法占据政治、商业等等领域的核心位置。在感情生活中,社会性属偏向于让“男人挣钱养家,女人貌美如花”,男人自古以来便在家庭权力地位核心中占据主导力量,男权主导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池莉的作品中显现十分突出,以此池莉在其爱情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中传递出了一种鲜明的爱情观。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到:“……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真实性是衡量文学作品是否源自于生活的尺度,文学作品从生活中取材,提炼加工形成文本高度凝练以达到一种陌生化的视觉体现。灵与肉的矛盾,就如言与意的矛盾一样,相互依赖却又不可趋达。《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是池莉塑造的在现实生活中绝望挣扎的若干形象之一。一整夜每个时辰的报钟点,催促着印家厚投入到生活的忙碌之中去,夫妻之间的爱情已然不复存在的,在的是默契的相互支撑,正如钱钟书所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可是生活在坟墓里的人连掘坟诈尸的勇气都没有。以印家厚为主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生活在绝望而无趣的资本压榨下,为一家老小的生计奔波,连停下来对现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婚姻里的爱情,或许在开始时确实存在吧,但这粗糙的生活终是磨去了最后一点激情。生活跌宕,好事坏事都是他们先摊上。一潭死水中,耗尽了所有的激情与幻想,放逐理想,消解爱情,他们“活着就好”,他们“不谈爱情”。
古代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上流社会也就是代指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家庭是戴着眼镜看下层社会的人民群体的。《不谈爱情》里庄建飞与吉玲的爱情就是这种“正统思想”扭曲下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在武汉大学樱花树下相遇,吉玲手持一部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让庄建飞感受到了一见倾心,直到最后庄建飞已经认为自己爱上了吉玲,违逆父母娶吉玲为妻,吉玲的步步为营初步胜利。整个恋爱过程对于吉玲来说是个精心预谋的“人工创作”,而庄建飞则成为她预谋的目标。吉玲婚后为得到丈夫和庄家的充分重视,又与娘家一起演了一场闹剧,甚至闹到庄建飞单位,惊动了庄家,并直接威胁了庄建非的前程。吉玲终原形毕露,当年樱花树下的美好记忆成了带有讽刺意义的一幕。庄建非从迷梦中惊醒,重新正视现实:爱情是虚幻的奢侈品,它不实用。从庄建飞与吉玲畸形的婚姻状态中,吉玲为了稳固自己作为庄家儿媳妇的地位手段频出,但是竟然已经取得法律的认定两人成为了正式夫妻,为何还存在需要用特殊手段获得庄家儿媳妇的地位呢?它的不正常,来源于正统社会对花楼街的偏见和抹杀;而正统社会又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他们的视域与权势直接影响了花楼街的社会定位。花楼街的女子是与“众”不同的、卑贱的、不可高攀的,这样一种社会认同,恰恰是男性话语对其自尊意识的解构,消解了其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达成了与正统社会的一致认同。吉玲的聪明之处在于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这个男权社会里,巧妙地装饰着自己,取得以男性(庄建飞)为中心的社会的认可。
婚姻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感情基础。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类学家莫尔顿在研究人类婚姻历史和现代的专著《情爱自然史》中如是评价:“浪漫本质上是自私的,虽然它表现出闪耀夺目的热情与开放,然而,它是不能实现的许诺”,多半人生都是在协调与另一半的关系中度过,而产生问题的根源则在于社会性属所自带的冲击和矛盾。池莉的小说中所展示出的阶级地位影响下的夫妻不平等地位、社会底层人民一潭死水的生活与爱情以及违背内心所愿的压抑。因此,爱情是社会秩序和个人生命流程中不可逃离的一环。它的价值不在于揭示爱情和婚姻的意义,而是满足社会和个人某种理想的合理化诉求,在于生命漂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