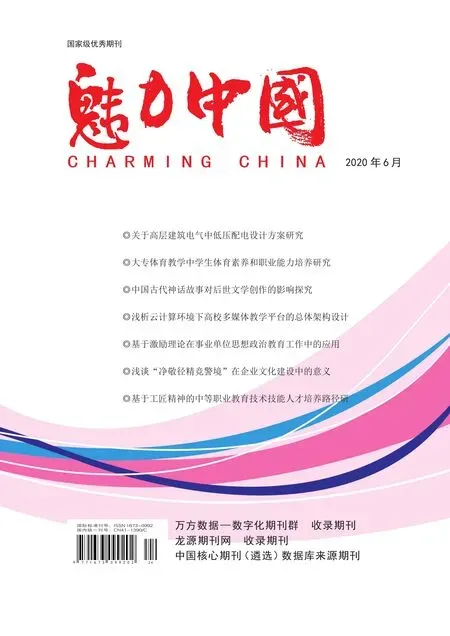“蘸染随类 ·五彩布成”
——简述山水中色彩的形式与表现
王子锟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100102)
色彩因附着于优秀的艺术作品而产生夺目的生命力,色彩的丰富是绘画作品产生艺术价值的重要表现元素之一。在绘画的各个领域,颜色的自如运用成为画家完成作品的有利因素,在色彩的专项研究中更成为一件作品完成的最终目的和使之产生价值的直观视觉因素。一副画作或清淡或浓郁或匀重或辉煌或凹凸有致的画面特殊材料效果,色彩都起着重要作用。山水画作为众多艺术语言形式的一种亦是如此,客观事物是色彩丰富的,并且随着环境季节气候的变化而产生颜色的变幻。如李可染所说“”雨后山水似彩云”,一定境界意味的表现离不开色彩”,它的表现是肉眼最直观的,内心易冲动的,情感易渲染和共鸣的。
对于颜色的应用,中国画古代亦称“丹青”这里的“丹”指丹砂(朱砂),“青”指石绿石青等矿物颜料。这两种颜色在古时得到最广泛和普遍的应用。从这一方面不难看出,古代绘画无不着色赋彩,自古至今,中国画的绘画表现形式随着漫长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渐趋成熟多样,无论是画面的表现形式,材料的多样性还是中国画的用色都形成了清晰的面貌鲜明的形式特征和系统的方式方法。中国画的用色跟笔墨无不想通,都是抒写画家心中的“笔墨”,心中的“色彩”。
“随类赋彩”出自古代南齐谢赫所著绘画理论专著《古画品录》,是其倡导的“六法论”其中之一。“随类赋彩”或“随类,赋彩是也”,是说着色。赋通敷、授、布。赋彩即施色。随类,解作“随物”。《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这里的“类”作“品类”即“物”讲。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随色象类,曲得其情”。随色象类,可以解作彩色与所画的物象相似。随类即随色象类之意,因此同于赋彩。这是中国画用色的根,为画家笔下的物象传神、为整个画面的意境服务,以此能彰显中国画的悠远意味。这里具体说一下“随”字并不是书面上简简单单的理解为依据客观现实事物的本像,更不是纯粹的由眼前的景像而到画面的视觉形式复制。“类”则是包含整个世界万物客观景物和在不同的环境变化下对景物产生的形式,颜色等方面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当然也包括绘画者对于客观事物的解读感受和寄予的内心情感的表达,这些因素都可以理解为“类”。“赋”简单可以理解为“给予”讲,深层次更包含了对万物的理解,对色彩的认识运用的高度和在不同材料上的表达能力。“随类赋彩”就是绘画者通过对客观物象的观察,基于内心的真实感动和感受和在艺术上的造诣,使客观景象的色彩和主观的审美趣味,艺术表达都达到高度和谐统一。这种绘画色彩得理念使中国画创作中的对于色彩的运用获得无比的灵活和高度的自由。
中国画山水除随类赋彩外也注重在山水中空间环境对物象的色彩影响,环境时间的不同对山石树木有着不同的影响。南北朝时的萧绎对环境影响物象色彩有着颇深研究和见解,正所谓“秋毛科骨,夏荫春英,炎绯寒碧,暖日凉星。”出自于《山水松石格》,此描述也是我国最早的对于四季节气不同描述的记载,也是对物象色彩受自然环境影响变化的有力说明。概括了季节的变化对水色和天色的影响变化在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也得到诠释:“水色:春绿,夏碧,秋青,科黑;天色:春晃,夏苍、秋净,科黯”。值得一提的是,有时国画的色彩并非完全符合现实自然以及节气不同状态下景物所呈现出的多姿色彩。但这样的色彩符合视觉审美的规律,能够被心理所接受,用色亦在情理之中。
中国画的发展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经过不断地创新发展积累沉淀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独有的艺术文化。中国画在色彩的运用上亦是如此,在出现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完善,壮大的历史过程中,色彩的在国画中的应用随着人类文化文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宗教艺术,宫廷画院等等的不断发展,对色彩的认识不断进步成熟,色彩颜料的增多和对于在不同材质上的应用技术不断提高完善,思想审美意识也得到不断深入。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体现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人物图》(现存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人物御龙图》。前者是我国现发现最早的一幅帛画,造型简洁生动,线条圆润挺拔流畅,曲直配合得当,主人公服饰的黑白配色颇有装饰意味。画中墓主人面左侧身而立,身着细腰袖衣袍裙拖地,双手合掌向上,用线垂顺自然。画面是墓主人合掌祷告在腾龙凤舞的接引之下飞升天国的景象。龙凤两者刚柔相继,形式感及造型意味对比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得色彩除了历史的沉淀感带给我们的厚重感外,用色也是饱满沉重,浓浓的赭石色带给我们对当时历史文化的无尽遐想,此外人物的嘴唇和衣袖上看得出施过朱砂色的痕迹,如此简练的造型下这些细致颜色的应用甚是讲究。设色的方法采用的是平涂与渲染兼用的方法,以达到格调的典雅庄重。
秦汉绘画以单线平涂及红黑为主色,少数运用渲染法和间色。所描绘的形象较前代更为复杂,因而在红黑基色的基础上白,黄,青,绿,金,赭也较多应用。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以赭为基色,物相以白黑红青为主。西安红庙坡出土彩绘铜镜车马人物图以红为基的基础之上,用绿,白,黑等色丰富了物象的描绘。作品中所运用的颜色并非符合客观实体的现实对象,而是由当时人们所处时代所形成的色彩定式审美观和对所绘事物的客观认识依类描绘。可以说,当时人们对于色彩的运用也超越的眼睛的直观描述,用一种特定的色彩倾向表达对事物的审美。正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随色象类,曲得其情”。这种色彩的应用,呈现出了作品浑厚,拙朴,绚丽夺目的风格。
没骨是中国画中不用墨笔为骨,直接用色彩描绘物象的技法。相传为南朝梁张僧繇所创。唐朝画家扬升善用没骨入山水,称之“没骨山水”。此法是用青、绿、朱、赭、白粉赭石等颜色堆染描写出山石松风的山水画。明代董其昌、蓝瑛等也频频效仿此法用于山水创作之中。董其昌精于鉴赏品评,富于收藏,善书法致力于山水画。董其昌对于此法的运用发展在山水绘画方面进一步提纯了作品的绘画表现语言和视觉语言,把色彩运用的绘画从中国画的综合因素之中作为重要的表现元素突出出来并加以放大处理,不仅使得色彩作为绘画的直接描绘手段更加突出其地位,也成为山水绘画的重要表现因素和表现目的之一。
五代西蜀宫廷画黄荃花卉鸟虫勾勒极细,亦肉离得色彩反复着色后,线色相溶,几乎隐去初始的墨色笔记,色彩韵蓉润泽,仿佛直接蘸色挥之一气呵成,对其遂有“没骨花枝”之称。代表作《写生珍禽图》。北宋徐崇嗣(徐熙之孙)效学黄荃,所绘花卉折枝摒弃墨线勾勒,只用色彩画成,后人称这种画法为没骨法。《图画见闻志》记载:“其(徐崇嗣)画皆无笔墨,惟用五彩布成”。明晚期人物画家曾琼(《王时敏像》)的人物肖像画也吸收了此法,用淡墨勾勒人物形象轮廓和五官,施墨色反复染出五官的凹凸结构,再赋予色彩平罩渲染。这种在传统画法的基础上重视没骨的绘画方法不仅突出了民间的写真方法,又显现出文人画的文质相兼的独特审美取向,因此追随者众多形成“波臣”画派。明代画家孙隆专攻没骨点染法,法北宋徐崇嗣设色没骨,不事墨笔勾勒,单纯以色彩在熟纸绘卷上写意表现,趣味横生,潇洒灵动。清代唐于光,恽寿平亦用此法。恽寿平画面工致细密但又不失脱俗,在灿烂之中求的平淡天真的意味,画风明净艳丽,风格清醇,物象多姿。他学习明代沈周,孙隆,更“仿北宋徐崇嗣没骨之法”,不用墨笔勾勒事物轮廓,直接用笔蘸染颜色写之,不求型似。因此画面情趣盎然,描写生动有趣且富有色彩的微妙变化。这也大大的发展了没骨的画法,而此法在清初的花坛上也令人“耳目一新”“别开生面之势”。市井画家,官宦画家追随者众多,从而形成以恽寿平为代表的“常州派”。
青绿山水,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的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的。以矿物质颜色石青,石绿为主要颜色,树根石根处配以浅赭石,有些或配以白色点染屋瓴人物,看去辉煌庄重,富有草木华滋万千气象之感。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前者多钩廓,少皴笔,着色浓重,装饰性强,长于灿烂明艳;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罩青绿,温蕴俊秀。青绿着色,重在渲晕得法,薄中见厚,浓中见雅,清王翠《清晖画跋》中讲"凡设有着绿.体要严重,气要清倩,得力全于渲晕。余于青绿法静悟,三十年始尽其小。”青绿山水操作性强,程序繁复。王石谷说:“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全力在渲染,余于青绿法镜悟三十年始尽其妙。”这也说明画青绿也需要深厚的水墨功底和对画面的整体把握能力。青绿山水从六朝时期开始,逐步发展至唐代时的二李(李思训,李昭道)从而确立了青绿山水的基本特色。两宋之交前后形成金碧山水、大青绿山水、小青绿山水。南宋时期,青绿山水画风复兴,以赵伯驹兄弟俩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传赵伯驹《江山秋色》(现藏故宫博物院)。元代垕说:“李思训著色山水,用金碧辉映,自为一家法。”南宋有二赵(伯驹、伯骕),以擅作青绿山水著称。在元、明、清三朝各自积累发展并相互传承影响,而其中以小青绿山水为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设色出现了多种风貌,是中国画用色的发展,完善时期。如张僧繇的《维摩诘像》。时至隋代,墨彩的结合成为作者在绘画作品中所选择的主旋律,如展子虔《游春图》,描水勾石,以石青石绿为主,金碧设色,辉煌饱满庄重,并且具有一定的装饰意味,绘画色彩的应用比较成熟。
浅绛山水清净明快,淡雅素丽。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浅绛山水,则全以墨为主,而其色轻重之足关矣。”《芥子园画传》:“黄公望皴,仿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浅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钩出大概。王蒙复以赭石和藤黄着山水,其山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色钧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影响至沈石田,清代的王原祁,都专用这一形式作画,格调高雅。董源的《江南》整幅气势磅礴开阔,山水围绕,柔美之势不可言喻。树木施以黑绿,古朴自然,具有灵性生命力。
近现代中国画色彩创新不得不提张大千的“彩墨山水”。从1927 年到1948 年的20 余年中,张大千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正是这一时期的游历积累,为他晚年的“狂涂”打下基础,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积累也为他后来彩墨泼墨的创作提供了帮助。“彩墨山水”祖于张大千,迭进于刘海粟、林风眠,兴盛于新世纪。“彩墨山水”就是用色彩去画山水画,讲究色墨相融,不人为地将色与墨分出宾主来。张大千泼墨泼彩画法的特点在于对技法的进一步研究和对色彩大胆的尝试和应用,这种创新继承了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更是揉入了源自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由此可见张大千的作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再创新和再创作。20 世纪六十年代,张大千已经从泼墨法过渡到泼墨法和墨彩合泼法。《幽壑鸣泉》(1961 年作)是张大千开始泼彩的佳作。
叶浅予先生这样评价张大千的彩墨艺术“墨法中的泼墨法,由来已久,其成因是水墨运用的大胆创造,即使运笔简化,又得形象浑厚,在运用复笔着色的基础上,大胆创造泼彩,是顺理成章,必然要走的一步。当然,这种创造不能排除外因的推动。”他不仅运用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在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上,将泼墨加以重彩,创造出彩墨淋漓的万水千。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在学习,领悟,钻研和继承发张中国画的传统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形式,以此来更好的适用现代社会的审美趣味和山水笔墨在当今社会多民族及全球文化相互影响繁荣发展下所呈现出得多彩多元。
中国画山水用色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石色,水色颜料和绘画表现方式。水彩丙烯的覆盖感都可以被尝试研究,把这些区别于国画颜料的综合材料融入到中国山水画的创新纸中去。色彩和材料变化创新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那就是整体上不失中国画的书写性,不失中国画的精神内蕴,学习古人留给我们宝贵的艺术(山水)发展史,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珍贵书画作品留给我们对于山水学习的丰富营养。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材料和形式都可以进行大胆尝试探索以增强色彩的更强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