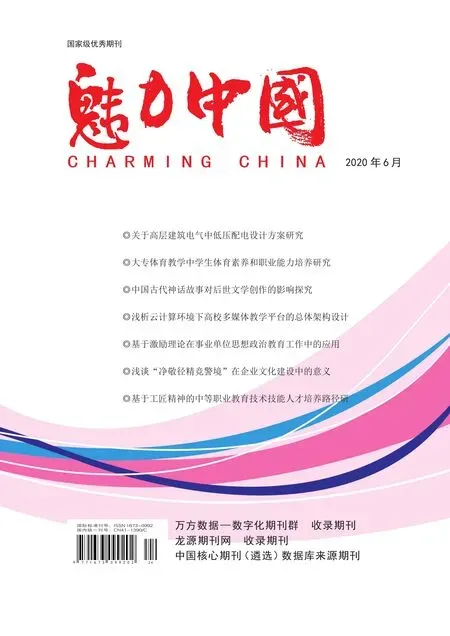谈电影《活着》的影像元素与现实意义
张贝尔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00)
影片中福贵这一角色,从富少沦落为贫民,家产尽输、子女遭祸,在时代的洪流中只能忍气吞声、四处漂泊。在几近绝望之际,仍以一种平和朴实却蕴藏着强大力量的精神内核裹挟着自己前进。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张艺谋通过独具匠心的影像化再创造,为观众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这一内涵。
一、别出心裁的影像元素
张艺谋对于影像的视觉表达向来是很固执的。拍摄在本片之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构图、色彩、光影十分讲究,将“红”这一色调融合中国传统美学,使电影影像极具象征意味;而拍摄在本片之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加大了色彩和符号的特殊运用,增强了场面的宏伟感,甚至给人虚幻的纯美感。而本片似乎是特别的。通过现实主义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是纪实风格的表达,似乎只是用摄像机将时代的变换记录下来。
即使如此,在本片中的细节之处,他又有自己的影像风格坚持所在。如果说电影的开篇常常为电影定下影像基调,那么本片中定下基调的不是第一个平淡无奇的街景镜头,而是片头的两个大字“活着”。方方正正的蓝色黑体字幕是客观的,在影片中的时代变换中,“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也是这样的字体,这是时代的洪流,是旁观者的视角;而那肆意伸展的笔触还带有残缺的橙色大字,显然是具有人情味的且给人以生机的主观表达。既直截了当地指明电影的主题,又暗暗的将人物的命运寓于其中。福贵一生看似是受尽磨难的,苦不堪言的,但他和家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忍受与抵抗却如同这张牙舞爪的字体一样,是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如果将视听结合起来看,张艺谋的改编也有不少可取之处。比如影片中福贵向龙二借来赖以谋生的工具由田地变成了皮影戏。这一视觉上的符号始终穿插在影片中。皮影戏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物,又是一种隐喻符号。皮影是受人操纵的,戏是戏剧性的。操纵皮影的福贵,命运也是受时代操纵的且太富有戏剧性。这一改编即使影片独有的中国色彩得到加强,又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命运。
在听觉艺术上,赵季平的配乐堪称电影情绪渲染的点睛之笔。开头就是两小节频率像人心脏跳动般的鼓声,给人以紧张感;底层的编曲还夹杂了迅速弹拨的琵琶声;随即凄凉婉转的二胡声便是人物命运的主旋律,时而哀切时而平和,中途降低一个八度的演奏使配乐结构更加的丰富;而与二胡声共同担当主旋律演奏的还有笛子,笛声更空灵高亢,增加回声效果,给人以一种不真切的感受,也很好的印证了福贵命运的戏剧性。整首曲子是影片主人公命运的主旋律,充满着一种极力抗争命运的顽强感,也让影片的主题“活着”得到了升华。
二、昭然若揭的现实意义
如果进行对比分析,中岛哲也的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也是一部将人物命运和时代命运相结合的影片,女主人公松子的一生也坎坷无比。其影片展现了一种哲学观念,甚至从某一方面可以说是日本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观念:信仰本身是无法对现世起作用的,唯有相信信仰并受其鼓舞的人的人生才会因信仰得到转变。
而本片的主题:活着本身没有意义,但为了活着而做出的努力却给人以极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有相似之处。“信仰”这个词来源于西方,西方人不能理解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特定信仰。当人们说到信仰自我时,往往还会被其嘲笑。但实际上,信仰自我是信仰人本身。福贵没有信仰,“活着”这个词所富含的意义是他主动赋予的。福贵的信仰是自己,是生命,是导演和观众把这个信仰命名为“活着”,以至于他在人生中不断地践行而自己却难以感知其多么可贵可敬。
影片的英文译名为“To Live”,“To”虽不是动词,却给人一种被驱使的感觉。这种译法既迎合英语语法,又很符合西方人普遍有信仰的特点:在上天的指引下活着。而在中文中,“活着”是一种状态,听起来平淡无味,却是不为任何所驱使的独立存在。活着是一种本能。我们民族向来是不把命运寄托在他人、他物上的,这种“人至上、生命至上”的观念,是那一代时代洪流中的中国人独特的彰显人生意义的方式,也是整个华夏民族在历史车轮不断碾压下的坚守。
三、结语
不管是从极为丰富的影像元素或是极具力量的现实意义来看,本片都无疑是一部佳作。“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尼采如是说。虽然福贵以及那一代中国人的人生之舟,一直在时代洪流中浮沉漂泊,不断地被倾覆,他们却从未放弃过。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功地克服了这个时代,并且终将执桨到达洪流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