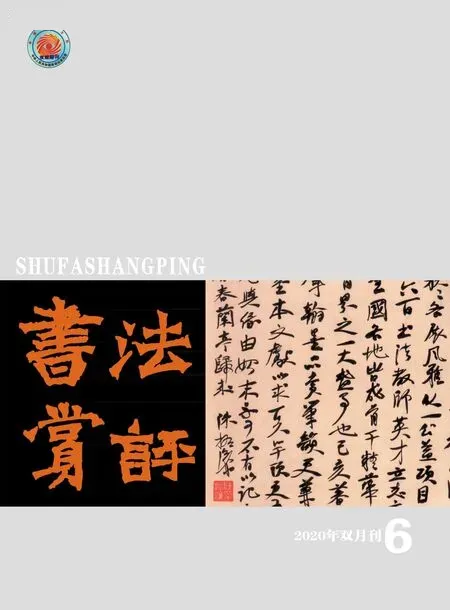论教育功能视角下的书法之“真”— —以少儿书法创作为中心
张 婕
近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艺术学科的学习也随之“升温”。这股加强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潮在书法教育这一领域中也得到了强烈的响应。少儿书法教育愈来愈加受到重视。书法教育不仅走进了校园,校外的机构也多设有专门的培训点。可以说,少儿书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焕发出生机。
一、当下少儿书法创作之优劣
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少儿的书法学习较以往更具系统化。在教学中,指导者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教学,从笔画描红、准确临摹、精准创作等各个层面事无巨细地引导着。总的来看,少儿对书法创作的掌握也更具系统性,这种创作模式显现了指导者的积极意义。可以说,即便是少儿不熟悉的某家某派,在指导者短时间的点播下,少儿也能创作出令家长满意的书作。
事实上,少儿书法不仅在风格表现方面体现出“成人思维”,在范本选择、作品构思等诸多方面也不例外。在指导者的影响下,少儿在遴选书籍时多仅选择指导者指定的一两种经典范式之作。同时,为了适应接受者的审美,在遴选书籍的过程中,适应教育需求、符合接受者审美的唐楷往往成了少儿书法学习的首选范本。
当少儿在书法的临、创中似乎表现得淋漓尽致时,笔者不禁想追问的是:这一切是合乎情理的吗?就创作方面来看,当下少儿书法的创作模式是否是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创作模式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既贴合了语文课堂的写字规范,也适应了展赛的创作模式,不仅能在教学效果中有其独特优势,亦能获得家长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这种创作模式是一种多数人认可的创作形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创作模式自然有一定的权威性、普遍性。但若以少儿书法的长远发展来看,不难发现,即便少儿是自身书作的创作者,但少儿却未必是其创作的主宰者。也就是说,少儿的书法在指导者的调整下更接近字帖的真实,但这却未必是少儿书法创作自身的真实。这里,笔者将少儿书法创作中依附于指导者特有的审美、缺少独立创作的思维模式称为“成人思维”模式。当然,这样的定义并非是单纯的命名上的不同,这也暗示着重新阐释少儿书法创作的另一视角。
这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创作模式又是如何风行的?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教育功利性相关。在大众看来,书法的学习似乎更有功利性色彩。如果说少儿学习绘画是为了开发其想象力,学舞蹈是为了锻炼身体的柔韧性。那么,书法的学习则更多是为了提高试卷上所谓的“卷面分”。多数为子女报名书法培训班的家长,要么是出于调整书写上某些不良习惯的需求,要么是出于提高孩子卷面分的需求。诚然,唯有书法能与语文等学科的卷面相挂钩。正是在这种功利性的驱使下,少儿的书法教育在多数情况下更彻底地沦为了语文等学科的附属品。书法教育又仅仅是追求书写的规范。当指导者、家长被功利心所遮蔽,这也导致他们对所谓的“美”不再敏感。对少儿书法的认知偏见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融入到人们的思维之中并侵蚀着人们将来的认知。应该相信的是,仅仅沉溺于书写规范,于少儿书法创作而言亦是有害的。进一步来看,在书法学习中,部分指导者的教学方法(如九宫格、米字格临写模式)都成了当下少儿书法创作、学习的重要手段。这种思维模式的创作也在一次次临写运用中建构了少儿书法的审美范式。趋向精致化、准确化的书作却俨然成为少儿追求的终极目标。可以这么说,创作中理性的发展加速了少儿创作的“成人化”,教育的功利化、僵化的创作思维又左右着少儿的自我审美。因此,少儿自我的艺术审美被分割成了片鳞碎甲。当这些临、创之作真的如同假的一般时,少儿书法也失去了其本该有的活力。
这么看来,很多时候,少儿书法的学习又是不自由的,少儿很少有机会选择自己中意的字体、表达自己的审美倾向。显而易见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少儿的书法创作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不同的创作内容。教育环境在成就了当下少儿书法创作准确化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情况。妍美和秩序化的书风成为少儿书法创作的权威旋律。然而,固定秩序的背后却隐藏着指导者对创作主体的支配。将少儿书法创作与世俗功利相提,这显然简化了少儿丰富的审美内涵,忽略其个体体验,也冲淡了少儿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笔者以为,对问题的反思是迫切且极为必要的。
二、去伪存真:少儿书法创作应有的思维模式
那么,何为少儿书法创作之“真”、少儿书法之“真”又表现在哪几个层面?笔者以为,所谓的少儿书法创作之“真”,这是指:不过多依附于指导者的成人思维,在作品表现的某些方面能体现出少儿的自我认知,这要求少儿从自身出发,寻找适合自己心性的思维方式,而不应是“他者”思维的简单折射。很多情况下,为了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指导者对少儿进行详细的指导,在教学中,指导者不断细化教学,少儿固然能更容易地接受,但却丧失了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的可能性。法国教育家卢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对儿童的教育从观念上就错了,我们用成年人的思维对待孩子,我们用成年人的方法教育孩子,其结果必然是误入歧途。”[1]
对于少儿的学习而言,当指导者为其量身定制一种字体时,这既是一种对美的“发现”,同时亦是一种“遮蔽”。有相当一部分指导者对学生的喜好、长处是非常模糊的,不管指导者们是否愿意承认,指导者都有必要了解少儿书法创作的特殊性。学者刘铁芳也曾指出:“早期的教育就其实质而言,其实就是唤起儿童身体感官直接地与感性世界的相遇。”[2]因此,少儿书法教育的成功并不完全在于技法形式的完满,亦包含一种对美的领悟和体验。
笔者以为,少儿书法创作之“真”,不仅表现在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更表现在少儿书法创作中特有的真趣。而真趣的审美则源于少儿的心灵深处。当少儿在习得必要法规后,可以凭借自己的心性去体悟、去发现、去创作,这就是其创作之“真”。这里,我们可借宋四家米芾对“真趣”的解读作进一步了解,米芾有言“出于天真,自然神异”[3],又有“随手落笔,皆成自然”[4]。这里的“出于天真”“皆成自然”应是指凭借创作者的心性为之,而非轻率为之。也就是说,在创作中,少儿以习得的知识为前提,融入自己的领悟、心境,其书作自然更有蕴含真趣的可能。正如许多书家常常提及,成年之后,一些书家再难写出少儿书法的那般趣味。应该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是一种书家自我调侃的言辞,而是发自肺腑的感叹。因为,相对于少儿的多样性认知,成人的理解似乎表现出更多的趋同性。可以看到,即便是对少儿而言晦涩难懂的图像、单字,他们总能以多样的联想进行自我认知。也正是这种“真趣”的存在,少儿书法才如此活泼可贵。而古今书家追求的“趣”,正是少儿这种无法磨灭的真趣。
对于当下少儿书法创作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当下的环境,亦不能不重视少儿的自我认识。从某些方面来谈,若不剔除偏见,少年的书法创作也将安于一隅。需要说明的是,少儿书法创作也并非要一味追求真趣而无需法则。“唯法则为中心”或“不顾创作之规则”,无论出自哪种创作模式,都是书法创作的大敌。笔者在文章中大篇幅地反对“成人思维”模式的规训,这并非要反对书法的必要规则而追求所谓的“丑书”。必要的规则是构成书法创作的重要成分。这里,笔者也并非要反对书法的实用性,而是希望少儿书法创作能在实用和艺用两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纵观书法史,标榜“自然”“丑拙”书风的书家也并非是要将其书作表现得“体无完肤”。蔡显良先生就曾辩驳了某些人对傅山“四宁四毋”的理解,蔡显良先生的理解显然不是将“四宁四毋”的书学观贴上所谓“丑书”等有色标签。他认为傅山是在“表达一种质朴自然之美”。[5]
三、少儿书法如何走向创作之“真”
我们如何越过偏见,让少儿书法创作呈现出生命的张力呢?也许一切皆有可能,只待我们去探寻。
这里,笔者以为,首先要准确把握指导者、少儿、书作这三者的内在关系,这三者存在着密切而又微妙的联系。如何发挥少儿的主体作用,使其在“成人思维”的创作模式中有所突破是当下少儿书法教育中的难题。在指导者的指引、教育功利性驱使下,少儿期望得到指导者认可、为观者所接受,少儿便更易听取指导者的指导,这便易造成千人一面的创作效果。另外,少儿有意无意地迎合指导者、家长的审美口味,这种学习态度也必然从反面促成“成人思维”审美模式的风行。在创作中,指导者的“成人思维”,通过书作的接受制约着少儿创作的方向。应该说,好的指导并非是给少儿书法创作制造压力、削足适履以适应成人的创作思维。如何挖掘少儿书法创作中的特殊审美才是教育的关键所在。
其次,改变以往认知的偏见是极为重要的,艺术作品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表现了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教育功能下,“成人思维”的普遍风行已悄无声息地压缩着少儿的书法创作的空间。家长普遍机械地认为:指导者的审美、指导是最正确的。如果我们仅从指导者的审美倾向去判断少儿书法创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减少这种偏激的认知,在正确的艺术思想的指引下,少儿书法创作才能日趋成熟,艺术也才会被阐释得愈加饱满而非更趋统一。牢牢地控制着少儿书法的风格、运笔、结字,这不仅限制着少儿书法的原生价值,也制约着少儿书法的创作活力。
再者,少儿可选择适合自己心智成长的临本。少儿书法创作之“真”是包含其自身审美认知。少儿对书法创作的认识与成人普遍感知的书法创作存在一定的差别。所以,一味学习唐楷又是不合时宜的。刘铁芳先生就有一席引人深思的话,他说:
如果说一个人初始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个体发展伊始,我们究竟要给个体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影响,以开启个体人生初始想象世界、打开自我生命的方式?[6]
笔者以为,少儿书法的创作思维是富有趣味性的。因此,将“成人思维”的创作模式套用至少儿书法创作,这不仅扼杀了少儿自我的思维,也容易导致少儿创作的庸俗化。当少儿在取得一定的基础之后,可适当学习一些碑刻书法,这些碑刻不仅有一定的法规,同时也综合了一定的趣味性,符合少儿思维中真趣的审美。或许,部分魏碑、大字摩崖石刻的范本在家长看来是粗俗的,甚至是荒诞的,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少儿的肯定。有趣的是,少儿在欣赏书作时,某些时候他们并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喜欢这件作品。这里,笔者以为,这类作品不仅表现了少儿的审美,亦传达了书法生命特征。在少儿自我的创作中,就绘画而言,往往带有更多的变形、夸张的成分。反观少儿书法的学习,笔者以为,碑版中部分字形的处理、结构的多样正符合少儿的创作思维。可以说,少儿书法创作的表现与部分碑版石刻的表现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生动活跃的思维习惯只能在恰当的自由氛围中存在。不加区别的书法法度更易使少儿的大脑变得麻木不仁。在书法一定法规的基础上,允许少儿选用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唯有如此,少儿才会对书法学习投入更大的热情。借苏霍姆林斯基所言以共勉:“我希望孩子们能成为这个世界中的旅行者、发现者和创造者。”[7]
结语
在当下的少儿书法教育中,指导者的“成人思维”往往附加于少儿书作之中,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应忽视少儿自我的审美认知。应该看到,少儿的思维方式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少儿书法创作之“真”,这不仅表现在其所特有的思维逻辑,也包含少儿书法创作中所特有的“真趣”审美观。在创作中,指导者如何平衡少儿书写规范与个体创作这两方面的关系,亦是当下书法教育的重中之重。“丑”“怪”也并非“真趣”等审美的特有标签。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理解指导者、少儿、书作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以个人喜好作为品评少儿书法优劣的唯一标准,选择适合少儿心性、思维的范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减缓当下少儿书法创作的尴尬境地。如果说交由少儿在创作中的自我探索是一种涉险,那么,缺乏少儿自我审美的书法创作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基于目标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