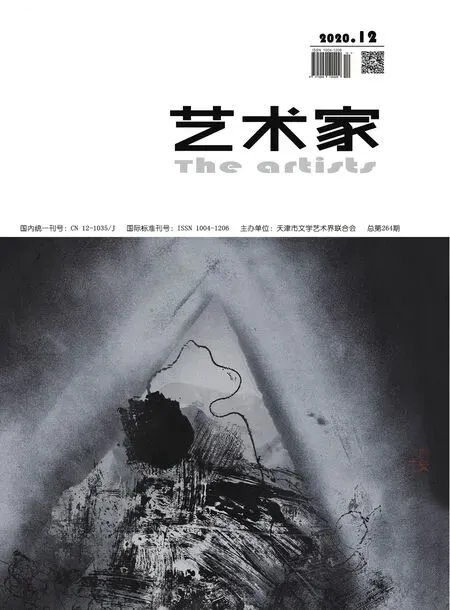浅析严歌苓笔下英雄的悲剧命运—以《雌性的草地》《芳华》《床畔》为例
□田佳平 江南大学
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严歌苓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体现着她的人生观、英雄观、价值观。她笔下的悲剧英雄大多被时代抛弃,其悲剧命运表现出的共性值得探讨。《雌性的草地》中的沈红霞、《芳华》中的刘峰以及《床畔》中的张谷雨,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悲剧英雄角色,通过分析他们悲剧命运的成因,可以窥见严歌苓对英雄的理解。一方面严歌苓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关照历史,创造的悲剧英雄群像彰显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另一方面在对英雄再书写的过程中,也进行着对自我创伤的疗愈。
一、英雄的悲剧命运
(一)绝对服从的英雄——沈红霞
《雌性的草地》中的人物以1976 年严歌苓采访的“女子牧马班”为创作原型,小说中一群年轻的姑娘被组织派往荒凉的西北草原,组成了一个神圣而庄严的集体——女子牧马班。沈红霞便是女子牧马班中的焦点人物。她意志坚强,吃苦耐劳,把集体荣誉看作第一位。面对组织交给的牧马任务,她绝对服从,即使腿瘸眼盲,也义无反顾。对信仰的崇拜甚至让她对马产生了“爱情”,在红马征召为军马的前夜悄然落泪。但这样的英雄最后的结局却是随着骑兵制度的消失,女子牧马班解散了,英雄在历史中无名,被人彻底遗忘。
(二)无私奉献的英雄——刘峰
在小说《芳华》中,刘峰是大家心中的雷锋。在文工团,他对待谁都有火一般的热情,帮助残障老百姓挑水,帮助女兵捎来家乡的信件和特产,帮要娶媳妇的马班长做沙发,帮被其他女兵嫌弃的小曼完成舞蹈中的托举动作……然而,因为向团里的舞蹈演员林丁丁表达了“爱意”,他被定性为流氓,站在批斗会上被迫说出最难听的话:“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这一英雄的结局是被下放到连队,在战场失去双臂,靠卖盗版书籍维持生计,在被批斗中被遗忘。
(三)英勇战斗的英雄——张谷雨
《床畔》中的张谷雨是一位被人民敬仰的革命英雄。在带领两个新兵排除哑炮的过程中,作为连长的他救了两个新兵,自己却被炸成了植物人,“进入了一种活烈士的状态”。起初,人们对他的崇拜是疯狂的。《床畔》中写道:“那时人们还把他的床摇起来,几乎摇成90 度,让他坐正,穿戴一新,让他们把军功章、纪念章、红纸花往胸口上别。”然而没过几年,人们渐渐忘却了他,就连主治医生都开始嫌弃他,只有护士万红对他心怀敬仰,坚持每日为他擦身、翻身,事无巨细地照料。英雄最悲惨的结局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不再被时代和人民需要,最终被无声地遗忘。
二、英雄悲剧命运的原因
(一)个体原因:英雄对自我悲剧命运的认同
古希腊悲剧命运观认为,命运是一种无法掌控和摆脱的力量,从俄狄浦斯王到阿喀琉斯,古希腊悲剧英雄明知自己的悲剧命运还要一步步走向最终的结局。笔者认为,沈红霞和刘峰这两个悲剧英雄对命运的态度与古希腊悲剧命运观有相通之处。他们提前感知到了自己的悲剧结局,却未积极反抗,而是顺从,甚至主动选择了悲剧结局。
队伍解散,知青返城,军马场也被移交地方,牧马班只剩下沈红霞一个人迟迟不肯离去。她想到的是集体荣誉:“我怎么能让一个社会渣滓,一个女罪犯逃避应有的下场,躲到我们这个光荣神圣的集体里呢?”革命理想的坚守,让她将自我置之度外。《芳华》中的刘峰在战场上身受重伤,却故意为搭救的士兵带错路,先为士兵们送去急缺的弹药和压缩饼干,最后差点因为耽误治疗而死。小说中这样写:“我也不知道,刘峰选择冒死帮驾驶员送给养弹药是源于他的高贵人格,还是他想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英雄面对生的希望却消极地放弃了生命,这是英雄主动选择了成全自己的悲剧命运。
由此可见,作为革命英雄的沈红霞和刘峰,在作出命运的选择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悲剧结局。他们丧失了对自我的个体意识,把革命理想的实现放在首位,认同了自我的悲剧结局。
(二)社会变革:英雄被新时代抛弃
俄国政治家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指出了伟人产生所需要的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时代的社会需要。第二,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1]可见,当英雄所具有的特性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英雄就会被社会所遗忘。
当时代需要宣传“无私奉献”“英勇战斗”时,他的护理员不仅要专业护理能力一流,连品德、身体、个人生活都要拔尖。然而,从秦政委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新时代不再需要“牺牲型”英雄。从前,他在报告大会上对张谷雨热情歌颂;几年后,又指出:“新时代的英雄,是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有起来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英雄张谷雨被时代抛弃了。
在《雌性的草地》中,女子牧马班的成立只源于部队首长的一句话:“有没有女娃敢放军马?!我看是有的。你们不信?我是信的。”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们来到荒凉的大草原,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开始牧马的生活。她们的脸上布满因常年风吹日晒形成的紫疤,穿的是不合身的军装,住的是随时都会迁徙的帐篷,每月配粮只够吃三天,连吃饱都成了一种奢侈。当地牧民还对她们图谋不轨,她们只好换上男装,伪装成叔叔,变成“非男非女”的人来吓跑牧民。但这样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却是彻底的遗忘。1985 年,骑兵制度被废除。女子牧马班自然也不再被需要。当牧马班解散的时候,被风沙消耗的青春都不存在任何意义。被时代所抛弃,被历史所遗忘,草原上的女英雄最后得到的只是无名的悲哀。
(三)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
对于个体来说,由于创伤的经验结构或接受和日常生活经验不同,创伤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而保留[2]。创作这些悲剧英雄的原因是严歌玲在童年时期和军旅时期的创伤记忆挥之不去。
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世家,但父母的感情并非和谐融洽。在她的记忆中,父母总是争吵不断,“离婚”是他们讨论最多的字眼。严歌苓几乎是在无人看管的状态下长大的,对爱情的怀疑在她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所以,当情窦初开的严歌苓遭遇失恋的打击时,感情的破碎似乎叠加了童年的隐痛。在《灰舞鞋》中,严歌苓以“穗子”的口吻讲述了爱人移情别恋对她造成的打击:绝望的穗子“从卫生室拿了三天的安眠药一次吞下去,以为自己从此不会醒来了”。此外,严歌苓的童年还目睹了太多死亡。在散文《自尽而未尽者》中,她写道:“自尽是我那单调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她在医院目睹了作家萌娘的自杀,也在大院中目睹过老夫妇跳楼。由于过早接触到鲜血的冰冷和死亡的残酷,严歌苓在潜意识里把死亡的悲剧性赋予笔下的人物。1970 年,12 岁的严歌苓因出色的舞蹈天赋被选入文工团,开始了军旅生活。舞蹈训练枯燥而无味,因为沉默寡言的性格,她常常独来独往,那时的生活是十分压抑的。直到严歌苓的第一部作品《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后,她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和热爱,并为之付出一生。
家庭记忆的隐痛、死亡的残酷、军旅时期的压抑生活,对严歌苓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心灵创伤和情绪创伤。所以,她笔下英雄的命运结局也是无力挣脱的悲情:张谷雨被世人所遗忘;刘峰的英雄称号也被时间抹去;沈红霞更是史上无名。
三、悲剧英雄群像在严歌苓小说中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对这三位英雄悲剧命运的剖析可知,他们的悲情结局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笔者认为,这些悲剧英雄在严歌苓创作的系列作品中有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有如下两点:
首先,严歌苓创作的悲剧英雄实际是对现实生活中英雄的歌颂和怀念。作者认为即使历史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作者的笔还可以记住他们。刘峰、张谷雨、沈红霞是英雄的代表,作者要纪念的远不止一个刘峰、一个张谷雨、一个沈红霞,而是千千万万已被历史遗忘的人,是对无名英雄的纪念和缅怀。
其次,英雄的悲剧命运更加凸显出了人性的美好可贵。严歌苓书写人性的执着来自她丰富的生命体验。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她过早看到了人性的复杂,这些创伤记忆都成为她今后的创作素材。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人性的扭曲和压抑,即使是英雄也无法在人性的丑恶下幸免于难。但是,严歌苓不是绝望的,她的心中还保留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关照历史,创造了一系列“地母”形象:王葡萄、少女小渔、护士万红,甚至是刘峰。“军旅题材”和“女性写作”在碰撞和结合中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张力和文学魅力。
结语
严歌苓对悲剧英雄的再创作体现了其面对创伤记忆进行的自我疗愈。童年目睹的荒诞异事,让她对人性有更深的体悟,军旅时期的训练更是磨炼了她的心志,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旅居各国,严歌苓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叙事视角从控诉批判转为审视剖析。在创造一系列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女性形象的过程中,严歌苓似乎找到了创伤疗愈的入口,那就是包容和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