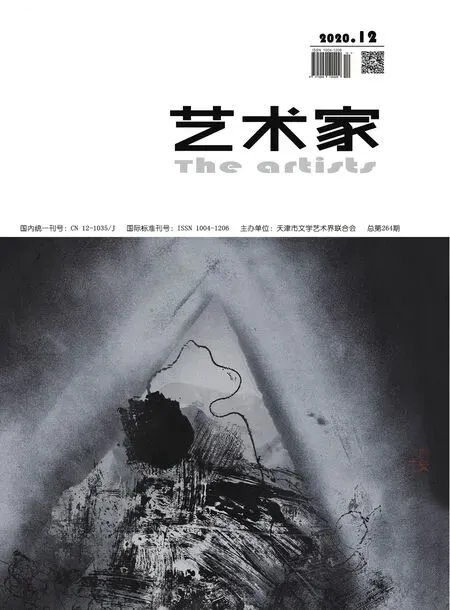再论萧友梅的“中西”音乐观及其“责任”问题
□徐金阳 岭南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不管是历史评论者,还是历史评论者的评论者,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是其根本任务。因为只有对历史做出中肯的评论,才能以史明鉴、服务当下。但历史评论是一个难题,因为评论本身不仅会受到史料完缺、真假的制约,还会受评论者本身价值观历史观制约。由于受限于这一难题,导致很多评论者在做历史评价时往往出现偏颇。笔者对萧友梅“中西音乐文化观”及其“责任”问题进行“再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一、“萧友梅中西音乐观评价”述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萧友梅在中国近代新音乐发展事业上所提出的“中西合璧、兼收并蓄”“借鉴西乐、改造旧乐、创造新乐”等音乐思想,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实践,都曾引起褒贬不一的评价。尽管这种持续至今的基于不同价值认识的评价,但“绝大多数论题上并非都以萧友梅为主要对象,但就其论争命题的深层次内涵而言,则无一不与萧友梅紧密相关。”[1]。褒之者主要着眼于萧友梅的音乐思想、音乐实践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开放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大背景下的大势所趋,并由此认为,萧友梅的音乐思想、音乐实践路径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贬之者主要着眼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政治需要及传统文化保护需要,认为萧友梅的音乐思想有“崇洋媚外”成分,音乐实践脱离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这直接导致我国现代音乐文化严重西化、传统音乐文化式微的局面,由此否定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和音乐实践。
当代学者中,对萧友梅功过评价视角较为新颖的有金桥博士,其在博士论文《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一书第三节“萧友梅本人的功过是非”的相关论述中,通过提出和解答“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等若干问题,对萧友梅一生事业功过作出了“萧友梅在音乐艺术诸多领域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要远远大于主观和客观因素所造成的消极作用……”这一较为中肯的评价[2]。就萧友梅音乐实践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及中西音乐文化关系的问题,金桥博士通过对萧友梅的言论如“采取其精英,剔去其渣滓,并且用新形式表出之……”、萧友梅对传统音乐研究改良社团如“国乐改进社”的支持等诸问题的讨论,得出了萧友梅对待传统音乐的态度是持发展的音乐观,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则体现出中西并重的特点。
其实,萧友梅在中西音乐文化关系上持何种态度,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角度看,都是无可厚非的。笔者提出“再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前对萧友梅评价的矛盾双方,贬之者说其全盘西化,对现代中国音乐文化领域“西方音乐话语霸权、传统音乐式微”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褒之者则说其虽中西并重,但客观上对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现象负有一定的责任。在笔者看来,无论褒者贬者,这两种态度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和音乐实践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西并重”,而是“厚西薄中”,但即便他不是“中西并重”,也无须为现代中国音乐文化领域的“西方音乐话语霸权、传统音乐式微”现象负责。
二、萧友梅的“厚西薄中”现象
(一)言论上
从萧友梅留下的有关中西音乐关系问题的主要论文如《中西音乐的比价研究》《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及《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重要的倾向性观点。
《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一文发表于1920 年10 月31 日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出版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8 号,是萧友梅向音乐研究者介绍“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包括教授法比较、乐谱比较、乐器比较、音阶比较四个部分。在介绍中国周朝“成均”乐官及音乐教育方法时,萧友梅认为,乐官没有眼睛,又不打拍子指挥,教学法很不精确,就是有再好的音乐也极容易失传;在评价中国传统记谱法时认为,即便中国有字谱,也只不过是记个大概,详细的地方还是需要人用听的方式学习,同一首乐曲不同的人演奏就会有不同的版本;在介绍乐器时,认为西洋乐器音域宽广,能演奏半音阶,而中国乐器音域窄,管乐器多半不能吹半音阶等。上述这些观点,明显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立场、以西方音乐文化体系为参照标准而作出的价值优劣评判。相反,如果站在多元文化、文化价值相对论立场来看待中国传统音乐的这些问题,那么,强调音乐听觉功能,重视听众内心感受,提倡一曲多变死曲活唱,追求五声音阶婉转清丽、中正平和等,就成了不可替代的民族特色。
《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一文发表于1934 年7 月15 日出版的音乐艺文社《音乐杂志》第3 期,是萧友梅对改造旧乐所发表的意见。文中萧友梅认为,西方音乐近千年来发达的原因有键乐器的发明、五线谱的发明、风琴师的固定职业、游吟诗人的兴起、贵族聘请作曲师的风气及音乐院的设立六个。与此对比,萧友梅认为中国唐朝前的音乐“自然是很幼稚”;隋唐时的音乐还是单音作曲没有进步,“让人失望”;明清时期还是单音音乐,于音乐本身没有改进;以前中国乐师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这些观点,出于萧友梅这样一个一心想发展中国音乐、盼望有朝一日能“与世界并驾齐驱”的爱国音乐家之口,让人有一种“爱之弥深,恨之愈切”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些比较,虽然在技术方法层面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从价值评价层面来看,却不能不说有失偏颇,这种偏颇的原因,正是萧友梅内心的厚西薄中。正因为厚西薄中,所以萧友梅常常不自觉地采取西方文化中心的立场,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土壤,以西方音乐的价值体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从而作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
《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发表于1938 年2 月1 日出版的《音乐月刊》第一卷第4 号,是萧友梅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何去何从问题的答刊物记者问。当记者问及复兴我国音乐,是否应全盘接受西方音乐,然后产生一种以我国精神为灵魂、以西洋技术为躯干的新音乐时,萧友梅认为,“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试验”。在回答中国音乐复兴的途径时,萧友梅认为,要取其精英,剔其渣滓,用新形式表现出来,“一切技术与工具须采用西方的,但必须保留其精神,方不至失去民族性”。萧友梅的这些观点中,指出新音乐要以我国精神为灵魂,要不失民族性,对待旧乐要取其精英,剔其糟粕等,无疑是正确的文化发展观,但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他却又不可避免地站到了西方文化中心的立场上,甚至提出“一切技术与工具须采用西方的”这种绝对的观点。其实,萧友梅在此不仅再次体现他的厚西薄中,也割裂了民族文化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民族精神或者民族性这种文化内容,很大程度是通过民族的形式来表现的,纯粹异质文化的形式不可能表现本位文化的内容。对于音乐而言,如果一部作品的创作和表演,一切技术和工具全部采用西方的,那必定成了西方的音乐作品,即便给它取上一个中国名字也是如此。
(二)课程上
从萧友梅在北大音乐传习所为甲、乙两种师范科设定的课表也可以看出他在专业教育上明显的厚西薄中倾向。1922年8 月19 日发布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了音乐传习所的一份公告,包括传习所简章和本年度秋季招生章程两个部分,在简章中就附有甲、乙两种师范科的课表。其中甲种师范科四年49 门课程,民族性的课程只有“词章”1 门,占比仅为2%;总157 学时,“词章”两年合4 学时,占比也仅为2%。乙种师范科两年24门课程,民族性课程只有“国文”1门,占比为4%;总74 学时,“国文”一年合2 学时,占比也只有2%。当然,萧友梅需要借鉴、也只能借鉴西方课程体系,这首先是由现实决定的,但如果不是厚西薄中的思想起指导作用,他完全可以开发更多与民族性相关的课程。事实上,萧友梅留学德国之日,正是民族乐派方兴未艾之时,比较音乐学也正在德国蓬勃发展,他本人的博士论文也是比较音乐学范畴的成果,因此他不可能不了解开设民族性课程或者比较音乐学课程对建设“国民乐派”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萧友梅音乐思想、音乐实践中体现的厚西薄中,在其他方面还有体现。例如,在他创作的一百多首(部)音乐作品中,只有《新霓裳羽衣舞》一部是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创作的,而其他作品全部是采用大小调式和古典和声技术。
三、萧友梅无须为“西方音乐话语霸权”和“传统音乐式微”负责
(一)萧友梅的“拿来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是时代的必然。萧友梅时代的主流社会思想,在中西关系上无论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吴稚晖等的“全盘西化”,章士钊等的“中西调和”,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些观点主观上都是出于民族振兴的目的,客观上都是认真对比了中西文化在制度、科学、技术及文化上的差异后各执一端的表达。各种观点尽管各有侧重,但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却保持着绝对的一致。社会实践甚至走在思想论争的前面,在思想界激烈争论中西关系的同时,学习西方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实践早已开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也好,“师夷长技以制夷”也罢,无论如何,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时代发展必然。
其次是现实的必然。萧友梅要开创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但正如他自己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没有专业音乐教育,甚至没有专业教育。借鉴历史上的成均、大司乐、太常寺、教坊、班社或者私塾,既无章法可循,又无现实基础。这种情况下,唯有学习西方现成的办学模式,才是便捷、可行和合时的方案。何况,高等专业教育、新式学堂、学堂乐歌等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蔚然成风,已经为引进西方专业音乐教育模式打下了社会基础。所以说,萧友梅的拿来主义,也是现实的必然。
最后是成长背景的使然。萧友梅5 岁时举家迁居澳门,受邻居葡萄牙传教士影响而喜欢上西洋风琴;8 岁时与孙中山先生成为邻居,其后成为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追随者;16岁时入广州第一所新式学校时敏学堂,接受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格致、算学、图画、唱歌、体操等西方式分科课程教育;18 岁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之后又在东京帝国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声乐,其后还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攻读教育学文凭,留日时间长达8 年;28 岁留学德国,先后在莱比锡皇家音乐院和莱比锡大学哲学科学习音乐和教育,留德时间长达7 年。从萧友梅这一成长经历来看,他所接受的几乎都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教育。所以,回国后的萧友梅厚西薄中,也是成长背景的使然。
(二)萧友梅偏重西乐是文化多元主义的题中之意
如果褪去萧友梅身上的光环,把他还原成一个普通的音乐家或者音乐教育工作者,那么他推崇西方音乐文化,拿来西式教育模式,就可以被理解为文化多元主义的行为。因为文化多元主义的题中之意就是承认文化的相对价值,就是认同多元文化并存,而且,始终不是站在本位文化立场上来谈论文化多元的。萧友梅虽然是中国人,虽然他更多地认同、实践和传播西方音乐文化,如同同时代大部分其他音乐工作者所做的那样,甚至他的厚西薄中还带有优劣价值评判,但无论如何,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的自由选择。所以,萧友梅无须为“西方音乐话语霸权”和“传统音乐式微”负责。
结语
最后,笔者再次重申,本文提出萧友梅在中西音乐观上存在明显的“厚西薄中”倾向,只是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尊重,绝对没有要贬低萧友梅历史地位的意思。笔者也提出,即便萧友梅厚西薄中,也无须为“西方音乐话语霸权”和“传统音乐式微”负责的观点,这也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出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尊重。毕竟,面对历史,我们首先要看到历史事实,但同时也要看到事实背后是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