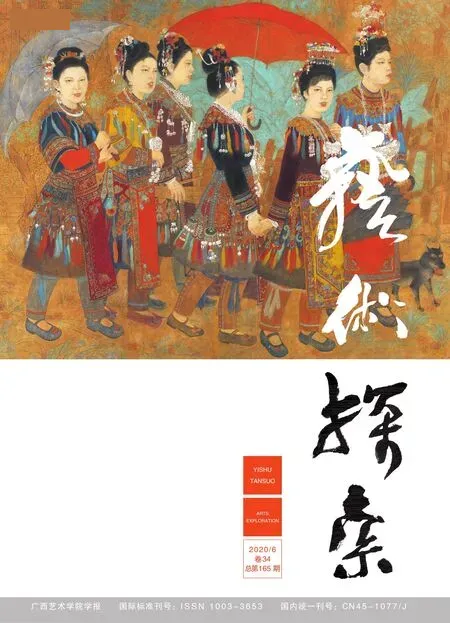身体叙事与意义构成:“圣母之舞”解析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0)
如何结合舞蹈去阐释社会文化一直是舞蹈研究的难题。《圣母之舞:新墨西哥托尔图加节庆中的身体与信仰》①Deidre Sklar.Dancing with the Virgin:Body and Faith in the Fiesta of Tortugan,New Mexico.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是一部关于身体和思想关系分析的舞蹈民族志,书中通过身体叙事(Body Narrative)的研究进路,强调舞蹈是人作用于身体感官的文化运动。作者黛德·斯科拉(Deidre Sklar)作为参与者、观察者和力行反思的女性舞者,融入当地人“共同神圣时光”的叙事体验,以扎实的民族志个案研究贡献了关于身体、思想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社会世界意义构成的新的理论思考。本文从该个案出发,结合对于其他学术著作的研读,讨论舞蹈民族志阐释社会意义的途径,希望能为舞蹈与人类学的结合带来一些新启示。
一、舞蹈民族志研究的探索
舞蹈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19 世纪末,有些学者用古典进化论理论范式分析和讨论世界各地的舞蹈,将舞蹈视为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例证,传播学派则把不同类型的舞蹈视为文化传播的结果。在摒弃了宏观臆测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具体社会中的舞蹈,或强调舞蹈在社会团结与凝聚、满足个体/群体的生理与心理需要方面的功能,或以舞蹈表现的二等分表象与二重性对立来展现无意识地进行两极对比的人类思维深层结构。然而,舞蹈作为人们的情绪情感和观念的重要感知、理解和表达的方式,如何使其成为对社会文化的分析、理解和阐释的有效研究路径,而不再被绕开去讨论与舞蹈相关的社会文化,成为此后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在这种背景下,舞蹈在特定社会中的文化象征意义表达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议题。
一批有过舞蹈训练体验然后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库拉斯(Gertrude Kurath)于20 世纪60 年代就开始倡导建立“舞蹈民族学”,并以“舞蹈民族志”作为实现这一人类学分支的进路和方法。她接受过舞蹈专业训练,认为舞蹈民族志应当包括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风格阐释、图形表示、舞蹈(基本动作、主题和舞式步伐)分析和综合研究、理论讨论与比较研究。[1]233—254凯普勒(Adrienne L.Kaeppler)通过微观和宏观角度的身体运动结构分析,说明汤加舞蹈与其背后的诗意隐喻之间的复杂关系。[2]173—217基里诺霍莫库(Joann W.Kealiinohomoku)通过对于霍皮人和夏威夷人舞蹈的比较研究,来讨论舞蹈美学、舞蹈与文化接触等问题。[3]429—450威廉姆斯(Drid Williams)则结合她在加纳等地进行的关于芭蕾舞演员、天主教牧师及修女等舞者群体的田野工作,探讨舞蹈研究中应用语意学(Semasiology)的理论与方法。[4]
然而,斯科拉在开始写作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对当时的舞蹈民族志研究并不满意。她认为,必须明确一个假设,即舞蹈民族志不但是建立在文化知识之上,也是体现在人体动作中的,应当将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知识加以考察。这样的认识也与她个人成长经历有关。斯科拉出生于美国纽约,成长在移民家庭,接受过十年之久的专业舞蹈训练,学习过鲁道夫·冯·拉班(Rudolf van Laban)动作记录分析法,后又从事舞蹈编导数年,对于舞蹈细节的感受十分敏感。她指出,舞蹈中的知识不仅是躯体的,也是精神的和情感的,包含着文化历史、信仰、价值和感觉。舞蹈民族志要描述有关社会价值、宗教信仰、象征符码和历史建构等地方场景性信息,以说明舞蹈的意义。舞蹈民族志不仅要以人们的活动为主题,更要认识和理解人们的运动方式及其缘由,运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舞蹈民族志必须基于身体和身体体验来进行探讨,从人体动作出发,采用拉班动作记录分析法、质性描述、录像来收集资料,并用理论框架来分析资料。[5]6—10在对民族志表述危机的反思之后,斯科拉强调对于细节的关注,既运用动作观察和技巧分析,又超越舞蹈具有社会文化关怀,对于舞蹈民族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重新审视身体时应当认识到身体是生命有机体,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身体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媒介,也是世界构成的实体。“当人类欲传达意义与情感时,人体是唾手可得的一项‘工具’,因此身体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亦即作为整体社会的展现。”[6]329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身体远远不止是叙事表征的一个不可抑制的个体‘他者’,它更是不断地被赋予意义,并被用作文本表征的一部分”[7]viii。斯科拉认为,“舞蹈民族志在众多民族志中是独特的,因为它必须植根于身体和身体的体验”[5]6—10,“具身/体现图式”作为一种在为人们提供感觉的身体和将表征概念化的领悟力之间进行调解的认知结构,能够将身体的体验和概念的经验组织一起,以避免精神和身体的二元分割。[8]91—92她对舞蹈民族志的思考也体现在了由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圣母之舞:新墨西哥托尔图加节庆中的身体与信仰》(以下简称《圣母之舞》)这一著作之中。
斯科拉的田野地点是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南部的拉斯克鲁塞斯(Las Cruces)的托尔图加镇(Tortuga),这里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西班牙人征服后将格兰河以北及以西之地都叫做墨西哥。美国接管后,在当地大规模种植棉花,大量移民蜂拥而至。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复杂性,此地居民混杂。多文化并置和话语权更迭使得当地社会趋于多元。西班牙通过战争和天主教,美国则是通过交通水利系统和工业化重塑了地景,也改变了当地人。
斯科拉以游记的方式将读者带入托尔图加的地理、历史和当下政治人文交织的关系中;深描了“瓜达卢佩(Guadalupe)”圣洁仪式的全过程;追溯了托尔图加小镇的变化,以寻求族群、社团、身体、表演和信仰问题的答案;此外还聚焦于“杂乱无序”的厨房和印第安女性的表述,勾勒出托尔图加社会意义构成的有序暗网,说明“异己者”如何通过身体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
二、仪式、族群与历史
“瓜达卢佩”早先是印第安人自然崇拜的节日活动,在多重合力下成为由天主教主导的歌颂圣母玛丽亚(Virgin Mary)恩典的圣洁仪式。节庆伊始,人们从德斯坎索营地(Casa de descanso)走到酋长所在地卡普拉(Capilla)后,抬着圣母像到达普韦布洛营地(Casa del Pueblo)。
圣母之舞开始时,在小提琴的伴奏下众人唱起献给圣母的赞美诗。舞蹈领袖莫纳卡(Monarca)和助手阿梅洛(Abuelo)指引18 位用印第安扎染印花手帕遮住面部的成年男舞者丹扎特(Danzantes)②根据斯科拉在《圣母之舞》中的描述,丹扎是圣母神授的印第安家族,丹扎特是丹扎家族的男性舞者。和9 位小女孩舞者马林切(Malinche)跳起了马林切—玛塔奇舞(Malinche-Matachine)。“竞赛般的玛塔奇舞蹈象征和隐喻着社团中印第安—西班牙(Indo-Hispano)关系的历史和特色。”[1]59马林切和阿梅洛走近莫纳卡时,队形改变,小提琴切换到另一个旋律,莫纳卡跳到舞场中间,在每一位丹扎特身边做按压动作,当莫纳卡转身时意味着信仰的转变,隐喻着印第安人从掌握话语权的原住民降格为天主教追随者。丹扎(Danza)指引着普韦布洛酋长洛瑞兹(Lorenzo)象征性地挥动着镐,丹扎特们重复着玛塔奇舞步连贯地绕出“8”字队形。“舞者用舞步雕刻出像摩尔人的(Moorish)绘画一样精美的花边式圆圈,就像西班牙基督教徒们踏着军事训练的步伐战胜了摩尔人(Moors),到达新世界。”[1]58仪式中人们以身体为叙事主体,完美地再现了历史与族群的复杂关系——西班牙军队沿着马林切提供的路线踏进托尔图加,马林切说服传说中的印第安蒙特祖玛君主改变信仰,为一个大国(阿兹特克)向一小支军队投降开辟了道路。征服者带来了玛塔奇舞,并通过墨西哥城的传教士和殖民者传播到印第安部落,现在雅基人(Yaquis)仍然称呼他们的舞者为“圣母的好士兵”。
“当舞蹈遭遇不同地方的现实(truths)时,就会被有强烈倾向的地方文化塑造。”[1]59在托尔图加普韦布洛人的历史传说中,“莫纳卡和马林切是关于对抗与转换的故事”[1]59,阿梅洛扮演一头公牛试图杀死马林切,莫纳卡在舞蹈结束前杀死了公牛。在当下仪式中,阿梅洛则化身为莫纳卡的助理,对抗的角色演变为信仰转换的推手,引导舞者变换队形,但人们还是用过去的名字称呼他。莫纳卡的扮演者里科(Rico)通过身体体验描述历史,他认为马林切举起手绕着莫纳卡转圈寓示着人们自愿付出,莫纳卡向下跪的人弯身是赐福,舞者服饰的不同部分涉及不同的人和故事。他所表达的不仅是记忆的口头言说,更是通过体感实践而引发的伴随着情绪情感的意义建构,这也是身体和象征两者之间关联的纽带。在社会情境的更迭中,仪式舞蹈的身体空间变化隐喻着社会意义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意义既通过集体性展演也通过个体体感实践实现正统化。
次日凌晨,信徒们在战争首领的指引下分男女两队赴托尔图加山朝圣,有光着脚的女人,也有背着婴孩的父亲。信徒们认为朝圣并非一般意义的行走,是“注入了思想的行动”[1]106,相信通过身体的磨练才能铭记圣母的恩泽。此刻,身体成为形塑记忆的媒介,进行圣洁仪式的载体。从人烟密集的生活场所到托尔图加山的空间转换隐喻着边缘和中心的空间划分所形成的信仰秩序,大山与城镇因朝圣被紧密联系起来,人们通过肉身在地理空间中的移动再现了历史记忆和实现了信仰实践的升华,并建构精神意涵,再生产符合当下环境的社会意义。
历史不但在地理空间的位移中被表述,也在族群的身体空间区隔中被再现。欢迎朝圣的队伍有丹扎家族舞蹈组、印第安舞蹈组和早先从墨西哥过来的阿兹特克(Azteca)舞蹈组。教堂认为阿兹特克们的表演和小丑舞蹈不够庄重,拒绝其加入到最后的游行仪式中。仪式期间,丹扎成员受到信徒家庭热情招待,而印第安舞者只能蜷缩在屋外空地上过夜。身体空间再现了社会空间的区隔。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在朝圣仪式中唤起不同的感官记忆,仪式场域中处于边缘状态的族群对该社会的功能被削弱,这种被“边缘化”的“仪式性”行为是通过身体被安排在不同场所来实现的。如果说朝圣是用身体的时空移动建构精神空间的意涵,那么对于不同族群的差别对待则通过身体在场所空间的区隔建构了社会空间。
第三天的弥撒是圣母仪式的最高潮,人们用印第安式的狂欢表达对圣母的忠诚,普韦布洛的古老歌曲在教堂弥撒中变成了歌颂圣母的诗,尽管唱词和旋律依旧,但已经没有人知道原本的意思。招待会标志着节庆的结束,随后是一场非正式的舞会。喝完威士忌的人们乱作一团,现场充斥着令人头晕的笑话和豪笑声,年长者跳马林切少女舞,女人跳丹扎特舞,少年装扮成足够老的战争首领跳舞,丹扎特跳印第安土著舞。人们在歌舞喧闹中尽情释放自我,仪式中强调的区隔被打破,身体表达了对彼此的接纳。形象、音声、谈话一同建构出社会世界的意义,贯穿在一个连续的仪式中,仪式反过来又加深自身意义的复杂性。“方济会修士贾尔斯(Giles)神父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告诉人们,这种彻夜狂欢的传统不是来自墨西哥,而是来自本土印第安。”[1]46—47
宗教权威和本土文化的调和通过仪式再现。狂欢是身体空间区隔的打破和精神空间的消解。放松的身体在共同场所中互动,弥合仪式产生的社会空间边界。人们从秩序严谨的仪式走出,通过身体表达文化的杂糅和释放情绪情感。狂欢的舞蹈像多文化共存的马赛克,打破了仪式中界限分明的社会空间秩序和文化空间边界,身体的互动淡化了社团中不同族群的等级差异,具象地呈现出现实世俗社会的交融,共享了社会世界的意义,是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真实写照。
在历史线索的交织中,舞蹈的身体是作用于人的多感官的文化运动,也是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实践民间仪式的方式之一。“舞蹈身体是社会秩序的表现。”[6]330仪式舞蹈中的身体建构了历史记忆的理想型模式,族群通过作为表征的仪式舞蹈建构当下的社会世界意义。互为交往对象的个体通过身体行为本身的感知,形成了指涉性关联的社会关系。当今的人们依托地景的历史叙事与前人世界联系在一起,借用舞蹈的身体表达仪式情境中的话语权。
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认为仪式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特别是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的过渡。[9]2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仪式中的狂欢是社会结构的反结构,是身份过渡的非乙非甲阶段。[10]在托尔图加族群混杂的社会中,圣母节庆仪式并非简单强调个体从一种身份过渡到另一种身份,而是对于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的再梳理,更多地是对既有社会等级秩序的巩固。斯科拉在该书中以仪式为切入点,聚焦身体化的仪式过程,深描作为主体的身体如何贯穿于整个仪式意义建构的过程,并如何通过身体空间的转换来呈现文本与历史言说的社会意义和族群间社会空间的区分。
三、社团、社会与认同
每年自11 月起,人们就开始忙着筹备节日。妇女制作食物、清洁和装饰建筑,男人为朝圣规划路线和收集供给,大多数共同参与的工作在厨房进行。男人洗盘子,女人切洋葱,偶尔男人也帮着切洋葱。女人们围着圆形案台,通过细微的身体动作和简洁的话语相互交流,用小而精确的手部动作处理食物。厨房模式像一段自发性的临时编排的后现代舞蹈,参与者默契的配合被任意的安排和互换。在这个意义共享的空间里,每一个环节的工作是一个肢体表演到下一个肢体表演的重复。如同教堂礼拜和托尔图加山朝圣一样,人们在厨房通过身体劳作表达对圣母的忠诚,是为圣母奉献的一种方式。所有的日常杂事围绕着圣母节庆,也使得节庆成为可能的社会网络。身体使信仰具象化,为信仰服务的劳作再生产的信念又通过劳作表达。
厨房间的身体劳作深化为责任,为社群(Community)间融合提供了可能。在规模比家庭和虚拟亲属关系群体(Compadrazgo)更大的网络中,义务服务促进了社团(Corporation)的情感凝聚,也强化了这种交换的动力场(Dynamic Field)的社会秩序,使社团更广泛深刻的存在。在托尔图加的圣母节庆中,社团的维系依赖于仪式中身体实践的个人行为自治与放弃履行原社群责任之间达成平衡,义务劳作也是忠于社团的具化在身体行动中的文化认同表达。一位妇女告诉斯科拉,因为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在厨房服务,她被排挤在社团外。厨房工作和教养孩子一样是一种微妙的抗拒同化的文化延续形式。在教堂里精神成就了肉体,此刻厨房中身体成就了精神。“厨房编排了适合社会的舞蹈”[1]82,是社团得以维持的深层社会空间和公开场所看不见的后台领域(Backstage Area)[11]112。如果说仪式是构建社团共同体的明网,那么负责后勤服务工作的厨房则是联结托尔图加社会的暗网。
人与周遭世界互动中,身体多感官的实践构成了社会世界的意义,人们之间的连接是精神的也是社会的。规模大的社团吸纳着人们来劳作,当地生意人和政客发现有利可图而捐赠食物和钱财以支持社团,并在节庆活动中露面,积攒象征资本。社团整合不同背景的人,兼容不同文化,构建更大的社会网络,拓宽人们的交往领域。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被联系起来,一同参与娱乐和宗教活动,交换工作、生活和政府施政信息。这些附着了文化模板的交换关系维持着社团,并在年复一年的神圣和世俗仪式中重复运转。圣母和神授家族的叙述赋予托尔图加天主教社团以特征,他们的故事在不同情境中被有选择地呈现,成为连接社群网络和形塑信徒思想的工具。比这个社会网络更为复杂的是,有着不同于“前人世界”的个体在天主教社团架构的离合交融的社会结构下不断抗争和调整自己。
20 世纪40 年代末,印第安血统问题和社团“印第安性(Indio-ness)”的分裂引发了托尔图加较大的社会动荡。天主教的传入影响了普韦布洛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印第安人”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指。米瑞雅(Mireya)是印第安原住民,她和酋长洛瑞兹家族都来自埃尔帕索北部(EL Paso del Norte)。当抬着圣母像的队伍经过时,大多数人畏惧地低下了头,而米瑞雅高昂着头朝着托尔图加山歌唱。米瑞雅说,印第安人不知道何为上帝,只知道与大自然对话,她不为圣母玛丽亚,而是为天空和大山歌唱。“身体是自我展演的载体,也是通过减损仪式而进行社会排除的目标。”[12]62那些转换信仰的印第安原住民不理解米瑞雅的行为,指责她和她的姐妹跳印第安舞而不去教堂礼拜和参加厨房服务。社团成员视米瑞雅家庭为“异己者”,给她们扣上 “虚假的印第安人”的污名,并在生活中与她们保持一定距离。米瑞雅对这些批评不予理睬,她坚持自己的喜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与别人保持不同,使得她有可能继续保持文化自觉。身体作为自我与世界区别与联系的桥梁,用无声的肢体语言表达着对文化的排斥或认同。“异己者”的身份恰恰折射出普韦布洛社会的意义变迁。
身体是意识在心理层面运作的条件,体验、表达和理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民族志研究中,个体感受的表达和体验应当建立在对于个体自身的熟悉之上,在对于个体自我的持续关怀中利用自我参照的维度。[12]59—60厨房里,洛瑞兹的妹妹伊莎贝拉(Isabel)紧挨在斯科拉旁边,她用手指着自己的女性私处,充满鄙夷地说,裸体跳舞和相信“万物有灵”是异教徒印第安人的特征,不代表选择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她把自己和那些她称之为异教徒(Paganisto)的印第安人区分开,不希望普韦布洛与墨西哥印第安人有关联,并认为传教士的到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感觉在教堂里像在家里一样。洛瑞兹不认同妹妹的说法,他认为伊莎贝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祖先住在墨西哥。米瑞雅则并不乐意看到教堂对“瓜达卢佩日”的影响,因为圣母来了,大自然之神就会离开。米瑞雅的印第安气质是前西班牙统治时期族群特质的延续,而伊莎贝拉在西班牙人的引导下已经改变,但她俩都是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去理解印第安人身份的,只不过选择了不同的信仰和实践方式。而同为印第安原住民的劳尔(Rual)却认为跳印第安舞和做弥撒没有不同,都是为了信仰,劳尔的这个观点是对在历史上经历过两种信仰转换的社团认同的整合。同一族群中的文化认同所依托的不仅是具体的人,还有群体中某一成员与其他人共同具备的特质。在交融互涉的社会关系中,每一方都是以想象的类型来理解另一方,并都能察觉到这种相互理解,同时期待他人解释世界的“语法”和自己是一致的。
对米瑞雅、伊莎贝拉和洛瑞兹来说,普韦布洛的历史是一个家族的传记,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它几乎可以说是族群传记的一部分。认同的结构建立在真实生活和想象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在仪式中的动作细节恰恰是仪式实践者社会文化认同的身体呈现。伊莎贝拉严肃地提醒别人绝不能背对着圣母像跳舞,可是在印第安鼓点声中,她情不自禁地就忘记自己所说的禁忌,背对着圣母像而舞了。音乐响起时,米瑞雅腰背挺拔、舞步刚劲,而洛瑞兹则目光低垂、姿态谦卑。如果说米瑞雅的文化认同是显性的表征,那么伊莎贝拉的则是隐性的“惯习”③“惯习”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中的四个关键词之一。,惯习使然的肢体动作代替了认同之争。在古老印第安鼓点中释放情绪情感和在天主教社团架构下的井然有序,二者并不是“身心二元”的对立存在。身体诠释着社会世界意义的同时进行着自我表演,这种表演随场景改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身体感受。尽管信仰规约着人的思想,但在特定情境中身体的表达是真实的,就如休息放松时低头坐着的丹扎舞者和一个站着的酋长,他们的身体姿态与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隐喻着社会关系的等级差序。
人是社会世界意义构成的实体,人的社会类型化是以行动过程为基础的,个体互涉的社会行为产生了意义。传统宏观社会学认为社会自成一体,文化仅作为功能附着在社会结构中,认同也只是依赖记忆的连贯性的存在。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身体—权力—社会的关系论,打破了这种重灵轻肉的偏见。[13]舒茨(Alfred Schutz)认为,“社会世界中所有复杂的现象固然都有意义,但这些意义都是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连结于其行动之上的。只有个体的行为及意向意义是可理解的,只有从对个体行动的诠释入手,社会科学才能够获得诠释那个社会关系与社会构作物的管道,而后者正是在社会世界的个别行动者之行动中建构出来的”[14]7。
托尔图加社会世界意义的形成,部分通过世系群体,大部分则是通过个体明确的选择。“‘国家’只是一些共同世界人的理念型的高度复杂网络的一个缩影。”④原文如此。见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xxxvii 页。在国家在场和宗教社团的作用力下,仪式规训着不同人的身体来建构相同意义的信仰。在不同情境中,个体的片段可以反映出社会世界的意义脉络。人们在通过文本言说历史、区分彼此、表达认同的同时,也通过身体具象表达对族群、族际、社团和主权国家的区分和认同。在身体力行的参与中,人们才能够成为族群或社团统一概念中的一员,这个概念不是其自身的统一,而是对共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紧张或友好关系的呼应。
四、意义的绵延
当印第安人最初到达拉斯克鲁塞斯的时候,只有印第安酋长部落成员朝圣托尔图加山,表达对自然的崇拜。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韦布洛原有的社会结构瓦解了,印第安原住民和当地教堂关系缓和,越来越多的人朝圣,朝圣的意义也从原来的自然崇拜转化为感恩圣母。1872 年前,“瓜达卢佩”节庆仪式为期9 天,由一系列交易集会和歌舞狂欢等艺术活动组成。当地政府认为长时间群体聚集不利于治安管理,从1904 年开始节庆活动被缩短至3 天,并改为由天主教社团主导,传统的9个神秘故事也被压缩在一个晚上讲完。
仪式的社会意义通过身份秩序的改变得以再生产。战争首领原是普韦布洛勇士社会中和平仪式的祈祷者,现在转变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净化天主教社团成员道德的权威,手执柳鞭象征性地鞭挞那些“犯错误”的信徒,成为朝圣的守护者。如今天主教成了当地人的信仰,但普韦布洛古老的宇宙观仍然表现在托尔图加朝圣中,并通过战争首领的角色将具有天主教意义的朝圣活动环节串联起来。
在人们的认知转变中,个体发挥能动性在原有资源基础上进行了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再创造,并通过个体具象化的行为得以表现。米瑞雅的缝纫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出自她手的缀满骨头、珠子、丝带和羽毛的三色布舞衣充满着印第安宇宙观的气息,成为男人们参加仪式的首选,现在当地几乎每个男人都穿着这款衬衫。
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倡导者沃特金斯(John W.N.Watkins)强调,所有复杂的社会情境、制度与重大事件,都是出自于个体、个体的倾向、处境、信念、物质资源与环境所形成的特定结构。[15]104—117米瑞雅回忆,在她小时候,“瓜达卢佩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比圣诞节还要隆重。每年她的妈妈都会为她们做新衣服。那时这种大型聚会对于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很美妙,他们并不在意是否跳印第安舞。人们在集市上购买墨西哥的陶器和小饰品,品尝在家从未吃过的食物。米瑞雅13 岁时,她的父母在政府施压下将她送进了教会学校,但她认为自己在学校并没有比在家里学到更多的知识,她的祖母教会了她很多东西,特别是印第安人的自然观。虽然时过境迁,但人们依旧期待“瓜达卢佩日”,许多人仍在为这个节日缝制新衣服,购买新东西。现代化设施改变了托尔图加村庄的生活方式,村里安装了自来水和污水管道,天然气取代了木头做燃料。从某种角度看村民的生活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但对普韦布洛后代来说却是令人惆怅的,大汇演和传统集市消失了,印第安家族从埃尔帕索北部带过来的表演传统因为新的社团规划而被强制禁止,社团中绝大多数人不再宣称自己的普韦布洛世系。人们在每一次活动中回忆往事,再生产“瓜达卢佩”圣洁仪式的意义,建构新的关系意涵。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忽略眼前的事实,紧抱着过去的影像不放,对一个群体的认知总是会将其特征化,绝少聚焦于具体存在的个人。从想象的类型化的世界过渡到面对面的世界,个体的意识体验在不断地变化。随着经验的增长,有可能用新的角度去看事物,那个别人眼中类型化的“他”已经变成了不同的人。米瑞雅曾经爬上屋顶,敲响印第安鼓,邀请邻里共舞。那时邻居们听到召唤会出来跳舞。现在当米瑞雅敲鼓时,邻居会探出头来,抱怨她是吵闹的印第安人。1984 年,普韦布洛族长老们和天主教人士踩着印第安鼓点跳玛塔奇舞,友好地比赛,米瑞雅和族长共舞,她的妹妹和洛瑞兹酋长共舞,这也是斯科拉唯一一次看到丹扎和非社团成员的印第安人同台而舞。几年后,斯科拉再一次来到托尔图加时,米瑞雅已经加入义务服务工作行列,玛塔奇舞又回到很久以前的形式。
“贾尔斯神父鼓励人们言说自己的印第安特征,同时也给这些特征赋予了天主教意义。”[1]164被建构出来的社会世界意义在个体构想的行动中绵延不断,在“后人世界”中完全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长老们吩咐洛瑞兹要“不断改变事物”,这就促成了他创编托尔图加特有的普韦布洛巴利拉舞的壮举,通过在舞蹈编排和造型上的创新,洛瑞兹成功地将普韦布洛的四次重大历史事件编进了四个方向的队形转换中,舞者们随音乐集体起舞,基本节奏与印第安舞蹈相同,但有别于后者的成双成对。舞蹈体现着蒙太奇般的历史和记忆交织的层次性,不同历史和意义的片段在集体展演中闪现出来,通过个体的身体叙事表达出普韦布洛的意义。普韦布洛的节奏仍在鼓声中绵延,舞者们仍在进行四个方向的队形转换,但下一代的孩子们却穿着软底鞋和运动服踏进了教会学校。
12 月12 日是圣母节庆的最后一天,集体游行和广场展演是节庆活动的高峰,社团群体的集体游行于早上9 点开始,然而一支自发组织的队伍8 点左右已经在普韦布洛营地门口汇集,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当天游行活动。后台的厨房工作持续重复,人们聚集在教堂里举行盛大的弥撒,四个舞蹈组集体共舞。可以说,圣母节庆是不同的文化层和历史脉络通过身体叙事相互渗透交织。这一天加入了地方长官的就职仪式,本来随意的民间自发性活动在仪式内容的置换中转变了原有的意涵。即将离任和即将上任的长官们坐在前排,牧师递给离任者和继任者各一支蜡烛,主教向来宾介绍未来的长官,继任者点燃蜡烛,离任者熄灭蜡烛,众人鼓掌,官方行政交接仪式完成。[1]161—162社会阶序再一次通过身体叙事得到完美的体现。
在特定的场景中,民间仪式积极地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时常带有一定程度的排他主义,从而有了差序之分。社团反对外部人从圣母活动中获益,强调对于内部的控制。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节庆活动本身是建立在选择之上的一个抵抗的形式。一些社团成员希望有部落自治权,想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不想屈于任何人之下。另一些成员认为,和政府没有联系会感觉很孤单。官方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和天主教社团成员的不同历史言说版本交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托尔图加社会意义脉络。在社会之网中,族群作为历史材料存在被碎片化,政治权力介入其中的重叠交错的社会关系,在多种文化交错盘结所形成的张力作用下,通过理念化的仪式过程,构成并延续社会世界的意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团力量的作用下被间离,在主权政治社会的大结构下,生活的细节则被一个假设共享的诠释世界的模式取代。人们单纯地希望圣母节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但是主权政治作用之下的民间仪式裹挟着混杂的历史和差异性,推动着社会永无停止的运动,构成了社会世界意义的绵延不绝。
结语
从“瓜达卢佩”仪式个案及其解析中,我们看到,斯科拉从反思性、文化敏感性、知识传授、民族主义、社会伦理、个体和群体身份、表演和表征等问题入手,以反身性的视角参与托尔图加圣母节庆仪式,深究文化如何通过身体运动被编码,并通过对于相关社会文化和政治场景的理解,深描其舞蹈动作背后的意义。“对每一传统的研究,应是历史的、相对的、动态的”。[16]34卡伦·巴布尔(Karen Barbour)指出:“舞蹈研究者认识到,无论是舞蹈编舞、表演研究,还是正规教育或社群背景下的舞蹈教学,创造性的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的参与。”[17]1-4
因此,我们应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基于舞蹈进而超越舞蹈,呈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关系、环境、宗教、美学、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语境中感知舞蹈,通过舞蹈的细节呈现复杂的和变化的文化社会意义的建构过程,这样舞蹈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对于社会文化的观察、认识和理解的重要角度。舞蹈研究的视野因此而得到开拓,社会科学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视角。
——战斗的圣母人
——太阳是如何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