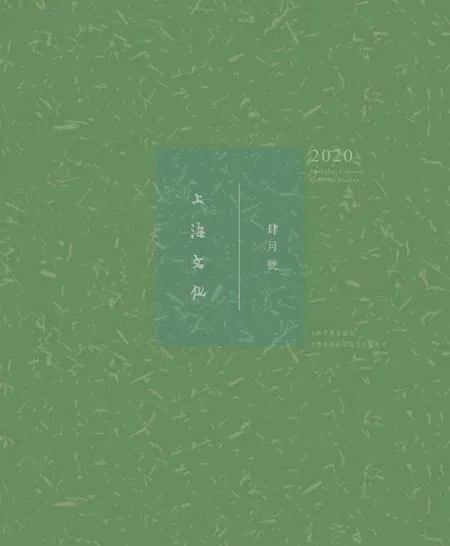生命美学的新境界
——评潘知常新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
范 藻
引言:美学的生命之爱
2017年,是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美学命题100周年。百年以来,回应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美学命题的论文不在少数。但是,以一部50万言的专著去加以回应的,在学术界应该还是第一次。
无疑,这肯定不是潘知常教授的率意之举。
早在2015年,潘知常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一文分为上中下3篇,约5万字,曾在《上海文化》2015年8、10、12期陆续刊出,并且引起较大反响。由此发端,潘知常将论文进而扩展而为50万字的鸿篇巨制,并且集中于与蔡元培先生的对话这一焦点。蔡元培先生提出的这一美学命题,堪称20世纪中国的第一美学命题,尽管不无偏颇,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审美救赎”的思想却是与世界美学同步的,所提出的美学方案,更是无论如何都十分值得关注。
一、“上帝死了”,虚无主义的肆虐
虚无主义的肆虐,是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新著所关注的思想背景。
在19世纪末,尼采这位以反叛著称的文化“独行侠”发出了“上帝死了”的惊呼:“上帝到哪儿去了?让我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①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人类自古希腊以来建立起来的“理想国”遭到了这个“疯子”的彻底摧毁。没有了上帝存在的人类社会,犹如失去了航向的轮船,随风漂流。毋庸讳言,世界进入了没有神圣的“群魔乱舞”和漠视律令的“江湖盛行”的时代,虚无主义肆虐的时代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之夜的贫困时代已够漫长。既已漫长必会达至夜半。夜到半夜也就是最大的时代贫困。”②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毫无疑问,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忽视,都不但会彻底阻断人类通向彼岸的道路,掏空数千年人类文明积累的价值,而且会导致生命存在意义的阙如,精神的人类必将蜕变成物质的人类。
“从表面上看,没有了上帝作为总裁判,真理的裁决就不得不由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空空如也的人们也有可能自己为自己去选择一种本质、一种阐释,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机会,然而,实际上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痛苦:因为失去了标准,因此所有的选择实际上也都是无可选择。”③潘知常:《“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美学困局》,《中州学刊》2018年第2期。潘知常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里再一次指出:“人类的日常生活已经在‘非如此不可’的‘轻松’中日益蜕化,也已经日趋空虚和无意义,最终,难免正如鲁迅所料定的:我们失掉了好地狱!它预示着一个漫长的意义匮乏时代的开始。”④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15页。
在古老的中国也是如此。在西方携带现代文明的“声光电化”进入20世纪的同时,古老的中国却在19世纪中叶遭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处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在历经洋务派李鸿章的实业救国、维新派康有为的改良救国、革命派孙中山的起义救国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终于发现问题的症结,但却开出了一个“不识时务”的药方:“以美育代宗教”。他认为美育“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⑤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2页。蔡氏心目中的美育实为康德的“纯粹美”的变体,立足于破除异端邪说和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而着眼于人的灵魂净化和情感美化,遗憾的是,蔡先生开出的,仍旧不是正确的药方。因为,在一个没有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度,关键的关键其实并非美育代宗教,而是通过美育开辟出通向灵魂的终极关怀和走向信仰的审美救赎的道路。
对此,潘知常在《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⑥潘知常:《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以美育代宗教”“本质上就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2017年他又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说不尽的百年第一美学命题——纪念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一百年》,直陈“其中根本的美学缺陷,美学失误”,而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的新著中,他更是详细予以阐述,揭示“在这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美学与宗教问题的无知,又反而被作为某种无可质疑的前提而在继之的美学进程中予以盲目认同,由此,导致了中国美学的现代思考的百年困顿,更导致了进入‘无神的时代’之后面对‘无神的信仰’的美学思考中的百年谜局”。①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11、24、31页。
具体来看,问题有三:
第一,就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存在。尽管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讲,不存在所谓的“彼岸”和“天堂”,但是从人类生存的意义看,生命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有精神存在就有精神活动,有精神活动就有意义诉求,有意义诉求就一定有灵魂世界,而这个灵魂世界的宽度和深度、厚度和高度,就决定着每一个普通生命。那么如何适应并战胜自然的法则而获得永恒?这正如潘知常多次阐述的:“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不能拒绝神性。”
第二,就是如何看待超越宗教的信仰。有宗教一定有信仰,但信仰不一定都隶属于宗教,信仰是一个大于宗教的概念,它广泛地存在于科学的求真、伦理的求善以及美学的审美等领域,德国哲学家沃尔特·考夫曼指出:“一种强烈的信念,通常表现为对缺乏足够证据的、不能说服每一个理性人的事物的固执信任。”但是,由于蔡元培执着于此岸的社会而放逐了彼岸的世界,他的美育救国理念当然会剔除宗教,同时也剔除了信仰。可是,这一切又如何可能?潘知常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只有灵魂(信仰)是在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之上的,它是对于一种价值的持守与践履,也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更是人类真正的觉悟。通过它对于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超越,人类表达了自己超越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愿望。因此,体验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结果,应该是更爱人类,应该是更充满了人所特有的欢乐与喜悦,否则,承担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动力何在?”②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11、24、31页。
第三,就是如何看待借助信仰的救赎。由于坚信信仰的力量,就必然导致救赎的出场,因为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人类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无限的未来,但现实依然是残酷而荒谬的,水深火热的人类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历经生活的悲欢离合,就像浮士德一一经历了爱情、学问、事业、政治的悲剧体验后,发现物质的享乐是短暂的,制度的维系是人为的,唯有精神的追求才赋予生命真正价值,而信仰的坚守又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因沉沦而走向信仰,因信仰而获得救赎,这正是潘知常对“审美救赎”中包含的全新价值的积极发现,就是“从全新的灵魂重建这一角度来看,在蔡元培所提出的美学方案中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过去却长期被我们忽略并且搁置起来,这就是:审美救赎”。③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11、24、31页。这,就是潘知常为“审美救赎”赋予的审美意义。
二、“无宗教而有信仰”,中国文化的启迪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但是在古老的中国又何尝有过真正的宗教?这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尽管历史上有过崇尚自然的道教、完善自我的儒教和注重心性的禅宗,但严格地说,由于它们仅有现实关怀而没有终极关怀、仅有超脱心理而没有超越意识、仅有鬼神观念而没有神圣信仰……总之,都不具备罗素在《宗教与科学》著作里总结的“教会”“教义”和“个人道德法规”这宗教三要素。但是,没有真正的宗教却并不等于就没有真正的信仰,例如,在儒家,秉持“仁者爱人”的理念,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就反复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回答弟子的疑问中,《论语·阳货》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论语·子路》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泰伯》中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此,潘知常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救世方案’和‘救心方案’”,他激赏道:
“以仁为本”作为“人是目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关于人之为人的绝对性原则的觉醒,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选择”意识,也恰恰意味着中华民族自身的“自由意志”原则的滥觞。人们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推动着人类自身从匍匐状态昂首站立起来的,是三次伟大的革命,它们分别是由孔子、释迦牟尼与耶稣借助于“仁爱”“慈悲”与“博爱”来完成的。而今,我们不得不说,确实如此!①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256、259页。
由此,立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潘知常揭示出“无宗教而信仰”这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并且由“无宗教而有信仰”推及“无宗教而有道德”“无宗教而有审美”。②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256、259页。
必须看到,若要理解“无宗教而有信仰”的中国文化,关键是如何理解其中的“信仰”。
如前所述,信仰是一种超越理智、悬置事实和不计功利的意义追求,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一种不讲理性的判断,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一场淡化目标的付出,其表现就是“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超功利选择。那么,其中的核心何在?在潘知常看来,无疑正是“无缘无故”的爱。正如生命美学一直强调的,只有学会了爱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完成了人与动物的最后告别,也才是马克思所期待的:“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不难看出,要证明你“是一个人”,就必须有在“以心交心”的信任基础上形成的“爱”,尽管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爱却是万万不能的。
由此相应,潘知常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的新著中通过对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这个“未完成的百年话题”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乃至生命美学,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爱”!对此,潘知常一如既往,无限深情地称之为: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指向的是世间唯有人自身才去孜孜以求的问题,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需求,指向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例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以及人类希望什么、人类将走向何处之类从人是目的出发而导致的意义困惑。总之,它是人类一旦为自身赋予无限意义之时就会出现的对于这无限意义的再阐释与再解读。①潘知常:《审美救赎:作为终极关怀的审美与艺术——纪念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美学命题一百周年》,《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无疑,这里的终极关怀绝不是来世的许诺,而是今生的兑现,更不是虚无缥缈的一张“口头支票”,而是以“爱”作为起点、也作为终点,贯穿于整个生命的旅程。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沈从文所殷切期待的“希腊小庙”。因爱而生命、因生命而爱与生命即爱、爱即生命,“我爱故我在”。由此,他一针见血地质问“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并且毫不留情地展开了对“无爱”和“失爱”的《三国演义》、“赢者通吃”的《水浒传》、“逃避自由”的《西游记》的美学批判,并且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学里,有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现世关怀”,而高度缺乏人与自我灵魂维度的“终极关怀”。同时,潘知常又指出:《红楼梦》的贡献巨大,“从‘仁之始’转向了‘情之始’(爱之始),并且希冀由此出发,去重新解释中国文化,重新演绎全新的中国文化精神乃至中国美学。而且,这情本体、爱本体意在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领悟无限’,由此,《红楼梦》开始寻找到‘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这就是终极关怀”。②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504、504页。因此,“用爱来交换爱”,这正是曹雪芹伟大之所在。
也因此,潘知常在新著中指出:“用爱来交换爱”,理应成为当代生命美学的神圣使命。它的最高境界是“为爱而爱”的终极关怀。因此,中国当代美学亟待完成的正是生命的华丽转身——“用爱获得世界”。
三、结语:从“以美育代宗教”到“审美救赎”
综上所述,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新著的最后一章“中国的救赎”也就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潘知常所开列的“审美救赎药方”,而且更可视为对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美学命题的一个回应。源自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哲学观,经过潘知常的总结提升,凝聚而成“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以及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结果,不但将中国美学重要范畴“仁”融合进了人类普世意义的“爱”,而且将中国传统有缘有故的“仁”升华为当代世界的没有差别、没有等次、没有利害的无缘无故的“爱”。终于,我们明白了潘知常几十年如一日对爱的一往情深:“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还不仅仅是一种爱的奉献,更是人类文明得以大踏步前进的前提。这是因为,转身之后,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的更加重要,更加值得珍贵。”③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504、504页。
也因此,不难看出,围绕由“仁”到“爱”的“仁爱”本体论,潘知常为他所创立的情本境界生命论美学大厦矗立起了的三根顶梁大柱,这就是:生命视界、情感为本、境界取向。
首先,以“生命视界”——生命的美学视界为基础。这是潘知常在1985年在《美学何处去》一文中首倡的概念,在这篇文章里他热切“呼唤着既能使人思、使人可信而又能使人爱的美学,呼唤着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整个人生的、同人的自由、生命密切联系的美学。”并且指出:“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美学应该爆发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人本学还原’,应该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的意义。”当然,在今天看来,这已经纯乎成为一个常识,可在当年“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时候,却实在是难能可贵。“人”固然要“实践”才能存在,但是实践的主体毫无疑问是以有着鲜活生命个体的人的存在为第一条件的,人与外在对象交往的依托是实践,但主体是生命,而生命是人在实践之前就已经与世界结成了“前世姻缘”,所以生命是先于实践而存在的。因此,回到生命的同时就是让美学的立足之地和逻辑源头不再是无本之木的“实践”,而是有源之水的“生命”。
其次,以“情感为本”——情感的体验为本为核心。解决了美学的存在之基——“生命”,让美学开始向生命的回溯,还有一道障碍必须克服,那就是美学意义上的生命究竟是理性还是情感。潘知常在1989年出版的《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就指出:情感“不但提供一种‘体验—动机’状态,而且暗示着对事物的‘认识—理解’等内隐的行为反应”。“过去大多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只是思想认识过程中的一种副现象,这是失之偏颇的。”①潘知常:《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72,73、3页。“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爱”就是情感直接而鲜活的体验和传达,就像没有情感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情感的美学只能是经院美学。鲍姆嘉通创立美学之初命名为“感性学”,就为美学的出生证上注入了情感体验的根本要素,康德称美是“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其中的情感性更不言自明。
最后,以“境界取向”——境界的自由取向为目标。如果说美学思考的是生命的意义,那么在生命的意义构成上是有高下之分的,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是生命的最大意义,当然也是最高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潘知常指出“美是自由的境界”。追求自由是生命的最大意义,因此,实现自由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潘知常早在1988年在《游心太玄——关于中国传统美感心态的札记》一文里就提出了“美在境界”,1989年更正式提出了美是自由的境界:“因此,美便似乎不是自由的形式,不是自由的和谐,不是自由的创造,也不是自由的象征,而是自由的境界。”②潘知常:《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72,73、3页。1991年河南出版社出版的《生命美学》,其中更是用较长篇幅阐述了“美是自由的境界”,尤其是在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诗与思的对话》一书之中,他这样阐述道:“假如说,实践活动实现的是自由的基础,认识活动实现的是自由的手段,审美活动实现的则是自由本身,只是不是现实的实现,而是理想的实现。进而言之,在对象方面,是实现为一种自由的境界。”③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46页。2012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里,他所写下的最后一章,就是“美在境界”,并直接提出了“审美对象涉及的不是世界,而是境界”的命题。无疑,这些论述都是要说明:人是有意义的存在,而境界是判别意义的多少和高下的标尺,因为人是以境界追求为目的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是境界性的存在。正如卡西尔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①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这样,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生命美学犹如一叶叶破浪的白帆,王国维、梁启超、鲁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张竞生、吕澂、范寿康……奏响了生命美学的主旋律。而在新世纪的今天,潘知常更高扬生命美学的大旗激流勇进,承前启后,为生命美学找到了“爱”的动力和“信仰”的航向。
生命美学,“他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都预言了这个胜利。”②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生命美学在所有的思考之中预言的,也正是“这个胜利”!
潘知常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一书的结尾处慨然宣称:
由此,美的尊严、爱的尊严、精神的尊严、信仰的尊严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整个世界也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而我们也因此而终于有可能第一次清醒地把未来还给自己,从而,得以第一次虔诚地将自己交到信仰的手中、爱的手中。③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