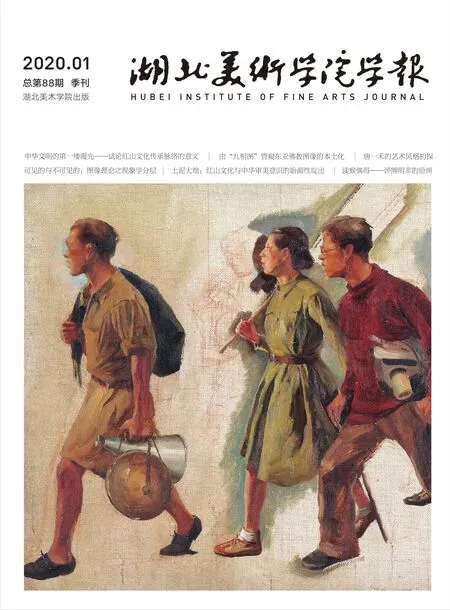土泥大地:红山文化与中华审美意识的始源性绽出
——艺术现象学视域中的原始艺术研究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系 | 宋伟
红山文化是中华史前文明发源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类型,作为华夏先祖的史前文明遗存,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红山文化积淀着中华文明源流发展的文化密码,其中也蕴藏着中华审美意识发生的原初秘密。从艺术考古学的角度看,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的大量出土文物向世人表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华夏先民的审美意识已初步形成并逐渐凝聚积淀为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由原始文化的浑融性特征所决定,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并非现代意义上区分清晰的“科学”意识,它浑融于现象学意义上的“前科学”文化观念之中。因此,运用“原初性”还原的现象学方法,探源蕴藏其中的审美意识之原初秘密,便成为破解远古华夏先民审美文化密码的关键所在。
一、前史原初:审美意识先于巫术意识
原始文化表征着人类文明的原初发端样态,其文化意识,尤其是审美意识具有始源性绽出的特征。因此,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观照或描述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及文化意识,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切身性地感受和领会其原初生态、样态和情态。
长期以来,在文化进步主义或工具进步主义理论的导引下,原始文化研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以后来文明发展的眼光,重点关注于原始文化所蕴含的进步要素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取向,如更多地关注于工具技术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建制和文化仪式的形制等等,但却忽视了原始文化原初生态、样态和情态的还原与呈现。以原始文化审美意识探源为例,诸多学者认为审美意识起源于巫术意识、艺术活动起源于巫术仪式活动,即艺术审美起源于巫术说。看上去,巫术活动似乎已经是原始先民最为古老久远的文化仪式活动,大量的考古发现似乎也确证了原始文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巫术文化,而且,这种巫术文化也确实发展积淀为传统的深层文化基因。如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派,以荣格和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理论”,甚至于马克斯·韦伯的“巫魅说”以及李泽厚的“巫史传统说”等,其理论前提都是共同指认巫术文化为原始文化的最重要形态。显然,这些学说观点的理论贡献值得肯定,然而,一旦我们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来看待这些理论观点,便会发现巫术文化虽然远古但并非人类意识最为原初的生态、样态和情态,它要比人类意识发端之原初生态、样态和情态更为复杂,因而也更为高级一些。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巫术文化已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形态了。也就是说,较之于更为原初性的人类意识或文化意识,巫术文化已经是一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文化形态。这意味着,从现象学追本溯源的意义上说,将巫术文化作为早期人类文明形态是不恰当的,因而还需要以“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回溯到人类意识发生更为原初的生态、样态和情态上来。例如,关于审美意识发生问题,究竟是巫术意识在先,还是审美意识在先?就一直是学术界难以判定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文化进步主义或技术进步主义思想观念的文化影响,巫术意识在先,艺术审美意识起源于巫术的观点似乎成为主流观点。显而易见,巫术意识较之于带有生物本能性的审美意识,是一种更为高级复杂的文化意识形式。从这一点看,广泛意义上的审美亦即具有生物本能性的审美意识总是要先于巫术意识。这种观点认为美是一种自然生命现象,人与动物一样具有天生本能的审美能力,因此,审美起源于自然本能天性。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达尔文,他认为美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并非人类所独有:“人和许多低于人的动物对同样的一些颜色,同样美妙的一些描影和形态,同样一些声音,都同样地具有愉快的感觉。”[1]美是一切有生命机体的本能特性,而这一本能特性的根本便是性的关注、吸引与追求。在达尔文看来,在人类早期生活中,更多表现出美的自然性与外在性的形体美,往往比后天社会化的仪态美更具有吸引力。只不过,当人类不断由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走向社会化的人时,审美发生中的生理性基础才逐渐被社会文化建制所驯化或“人化”。
陈望衡先生在《文明前的“文明”》一书中也明确提出了审美意识先于巫术意识的观点。在他看来,“审美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本原性意识,人类并不是为了功利的需要,也不是巫术的需要才去制作那些具有审美意味的艺术品的,其最初的动机就是审美。不是功利抑或是巫术产生了审美,而是在审美之中实现了功利和巫术。”[2]然而,需要明确的是,陈望衡先生主张审美意识先于巫术意识并不是在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来立论的,因为他并不认同动物也具有审美意识的观点,而是指认审美意识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意识。虽然,陈望衡先生在阐述自己观点时未言明其所具有的现象学旨趣,但从其将审美视为一种本原性意识的角度看,即从强调本原或本源的优先性原则上看,其思路与现象学原初性原则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正是这一点,陈望衡先生启发了我们以现象学方法来思考史前艺术史的问题,以使我们从现象学视域出发看待审美意识与巫术意识的先后关系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望衡先生使用了“文明前的‘文明’”,或者说“前文明”这一概念来描述原始文明;历史学界也习惯于使用“史前史”或“史前文明”等概念,这也让我们想到了胡塞尔的“前科学”的概念。胡塞尔强调:“必须像前科学的生活本身对它理解的那样来理解。”[3]现象学方法的旨趣在于,要尽量去除科学态度所造成的对于“生活世界本身”的遮蔽,返回“直观明见性”的“前科学”状态,这即是“现象学的原初性”要求。从现象学的时间维度看,原初性要求即是还原事情发生的原初状态;从现象学的直观维度看,“现象学的原初性(radicalness)要求人们回避简单地把物自身等同于经验的给予物,把物自身等同于经验的给予物就是把现象学诠释为经验论,这恰恰是丧失了现象学的原初性,现象学的原初性就是要排除早熟性地 (prematurely)和独断论地把物自身等同于任何东西。现象学恰恰是要把物自身的同一性看成是一个问题,而追问在原初意义上什么是物自身?”[4]诚然,从“现象学的原初性”意义上看,并不存在单纯意义上的审美意识,所谓审美意识也一定是混融于人类生活意识之中的意识。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如何以“前科学”的态度回归“现象学的原初性”?这种“前科学”的态度,对于我们研究史前文明史尤其是史前审美文化史,将具有怎样的方法论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思考的。
二、泥质塑型:土泥时代艺术形态的原初性绽出
基于前述现象学原初性的视角,探源“土泥性”所蕴藏的审美意识之原初秘密,可成为破解远古华夏先民文化密码的关键所在。在此,我们尝试以“前科学”的态度来考察红山文化审美意识的“原初性”,这就需要运用现象学方法重新看待或表述红山文化的时代特质。众所周知,以往的史前文化研究主要采取“科学”态度。从历史断代表述上看,历史命名模式虽侧重点不同,但都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进步主义或技术进步主义的理念,如有以工具制作为主要命名依据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有以社会建制为主要命名依据的“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有以文明进步为主要命名依据的“蒙昧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等。倘若我们不以文化进步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的“科学”态度来表述“红山文化”,而是以一种“前科学”的现象学原初性还原的态度来表述其史前文化的质地,我们是否可以将“红山文化”想象性地表述为“土泥时代”呢?如果这种从“前科学”态度出发所表述的“土泥时代”可以成立,我们将会以“土泥性”为原始农耕时代的主要文化质地,重新看待与阐释“红山文化”审美意识生成及其深层文化意蕴。
“红山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农业时代,其文化特性可以概括为“土泥性”。所谓“红山文化”是一个具有“土泥性”的文化,主要是指生活在红山文化广袤地域范围内的远古先民,以原始农耕生产为主业,以大地四方为化育基地,以土地崇拜为信仰根基,以泥塑文化为实践技艺,因而得以积淀形成的一系列与“土泥性”紧密相关的原始农耕时代的文化意识或审美意识。
中外艺术考古发现表明,泥塑艺术的历史非常古老久远,甚至我们可以说泥塑是最为古老的人类造型艺术活动之一。目前所知最早的洞壁粘土浮雕是约公元前13000 年的《两只野牛》,该泥质雕塑发现于法国阿里热地区,长63.5厘米,高61 厘米。以往,由于埋藏地下的泥质品不易保存下来,原始泥塑艺术得以存世的机会极其微小,后人更多看到的是石质塑像、陶质塑像或壁画艺术等比较易于存留下来的原始艺术作品,这就势必导致人们几乎忽略了在远古时期曾经大量存在的泥质作品,因而遗忘了那个曾经存在的“土泥时代”。陈望衡先生在《文明前的“文明”》第一章“泥火艺术:文明之始”中,曾提出一个颇有创意的想法,他认为可以考虑用“陶器时代”来替代“新石器时代”,因为“最能体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品位的无疑是陶器”。受陈望衡先生观点的启发,我们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否可以推想在“陶器时代”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漫长的“泥器时代”,在“泥火艺术”阶段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漫长的“土泥艺术”的阶段。需要说明的是,采用这种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追溯人类文明的初始状态,并非为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分期定义,其目的主要在于在这一还原追溯过程中尽可能呈现人类文明初创时的原初样貌,以破解蕴藏于远古的中华文化密码。
倘若存在一个远古的“土泥的时代”,那么“泥塑艺术”自然就成为“土泥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从艺术考古学意义上说,泥塑造像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原始艺术形式。红山文化艺术考古发现了大量的人塑像,从质地上看,可分为泥质、陶质、石质、玉质,其中泥质人塑像9 件以上,陶质人塑像15 件,石质人塑像8 件,玉质人塑像4 件;从体量上看,可分为大、中、小型,其中大型塑像相当于真人大小或超过真人大小,中型塑像相当于真人一半,小型塑像小于真人一半以下,其中大型塑像以泥质和陶质人塑像为最。泥塑人像主要发现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和山台北缘。应该注意到,在总共36 件人塑像中,泥质和陶质共有24 件之多,其中泥塑残块20 余块之多,大致来源于9 个单体塑像以上。较之于陶质、石质和玉质,泥质塑像最不易保存下来,由此可以推断红山文化应存有相当数量的大中型泥质塑像。这表明,泥质塑像构成红山文化人工造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制,对其进行现象学还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溯源中华审美意识的发生,更有助于探寻华夏先民的文化——心理奥秘。
从艺术考古学或文化考古学的意义上看,红山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无疑是牛河梁女神庙,而女神庙中泥塑女神头像的出土无疑是最令世人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这尊女神头像基本接近真人的尺寸,近旁还有比真人尺寸大两倍到三倍的人体塑像残片,表明这是一组大型塑像群。也就是说,现保存下来的女神头像并非主神,即便这样,这尊女神头像所传达出的神秘魅力也足以令世人惊叹不已,她所包含的文化密码也足以生发出我们无穷的想象和无限的神往。“牛河梁遗址曾经是一个女神成排、栩栩如生、气韵生动的女神群像的‘万神殿’。在这个‘万神殿’里,甚至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从这些情况来判断,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像也是被当作先民祭祀的偶像而安置在‘女神庙’这座神殿中的。……牛河梁女神像,最大的可能是氏族的女祖先——始祖女神,而且很可能是氏族联盟共同祭祀的始祖女神。”[5]这尊女神头像脸圆颧高,额头丰满,嘴阔鼻宽,耳厚敦实,威严中透显出慈祥温厚,尤其是那一双镶玉的眼睛,炯炯有神,更敷之以红色绘彩使其整个脸庞熠熠生光。还有,与石质塑像的坚硬质地不同,泥塑质地的浑圆可塑性使其型塑效果更为浑厚圆融,每一寸肌肤都散发出北方女性所特有的“高粱红”健康色调。研究表明,这种大型泥塑人像一般经过搭建骨架、选料加工、手与工具塑型、镶嵌装饰和压光彩绘等工艺程序,其泥塑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这尊女神头像可以想见,当年先民在神庙之中供奉膜拜一组或几组真人大小或两三倍真人大小的泥塑群神像,真可谓堂煌溢彩,恢弘瑰丽,难怪后人将其赞叹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先祖或女神。
可以推想,泥塑造型艺术在远古中国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泥塑艺术传统一直绵延几千年之久而艺脉不息,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历久弥新的坚固传统。其中,主要的传承是民间泥塑艺术和佛教泥塑艺术,其制作水平虽日臻精细,但基本上沿袭了红山女神泥塑造像的工艺程序;另一个艺脉传承则当属陶塑艺术,从本源意义上看,陶塑艺术从出于泥塑艺术,亦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造型艺术类型之一。
如前所述,由于泥塑作品不易存留,往往埋于地下重归于土,后人考古发现多见的是陶质、石质、金属质等较为坚固不朽的造型作品,这就导致了后人对泥塑艺术作品的忽视和遗忘。再加之,由于石质雕塑艺术在古希腊时期就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以至成为独具永久魅力的高不可及的典范,使之构成主流艺术史叙事中的典范类型,而泥塑艺术则逐渐变成始终难入主流的一种雕塑艺术类型。泥塑艺术之所以难以成为主流艺术类型,除上述缘由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没能以一种原初性的眼光来理解泥塑艺术发生的历史,从而忽略或遗忘了泥塑艺术的原初性历史内涵——即土泥性的原初历史文化意义。
三、地道坤元:土生土长的生生审美意识
从文化进步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的角度看,泥质造型艺术显然落后于石质造型艺术,这似乎也成为主流艺术史叙事相对轻视泥塑艺术而特别钟爱于石质雕塑艺术的主要理由之一。然而,从现象学意义上追溯其原初性,我们应该重视而不是忽视或遗忘泥质塑型的艺术史地位,这其中,不仅涵育着华夏审美识诞生的原初秘密,更蕴藏着中华远古文化的原初基元。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有所谓“天地人”三才之说,此三才也称之为“三道”,即天道、地道与人道。《周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
虽然,天地人三才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架构,但在历史上,“天地人”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谁更为根本原初?其从属关系又是如何演化的?这些问题依然在历史的迷雾中难以明细。以后来的眼光看,天为大为高为本为贵,“天地人”三才似乎遵循着“天道”优先的原则,尤其是发展建构起“天人关系论”——“天人合一论”之后,“地道”几乎完全被“天道”和“人道”所遮蔽或排除,三才几乎演变为两才,即“天道”与“人道”的两维思维架构。近代以降,在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影响下,哲学思维架构几乎完全变成了“天人合一”或“天人分立”的问题,而三才或三维中的“地道”则不再作为哲学思维架构考虑的问题了。然而,如果我们返回中国文化思想的原初语境,就会看到,在“天地人”三才或三维架构中,“地”或“地道”实乃“天地人”三才之中最为根本和最为始源的维度。这里的问题是,“地道”是如何被遮蔽或遗忘的?重新发现“地道”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原初性的回归?这种原初性回归对于我们理解中华远古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将具有怎样的意义?
大致上说,“地道”之被遮蔽或遗忘,与华夏文明上古史上所发生的“绝地天通”的重大历史变革紧密相关。“绝地天通”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后有《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后人解释虽有所不同,但基本认同此乃上古史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绝地天通”都是中国远古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然而,应如何理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变,确是学术界争辩不休的议题。其中,一些学者看到,“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余英时和李零都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冲突。余英时认为:“‘绝地天通’神话和‘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至少在字面上是互不相容的。”[6]李零则明确指出“‘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7]这些论述业已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我们想指出的是,无论是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还是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实质性冲突,其视点依然未跳出“天人”的思维框架,倘若我们以现象学还原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亦即将“土泥性”——“地道”、“地维”作为原始先民的“前科学意识”,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天地之裂”,而不是“天人之裂”的历史事件;这是一场“地天之争”,而不是“天人之争”的哲学之辨;这是一场“天时”战胜“地利”的战争,而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交融。诚然,这其中也有“天地神人”的妥协和融合,但“天道”最终战胜了“地道”,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按照“六经皆史”的思路,可以大致推想远古时代曾经经历了一个“天神崇拜”部族战胜“地神崇拜”部族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诗经》)。“绝地”而“维天”,“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孔传》)本文的目的不是证实或还原这段历史,在此,我们只是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推想或猜想中国上古史上从“地神崇拜”到“天神崇拜”的历史,还原“地道”在“天地人三才”中的原初性地位,还原以“土泥性”为原初文化意识的“地神崇拜”意识,以察看“地道坤元”在中国原始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初建时的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代表了更为原始的“地道坤元”的大地观念和“地神崇拜”的巫魅文化,虽然,在“绝地天通”的历史事变中,这种基于“土泥性”的更为原始的“地道文化意识”被基于“天时性”的更高一级的“天道文化意识”所战胜,所取代,所遮蔽,所改造,所溶解,最后,“天道”昭告“地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但“大地之为大地”的“地道坤元”意识依然生生不息地存在于中国古老的大地之上。一方面,“绝地天通”之后,当“天道”确立了至上地位,便逐渐融合吸纳此前的“地道”,因为完全“绝地”是不可能的。“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彖·谦》)“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 (《管子·霸言》)于是产生天地阴阳、天地尊卑、天地上下、天地刚柔、天地经纬的对待交通,这大概就是“文王演周易”的真实历史面貌,只不过“地道”必须屈尊于“天道”,“地道”从此成为依附于“天道”的传统;另一方面,“绝地天通”之后,“地道”依然保存于传统文化之中,尤其是存留于民俗民间之中土地崇拜意识,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遍布民间的“地母娘娘庙”、“后土娘娘庙”、“土地庙”。由此可以看出,源自于土地的原初性意识,因其文化生成的原始古朴而极具原始生命力,常以民间习俗或信仰的方式经久传承,绵绵不绝。
从文化进步主义的角度看,“绝地天通”、“维天革命”无疑是一种从更为原初、更为原始、更为素朴的“巫魅文化”到“礼仪化巫魅”或“政教化巫魅”历史变革过程,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其历史进步意义在于,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天地混沌”、“民神杂糅”的原始混沌状态。然而,从现象学的原初性意义上看,“绝地天通”——以“天道”压“地道”,实质上形成了一个逐渐遮蔽或遗忘“地道”原初性的文化建构过程。因此,以现象学还原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地道”对于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原初性意义,自会获得独特的领会和体悟。显而易见,极具原初性的“地道文化”内涵丰厚,在此择其大要,只简要阐释其基于大地意识所建构起来的以生生论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和以俯仰观为方法的审美意识。
基于大地意识的生生论哲学意识。地道坤元,地坤为母,万物滋养,生生不息。正如朱熹在《说卦传》中所言:“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坤,地也,故称乎母。”万物生长于大地,人类栖居于大地。土地与人类的亲缘性关系最为紧密,由此自然萌生出以土地为基础的淳朴原初的文化意识。原始先民的土地意识并非外在的客观实体世界,而是与万物生长息息相关的“生生”意识或“土生”意识,“土”即为“生”,“生”即为“土”,正所谓“土生土长”,生生不息。从最古老的甲骨文字看,“土”即是土地上生长出植物的象形,《说文解字》中解为“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土物出形也。” 植物生长于土地,“百谷草木丽乎土。”( 《易·离彖传》)动物生长于土地,“龙返其渊;安其壤土。”(《传先秦古诗》)人类同样也生长于土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风俗通》)。总之,世间万物——大地上的生生之物——植物、动物和人类都生长生成于土地,土生土长,生生不息。我们看到,华夏先祖正是基于这种“土生土长”的“生生意识”,逐步发展形成出中国文化所独具的“生生论”哲学。作为“前哲学”状态的“哲学”,基于大地的生生论哲学,与后来的生存论哲学和生命论哲学不同,其重要之处在于,先民的生生论源出于土地,因而“地”与“生”从不划分隔断,而后来的生存论或生命论哲学则建立在“地”与“生”划分的基础上,其“生”也主要是“人之生命存在”。
基于大地意识的俯仰审美观。地,土也;地乃大土,又名大地。地厚载物,厚实浑朴的苍茫大地,负载着山峦河川,云蒸气化,生息万物。原始先民“背朝黄土”以俯视大地,大地之为大地乃在于承载滋生天地万物,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淳朴的土地观念扑面而生,逐渐凝聚积淀为踏踏实实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国古人常言之“天地之间”“天人之际”,或者是“天地人”三才并举,看上去“地”的位格似乎越来越低,“天”与“人”的位格逐渐抬升,往原初处回溯,实乃“大地”为先为重,由此形成中国文化独特的“基于大地”“始于足下”的“俯仰观”和“近远观”。“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说文解字·序》)“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经·系辞》)“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等都表达了古代先民对大地泥土的深深眷恋和执著情结,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早在《易经》《系辞》的传里已经说古代圣贤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俯仰往来,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8]有人说,西方哲学源自于仰视天空的惊叹,而中国哲学则源自于俯视大地的观察。俯地近观,虽然缺少高远超越与彼岸想像,然而,它的确如厚土黄泥,地地道道、踏踏实实,不落于玄想空虚。由是观之,中国远古之文化意识源于大地土泥,在基于大地的基础上逐渐升扬“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审美意识。
追溯文化原初性并非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马克思)。因为我们无法回到曾经的远古过去。但是,华夏先民的童年时期依然会让我们有“复归于婴”不尽想往,更何况,华夏审美的文化密码涵育在大地泥土的原初性呈现与绽出中。因此,以“土泥性”为基点,探源蕴藏其中的审美意识之原初性秘密,将有助于我们破解远古华夏先民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