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用《韩昌黎集》
孙羽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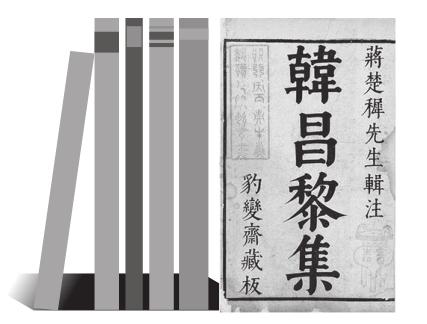
眾所周知,毛泽东一生与中华文化经典结下不解之缘。无论是在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还是戎马倥偬的革命岁月,一直到江山红遍的晚年时光,毛泽东始终手不释卷,孜孜以求。对于这位伟大领袖而言,阅读中华文化经典不仅是繁忙工作之余的消遣,同时也贯彻着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观念的探索与实践。这在他学习、借鉴和批判《韩昌黎集》的过程中有着生动的体现。
《韩昌黎集》是唐代大文豪韩愈的诗文作品集。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昌黎,世人敬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在思想观念上,韩愈大力提倡儒道,力抵佛老二教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并审时度势地提倡儒学的心性之维,为汉唐儒学向宋明儒学的转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在政治生活上,他积极用世,先后在多地任职,官至吏部侍郎。他忠君爱国,犯颜直谏,奖掖后进,关爱百姓。面对安史乱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他勇于维护唐王朝的统治权威,只身赴叛乱藩镇宣慰陈说,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奇功。在文学创作上,他有力地纠正了东汉以降的形式主义文风,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文道并举,提倡修辞明道,被后世推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纵观韩愈的一生,可以说已基本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境界,正如苏东坡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道兼善、忠勇并济的韩愈,可堪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后人要了解韩愈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和文学造诣,就要到收录了他各体文章的《韩昌黎集》中一窥究竟。因此,这部《韩昌黎集》,从宋代开始就被推尊为文化经典,羽翼六经,以一代文豪欧阳修、理学宗师朱熹等人为代表,宋代许多文人士子都对《韩昌黎集》做过详尽的校勘和研究,以至有“五百家注韩”的名号。直到清末,《韩昌黎集》都是历代读书人案头必备的要籍,其中的一些经典篇章,甚至成为私塾里的启蒙课文。可以说,《韩昌黎集》以其雄浑刚健的文学气质、鲠骨忠爱的精神力量,对千年以来中国人的为文处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华文化经典宝库中熠熠生辉。
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就对《韩昌黎集》格外关注。从今天保存下来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韩昌黎集》中的多首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摘录、注释和评点。其中,除了《谏臣论》《感二鸟赋》这样的名作之外,还有诸如《改葬服议》《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等相对艰涩、鲜为人知的学术性论文。由此可见,毛泽东阅读韩愈作品,应是逐篇细读《韩昌黎集》全文,而非泛泛浏览或阅读某一节选本,其认真的态度和深入的程度可以想见。也正是由于这样细致而深入的阅读,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全面汲取韩愈思想和文学上的养分,同时也能清晰看到其间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活学活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予以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这里,我们不妨列举三例。
其一,毛泽东借用韩愈攘辟佛老的观点,廓清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论述。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二者“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因此,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这里,“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出自《韩昌黎集》中攘辟佛老的名篇——《原道》。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以儒学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日渐衰微,佛老二氏思潮甚嚣尘上,对当时政治制度、社会生产、思想文化等领域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韩愈作为唐王朝的坚定维护者,试图追溯现实问题的思想根源,于是他从佛老思想入手,作一全面批判。在《原道》一文中,韩愈历史地分析了思想文化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激烈斗争:
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道德仁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范畴,不同流派的定义和主张各不相同,除了儒家,还有杨朱、墨翟、老庄和佛教等诸多论调,一旦某一派的主张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就会对其他思潮和主张形成攻击、奴役之势。因此,在韩愈看来,对于阻碍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和历史进步的思潮,理应才取“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方案,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只有反对和禁止腐朽的、反动的,才能推行和弘扬正确的、进步的。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间,虽然已非封建文化内部诸派的纠葛,但他们的关系仍然是反动与进步的关系,因此韩愈昔年攘辟佛老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有必要拿来警醒民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廓清道路。
其二,毛泽东通过批判韩愈儒家式的“民主个人主义”观点,唤醒并团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49年,就在解放战争形势大好、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之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观望摇摆,对美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毛泽东借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黯然回国之际,写下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文中说道: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伯夷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隐士形象,韩愈在《伯夷颂》中称赞伯夷不苟同武王、周公那些当世的圣人,而能坚守“特立独行”的品格,堪称“豪杰之士”。20世纪上半期,在政权更迭、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许多知识分子以伯夷“特立独行”“独善其身”的人格自诩,试图逃避一切政治、政党纠葛,正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所说:“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即便是闻一多、朱自清,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也深受古贤伯夷和当时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然而,当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之际,以闻、朱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再也无法沉浸在自由主义的小圈子中,最终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想和光荣使命。正是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别了,司徒雷登》这样的雄文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抛弃了幻想,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一回,毛泽东借助的是对韩愈的批判而非继承,而这种批判恰能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华文化经典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眼光和胆略。
其三,毛泽东提倡韩愈修辞明道的观念,用以加强和改进党的宣传工作。无论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他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批判了党内各式空洞的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文风,如所谓“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随后,毛泽东为党八股开出了药方,其中特别提到了韩愈“行成于思”的观点,强调“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韩愈在《进学解》中有句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毛泽东提炼出“行成于思”四字,目的即为了强调撰写宣传文章要需要反复研究思考,力求准确反映客观事物,符合客观规律,这里实际包含着勤于思考(“业精于勤”)和善于思考(“行成于思”)两个层面。如果进一步来看,韩愈对于文风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强调通过修辞的手段实现明道的目的。他曾在《谏臣论》中表示“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用今天的话来理解,修辞的最终目的并非为文章而文章,而是通过文辞的修饰、文风的改进,最终达到彰明某一道理、某一精神甚至某一方针、某一路线的目的。而谙熟韩集的毛泽东,在其《反对党八股》一文贯穿的主线即充实“新的文风”,用以“表现革命精神”,“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反对党八股》的这条主线,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韩愈“修辞明道”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这对于今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