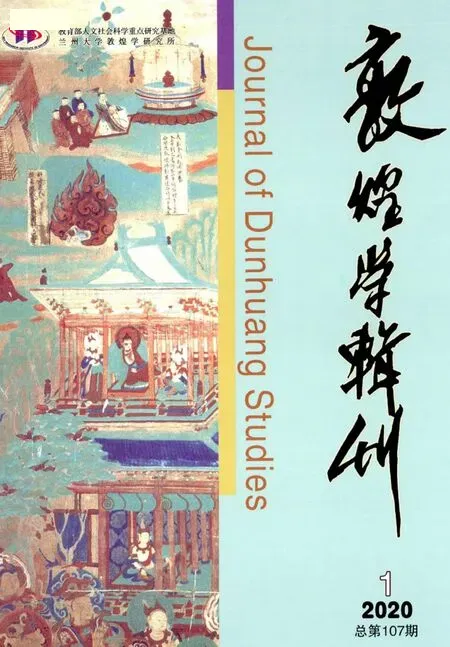吐蕃大虫皮制度刍议
崔 星 王 东、2
(1.西北民族大学 图书馆,甘肃 兰州 730000;2.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搜神记》卷2《扶南王》载:“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虫,亦曰大灵。”①[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 《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4页。这是汉文典籍中较早将大虫作为老虎代称的记载。《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记载了吐蕃社会的大虫崇拜现象,“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②[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卷216下 《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3页。。大虫皮制度是以虎皮作为衣饰对有战功者颁行 “生衣其皮,死以旌勇”褒奖的一种勋号,也是吐蕃王朝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吐蕃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大虫皮制度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①譬如 [日]山口瑞凤 《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东京:岩波书社,1983年,第477-480页;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02-117页;段文杰 《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李其琼 《论吐蕃时期的敦煌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1-20页;姚士宏 《关于新疆龟兹石窟的吐蕃窟问题》,《文物》1999年第9期,第68-70页;陆离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 《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第35-41页;《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110-121页;《关于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再探讨——英藏新疆米兰出土古藏文文书Or. 15000/268号研究》,《藏学学刊》2016年第1期,第11-13页;杨铭、索南才让 《南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百年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杭州: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2010年,第782-792页,后刊于 《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第15-22页;王东 《西域出土一份古藏文告身文献补考》,《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第73-77页。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利用古藏文文献及其壁画、题记等对该制度再作进一步补充考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大虫皮制度确立时间再议
关于大虫皮制度创立时间,多依据藏族史籍 《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统治青藏高原后,建立完善吐蕃社会各项制度,包括制订 “以万当十万之法 (khri-rtse-vbum-bzher)”,虎皮袍是勇者标志,告身是贤者标志。 “所谓六勇饰 (dpav-mtshan-drug)是:虎皮褂,虎皮裙两者;缎鞯 (zar-chen,即gzar-chen) 及马蹬缎垫 (zar-rgyung)两者,项巾及虎皮袍等,共为六种。”②[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页。陆离教授根据该条文献记载认为 “吐蕃的大虫皮制度首设于松赞干布统一全境制定法律之时,时间为公元7世纪前期,正是唐武德、贞观年间。”参见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第36页。“又,对战争中的勇士,以六勇饰奖之。”提示了在松赞干布早期已制订 “大虫皮制度”以褒奖勇士,贤者用 “告身制度”褒奖。这成为一些学者将大虫皮制度确立时间定为松赞干布时期的基本依据。③参见陆离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第35-36页;赵心愚教授对于陆氏观点并未提出反驳意见,可视为赞同其观点,参氏著 《唐樊衡露布所记吐蕃告身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74页。
敦煌文献P. T. 1287《赞普传记》、P. T. 1288《大事纪年》 是研究吐蕃历史重要文献,纵观其内容,仅发现一处疑似大虫皮制度的记载,“大论囊热达赞贤良敏明,吉祥走运,乃颁以瑟瑟告身。民庶之中攻克夺迪部与秋琛部之英勇善战之勇夫,颁赐虎皮臂章。”④最初王尧、陈践译作 “虎皮牌”,参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后来,改译为 “虎皮臂章”,参见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陈践教授指出: “赤松德赞时期给勇士颁发的 ‘虎皮章饰(stag-gi-thog-bu)’可能指大小如果子的虎皮小章饰,不能算虎皮告身。”参见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P. T. 1288《大事纪年》载:“及至鸡年 (肃宗至德二年,丁酉,公元757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由论芒赞、论多热二人于 ‘则·南木夭’召集之,大论囊热等攻陷唐廷之大宗喀及临洮城二城。”①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9页。大论囊热等率兵攻占大宗喀、临洮城,军功之著自不待言,按照大虫皮告身授予原则,囊热必然会被授予高规格大虫皮告身。《贤者喜宴》关于囊热两种告身的描述,“所谓九大尚论 (zhang-blon-che-dgu)是:贝·囊热拉赞(sbas-snang-bzher-lha-btsan),其英武的标志是:穿虎皮袍、饰以碧玉之文字告身及大雍仲之文字告身 (yig-tshangs-gyu-yig-dang-gyung-drung-chen-po) 以及珍宝、 黄色宝石文字告身 (dkon-nor-ke-ke-ru) 等等,故其为大 (尚论)。没卢氏墀松热霞 (vbrokhri-zungs-ra-shags)穿白狮皮袍,故为大 (尚论);……上述诸尚论均各有勇武之标志,其告身分别是金、玉之文字告身,或各 (饰以)珍宝。”②[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200-201页。P. T. 1287《赞普传记》中记载 “大论囊热达赞贤良敏明,吉祥走运,乃颁以瑟瑟告身。”P. T. 1287《赞普传记》、P. T. 1288《大事纪年》对告身制度记载不辍:如南日松赞时期,赞普近侍娘·尚囊驳斥琼保·邦色得到小银字告身奖励;松赞干布与大臣韦·邦多日义策盟誓,“(韦·邦多日义策)子孙后代中一人,赐以金字告身,不会断绝”;大论囊热达赞被赐予瑟瑟告身等等,而对大虫皮制度缺乏记载是难以想象的。
究其原因,我们可从前揭 “大论囊热达赞贤良敏明,吉祥走运,乃颁以瑟瑟告身。民庶之中攻克夺迪部与秋琛部之英勇善战之勇夫,颁赐虎皮臂章”中寻找蛛丝马迹,作为大论囊热达赞在为吐蕃开疆拓土中战功显赫,自然会授予大虫皮告身,而此处重点强调其 “贤良敏明,吉祥走运”,而被授予瑟瑟告身,这与贤者授予告身制度相对应。赤德祖赞时期 (704-755在位),吐蕃君臣关系异常紧张,根据P. T. 1288《大事纪年》载,公元705至754年 (其中747至754年记录残),获罪谴大论2人,遭放逐8人,获罪谴大臣1人,被撤职1人,被控告1人,被抄没家族财产的大臣2人。③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2-99页。同时,这一时期大相 (论)更换频繁,赞普与大臣关系表现出四个显著特点:“大相的设置由一人增至四人。重用外戚的倾向明显趋强。任用吐谷浑小王为朝廷重臣。对大臣的猜忌与防范甚严。”④石硕 《吐蕃政教关系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赞普与大臣盟誓中,更强调大臣的忠贞,如 《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载 “恩兰 [达扎]路恭忠贞不贰”、《谐拉康碑》载 “班第·定埃增终忠贞不贰”以及“忠贞之念耿耿”⑤王尧 《王尧藏学文集》卷2《吐蕃金石录·吐蕃藏文碑刻考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90页、131页。,因此,同时拥有两种告身的朝臣边将往往更看重标志贤良的告身,这也是达日札夏向上级申诉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唐书·吐蕃传下》关于以虎皮表彰有战功将士的记载表明,只有具有军功者才有资格以虎皮为衣饰,作为一种勇士荣耀标志。西南古羌人自古有虎崇拜习俗, “宕昌,羌种也。……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货”⑥[南朝梁]萧子显 《南齐书》卷59《氐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32-1033页。。有学者指出, “吐蕃崇拜猛虎,以虎皮褒奖勇士,并授以大虫皮称号正是源自于古羌人的虎崇拜”①陆离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第37页。。关于吐蕃大虫皮有明确记载时间是在开元 (713-741)中,河西骑将宋青春与吐蕃交战中曾俘获有身穿大虫皮衣饰的吐蕃将领, “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勇暴戾,为众所忌。……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②[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 《酉阳杂俎》卷6《器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页。。这是晚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一段记载。依据 《贤者喜宴》对九大尚论 (zhang-blon-che-dgu)的描述,③[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200-201页。P. T. 1287《赞普传记》中记载:“大论囊热达赞贤良敏明,吉祥走运,乃颁以瑟瑟告身。”表明虎皮袍、白狮皮袍成为大论级别官员标志之一。因此,大虫皮制度在囊热拉赞已担任大论的 “757年”在高级军事官员中已经使用,加之前文提及开元中唐蕃交战过程中被俘获的吐蕃大虫皮将领,表明至少在赤德祖赞时期 (704-755),大虫皮制度已经完备,并在军队中广泛施行。
二、大虫皮来源
新疆出土木牍中曾出现有 “虎兵 (stag-so-pa)”字样,英国学者托马斯认为 “单个战士是so或so-pa,也经常是stag,虎 (或许它是一个官员的称谓,或作为一个 ‘勇士’的称号),这是吐蕃军队中许多特定称号中的一种。”④See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p. 424.如M. Tgh. a,iii,0016号木牍载: “送驻扎在于阗玉姆的虎兵 (stag-so-pa)⑤王尧、陈践教授将此处的 “虎兵”译为 “斥候”,参见氏著 《吐蕃简犊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4页。陆离教授依据托马斯的译文,认为 “这些被赐予虎皮衣的士兵据简犊内容来看担当着公文传递等任务,授予士兵的虎皮衣规格当较低,可能是 《贤者喜宴》中提到的虎皮褂。”参见氏著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笔者认为虎兵没有资格享受规格较高的虎皮褂。,长草滩的士兵的请求信件。”⑥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p. 202.Or. 15000/418残卷载:“俄卓 (vo brog) 之小罗布 (nob chungu)⑦杨铭认为小罗布 (Nod chungu)即七屯城,今天的新疆米兰古城。参见氏著 《吐蕃简牍中所见的西域地名》,《新疆社科科学》1989年第1期,第87-94页。……上阿骨赞斥候(rgod tsang stod so pa)十三人已到。部队,五个虎兵抵达,虎兵首领……”⑧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p. 128.汉译文参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 《敦煌西藏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拉丁转写参见 Takeuchi. T,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of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 The Toyo Bunko-The British Library, 1997,1998, p. 176.虎兵标志与虎皮有关,符合文献中勇者授予虎皮衣的记载。“是月 (贞元二年九月),凤翔节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轶,遣其将王佖夜袭贼营,率骁勇三千人入汧阳,诫之曰: ‘贼之大众,当过城下,无击其首尾。首尾虽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则其中军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佖如其言出击之,贼众果败,副将史廷玉力战死之。”①[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卷196下 《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49页。“中军”属于吐蕃精锐部队,特有标志是“五方旗、虎豹衣”;另,敦煌文献载有 “民庶之中攻克夺迪部与秋琛部之英勇善战之勇夫,颁赐虎皮臂章”,②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15页。表明 “中军”和 “勇夫”都有虎皮衣饰 (或臂章)。因虎皮珍贵,不大可能大面积在将士中使用,只有那些因英勇作战被赐予虎皮臂章的士兵才能称为 “虎兵”,以区别其他军队,且仅适用于作战英勇的普通士兵。
既然虎皮被广泛应用在军队中 (特别是被授予高规格大虫皮,如虎皮袍),如此多数量的虎皮又来自何处呢?
其一,吐蕃本土。吐蕃统治者在各地建有狩猎场地, “及至羊年 (公元659年),赞普驻于 ‘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及至龙年 (公元668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并于且末国建造堡垒。”“及至鸡年 (公元673年),冬,(赞普)牙帐巡临 ‘襄’之 ‘让噶园’,于 ‘董’之虎苑集会议盟”“及至蛇年 (公元693年),夏,于董 ‘畿之虎园’集会议盟”“及至狗年 (公元746年),冬,驻于札玛,于 ‘畿’之狩猎园,由大论穷桑与论结桑顿则布二人集冬会议盟。”③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8-89、98页。在今天西藏东南金珠藏布流域依然存在丰富的植被和动物群,为老虎生存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环境与食物链,通过对虎足迹的数据分析,确认这里至少分别有5只虎。④张明等 《西藏东南部金珠藏布流域虎的数量和分布现状》,《兽类学报》1998年第2期,第81-85页。
其二,西域、中亚地区。《穆天子传》载:“舂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兽,食虎豹,如麋而载骨,盘□始如麕,小头大鼻;爰有赤豹、白虎、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⑤[晋]郭璞注 《穆天子传》卷2,《四部丛刊初编》子部第80种,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0-11页。舂山即今天新疆吐鲁番北部的天山,⑥王守春 《〈穆天子传〉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21页。古代新疆地区飞禽走兽众多,包括赤豹白虎等猛兽。吐蕃与西域联系早已有之,敦煌文献P. T. 960《于阗教法史》记载了于阗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⑦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吐蕃文献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40-158页。霍巍教授指出:新疆皮上桑株岩画与西藏阿里的古代崖画在分布场所、雕凿风格、技法题材等有许多共同点;⑧索朗旺堆主编 《阿里地区文物志》第2章 《古代岩画地点》,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84页。利用考古资料对吐蕃与中亚、西亚等地的交通路线进行论述,指出吐蕃与这些地区的密切联系;⑨霍巍 《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第48-63页。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当时于阗人容貌并非深目高鼻,反类华夏云云,决非指汉人移居此地,其实应为类似汉人的西藏人混合的结果。”①[日]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 《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2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36-137页。这种以汉文传世典籍所作推断,已得到考古人类学资料印证。1986年进行考古发掘的新疆焉不拉克古墓群大致年代在西周或春秋之间,墓葬中出土人骨与现代藏族卡姆型头骨之间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②韩康信 《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第371-390,407页。再次证明了早期中亚与吐蕃地区的密切联系。
其三,南亚。秦汉时期,中国西南与中亚、南亚的交通路线已被开通,从传统观点来看,西南丝绸之路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 “蜀身毒道”,即从蜀地经由云南、缅甸等地到达古代印度的道路。南亚半岛是孟加拉虎 (包括印度虎)重要分布区域,印度教中湿婆神形象为 “他头上有恒河,额上是弯月和第三只眼,脖子上是蛇环和髑髅之环,全身涂灰,披虎皮,四只手分别持三股叉、兽主之宝、棍棒和套索,颈项青色,坐骑是白色公牛南迪。”③拉纳·普拉萨德·夏尔玛编著 《印度神话辞典》,瓦拉纳西版,第494页;转引自周志宽 《对印度教中湿婆神的思考》,《南亚研究》1994年第3期,第42-47页。吐蕃王朝建立前,女国一直将盐销往天竺,多次与其发生战争;④[唐]魏徵 《隋书》卷83《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51页。松赞干布时期,迎娶尺尊公主入蕃;⑤[元]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 《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59页。贞观二十二年 (648)五月,右卫率伏长史王玄策借吐蕃精锐大破中天竺阿罗那顺;⑥[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 《校订本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64页。特别是1990年西藏吉隆县发现的 《大唐天竺使出铭》为古代吐蕃与泥婆罗之间的交通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⑦霍巍、李永宪 《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 〈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第619-623页。从考古资料印证文献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其四,西南巴蜀、云贵地区。先秦西南多虎患,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 (通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⑧[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页。西南民族以虎为图腾崇拜的习俗源远流长,“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为祠焉。”⑨[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0页。“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长披虎皮,下者披毡”⑩[宋]薛居正等撰 《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昆明部落》,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46页。,也存在因功受 “大虫皮”的习俗,⑪⑪ [唐]樊绰著,向达校注 《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8页。⑫ 参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79页;陆离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第37-41页。甚至有学者认为吐蕃和南诏的大虫皮制度存在一定联系。⑫⑪ [唐]樊绰著,向达校注 《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8页。⑫ 参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79页;陆离 《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第37-41页。南诏皮逻阁于752年接受 “赞普钟”封号后,与吐蕃结盟,双方交流日益频繁,作为西南特产之一的虎皮 (《宋史》卷493《蛮夷一》载:“西南溪峒诸蛮上乾德四年,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通过贸易或交换流入蕃地。
其五,中原。文成公主入蕃后,吐蕃与中原交流日益密切,虎皮也属于贸易商品之一。另外,吐蕃 (部落)朝贡中原王朝中,统治者按照吐蕃社会习俗对入贡者赏赐虎皮,后唐长兴三年 (932) “十一月,吐蕃朝贡使辞。人赐虎皮一张,皆披虎皮拜谢”,①[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 《校订本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第三》,第11301页。“至道元年,凉州蕃部当尊以良马来贡,引对慰抚,加赐当尊虎皮一,欢呼致谢”②[元]脱脱等撰 《宋史》卷492《外国传八·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54页。。
三、大虫皮规格类别
《贤者喜宴》载:六勇饰分别为用于服饰的虎皮褂、虎皮裙、虎皮袍、项巾 (此处将项巾列为服饰)与装饰功能的缎鞯、马蹬缎垫,这应是早期大虫皮的六种基本规格。随着吐蕃王朝各项制度日益完善,该制度内容不断补充,不再限于六种规格。
敦煌古藏文ITJ370号 (大英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编号Or. 15000/269)文本蕴含大量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信息,对于研究吐蕃告身制度及大虫皮制度价值颇大,引起武内绍人、杨铭等学者的关注③T.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Tokyo, Daizo Shuppan, 1995;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The British Library, 1997, 1998, p. 121, no. 370.杨铭、 索南才让 《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第15-22页。。陈践教授也注意到该文献的重要价值,并重新解读。④汉译文参见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第189-190页;图版参见第362页。这份残卷大虫皮种类超出六种规格,除包括虎皮褂、虎皮鞍鞯 (也译为缎鞯)、虎皮蹬垫 (也译为缎垫)外,又增加草豹桑踏 (gung-gi-phram-thbas),超出大虫皮制度仅限于虎皮的范畴。 “所谓六褒贬 (rkyen-drug)是:勇士褒以草豹与虎;懦夫贬以狐帽;显贵褒以佛法 (lha-chos);贱民 (g·yung-po)贬为纺织工与本教徒;贤者褒以告身;歹徒则贬作盗贼。”⑤[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51页。既然草豹 (皮)与虎 (皮)是勇士的标志,那么草豹皮成为大虫皮规格的一种形式合情合理。另外,《吐蕃兵书残卷》载:“无论是上自众兵卒,下至‘孜阐’,在大战小战中奋勇战斗者,视为勇士。奖赏大至……告身及虎皮以下,小至‘桑尝’⑥桑 (srang)意思为重量单位 “两”的音译,“桑尝”系藏文词汇 “一两 (srang-gang)” 的对音,由于草豹桑尝 (踏)是最低级的大虫皮告身,因此无法与大块虎皮相提并论,笔者推测所谓草豹桑尝 (踏)大概是用极少量 (如一缕)的草豹皮来装饰衣服的袖口、领口等显眼处,成为一种标识。巴桑旺堆先生认为 “其意似乎是说奖赏少量金银,如几两、几钱、几分等。”显然与 “大律”中关于奖赏勇者的措施不符。以上,按大律授之。”⑦巴桑旺堆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书残卷解读》,《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第16页。残卷中所载奖赏是依据军功大小,立功受到奖励有差别,大到某某告身和虎皮以下,最低授予 “桑尝 (系srang-grangs对音)”,这与 《虎皮告身残卷》中第5行提到的 “草豹桑踏”所指应为同一规格的大虫皮告身,是大虫皮告身中最低等级,又有别于专门授予普通士兵的虎皮臂章。
“贝·囊热拉赞,其英武的标志是:穿虎皮袍、饰以碧玉之文字告身及大雍仲之文字告身以及珍宝、黄色宝石文字告身等等,故其为大 (尚论)。……上述诸尚论均各有勇武之标志,其告身分别是金、玉之文字告身,或各 (饰以)珍宝。”①[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200-201页。另,P. T. 1288《大事纪年》载:“及至兔年 (公元763年),……蕃地举行大议事会,对大尚论予以褒奖。授大论囊热以白宝石文字告身,任命为大论。”②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00页。公元757年,囊热首次以大论身份主持夏盟。③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9页。8世纪中期左右,白狮皮已成为大虫皮制度多种规格的之一。高昌故城曾出土一块方形麻布上绘有一头戴狮头皮冠的金刚力士形象,④图版参见 《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封里图版11《高昌故城佛寺·金刚力士》;彭杰研究员认为可能身披一整张虎皮,参氏著 《丝绸之路流散国宝:新疆绘画艺术品》,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51页。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在犍陀罗与金刚力士结合后,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狮子头盔逐渐变成了虎头头盔。⑤李凇 《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图像及其西方来源》,载 《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4页。地处西域的高昌受犍陀罗和龟兹艺术风格影响颇深,金刚力士的狮头皮冠借鉴了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形象,虎头盔和狮头盔形象金刚力士都曾在高昌流行。⑥霍旭初 《龟兹金刚力士图像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1-7、115页。佛教东传至河西后,狮头盔力士形象逐渐消失,仅发现虎头盔力士形象,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天王右侧侍从身披一张完整虎皮,虎头、四肢以及虎尾均清晰可见。狮皮的出现,或许是吐蕃占领西域时期受到西域佛教艺术影响之故。赤松德赞时期九大尚论中出现有虎皮袍,与 《贤者喜宴》关于大虫皮制度中六勇饰的记载相符,白狮皮袍出现,可能源于西域佛教艺术元素的影响。贝·囊热拉赞作为众尚论之首被授予虎皮袍,大尚论没卢氏墀松热霞穿白狮皮袍,可视为大虫皮制度的衍生品,理应低于虎皮袍规格。无疑,超出六勇饰之外的猛兽 (如狮、豹)皮饰使得大虫皮制度内容大大丰富,以虎皮为基础的大虫皮制度内容增多,甚至包括草豹皮、狮皮,趋于成熟完备。九大尚论中大尚论没卢氏墀松热霞穿白狮皮袍,说明白狮皮袍属于大虫皮制度中较高的一种规格。
莫高窟中 《吐蕃赞普礼佛图》中赞普及其属从以虎皮为衣饰,反映了吐蕃族的服饰特色。⑦参谢静 《敦煌莫高窟 〈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第65-73页。其中,第159窟 《吐蕃赞普礼佛图》中第4身吐蕃赞普身穿白色翻领长袍,衣领和袖口均有虎皮缘边;第231窟表现最为典型,赞普脚下踩着的方坛之上铺有虎皮,赞普身后有并排三人,第一身内穿黑色翻领长袍,上身外套为虎皮褂,下身为豹皮裙,第三身身穿红色翻领长袍,领袖用虎皮缘边。第367窟中吐蕃供养人中有以身披虎皮大衣,头戴虎皮帽的武士形象。①参段文杰 《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以虎皮作为衣饰不仅在大臣服饰中出现,赞普衣饰中也同样使用虎皮。虎皮衣饰已不再仅限于吐蕃政权中勇武臣属所使用,向上扩展到赞普日常服饰中,突出展示了吐蕃社会尚武精神与军事立国的传统。
四、接受者与大虫皮、告身之关联
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松赞干布早期,完善各种法令制度,制订“以万当十万之法 (khri-rtse-vbum-bzher)”作为六法之首,用于奖励贤良的告身制度包含在六法之内。南日松赞时期,内侍扈从官尚囊在宴会上驳斥了居功自傲的大臣琼保·邦色 (苏孜),得到赞普赞赏,被任命为论布之职,还授予了小银字告身②参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第163页。陈践践教授曾告知笔者,认为此处小银牌告身的中间镶嵌有冰珠石,属于告身的一种形式。,这是关于告身的最早记载。
对于勇者而言,用于奖励勇者的大虫皮与奖励贤者的告身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就目前文献而言,因吐蕃王朝早期文献关于大虫皮的记载缺失,早期大虫皮与告身关联性无从得知。大尚论贝·囊热拉赞标志是 “穿虎皮袍、饰以碧玉之文字告身及大雍仲之文字告身以及珍宝、黄色宝石文字告身等”,表明囊热既被授予高规格的告身同时又享有身穿虎皮袍的特权。据P. T. 1288《大事纪年》载: “及至兔年 (763),……蕃地举行大议事会,对大尚论予以褒奖。授大论囊热以白宝石文字告身,任命为大论。”③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第97页。囊热于公元763年担任吐蕃大尚论,我们相信在墀松德赞时期,传统告身制度和大虫皮制度已在吐蕃政权核心层的 “大尚论”级别的官员中并行使用。P. T. 1217《一封文告的副本》④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吐蕃文献选》,第58-59页。内容为一名叫达日札夏的边将因不满上级对其战功仅奖赏虎皮鞍鞯告身而申诉告身的文告,如愿终获小银字告身。《贤者喜宴》记载 “保卫边境哨卡者”可授小银文字告身,⑤[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36页。达日札夏属于保卫边境哨卡之列,级别应与P. T. 1089《吐蕃职官考信录》中 “副都督”⑥王尧、陈践 《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10页。大致等同。据陈氏解题,认为文书中 “龙年”当指 “800年或812年”,⑦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第97页。笔者认为 “龙年”为公元812年更为准确,P. T. 1217号提到 “达日札夏于赞普政躬幼年时,臣下麦啜叛离”,与 《谐拉康碑 (甲)》载: “迨父王及王兄先后崩殂,予尚未即位,斯时,有人骚乱,陷害朕躬。”应同为赤德松赞幼年朝廷内乱之事,边将达日札夏为赞普的支持者,《唐蕃会盟碑》中吐蕃方面参与盟誓臣属位列首位者为 “钵阐布允丹 (dpal chen po yon tan)”,《仁达摩崖造像》题记①霍巍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关于 《仁达摩崖造像》题记译文,还可参考恰白·次旦平措撰文,郑堆、丹增译 《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 《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78页;土呷 《吐蕃时期昌都社会历史初探》, 《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第85页。霍巍教授指出,恰白·次旦平措译文中的赞普年号 “赤松德赞”系笔误,应是 “赤德松赞”,参氏著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325页。中已明确了赤德松赞时期,“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口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赤德松赞在位时间为公元798年至815年,而这一时间段内只有公元804年为猴年,题记中 “猴年”应为公元804年,表明该时间点以后比丘阐卡云丹参政合法化得以确认,并位于大尚论没庐赤苏昂夏等人之前。那么,《仁达摩崖造像》题记 “比丘阐卡云丹”、P. T. 1217号 “大尚论喻寒波掣逋(zhang yun chen bo yon gal)”以及 《唐蕃会盟碑》“钵阐布允丹 (dpal chen po yon tan)应同属一人。因此,我们推测P. T. 1217号所载 “龙年”时间在公元804年以后,即第二个龙年 (812)。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公元9世纪早期,两种告身并行使用的适用对象已由高级官吏延伸至中低级官吏,并广泛适用于吐蕃统治区域。
《虎皮残卷》包含大量大虫皮和告身信息,如 “大金告身与虎皮褂” “大银告身与虎皮鞍鞯告身”“红铜告身和草豹桑踏告身” “小黄铜告身和虎皮鞍鞯告身” “大黄铜告身和虎皮褂告身” “小黄铜告身和虎皮蹬垫告身”。大金告身和大黄铜告身均可与虎皮褂对应、大银告身与小黄铜告身均可与虎皮鞍鞯告身对应,而具有小黄铜告身品级的官员又可同时与虎皮鞍鞯告身、虎皮蹬垫告身对应。大金告身与大铜告身之间相差颇罗弥告身与银告身两大等级的告身,却都可授予虎皮褂告身,低等级大铜告身获得者鲁多杰历 (klu-dog-rgyal-[slebs])获得虎皮褂。陆离教授推测: “吐蕃官员的等级排列有可能是将所授告身等级和虎皮制品等级相加,告身和虎皮制品两者等级总和高者排位靠前。”②陆离 《关于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再探讨——英藏新疆米兰出土古藏文文书Or. 15000/268号研究》,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 《藏学学刊》第16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但笔者认为官职品级高低似乎与虎皮告身授予规格没有必然联系,军功大小是衡量大虫皮规格高低的唯一标尺,更表明大虫皮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与体现。③王东 《西域出土一份古藏文文献补考》,《敦煌研究》2015年第3期,第76页。因在P. T. 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④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326-337页。条文中,以告身等级来决定赔偿数额,丝毫未体现到大虫皮告身的特权。莫高窟第144窟东壁供养人题记 “夫人蕃任瓜州都□ (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如祥□ (弟)一心供养”⑤敦煌研究院编 《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5页。题记中康公官职后依次为 “金银间告身” “大虫皮”,告身位于大虫皮之前,表明康公更重视“告身”故将告身列于官职之后。因此,赵心愚教授指出:“由于虎皮袍也是一种荣誉性标志,或为一种勋号、职官名号,与告身有相同之处,樊衡露布中的几位无告身的吐蕃将领,也可能拥有的是这一类的标志。”①赵心愚 《唐樊衡露布所记吐蕃告身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74页。
告身作为贤良标志,是赞普信任依据之一。赞普与大臣盟誓中无不强调告身的重要性,《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中 “论达扎路恭之子孙后代,无论何时,地久天长,赐以大银字告身,永作盟书证券,固若雍仲。……论达扎路恭之子孙后代,当其手执盟誓文书,或因绝嗣,或遭罪谴,亦不没收其银字告身。”②陈践、王尧译注 《吐蕃文献选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2页。《仁达摩崖造像》题记③题记内容详参土呷 《吐蕃时期昌都社会历史初探》,《西藏研究》2002年第3期,第95页。提到“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赤德松赞在位时间是公元798年至815年,中间只有804年为猴年,期间,赞普曾与娘·定埃增盟誓:“其 (娘·定埃增家族)永久持有之告身及家世令名不得湮没,所任职司大位仍着令继续操持。”④陈践、王尧译注 《吐蕃文献选读》,第89页。但其在此时不再担任僧相一职,⑤林冠群 《唐代吐蕃僧相官衔考》,《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第66-67页。可能贝吉云丹已接任该职位。这里告身应是 《仁达摩崖造像》题记中 “金以下告身”,拥有世袭罔替特权,吐蕃僧人参政合法化,云丹成为吐蕃僧相。长庆会盟中,“□□□□□□政同平章事沙门钵阐布允丹”,⑥王尧 《唐蕃会盟碑疏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94页。云丹以吐蕃宰相身份参与会盟,位列吐蕃众官员之首。僧人被授予告身的现象,使得从早期近臣、重臣扩展至僧侣这一特殊社会阶层,更突出告身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载,达日札夏得到虎皮鞍鞯告身并不满意,而要求告身赏赐,最终获得满足 (虎皮鞍鞯告身的基础上,又授予小银字告身),意味着他更看重具有某种特殊政治意义的告身。敦煌莫高窟第144窟东壁供养人题记中,从康公姓氏来看,属昭武九姓之一,应为粟特人,因此,大虫皮除授予吐蕃本土将士外,还授予占领区有战功的其他民族,这也P. T. 1089《吐蕃职官考信录》中也得到证实,除了吐蕃人外,还有唐人、于阗人粟特人等。
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长期对河陇统治,吐蕃化特征凸显,藏语仍作为官方语言在河西地区使用。⑦G. Uray,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Journal Asiatique Vol. 269, No. 1/2. 1981, pp. 81-90; [日] 武内绍人 《归义军期からのチべット语文书とチベット语使用》, 《东方学》第104期,2002年,第124-106页 (逆页);Tsuguhito Takeuchi,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n (9th-12th c.),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2004, pp. 341-348.大虫皮制度无疑得到了延续,至五代、北宋时期,这种制度在吐蕃政治生活中仍有所体现。中原统治者对朝贡吐蕃部族使者或首领所赐虎皮 (或虎皮翻领)已失去原来与官职、社会政治地位的对应关系,演变成为身份尊贵的荣誉性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