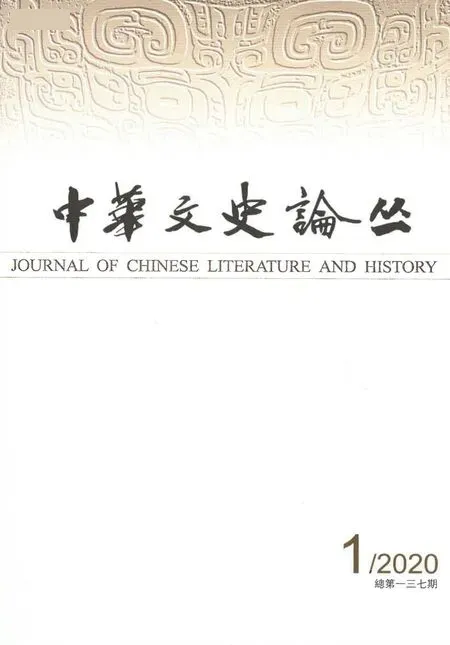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
徐大軍
提要: 底本、録本、擬編本代表了宋元時期與説話伎藝結緣的三種話本形態,其間藴含着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發展的基本邏輯和路徑,以及伎藝口演内容分解式文本化的演進過程。這種分解式的文本化,體現了口演内容從口頭形態轉化爲書面形態的矛盾衝突與碰撞調適,它作爲一種方式,寓含了一個立場,即基於書面編寫而對伎藝口演内容的主動性文本化意識;作爲一個過程,寓含了一個方向,即從伎藝故事負載的文本化向着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的轉變。擬編本所表現出的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方式,確立了朝着文體話本發展的文本化方向,並得益於宋元之際書面編寫領域重要變革的促進,引動了話本文體這一書面文體的出現。
關鍵詞: 伎藝話本 文體話本 文本化 録本 擬編本
宋元時期那些可以歸類於“話本”的書面文本在形態、體制上並不一致,甚至相互牴牾,有文言的,有白話的;有散文的,有韻文的;有講唱體制的,無講唱體制的。對於這些話本的屬性認定,有的着眼於文本的功用,有的着眼於文本的體制;有的定其爲底本,有的定其爲録本。但無論如何,這些觀點都糾纏着書面領域、伎藝領域的格式體例因素,這也是話本一直關涉的兩個領域,即使到了“二拍”這樣的個人獨創型話本時期,仍然保留着來自説話伎藝的體制因素。當然,這些話本所體現的伎藝、書面兩個領域的關係狀態(多少、疏密、隱顯)是不同的,比如所謂的底本、録本,並不必有説話伎藝的表述體制,它們之所以被歸屬於話本,乃因其爲伎藝而作,或由伎藝而來;而所謂的擬編本,即使故事未經伎藝口演,即使語體不是口語白話,但因其表述體制有説話伎藝的程式格套,亦被歸爲話本。前者着眼話本的故事情節用於或來自説話伎藝,可稱之爲“伎藝話本”;後者着眼話本的敍述體制取用自説話伎藝,可稱之爲“文體話本”。
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有一個長期累積、演進的過程,出現了不同形態的書面作品,它們並非處於話本小説發展進程的同一層面或同一階段,我們不能如“底本説”、“録本説”那樣把它們歸於同一屬性來認識。立足於話本一端,學界普遍認爲話本文體的體制因素來自於説話伎藝,宋元説話伎藝的繁盛是導致話本小説興起的直接原因,由此説明説話伎藝的表述手段、體制因素已經從伎藝表演領域進入到書面編寫領域。可是,從伎藝一端來看,伎藝口演内容進入書面領域後,是否就能整體、齊備地落實於文本,是否就會必然地出現所謂的宋元話本,從而走向一個書面文體的生成呢?基於這一思考路徑,本文即立足於伎藝一端,重新梳理一下宋元時期形態紛雜的話本小説與説話伎藝的關係,進而考察伎藝口演内容進入書面編寫領域而進行的“文本化”,是如何把口演内容落實於書面文本的,又是如何能够走向一個書面文體的生成路徑的。
一 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的三種文本形態
討論話本問題時,會涉及文本與伎藝的關係。在話本的學術史上,最通行的底本、録本兩種説法都是立足於這個關係框架,而針對的都是話本的出現問題: 一者,指出了文本的來源(而不是文體的來源),即這些文本是因爲説話伎藝而出現的;二者,指出了文本的功用(而不是文本的體制),即這些文本是緣於説話伎藝而存在的(或爲伎藝而編寫,或據伎藝而書録)。(1)胡士瑩指出:“話本本身原不是説話,它是按照‘説話’的藝術形式記録下來的。……它開始被寫下來的目的,不是爲了文學,而是爲了職業,爲了實用。”《話本小説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31。所以,底本、録本這兩個名稱,是站在書面領域的話本一端,着眼於這些文本的功用,而非這些文本的體制;着眼於“伎藝話本”的屬性,而非“文體話本”的屬性。可是,在話本的討論框架中,底本、録本卻又都指向於同一種文體意義上的話本形態,這是把宋元時期的話本作品視爲同一層面、同一屬性的文本了。如此一來,這兩種説法就不得不面對一些作品屬性歸類上的尷尬,因爲對於通行看法的“宋元話本”來説,若視之爲“底本”,則必須面對《醉翁談録》、《緑窗新話》中那些文言表述的故事,因爲它們是專門爲伎藝編寫的文本;若視之爲“録本”,則必須面對《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那樣的文言表述的作品,然而它明顯不是來自於伎藝講唱内容的記録。
實際上,宋元時期,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之間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出現了多種文本形態,按照它們與説話伎藝的結緣形態,有底本、録本、擬編本三種類型,(2)這三種話本形態的劃分及其擬名,參照了前輩學者的相關論述。胡士瑩在談到話本的出現時認爲:“初期的話本,並不是書面的著述,而只是説話人所説故事的書面記録或底本。”《話本小説概論》,頁131。石昌渝言及話本小説的生成時指出:“書面化的‘説話’就是話本小説。話本小説不是説話人的底本,而是摹擬‘説話’的書面故事。它最初是記録‘説話’加以編訂,發展下去它同時也采集民間傳聞進行編寫,還選擇一些傳奇小説和筆記小説的某些作品加以改編。”《中國小説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頁230。分别代表了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的三種文本屬性。
(一) 底本
底本是緣於説話伎藝而出現的,服務於説話伎藝的文本。但藝人需要底本提供什麽呢?這就涉及藝人如何使用底本的問題了。藝人的伎藝表演屬於口頭創作,他需要按照伎藝的程式格套,進行場上的口頭表演。這一環節屬於伎藝領域,而非書面領域,即書面領域無需提供伎藝領域的因素。魯迅《中國小説史略》談到“宋之話本”時説:“説話之事,雖在説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爲話本。”(3)魯迅《中國小説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3。語中稱説話藝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就指出了説話伎藝的口頭創作屬性,它講究的是藝人遵守伎藝的口演體制,把程式格套、故事情節進行當場捏合,而不是照搬現成的書面文本來演述,此即陳乃乾所説的“以話爲主”、“各守其家數師承而已”。(4)陳乃乾《三國志平話跋》言:“宋元之際,市井間每有演説話者,演説古今驚聽之事……大抵與今之説書者相似,惟昔人以話爲主,今人以書爲主。……昔之説話人則各運匠心,隨時生發,惟各守其家數師承而已。”並指出宋代“演説話”者有“話”而無“本”,而“話”指代故事的口頭講演形態或口頭講演形態的故事。《陳乃乾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頁361。
如果藝人的表演如魯迅所説的“有底本以作憑依”,那麽又是依憑底本的什麽呢?魯迅是最早提出“底本”概念的,他依據的文獻是吴自牧《夢粱録》(成書於南宋末年)卷二“百戲伎藝”條有關“話本”的記述:“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弄此多虚少實,如巨靈神、姬大仙等也。……更有弄影戲者……杭城有賈四郎、王升、王閏卿等,熟於擺佈,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間耳。”(5)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録(外四種)》,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頁304—305。另外,早於此書的《都城紀勝》(成書於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即公元1235年)亦有相類記述。(6)《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言:“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虚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録(外四種)》,頁86。魯迅據此把話本解釋爲“説話藝人的底本”,而學界普遍把這“底本”理解成具有口演體制的書面作品。其實,這種伎藝底本性質的“話本”在當時的傀儡戲、影戲、雜劇、講史、崖詞等伎藝中都存在着,它們題材相通,形態相近,各家伎藝即據此而按各自的體制規範進行口頭創作性質的加工、表演。上述兩則筆記所説的“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着眼的就是這些伎藝底本在故事内容上“大抵多虚少實”、“大抵真假相半”這一相同的題材性質,而不是指它們的伎藝底本體現出了相同相類的形式體制(實際上各家伎藝的形式體制也不可能相同)。因爲在當時,伎藝口演體制尚未成爲書面領域的表述體制因素,而只是伎藝領域的表述體制因素,是藝人的基本藝能——藝人要按照伎藝的體制規範來進行口頭創作,而伎藝底本不需要也不可能負載這些伎藝領域的格式成分。所以,底本不需要呈現伎藝口演的形式體制,其形態並非後世作爲書面文體的話本小説樣式。
至於底本是什麽形態的呢?南宋羅燁《醉翁談録·小説開闢》提到了説話藝人要熟悉《太平廣記》、《夷堅志》、《琇瑩集》等故事類作品,如此一來,它們在伎藝領域也就相對地具有了底本的功用。但它們又皆非爲伎藝準備的作品,不能視爲真正的説話藝人使用的“底本”。而真正的底本乃是那些專門爲伎藝編寫的資料書。石昌渝即認爲:“説話人有一些是瞽者,他們只能靠耳聞心受,依賴不了底本,即使有底本,那底本也不會是今天看到的話本小説的樣子,大概只是一個故事提綱和韻文套語以及表演程式的標記。”(7)石昌渝《中國小説源流論》,頁230。周兆新也指出:“如果我們認爲説書藝人有底本,那麽這種秘本就是底本。秘本的内容大致包括兩部分。一是某一書目的故事梗概,二是常用的詩詞賦贊或其他參考資料。”(8)周兆新《“話本”釋義》,《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97。根據這樣的認識,許多學者就直接指出南宋皇都風月主人《緑窗新話》、羅燁《醉翁談録》就是這類爲説話伎藝編寫的資料書,(9)程毅中《宋元小説研究》指出“《緑窗新話》是説話人必用的參考書”,“是供説話人據以敷演故事的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87,188。董上德《論〈醉翁談録〉的性質與旨趣》一文認爲,《醉翁談録》“是一部專供‘小説’和‘合生’藝人參考使用的、以男女風情爲旨趣的故事與資料的類編”。《學術研究》2001年第3期。此外,胡士瑩、陳汝衡都表達過相同的觀點,參見《話本小説概論》,頁150,152;《宋代説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頁91。而盧世華更明確提出,宋代書會才人參與編寫的、用於説話伎藝的“底本”,如《醉翁談録》、《緑窗新話》,只是爲藝人講説而準備的參考材料,以文言出之,而非以白話出之,與後來的用於閲讀的話本小説不同。(10)盧世華《試論宋代説話人的底本》,《江漢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6期。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文本屬性,就是不提供伎藝範疇的口演體制因素。
(二) 録本
録本也是緣於説話伎藝而出現的一種話本形態,只是它來自於説話伎藝的書録,是由説話伎藝口演内容記録、整理而來的書面文本。那麽,“録本”記録伎藝口演内容的什麽?形態又如何?
在話本小説的討論框架中,録本被用以指向所謂的宋元話本小説,即宋元話本小説被認爲是由説話伎藝口演内容的記録而來。胡士瑩指出:“話本本身原不是説話,它是按照‘説話’的藝術形式記録下來的。”(11)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頁131。周兆新認爲宋元話本“都不是底本,而是依據説書藝人口述整理而成、專供廣大羣衆案頭欣賞的通俗讀物”。(12)周兆新《“話本”釋義》,《國學研究》第二卷,頁202。基於話本即“録本”的認識,胡士瑩、章培恒認爲宋代並無話本小説。章培恒認爲,所謂的“宋代話本”並不存在,宋人並無針對文本形態的白話小説的編寫和刊刻,我們至今無法確定宋刊白話小説文本的實物存在。(13)章培恒《關於現存的所謂“宋話本”》,《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1期。胡士瑩指出《醉翁談録·小説開闢》所列舉的一百一十七種名目指的是伎藝性故事,並没有與之相對應的書面形態,所以,宋代有口頭的“話”而無書面的“本”。(14)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頁235。
但是,站在説話伎藝一端,對於伎藝口演内容的書録,其結果並非必然是後世話本小説的樣式,故而即使話本小説在宋代不存在,但録本肯定是存在的。胡士瑩認爲早期話本是對藝人口頭講唱内容的記録,但又特作强調:“在記録時,不可能是故事的全部,往往是較爲主要的精彩部分,内容簡要,有的只是一個故事的輪廓而已。”(15)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頁131。按照這種思路,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個記録伎藝口演内容的書面文本,並非是把藝人的口演内容整體、齊備地落實於文本,而是選取伎藝口演的部分内容落實於文本,基本的原則是剪輯故事情節,甚至要作文言語體的轉化。
《緑窗新話》是南宋初年編輯的短篇文言小説集,它被普遍認爲是説話人必用的資料彙編,程毅中即認爲“其中有不少是已知話本的素材,還有一些故事可能就是當時説話故事的紀要”,(16)程毅中《宋元小説研究》,頁187。比如《郭華買脂慕粉郎》、《楊生與秀奴共遊》、《章導與梁楚雙戀》等,就是來自於伎藝口演内容的故事文本,只是經過了文言語體的轉换。當然,有的故事文本在人物語言上保留了口語白話,但即便如此,它們仍有一個簡略的文言敍述框架。而更爲普遍的做法是要進行文言語體的轉换,這是當時文言編寫環境中書面領域呈現口傳故事的常規做法,唐代白行簡的文言小説《李娃傳》以及宋代洪邁《夷堅志》中的許多作品皆如此。
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録》是另一部被視爲説話人使用的資料書、參考書,其《小説開闢》一篇所載録的一百一十七種説話名目中,有一些在該書中有相對應的文言故事文本,比如《李亞仙不負鄭元和》(癸集卷一)之於《李亞仙》,《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壬集卷一)之於《鴛鴦燈》,《王魁負心桂英死報》之於《王魁負心》,《樂昌公主破鏡重圓》(癸集卷一)之於《徐都尉》,《韓翊柳氏遠離再會》(癸集卷二)之於《章台柳》,等等。然而,説話名目只是表示當時存在着流傳於藝人口頭的伎藝故事,屬於活態的口演故事,並不指代書面作品。而這些敍述簡短的文言故事文本,對於説話伎藝來説,則是一個底本,這與《醉翁談録》總體上的説話人資料書屬性相適配;再溯及它們的故事内容來源,則應是來自當時活態的口演故事。也就是説,這些文言故事文本屬於伎藝口演故事的録本,只是作了情節内容的簡略,並予以文言語體的轉化表述。
與底本一樣,這些録本同是緣於説話伎藝而出現的,但二者與説話伎藝的關係並不相同,底本指向於伎藝表演,而録本則指向於書面閲覽。在伎藝領域,藝人在底本基礎上,有一個“加伎藝語境”的過程,即按照説話伎藝的程式規範作口頭創作的表演。而在書面領域,編寫者在伎藝口演内容的基礎上,則有一個“去伎藝語境”的過程,因爲在説話伎藝初興之時,其口演體制尚僅僅屬於伎藝領域的表述方式,而未進入書面領域成爲書面編寫的表述體例。所以,録本不一定要把伎藝口演的全部内容記録下來,也不一定就呈現出後世話本小説的樣式。故而這些録本在故事情節上,有的是詳細的描述,有的是簡略的剪輯;在表述語言上,有的使用説話伎藝的白話語言風格,有的使用當時書面編寫通用的文言語體風格。如此一來,那些書録説話伎藝口演内容的文本,就不會必然是形態一致的書面作品,就會出現經過情節剪輯、文言轉述而無口演格式的書面作品。雖然這還不是後世話本小説的樣式,但不能否認它是由説話伎藝口演内容書録而來的文本。
(三) 擬編本
擬編本是摹擬説話伎藝形態的書面故事文本。所謂的摹擬説話伎藝形態,摹擬的是説話伎藝的口演體制,而非書面的底本、録本這樣的話本體制。那麽,這個“擬編”是否如胡士瑩所説的“依照説話的口氣、方法,寫成一個概略”(17)胡士瑩認爲記録説話伎藝的口講内容而出現話本,又説:“説話人原來口頭嫻習的成套的老故事,已不能適應廣大市民的要求,於是出現了文學市場,一些文士們組織了書會,專門替説話人編撰話本(也有説話人自編的)。他們多方搜羅歷史故事、民間傳説和當代新聞,自出機杼編造一些故事,依照説話的口氣、方法,寫成一個概略,提供給説話人,説話人憑着自己的生花妙舌,添枝添葉,在書場上獻技。”《話本小説概論》,頁131。呢?
根據現知相關文獻來看,擬編本並非必須在整體上按照典型的説話伎藝形態(故事情節、表述語言、體制格套等)來摹擬編寫,因爲有的擬編本並未采用説話伎藝的故事情節,只是在體制格套上摹擬説話伎藝,或者只是在敍述語言上摹擬説話伎藝。
元代刊刻的《五代史平話》一書,寧希元、丁錫根將其與《資治通鑑》的五代史部分對勘後,認爲它是依據《資治通鑑》改編而成的,但其編寫又在體裁、語言和細節描寫等方面受到民間講史伎藝的影響。(18)寧希元《〈五代史平話〉爲金人所作考》,《文獻》1989年第1期。丁錫根《〈五代史平話〉成書考述》,《復旦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5期。比如《五代唐史平話》卷上敍李嗣源軍隊與契丹的幽州一戰:
契丹以馬軍萬人拒之於前,將士皆驚愕失色,李嗣源獨將馬軍百餘人先犯陣出馬,免胄揚鞭,用胡語與契丹打話道:“是汝無故犯我邊塞,晉王使我統百萬之衆,直趣西樓,滅汝種類。”説罷,躍馬奮檛,三入契丹陣,斬訖酋長一人。後軍相繼殺進,契丹兵退卻,晉軍盡得出。李存審下令使軍人各伐樹木爲鹿角,每一人持一枝,到止宿處,則編以爲寨。契丹馬軍從寨前過,寨内軍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積屍滿路。(19)丁錫根編《宋元平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80。
對照《資治通鑑》相應敍述段落,(20)《資治通鑑》卷二七《後梁紀·均王貞明三年》記:“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8818。編寫者是謹按史書而作説話伎藝表述語言風格的白話翻述。這樣的情況在《五代史平話》中不止一處,在《全相平話五種》中亦存在,比如《秦并六國平話》卷下敍劉邦攻陷咸陽並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一節,即是根據《資治通鑑》卷九高祖皇帝元年所記内容的白話翻述。
同樣是摹擬説話伎藝的部分因素,有的擬編本只是體制格套來自於説話伎藝。《清平山堂話本》中有《藍橋記》一篇,它與南宋羅燁《醉翁談録》辛集卷一《裴航遇雲英於藍橋》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且二者皆以文言呈現,文字敍述幾乎全同,並且二者與原作裴鉶《傳奇·裴航》的不同之處亦相互一致。只是《藍橋記》框套了説話伎藝的入話、散場詩格式,在開頭加了以“入話”領起的四句詩:“洛陽三月裏,回首渡襄川。忽遇神仙侣,翩翩入洞天。”在結尾加了以“正是”領起的兩句散場詩:“玉室丹書著姓,長生不老人家。”(21)程毅中《清平山堂話本校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01,103。
與此類似,有的擬編本則是在正話的敍述段落中框套了説話伎藝格式。比如《秦并六國平話》多有以“話説”領起的文言敍述段落,此書卷下敍及田儋事迹一節:“話説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傑人。陳王令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太守。田儋佯縛其奴之廷,欲謁見狄令,因擊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田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齊地。”(22)丁錫根編《宋元平話集》,頁655—656。此段敍述以伎藝口演體制中常用的格套語“話説”領起,其下相從者爲純正的文言敍述,考其來源,乃抄録《資治通鑑》原文。(23)《資治通鑑》卷七《秦紀·二世皇帝元年》記:“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横,皆豪健,宗强,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頁262。這種情況亦見於《五代史平話》,此書常見以“話説”、“卻説”、“話説裏説”(此套語用於引領插敍段落)領起的文言段落,如《唐史平話》卷下敍述劉皇后一節:
卻説那劉皇后生自寒族,其父以醫卜爲業,幼年被擄入宫,得幸從唐主。在魏時,父聞其貴,詣魏州上謁,后深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爲亂兵所殺,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宫門外。后性狡悍淫妒,專務蓄財,如薪蔬果菜之屬,皆販賣以求利。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 一以獻天子,一以獻中宫。皇后無所用,惟以寫佛經佈施尼僧而已。(24)丁錫根編《宋元平話集》,頁99。
對照《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五相應段落,(25)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五“唐立夫人劉氏爲后”條記:“后生於寒微,其父以醫卜爲業。后幼被掠得入宫,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宫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販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爲二: 一上天子,一上中宫。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朱子全書》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3219—3220。“卻説”領起的文言部分與之高度重合,明顯是據史書原文的抄録。
上面所列話本的主體故事皆來自現成的文言作品,但又簡單地混合了“話説”、入話、散場詩這些屬於伎藝口演體制的成分。據此而言,這種話本肯定不是伎藝口演内容的記録,而是屬於前文注引中石昌渝所説的“摹擬‘説話’的書面故事”,是立足於書面編寫而取用了説話伎藝的體制格套,並與現成的文言作品混合而成的擬編本。
另外,《藍橋記》一篇立足於書面編寫而取用伎藝格式的文本屬性,又引導我們看到了《清平山堂話本》中更多的擬編本方式。
《清平山堂話本》所輯多爲早期的話本,各篇“正話”的文本形態頗爲雜亂。一者,各篇“正話”的語體樣式並不一致,有的是文言表述(《藍橋記》、《漢李廣世號飛將軍》),有的是韻文表述(《快嘴李翠蓮記》、《張子房慕道記》),有的則是白話散體表述(《簡帖和尚》、《合同文字記》);二者,各篇“正話”的故事來源並不一致,有的來自前代的書面作品,有的雖然來自伎藝的口演内容(或是現成的伎藝故事的録本),但來源的伎藝又不單一,或是“小説家”説話伎藝(《簡帖和尚》、《合同文字記》),或是詞文類伎藝(《快嘴李翠蓮記》、《張子房慕道記》)。
然而,無論各篇“正話”的文本形態如何不一致,從總體上來看,除了幾篇首尾殘缺的作品,《清平山堂話本》中各篇皆框套了同一種伎藝口演體制的結構程式——開篇有“入話”領起的詩詞,結尾有“正是”領起的散場詩,無論是白話敍述者,還是文言敍述者皆如此,即使《洛陽三怪記》一篇没有“入話”二字標識,但它實際上仍有作爲“入話”開篇的四句七言詩。這説明這些話本並非由記録伎藝口演内容而成篇,而是有意識地取用伎藝口演體制而作書面擬編,並且表現出了對伎藝口演格式的有意識地選擇,比如《藍橋記》一篇只是選用了入話、散場格式,而“正話”則使用了文言語體表述。由此可以説,《清平山堂話本》中那些“正話”形態雜亂而框架體例統一的文本,乃是立足於書面編寫而統一取用了伎藝格式以作文本擬編後的結果。
具體來看《藍橋記》這樣的擬編本,其“正話”來自於現成的文言作品,而非來自説話伎藝口演内容的書録,這已然屬於作家立足於書面編寫而摹擬伎藝體制格式的一次文學創作實踐。立足於擬編本一端,我們追索其敍述體制的諸種成分的來源,雖然仍要溯至説話伎藝的口演體制,但擬編本中的伎藝體制因素已不是出自對伎藝口演體制的直接抄録式的模擬,而是經過了此前録本階段對於伎藝口演體制的過濾、改造、調適,最後形成了一種故事文本編寫的書面表述方式,這正是擬編本據以進行反復編寫實踐的體例規範。所以,底本、録本、擬編本三種文本形態,一同關聯了説話伎藝體制因素文本化形態的演變進程。
那麽,説話伎藝的口演體制是如何成爲書面文體的標誌性特徵的?擬編本的敍述體制中那些原本屬於伎藝範疇的成分,又是如何成爲書面領域的表述方式、編寫體例的?這個問題值得深加探討,因爲它關乎一個書面文體生成的基本邏輯,以及伎藝口演内容進入書面編寫領域後的演進軌迹。
二 録本、擬編本是説話伎藝文本化的兩種形態
根據上文分析,底本、録本、擬編本三種話本形態皆與説話伎藝的諸種因素有着或多或少的關聯。其中,底本是服務於伎藝口演,藝人各守規範,根據它進行口頭創作和表演,如此,從書面的底本到伎藝的口演,有一個書面内容的“伎藝化”問題,這是伎藝領域的事;而録本、擬編本,皆針對説話伎藝的某些口演成分而作書面呈現,如此,從伎藝的口演到書面的文本,有一個口演内容的“文本化”問題,這是書面領域的事。
立足於書面領域,我們看到話本具有源於伎藝的故事情節、敍述體制和語言格套,只是應注意到,並不是話本的全部成分都來自説話伎藝。比如擬編本的敍述體制原生於伎藝,但故事及其文本並不一定來自於伎藝;即使較擬編本更爲近緣於説話伎藝的録本,我們説它是記録伎藝口演内容而成篇,但這個記録的忠實度也不會很高,並且不會必然出現口演内容整體性地落實於文本的情況。因爲對於伎藝的口演内容來説,録本是要按書面編寫的表述規範來呈現的,甚至要經過文言語體的轉换。
我們知道,伎藝口演内容是藝人按伎藝規範來呈現的,如果藝人有底本以作依憑,則表演時會有一個對底本的伎藝化過程,需要一個“加伎藝語境”的環節。而伎藝口演内容落實於書面文本,則需要按照書面規範來予以呈現,這是一個“文本化”的過程,其間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伎藝口演内容在口頭形態、書面形態之間的生存狀態的變化,以及伎藝語境的内容與書面呈現的體例之間的矛盾衝突。因爲那些伎藝範疇的體制因素,比如入話—正話敍述結構,以及講説人語氣的白話表述和程式化套語,皆是因口頭創作而生成,因口頭講唱而存在的。而書面呈現的規範則是按照書面語言的表述規範而形成的,它不會天然地與口頭表演的格式、體制相調適融合。所以,伎藝口演内容在落實於文本的過程中,不可能一步到位地適應書面領域的各種表述規範和文本體例,其間肯定有對伎藝語境的口演内容的排斥、接納、改造過程。《清平山堂話本》中那些形態雜亂不一的話本就是這種伎藝口演内容與書面呈現規範相互調適的結果。據此而言,話本中的録本、擬編本所負載的説話伎藝口演内容諸種成分的文本落實,並不是整體的、齊備的,而是局部的、分離的,存在着一個分解式落實於書面文本的過程,其間藴含着伎藝口演内容從口頭形態轉化爲書面形態的矛盾衝突與碰撞調適。
具體來看,宋代就已出現了話本的録本形態,這説明當時已經出現了説話伎藝的文本化現象,只是這一文本化是立足於書面編寫的立場而對口演内容的選擇性取用,具體來講,就是針對口演内容的故事情節這一成分進行文本化。所以,雖然録本的故事肯定來自於伎藝,但文本呈現、敍述體制就不一定使用伎藝的方式、按照伎藝的規範了。上述《緑窗新話》、《醉翁談録》中那些來自説話伎藝的篇章所反映的文本化形態,就只是針對於故事情節的文本落實,並在表述上作了文言語體的轉换。
即使那些未作文言轉换,而以伎藝口演風格表述的話本,也並非就是記録了伎藝口演的全部内容。這有兩種情況,一是録本中那些只在人物語言上保留口語白話的文本,如《緑窗新話》中《陳吉私犯熊小娘》、《楊生與秀奴共遊》(下文詳述);二是擬編本中那些具有伎藝口演風格的正話,當是來自現成的節略録本,而被擬編本所采用,如《清平山堂話本》中《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陰騭積善》、《曹伯明錯勘贓記》等。它們有些情節不完整,邏輯不周全,完全没有《醉翁談録·小説開闢》所描述的説話人口演風采:“講論處不滯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26)羅燁《醉翁談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5。這些文本明顯擔不起書録説話伎藝口演内容這樣的結論。另外,在擬編本中還出現了單獨摹擬伎藝體制格套的情況,比如上文提及的《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或者單獨摹擬伎藝敍述語言風格的情況,比如上文提及的《五代唐史平話》。這些都體現了基於書面編寫而對説話伎藝體制因素的分解式文本落實。
再者,即使那些既作伎藝風格的白話表述,又有伎藝風格的敍述體制的話本,也不會是對伎藝口演内容的整體性文本落實。比如《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一篇,整體上有一個入話、結語的敍述框架,而入話小故事是唐末皇甫枚《非煙傳》的文言節略版,正話是説話伎藝風格的白話語體故事。此篇明顯是一個擬編本,它以現成的文言小説内容與伎藝口演内容的白話録本相混合,又鑲嵌在一個入話、結語構成的敍述框架之中。這對於説話伎藝口演内容的整體、全部來説,仍是分解式的文本化形態。
上面的梳理表明,在説話伎藝文本化的路途上,伎藝口演内容的諸種成分並非完整、齊備地落實於文本,而是可以與口演内容的整體相分離而單獨地落實於文本。從録本最初表現的故事情節單獨落實於文本,到擬編本表現的程式格套或語言風格單獨落實於文本,都説明了這個文本化不是伎藝領域的口演内容與書面領域的話本作品兩端的靜態關聯,也不是口演内容諸種成分因素在書面文本上的一一對應的落實,而是一種分解式的文本落實。
這樣一個伎藝故事從口頭講演到書面呈現的落實過程,對於説話伎藝的文本化來説,是分解式的文本落實;而對於書面編寫的内容取材來説,則是書面編寫對伎藝口演内容的選擇性取用。所以,這個伎藝口演内容的分解式文本化,首先是作爲一個方式,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立場,那就是説話伎藝的文本化藴含着來自於書面編寫領域的主動性。
説話伎藝口演内容的諸種成分因素是互相適配的,比如它的敍述程式、講演格套與口語白話是基於伎藝講唱而融合在一起的,但它們在進入書面領域後卻不能彼此伴隨而齊備地落實於文本中。因爲在書面領域,伎藝口演内容如何落實於文本,並不是伎藝領域的事,而是需要遵循書面編寫的表述規範,也不得不面對書面編寫的體例局限,編寫者只好遵從這些規範、局限,選取口演内容的一種或幾種成分而把它們落實於文本中。這表明説話伎藝的文本化從一開始就寓含了一個來自於書面領域的基本立場——書面編寫的主動性,即編寫者在面對伎藝口演内容時在材料取捨、呈現方式上的選擇態度,比如對於故事情節、敍述體制、語言風格等因素的選擇。
上文所述《緑窗新話》、《醉翁談録》中的那些篇章是選擇了説話伎藝的故事内容進行文本化,並在文字表述上作了文言語體的轉换。同樣作爲説話伎藝文本化結果的《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也表現出了這種書面編寫的主動性,它選取了説話伎藝的入話、散場詩程式因素,用以框套那個作爲正話的文言版藍橋故事文本。編寫者的這個主動性,是立足於書面編寫而面對故事材料、呈現方式等方面的選擇問題時,表現出的對伎藝口演内容諸種成分的取用,而不是基於記録、整理伎藝口演内容的目的而要把某一伎藝口演内容落實於文本。據此分析,我們即可認識到,這些話本中伎藝因素的存在,乃基於書面編寫而對伎藝口演内容諸種成分的吸納和取用,而這些話本所表現的表述語體不一、故事來源不同,則是出於編寫者對他所面對的各種材料主動選擇後的結果(編寫者面對的材料有口頭的、書面的,文言的、白話的,散體的、韻體的)。《清平山堂話本》中那些正話形態雜亂而框架體例統一的文本,即是這一主動的材料選擇、文本編寫後的結果。這種基於書面編寫而取用伎藝口演内容的編寫行爲,與《緑窗新話》節略説話伎藝口演内容而作文言轉换的編寫行爲一樣,都體現了書面領域對伎藝口演内容的主動性文本化意識——基於書面編寫而對伎藝口演内容的有意識的文本化。
其次,這個伎藝口演内容的分解式文本化,作爲一個過程,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方向。
説話伎藝口演内容可以各自分離而單獨地落實於文本,從一部或一類話本來説,是一個文本化的方式;從不同時期、不同類别的話本來説,則體現出一個文本化的過程——伎藝口演内容的諸種成分被逐步落實於文本中,一個個被書面呈現,並漸趨與書面表述體制調適、融合而成爲書面文體的標誌性因素,其間即存在着一個分解式文本化的過程。所以,這個分解式文本化,不但是一種方式,也是一個過程,一個複雜的、長期的累積演進過程。從録本階段把口演内容的故事情節落實於文本,到擬編本階段不依傍伎藝故事而進行伎藝體制因素的文本化,就是這個累積演進過程的兩個重要節點,其間湧動着一個重要的文本化發展方向——從伎藝故事負載的文本化向着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轉變。
上文提到《緑窗新話》、《醉翁談録》所體現的録本階段説話伎藝的文本化形態,是針對伎藝故事情節的文本落實,並在語言表述上作了文言語體的轉换,這屬於伎藝故事文本化主導的書面編寫。但有些録本並未作徹底的文言轉换,而是保留了口語白話成分。比如:
一夕,月明,熊氏領妮子惠奴出簾前看月,問陳吉:“睡也未?”又問:“你前隨官人入蜀,知他與誰有約?”吉曰:“不知。”熊氏遂入,一夜睡不着。……熊氏乃進抱吉曰:“我也不能管得。”遂爲吉所淫。(《陳吉私犯熊小娘》)
(楊廷實與散樂妓湯秀奴)一見兩情交契,海誓山盟。生亦不顧家有雙親妻子,行與秀奴比肩,坐則疊股,日夕貪歡,無時或棄。每相謂曰:“我兩個真正可惜,但願生同鴛被,死同棺槨。”(《楊生與秀奴共遊》)(27)皇都風月主人編《緑窗新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70,116。
在這些篇章中,它們的敍述語言、人物語言都表現出了一些口語白話的特色,尤其在人物語言中多見,亦尤爲明顯,但總體上仍是夾雜於文言敍述框架之中。在伎藝故事文本化總體上要作文言語體轉换的情況下,這些録本中出現的口語白話,是在書面呈現伎藝故事時對其語言表述風格的保留,並非基於書面編寫而有意識地模擬伎藝格調的口語白話所致。所以,這些録本中零散出現的白話表述,是負載於伎藝故事的文本化之中的,因爲要把伎藝故事落實於文本,而順便保留了其表述方式。這樣的説話伎藝文本化結果,是附庸於伎藝故事的文本化之中的,屬於伎藝故事文本化負載的表述方式。
但是,有些擬編本中出現的白話表述,已不是附庸於伎藝故事的文本化之中了,因爲它們的故事並非來自於伎藝講演。比如元代的平話文本中就出現了據史書作白話翻述的現象,雖然其表述語言的風格來自於伎藝,但故事情節明確來自於現成的文言作品;與此類似的情況還有擬編本中出現的伎藝程式格套,如平話文本中“話説”領起文言敍述段落,以及《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那樣以入話、結語程式框套文言敍述段落的作品,它們的故事情節也明確不是來自於伎藝。這説明伎藝體制因素已經不是作爲書面呈現伎藝故事的附屬品而出現在文本中了,而是脱離了伎藝故事,單獨作爲一種伎藝口演成分而進入書面領域,成爲書面編寫的一種表述方式了。那麽,這些擬編本即屬於伎藝體制文本化主導的書面編寫。如此一來,這些伎藝格調的語言表述、講唱套語就不是負載於伎藝故事的文本化之中了,而是基於書面編寫而模擬了説話伎藝的體制格式,有的取用了伎藝的語言表述風格,有的取用了伎藝的敍述程式格套。所以説,這些伎藝體制因素在擬編本中的出現,已不是附屬於以伎藝故事爲宗旨的文本化了,而是出於以伎藝體制爲宗旨的文本化,屬於伎藝體制文本化負載的表述方式。
伎藝故事負載的文本化出現於説話伎藝文本化的早期階段,這是以伎藝故事爲主體、目標的文本化,其書面呈現要遵從書面領域的體例規範,而零散的口演表述方式只是伎藝故事落實於書面文本過程中的附庸,負載於以伎藝故事爲宗旨的文本化之中。
至於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則是以伎藝體制爲目標的文本化。由此,那些伎藝體制因素就可以從口演内容中分解出來,作爲這個文本化的主體,被單獨用來作爲書面編寫的表述方式。於是,那些口演形態的程式、格套開始與書面編寫的體例規範相調適、融合,漸趨成爲書面領域的表述方式、體制因素。這説明説話伎藝的敍述體制因素已經可以獨立進入被書面領域接納、改造的軌道,能夠單獨落實於文本而成爲書面編寫的一種表述方式。如果沿着這個方向發展,説話伎藝的文本化就會走向書面文體的生成了。因爲隨着伎藝體制因素分解式地落實於文本,不同的伎藝體制因素一一落實於文本,在書面領域裏逐步地被調適、被改造、被融合,漸趨形成了一種書面編寫的表述方式甚至體例規範,而這些原來因伎藝口演而存在、適配於伎藝故事表述的各種伎藝體制因素,在進入書面領域之後就被改造成一個書面文體的構成要素、標誌特徵了。在此過程中,擬編本所表現出的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方向的確立是個關鍵環節。
這個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發展方向的確立情況,我們可以據《清平山堂話本》收録的作品稍窺一斑。
細勘《清平山堂話本》中的作品,形態有三: (1) 有《簡帖和尚》、《合同文字記》這樣的典型的話本小説樣式,其形態與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説》殘頁所示一致,有入話、散場詩組合的程式結構,有散體白話的敍述話語,有口演伎藝的格套和語氣。(2) 文言敍述與説話程式組合的文本,如《藍橋記》、《漢李廣世號飛將軍》,雖有入話、散場詩組合的程式框架,但納入其中的正話不是帶有説話格套、語氣的散體白話敍述,而是深淺不一的文言敍述。(3) 詞文敍述與説話程式組合的文本,如《快嘴李翠蓮記》、《張子房慕道記》,雖有入話、散場詩組合的程式框架,但納入其中的正話是以人物話語出現的大段詞文。而且,這些作品還表現出明顯的文本層次差異、内容來源差異。比如,語言上,有文言的,有白話的;語體上,有散體的,有韻體的;故事來源上,有來自於“小説家”説話者,有來自詩贊體講唱伎藝者,有來自書面文言或白話作品者。
需要强調的是,雖然上述三類文本的具體形態有如此差異,但它們都有一個入話、散場詩組合的程式結構框架。最值得關注的是《藍橋記》、《漢李廣世號飛將軍》這樣的文言敍述内容與説話伎藝程式組合的文本,明顯是基於書面編寫而混合了現成的文言故事文本和伎藝講唱格式。在此,入話、散場詩敍述體制已經作爲一種書面編寫時反復套用的敍述體制,初步表現出一種書面編寫的體制規範,既使用於有説話伎藝格式的白話故事文本中,也使用於無説話伎藝格式的文言故事文本中,而且還對其他講唱伎藝的文本化具有示範、引導作用。比如有人在把其他講唱伎藝的内容落實於文本時,也使用了這種爲時人所熟悉的口演敍述程式,《張子房慕道記》、《快嘴李翠蓮記》、《刎頸鴛鴦會》即如此,這樣的韻體詞文敍述内容與説話伎藝程式組合的書面編寫,就是基於通俗故事文本的編寫而取材非“小説家”伎藝的口演内容,並套用了已在書面編寫中相對定型的口演敍述體制。這表明入話、散場詩敍述程式已經從伎藝故事中被剥離出來,成爲一種書面編寫的表述體制,被用來對其他伎藝來源的口演内容進行書面呈現了。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説話伎藝的文本化過程中,伎藝口演内容的諸種成分在書面文本上的分解式落實情況。正因如此,這個分解式文本化會出現不同的文本化方向,由此出現了不同形態的文本化結果,所以,説話伎藝的文本化落實,並非一開始就會出現整體性的文本化,也不會必然地出現整體性的文本化,從而出現後世話本小説樣式的書面作品。雖然伎藝口演内容諸成分在伎藝領域是相互適配而融合呈現的,但這並不是它們進入書面領域後能夠整體性書面呈現的必然形態。因爲書面領域接受伎藝口演内容的何種成分,要取決於書面領域的接受觀念、表述能力和體例規範,而非伎藝領域的成熟程度和影響力度所能單方決定的。
另外,我們還應注意,在這個文本化的過程中,伎藝口演内容的諸種成分落實於書面文本,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上面所説的各種分解落實於文本的形態就是這個長期、複雜的文本化過程中的各種結果,我們把它們歸類於録本、擬編本。對於這些文本化的結果,如果站在話本作品一端, 我們可以籠統地説它們來自於説話伎藝,只是要注意它們並不是全部、整體地來源於説話伎藝的内容;而如果站在説話伎藝一端,我們可以看到它們把伎藝口演内容落實於文本的程度並不一致,性質並不相同,階段並不同步,由此有形態呈現上的差異,也有出現時間的差異,由此而處於這個文本化過程的不同節點。《緑窗新話》中那些經過文言轉述的伎藝故事節略,《藍橋記》那樣的文言敍述與伎藝格式相混合的文本編寫,《刎頸鴛鴦會》那樣的文言敍述、白話敍述與伎藝格式相混合的文本編寫,就是這些不同節點的體現。
由此我們知道,録本、擬編本的各種形態不同的文本作品,是這個文本化過程中的一個個文本化結果,處於這個文本化過程中的不同節點。雖然站在話本一端,我們會説它們與説話伎藝有關聯,有結緣,但當我們籠統地這麽説時,需要警醒,作爲説話伎藝的文本化結果,它們並不是處於同一層面的文本,而是處於這個文本化不同層面的書面編寫,而且是處在這個文本化過程的不同階段。它們呈現出的不同形態,乃由它們處於説話伎藝文本化的不同階段、不同層面所致。
三 説話伎藝文本化朝向文體話本發展的促動因素
擬編本作爲説話伎藝文本化的一個結果,它以及它所負載的書面表述體制是在這個文本化過程中出現的。因此,對於擬編本的出現,對於擬編本所負載的書面表述體制的出現,我們應該放在這個文本化過程中來考察,而不是放在文本與伎藝的因果關係框架中,説它是受説話伎藝影響而形成的,或是記録説話伎藝口演内容而生成的。因爲説話伎藝的影響並不是這個文本化的主動因素、直接動力;説話伎藝進入書面領域後也不會必然地朝着擬編本這個方向發展,而是存在着不同的發展方向。那麽,在這個文本化過程中,朝着擬編本發展的文本化方向是怎麽出現的呢?是什麽因素促成了這個文本化朝着文體話本的方向發展,促成擬編本這個結果出現的呢?
録本是説話伎藝進入書面領域後的第一個文本化形態,它以伎藝故事的文本化爲目的(而不以伎藝體制的文本化爲目的),即要把口演的故事内容呈現於書面文本。但其語言表述總體上還是遵循書面領域通用的文言編寫規範,具體表現出兩種情況: 一是轉换爲文言語體表述,二是敍述語言爲文言語體,而在人物語言中保留零散的口語白話。人物語言中出現的這些口語白話,不是以文言編寫立場或白話編寫立場“寫”出來的,而是以文言編寫立場“録”下來的。
其實,録本所體現的這兩種文本化形態,與當時口傳故事普遍的文本化形態是一致的,並没有超越這個時代對於書面表述語言的使用觀念和水平。
朱熹論古人文章,分“説”出來和“做”出來兩種:“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説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説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28)張伯行編《朱子語類輯略》卷八“論文”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73。由此而言,“説”出來的文章就是對口説内容的記録,而“做”出來的文章就是用書面文字進行的書面創作。那麽在當時,故事的呈現方式,也可分爲“説出來”的和“寫出來”的兩種,二者各有表述規範。前者是口頭呈現,用口語白話表述;後者是書面呈現,用書面文言表述。那些“説出來”的故事,有伎藝性的,如説話伎藝;更多的是日常性的,這類故事被書面記述者亦不在少數,比如唐傳奇《李娃傳》即是對口傳“一枝花”故事的書面記述,而宋代的歷史著述、白話語録、文人筆記更多有例證。書面領域對於這些“説出來”的故事的呈現,總的觀念是“録”,在表述語言上,或是整體上轉换成文言語體,或是在人物語言中保留口語白話,但即使如此,這些白話表述成分也是書面呈現意義的“録”,而非書面創作意義的“寫”,也就是説,這些白話成分並不是書面創作時使用的表述語言。比如下面對五代梁太祖朱温的兩段記述:
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樹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須用夾轂,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爲車轂者,悉撲殺之。(29)《舊五代史》卷二《太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38。
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説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30)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一“梁太祖優待文士”條,叢書集成初編本,頁3。
這兩段文字敍寫了關於朱温的同一個傳奇故事,應是來自於民間口傳。對於這個口傳故事,《舊五代史》在書面呈現時整體上轉换成文言表述,而北宋初年的《洛陽搢紳舊聞記》則在人物語言中保留了口語白話,既有“措大”、“順口”、“弄人”等口語詞彙,也有白話語體的句式,這樣的語言格調符合朱温這個出身貧寒、文化低劣的草莽英雄形象,既描摹生動活潑,也符合生活事實。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段文字在人物語言中保留白話表述,乃出於對史家實録求真觀念的遵循,或是文言編寫立場上對人物身分、性格刻畫的修辭考慮,而非書面編寫意義上語言表述觀念的重要轉變,所以,即使人物語言普遍使用口語白話,仍是被鑲嵌在一個文言敍述的框架中。這正如當時禪宗大師、理學大師們的白話語録,如道原《景德傳燈録》、張伯行《朱子語類輯略》、王守仁《傳習録》等,亦有一個“某某曰”、“某某云”領起的文言敍述框架。在此,編寫者仍是遵循書面領域的文言表述規範,而不是把口語白話作爲自己進行書面編寫的一種表述方式,如此一來,那些“説出來”的口傳故事在進入書面領域後,就被按照書面領域的文言表述規範予以呈現,即使人物語言中保留口語白話,也是基於實録求真的觀念而對口傳内容的“録”,而非書面白話編寫立場的“寫”。因爲按照文言編寫的規範,那些口傳領域“説”的表述方式不可能被用作文言編寫立場的“寫”的表述方式。
這種日常性口傳故事的文本化形態,同樣存在於當時的伎藝性口傳故事的文本化之中,這是當時口頭内容落實於書面文本的普遍規範。我們看到,録本中出現的白話表述的人物語言,是緣於伎藝故事負載的文本化而對口演話語的保留,它附庸於伎藝故事的文本化。而伎藝口演内容進入書面領域後的録本階段,總體上是要遵循文言編寫的體例和規範,因爲録本仍是文言編寫立場的著述,而非白話編寫立場的著述。在文言編寫的規範中,伎藝口演體制是外在於書面領域的表述方式,它不可能與文言表述規範相容,而被用作文言編寫立場的一種表述方式。
但元代普遍出現的擬編本則較此發生了明確的變化,出現了伎藝體制因素與伎藝故事内容相分離而單獨落實於文本的現象,這種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在《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中表現得甚爲典型、明顯。一是出現了白話編寫立場的文本,二是把伎藝體制作爲書面編寫立場上的一種表述方式。在此,伎藝體制已經作爲説話伎藝文本化的主導、主體因素,而不再是附庸於伎藝故事的文本化之中了,這樣的擬編本就是有意識地取用伎藝體制因素而進行的書面編寫。
需要强調的是,這些服務於藝人口演的伎藝體制因素,從伎藝故事的表述體制發展到書面故事的表述體制,從伎藝領域的表述方式發展到書面領域的表述方式,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直線對接,也不是點對點的垂直對應,而是有一個與書面表述規範碰撞、調適的過程。在録本階段,它是伎藝故事文本化的附庸,是負載於伎藝故事文本化之中的。而在擬編本階段,它已經開始成爲説話伎藝文本化的主體了,而伎藝口演内容的文本落實也表現出以伎藝體制爲宗旨的文本化形態,由此而出現了一種不以伎藝故事爲目的的文本化方式。這表明,伎藝口演體制已經不是書面落實伎藝故事的附屬,而是一個可以從伎藝口演内容中分離出來單獨進入書面領域的表述體制。於是,擬編本所表現出的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即開始確立了説話伎藝文本化的一個方向——朝着話本文體形成的方向演進。這就是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那麽,擬編本是如何得以出現,或者説是什麽因素促使它出現的呢?是來自伎藝領域的動力,還是來自書面領域的動力?
口演領域、書面領域本無多少交集,它們各有自己的創作規範、表達手段、發展方向。伎藝領域的發展方向,肯定是伎藝的口演;書面領域的發展方向,肯定是書面的編寫。説話伎藝按着自己領域的發展方向、實現目標前行,它本不負責、也不關心書面領域對自己口演内容的呈現,不會以落實書面文本作爲自己的發展目標。這是因爲,其一,藝人不需要這種口演内容的文本落實。説話藝人的口演屬於將各種成分臨場“捏合”的口頭創作,而熟悉口演的體制、格套是藝人們的基本素質,其場下訓練、場上表演並不依賴那些程式、格套、情節等成分齊備完整的白話文本。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録》是一部爲藝人講説表演而準備的參考資料書,反映了藝人的藝能訓練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識——有“演史講經並可通用”的入話,有傳奇、煙粉之類的故事梗概,有常用的詩詞賦贊,有笑話綺語之類的諢語,這些都是藝人口演時需要臨場組合的各種成分,以便在口演時根據故事情境的需要,隨手拈來以作口頭創作性質的臨場組合。在説話人那裏,這樣的組合只存在於口演形態中,而不是存在於文本形態中。其二,當時社會以講—聽作爲説話伎藝的接受方式,而且這個講—聽方式的傳播渠道暢通,民衆對伎藝領域裏書面落實口演内容没有産生需求,因此,伎藝領域裏自然不會出現參與書面落實口演内容以爲閲覽之用的動力。其三,説話伎藝在當時是末技,地位卑下,難有影響書面領域的力量。況且,伎藝領域生成、使用的口演體制規範,與書面領域的文本編寫規範没有直接關係,故而説話伎藝的發達繁盛程度,對於書面領域的主動影響也極有限。
當然,説話伎藝的繁盛發達肯定會引動人們的關注而出現對其口演内容的文本化,但在伎藝口演内容進入書面領域而有了文本化這個大的方向的過程中,這個文本化一直存在着書面領域的主動意識,這就是基於書面編寫而對伎藝口演内容的有意識的文本化。如此一來,這個文本化雖與説話伎藝的繁盛有關,但最終是要通過書面領域的主動接受意識來起作用的,而不是出於對説話伎藝口演内容的被動記録。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各種物質與非物質因素的促進,比如市民階層的擴大、市井文化的興盛、印刷業的發達等,也是要通過這個文本編寫的主動性而起作用的。上文已經提到,説話伎藝的白話表述方式,以及入話—結語敍述格式,都是説話伎藝文本化一開始就要面對的伎藝因素,但口語白話並非一開始就能落實於書面作品,而擬編本也不是這個文本化的最初結果、唯一形態。因爲在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書面領域缺少對伎藝口演體制因素的接受觀念、能力和經驗。只有書面領域出現了對説話伎藝表述方式的接受觀念、接受能力的變革,上述各種因素的促進作用纔能得以落實到這個文本化進程中,進而在書面領域醖釀出説話伎藝表述方式落實於文本而成爲書面敍述體制的一步步深化。
擬編本體現出的對伎藝體制因素有意識的取用,即是這一文本化的主動意識的典型表現。在此,伎藝體制因素作爲一個表述方式已單獨進入書面編寫領域,於是,伎藝體制因素就不只服務於伎藝表演,還服務於書面編寫;不只是伎藝故事的表述方式,還是書面故事的表述方式。擬編本中的《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等元代作品,即尤爲典型、明顯地表現出了書面編寫立場上表述方式的這一變化。
與此變化相應的是,比較於宋代,元代的書面領域也出現了重要的變化,即在文言編寫立場的“寫”、“録”之外,出現了白話編寫立場的“寫”。這主要得力於白話在書面編寫領域的觀念變化和地位提升。
在文言著述和文言閲讀已成習慣思維的社會環境中,閲讀、編寫都是文言的思維習慣、文言的接受立場。宋代的史著、筆記、白話語録中出現了多多少少的白話表述(主要在人物語言中),是在文言敍述框架内的白話使用,是以文言創作的立場或態度來使用白話,而不是以白話創作的立場來使用白話,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它的白話成分如何多,亦不屬於自覺的白話著述。所以,自覺的書面白話作品的出現並非易事,文人們涉足此領域需要相應觀念的推動,相應環境的激發,相應閲讀需求的促進,否則文人們不會有動力來涉足白話文本的編寫,也不會有能力來從事白話文本的編寫。
但在元代,自覺的書面白話編寫的觀念、環境和實踐出現了。這是因爲元代獨特的社會狀況確實改變了白話地位低下的觀念,也改變了書面白話使用的環境,這爲文人涉足白話文本的編寫營造一個非常好的氛圍。(31)此問題可參見徐大軍《元代的直説作品與書面白話著述的自覺》第四部分,《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4期。尤其是蒙古權貴這個特殊羣體對於白話著述的閲覽需求,引導了下層社會對於白話著述的需求,也激發了社會上更普遍的人羣對於白話文本編寫、閲覽的參與,當時許衡、吴澄這樣的碩學大儒都涉足白話著述,(32)許衡在國子學任職時編寫了一批面向蒙古生的白話講義文本,如《直説大學要略》、《貞觀政要直説》、《大學直解》、《中庸直解》、《孝經直説》,以俗語白話闡述經史義理。吴澄於元泰定年間(1324—1327)任職經筵講官時,爲了講説《資治通鑑》而編寫了白話文本《經筵講義》。就是一個很好的表現,這對於更多文人參與白話文本的編創,具有積極的激勵、推動和示範作用,從而湧現出了立足於普通民衆易曉易解的閲讀需要而自覺編寫的白話文本,其中有敍事的白話歷史作品,也有非敍事的白話經籍作品。
吴澄的《經筵講義》、鄭鎮孫的《直説通略》就是這樣兩部具有典型意義的白話故事文本。我們由下面兩個段落即可見一斑。
漢高祖姓劉名邦,爲秦始皇、二世皇帝的時分好生没體例的勾當做來,苦虐百姓來,漢高祖與一般諸侯只爲救百姓,起兵收服了秦家。漢高祖的心只爲救百姓,非爲貪富貴來。漢高祖初到關中,唤集老的每、諸頭目每來,説:“你受秦家苦虐多時也,我先前與一般的諸侯説,先到關中者王之。我先來了也,與父老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隨他所犯輕重要罪過者,其餘秦家的刑法都除了者。”當時做官的、做百姓的,心裏很快活有。(33)吴澄《吴文正集》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97册,頁840下。
卻值淵與突厥戰不利,心裏煩惱。世民乘時對淵説道:“主上無道,百姓窮困,晉陽城外都是戰場,不如順民心,起義兵,轉禍爲福。”淵大驚,説道:“恁怎生説這般言語,我拿恁去告縣官。”取紙筆要寫表。世民説道:“孩兒覷着天時人事如此,以此發言。父親必欲告呵,不敢辭死。”淵説道:“我那裏便肯告你,你再休胡説。”第二日,世民又對淵説道:“如今盜賊滿天下,父親受詔討賊,賊人怎能勾得滅,終不免罪。人都道李氏當應圖讖,父親總若滅盡諸賊,功高不賞,身更危險,只有昨日的話,可以救禍。這是萬全計策,父親休要疑惑。”淵説道:“我一夜尋思恁的言語,也好生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也由你,變家爲國也由恁。”(34)鄭鎮孫《直説通略》卷九,明成化庚子重刊本,葉12A—B。
這是兩部完全基於白話立場編寫的歷史著作,二書所藴含的各方面意義比較豐富,但就書面白話編寫的意義而言,主要有三: 一是它們的作者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文人,吴澄是元代的理學大儒,鄭鎮孫曾爲監察御史;二是它們都有着明確的面向人羣,吴澄是任職經筵講讀官時面向蒙古皇帝而有此編寫,鄭鎮孫是面向下層的歷史知識普及而編寫此白話史著,“以時語解其舊文,使人易於觀覽”;三是它們都有明確的編寫原由,關聯着一個閲覽白話文本的社會需求,以及編寫白話文本的社會動力。吴澄是出於服務蒙古皇帝的閲覽需要而盡力語言平易,以便向他們傳播一些漢地的政治、歷史知識;鄭鎮孫是受元初理學大家許衡白話解説《大學》、《貞觀政要》的啓發而編寫了《直説通略》,“以俚俗之言爲能盡聖賢之藴奧”,如此則“世代興衰,往事因革,直而言之,亦差勝於閭閻小説耳”。(35)鄭鎮孫《直説通略自序》,《“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録·史部》第三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年,頁1。
對於這兩部白話著述,有的學者把它們放在話本小説的研究框架中,站在講史伎藝影響深遠的立場上,把它們視爲借鑑講史伎藝體制的作品,視爲受講史伎藝影響而出現的“平話體”作品。(36)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編《説唱藝術簡史》認爲:“元代講史在當時社會上造成極大影響,它超出了文藝的範疇,成爲講説歷史通用的體裁和語言形式。據記載,當時的道學先生吴澄在給皇帝講《通鑑》,監察御史鄭鎮孫摭録《資治通鑑》編寫《直説通略》,都采用了這種受歡迎的平話體。”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頁83。其實,這種書面編寫領域的白話表述、白話敍事,並非起於講史伎藝的影響,而是因爲元代書面白話觀念的變化而引起的書面編寫領域的變革——社會的上層、下層都出現了白話閲覽的需求,因此促動了文人涉身參與其間;而這些白話作品所代表的書面編寫實踐,又關聯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白話閲讀需求,並爲當時的下層社會營造了一個編寫白話作品的氛圍。
這種白話編寫立場上的文人創作,在書面領域中引起了兩個方面的影響和促進。
其一,在觀念上,衝擊了文言編寫的體例、規範,爲更廣範圍的白話編寫拓開了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許衡、吴澄等上層文人編寫的白話作品對話本中擬編本的編寫有着示範和推動作用。
其二,在方法上,白話編寫立場的創作,必然會促使書面領域在文言編寫的規範之外尋求新的表述方式。文人們進行這些白話作品的編寫,必然會面臨着材料内容、呈現方式的選擇問題。比如鄭鎮孫、貫雲石都明確表示自己是因爲受到許衡取“世俗之言”以解説《大學》的啓發,纔有心仿效其“直説”方式以成白話著述,(37)貫雲石在《孝經直解自序》中言及編寫緣起:“嘗觀魯齋先生取世俗之言,直説《大學》,至於耘夫蕘子皆可以明之。……愚末學輒不自□,僭效直説《孝經》,使匹夫匹婦皆可曉達,明於孝悌之道,庶幾愚民稍知理義,不陷於不孝之□。”《新刊全相成齋孝經直解》,北京來熏閣書店影印元刊本,1938年。不但人物語言使用白話,就連敍述語言也使用白話,這是宋代那些白話語録所不具備的。
其實,當時文人在編寫這類通俗作品時,都會考慮到面向人羣的閲讀能力,並且認真嚴肅地求索着簡單有效的表述方式,於是,那些有着深厚民衆基礎的口演故事及其表述方式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比如元延祐五年(1318),錢天祐面向蒙古皇帝、皇子編寫的介紹漢地歷史的通俗作品《敍古頌》二卷,就取用了荀子“成相”體的韻唱方式。
唐之季,閹寺熾,藩鎮强梁制主勢。閽司袞職,榦弱枝强本根蹶。
起神堯,訖僖昭,巍巍宫闕帝黄巢。克用逐之,朱温嗜炙士民號。
温狂躓,行汙穢,身服鹿麀見子弑。懷璽七年,殘骸僅獲敗氈瘞。
莊狎媟,行不厭,新磨遽前批其頰。矢石勤勞,一朝灰燼墮前業。
閔敬瑭,賂强方,穹廬丈人許石郎。再傳一主,歷年十一遂以亡。
嘆漢劉,用婦謀,帝羓還塞主中州。嗟哉二主,四年之後即歸周。
周之威,膺明資,奉法利民無所私。天將厭亂,袞服三載傳養兒。
嗟世宗,處季終,謀爲舉措有帝風。亂極思治,畀之孤寡騰英雄。(38)《永樂大典》卷一八八八,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8年,頁4498上—4499下。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九言《敍古頌》“詞意鄙俚,殊不足采”,(39)《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759上。錢天祐本人也承認“俗言淺語,無所發明”。他與許衡、吴澄涉身編寫那些白話文本一樣,都是希望能爲蒙古皇帝、皇子提供快速有效地瞭解漢地文化、歷史的通俗讀本:“無瑣碎繁茸之患,可以備諸巾篋,不煩檢閲,而數千載行事大略可觀,此則臣之鄙諶也。況陛下萬機至衆,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史册哉!”正是基於這個目的,錢天祐“采摭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爲聲韻之辭,著爲一編”,如此,“既可以謳吟歌詠,又掇前史於片紙之間”。此前,錢天祐還於延祐元年(1314)進獻過《大學直解》,延祐二年進獻過《孝經直解》,都是“俗言淺語,無所發明”之作,而且《孝經直解》還被皇帝降旨命翰林官書寫鏤板印行,廣加傳布,所以錢天祐也希望自己的《敍古頌》還能被皇帝降旨頒行,“使自朝廷,而鄉人,而邦國,咸資用焉”。(40)錢天祐《敍古頌表》、《中書省進敍頌狀》,《全元文》第37册,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107,110。由此可見,上層社會的閲讀需求以及大力推動,對於錢天祐涉身此類通俗文本的編寫是一個極大的激勵和促動,這也必然會激勵、推動當時更多文人參與白話文本的編寫,上述那些文人編寫的白話作品即可爲明證。
正是在這種白話閲讀、編寫的需求環境中,那些面向下層社會的更爲普及的白話編寫,與錢天祐編寫《敍古頌》一樣,也必然要面臨着選擇、借鑑、學習何種呈現方式的問題,也必然要尋求一些有力有效的通俗表述方式。而在當時,白話敍述故事的能力、經驗有兩個來源,一是書面領域裏文人據史書的白話翻譯文本,二是伎藝領域裏藝人的敍事性講唱伎藝。前者是書面形態,後者是口演形態,這些都是書面編寫領域通俗敍事、白話敍事可資借鑑的實踐經驗。《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五代史平話》、《秦并六國平話》的編寫就體現了這種借鑑伎藝領域口演體制因素的蹤迹。只是由於處於草創階段,這種來自於伎藝領域的表述體制並未能與文言體系的書面表述體制調適、融合得恰當,從而出現了伎藝體制與文言故事的混合形態,由此在作品整體敍述風格上存在着不協調、不融合的剥離感,這恰恰反映了伎藝體制處於文本化早期的過渡性形態。
雖然如此,這些擬編本已經把伎藝體制當作書面編寫領域的一種表述方式、表述體制了。在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中,這種鑲嵌着伎藝體制因素的故事文本還成爲一種示範,它們所具有的表述體例也漸而成爲書面編寫的一種習見形態,被通俗故事文本編寫一次次地實踐着,而取用的故事材料則五花八門,或者取用現成的文言作品直接框套,或者取用史書作品進行白話翻述,或者取用已有的説話伎藝的録本。此外,那些非“小説家”講唱伎藝的口演内容在落實於文本時,也會以這種通用的表述體例予以書面呈現。有的如《快嘴李翠蓮記》、《張子房慕道記》,其正話中的人物話語爲大段的韻體詞文,這明顯不是“小説家”説話的格調;還有的如《刎頸鴛鴦會》,正話在白話敍述中夾雜着韻語唱誦,此篇即夾雜了十首商調(醋葫蘆)曲,這是取用了鼓子詞伎藝的講唱格式,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有一個入話、散場詩的敍述框架。這説明,當時的一些非“小説家”説話伎藝的口演内容在文本化時,也被按照一個通用的敍述框架予以書面呈現。這一情況表明,那些來自於説話伎藝的敍述體制在書面領域裏已經成爲一個獨立的敍述體制了,據此而來的書面編寫,就打破了文言體系書面著述的思維、規則、體例,從而爲書面編寫開掘出文言編寫體例之外的另一條路徑。
四 結 語
通過上述理析,我們可以看到,元代文人參與的白話編寫立場的白話著述,衝擊了文言編寫立場的體例、思維的禁錮,激發了白話編寫吸收新異質素的需求。這些條件爲説話伎藝體制因素落實於書面文本提供了觀念上的支援,也營造了良好的生長環境,由此鍛煉出了不同於文言編寫的敍事文本體例。
如此一來,書面編寫可以在文本中接受、呈現的内容就有了變化,人們在書面呈現説話伎藝的口演内容時,可以不用作文言語體的轉换,也可以接受伎藝口演格調的白話詞彙、程式格套來作爲書面編寫的表述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伎藝體制因素就不只服務於説話伎藝表演,還進入了書面編寫領域,在書面編寫實踐中被一步步地改造、調適、消化、融合,漸趨成爲一種立足於書面故事編寫而使用的表述體制。這就是説話伎藝文本化走向文體話本的基本邏輯和路徑。沿着這條道路前行,那些源自説話伎藝的體制因素,就被改造成爲書面敍事的構成要素和標誌格式,由此而朝着文體話本這個書面文體生成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