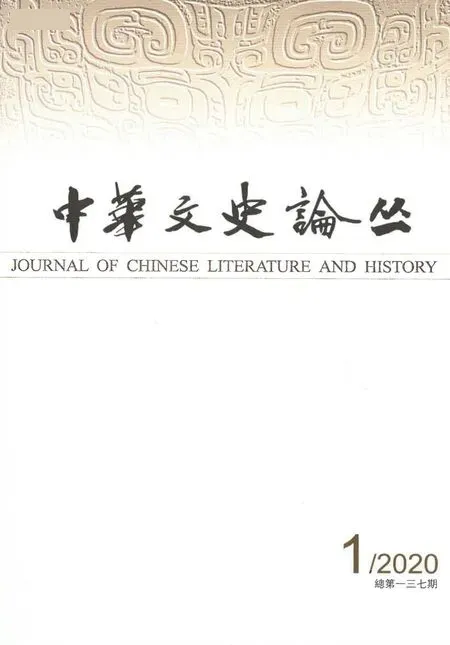論宋僧惠洪的佛教文學創作成就及影響
周裕鍇
提要: 宋僧惠洪是佛教史和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石門文字禪》是其撰述理念及寫作内容的集中代表,共收古近體詩1658首,各體文535篇。其詩學蘇軾、黄庭堅,各體皆工,被譽爲“宋僧之冠”。其文受北宋古文運動影響,長於議論,疏文、題跋、字説在禪林書寫史上有示範意義。歷代士林和禪林對其著述評價褒貶不一。《石門文字禪》南宋初即刊行,今存最早爲萬曆徑山寺本。日本江户僧廓門貫徹爲之作注,然而較粗疏,理應重新整理校注。
關鍵詞: 宋僧 惠洪 《石門文字禪》 徑山藏 廓門貫徹 佛教文學
一 惠洪的生平和著述
宋代名僧惠洪是中國佛教史和文學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奇才,其著述範圍之廣,在兩宋禪林中可稱第一,後世僧人也罕有其匹。他既致力於佛教論疏、禪門旨訣、僧史僧傳、禪門筆記、語録偈頌的撰寫,又流連於世俗詩文詞賦的吟唱與詩話、詩格的創製,甚至會偶爾旁及儒書注釋。惠洪的詩文集《石門文字禪》(1)下文引用《石門文字禪》時皆簡稱“本集”。所引文字皆據後文交代的萬曆徑山寺刻本。正是他整個撰述理念以及寫作内容的集中代表,不僅體現了佛教内部禪教合一的傾向,如明僧達觀揭櫫的那樣,“禪與文字有二乎哉”,(2)《紫柏尊者全集》卷一四《石門文字禪序》,《大藏新纂卍續藏經》(73)(以下簡稱《卍續藏經》),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2006年,頁262下。而且也顯示出僧人借鑑士大夫文學傳統而交融儒釋的自覺努力,如宋僧祖琇稱其“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3)《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傳》,《卍續藏經》(79),頁563上。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掙扎於出家忘情與世俗多情之間的詩文僧的絶佳樣板,即其自供的“以臨高眺遠不忘情之語爲文字禪”。(4)本集卷二《懶庵銘》。
《石門文字禪》收録了惠洪一生的詩文詞作品,跨度近四十年,因此,從知人論世的角度看,要閲讀本書,最好先了解惠洪的大致生平。
惠洪(1071—1128),字覺範,世稱洪覺範。自號寂音尊者,又號明白庵、甘露滅、冷齋、石門精舍等。江西筠州人,俗姓彭氏,一説姓喻氏。十四歲父母雙亡,到本鄉三峯山禪院裏爲童子。十九歲至東京開封府,冒惠洪名,於天王寺試經得度。四年後南下師從真淨克文禪師於廬山歸宗寺、靖安縣寶峰寺,凡七年,得臨濟宗旨。二十九歲開始遊方,往返於吴、楚之間。他曾在杭州禮拜永明延壽和明教契嵩禪師遺迹,深受禪教合一觀念的啓發。又在湖南長沙與黄庭堅相會,得其傳授詩法。從三十六歲起,因受地方官員朱彦、吴幵之請,他先後住持撫州北景德寺、江寧府清涼寺。爲人告發冒名度牒,下江寧制獄,得赦,還俗。到東京謁丞相張商英,再得度,改名德洪。因太尉郭天信奏,賜號寶覺圓明大師。張、郭爲蔡京黨羽排擠打擊,惠洪連坐而下開封府獄,遭削除僧籍,刺配海南朱崖軍牢。在海南三年,自稱“海上垂鬚佛,軍中有髮僧”,曾訪問蘇軾遺迹,作《補東坡遺》詩若干首。遇赦,北歸筠州故里,於石門、洞山、九峯一帶,著儒生冠巾而説佛法。其間又曾兩次下獄,即證獄太原與入南昌右獄。再遇赦,晚年住長沙谷山,遷南臺寺,潛心撰寫僧史僧傳,注疏佛教經論。宣和七年北上襄州,靖康元年恢復僧籍。北宋亡後避居廬山,移居建昌縣同安寺。建炎二年卒。諸傳燈録將其列爲南嶽下十三世,屬臨濟宗黄龍派。惠洪一生經歷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五朝,見證過哲宗朝元祐、紹聖的新舊黨爭,親歷過徽宗朝張商英與蔡京的黨爭,遭遇過宣和初崇道排佛的宗教大事件,更經受了靖康之變的亡國慘痛。這些經歷在其詩文中或隱或顯有所表現。當然,作爲宗教徒,惠洪更關心的是佛教興衰的問題,故其詩文中對禪林的墮落尤爲痛心疾首,而其志向也在試圖用自己的枯筆一支,以文字爲禪,“光輔叢林”,(5)《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卍續藏經》(79),頁563中。痛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禪風,力挽禪宗的頹勢。
惠洪平生博覽羣書,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喜結交士大夫,關注世事,因而屢受政治牽連,下獄流放,遭遇極爲坎坷。但他始終將以文字弘揚宗教視爲己任,并始終將吟詠情性的詩文詞作爲畢生的嗜好,歷盡艱辛而手不停筆。據各種僧傳、書志記載,惠洪一生著述有二十多種,一百多卷。僅《僧寶正續傳》本傳便稱他:“著《林間録》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録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於世。”(6)《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卍續藏經》(79),頁563上。加上《郡齋讀書志》、《通志》、《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江西通志》諸書及惠洪自己的《石門文字禪》記載,尚有《筠溪集》十卷、《甘露集》九卷、(7)釋正受《嘉泰普燈録》卷七作三十卷,見《筠州清涼寂音惠洪禪師》,《卍續藏經》(79),頁333下。《物外集》三卷、《臨濟宗旨》一卷、《雲巖寶鏡三昧》一卷、《易注》三卷、《五宗綱要旨訣》(卷次未詳)、《注華嚴十明論》(卷次未詳)、《證道歌》一卷等。去其亡佚和重出,今存著述尚有十種一百零四卷。詳情可參見拙著《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附録一《惠洪著述著録情況一覽表》。此外,《全宋詞》輯有其詞二十一首;我嘗作《全宋詞輯佚補編》,又得其詞十六首;近年來,又作《石門文字禪校注》,從《鳳墅帖》、《永樂大典》、《樂府雅詞》中再輯出四首。則目前所見的惠洪詞共有四十一首,亦近一卷。
我們説《石門文字禪》是惠洪撰述理念以及寫作内容的集中代表,理由在於本書内容的豐富性、包容性和駁雜性,它與惠洪其他各種性質的著述多有關涉,其間的互文性交織爲一張複雜的網,舉本書而證以羣書,頗有綱舉目張之效。比如卷二三的《昭默禪師序》、《定照禪師序》,可能是《禪林僧寶傳》中惟清、道楷禪師傳的藍本。卷二五的《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題古塔主兩種自己》,其大致内容也見於《林間録》與《禪林僧寶傳》,《題靈驗金剛經》則可參見《冷齋夜話》的記載。卷三的《十世觀音應身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傳》,可能是對慧皎《高僧傳》的改寫,卷二五《題修僧史》説明改寫的理由,卷四的《追和帛道猷一首》也可作旁證。卷二四的《記西湖夜語》中的討論,《林間録》有簡要論述。卷二五《題谷山崇禪師語》,略同於《禪林僧寶傳》之《谷山崇禪師傳》的贊詞。卷一五《與韓子蒼六首》,其詩寫作背景可參詳《智證傳》的記載;《合妙齋二首》的本事,則見於《冷齋夜話》卷六《鍾山賦詩》。卷二三《五宗綱要旨訣序》,所述有與《臨濟宗旨》相類者。卷二五《題光上人書法華經記》蓮生齒頰間事,既見於卷二一《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又見於《法華經合論》卷五。
《石門文字禪》共收古近體詩(含偈頌)一千六百五十八首,收各體文五百三十五篇。古近體詩中除去卷一七《述古德遺事作漁父詞》、八首《漁家傲》詞以及卷八《雨中聞端叔敦素飲作此寄之》以下十八首《浣溪沙》詞以外,尚有一千六百三十二首。此外,在各種内外典籍中,我們還輯得惠洪詩(含偈頌)三十四首,斷句若干,詞四首,文五篇。
二 惠洪詩文的藝術特點和主要成就
惠洪的詩文創作主要繼承了以蘇軾、黄庭堅爲代表的元祐文學傳統,同時借鑑了佛教禪宗的思維方式及部分語言特點,文字與禪的雙向交流融會,使其成爲宋代禪僧文學書寫的典範。惠洪的文學觀念受蘇軾影響甚深,主張“風行水上,涣然成文”,(8)本集卷二七《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沛然從肺腑中流出”。(9)李保民校點《冷齋夜話》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1。他寫詩作文常以快意爲主,所謂“横口所言,横心所念,風駛雲騰,泉湧河決,不足喻其快也”,(10)許顗《智證傳後序》,《卍續藏經》(63),頁195下。便很有幾分蘇軾的風格。而佛教義學經論的博辯無礙,禪宗語録的靈活通透,則從般若智慧方面給惠洪更多的助益。他自稱學出世法之後,“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11)本集卷二六《題佛鑑蓄文字禪》。圓悟克勤禪師稱他“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僧傳也稱他“落筆萬言,了無停思”。(12)《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卍續藏經》(79),頁563上。
與一般詩僧相比,惠洪詩無清瘦寒儉的“蔬筍氣”,題材廣泛,内容豐富,體裁多樣,風格豪放,頗爲當時及後世論者推崇。論題材則包括詠史、詠物、贈别、紀行、紀事、登覽、雅集、節序、讀書、論詩、題畫、談禪、説理、書懷等等,尤善寫世俗與方外的日常生活。論體裁則包括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五絶、七絶,甚至六言絶句。六言絶句有九十首,數量居北宋詩人第一。同時代王庭珪便讚嘆其詩“惠休島可没已久,二百年來無此作”。(13)《盧溪先生文集》卷三《同陳思忠訪洪覺範》,《四庫提要著録叢書》(16),北京出版社,2010年,頁522。許顗《彦周詩話》更稱其詩“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14)何文焕輯《歷代詩話》,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82。清吴之振、吕留良等編《宋詩鈔》稱其詩“雄健振踔,爲宋僧之冠”。(15)吴之振等選,管庭芬等補《宋詩鈔》(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008。延君壽《老生常談》稱其“今體七律殊佳”,“真能於蘇黄外,又作一種筆墨,讀之令人神清骨爽”。(16)《山右叢書初編》(16),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整理編輯室,1986年,頁17,18。近代陳衍《宋詩精華録》稱其詩“古體雄健振踔,不肯作猶人語,而字字穩當,不落生澀,佳者不勝録”,(17)《宋詩精華録》卷四,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689。又稱其所選數詩“何止爲宋僧之冠,直宋人所希有也”。(18)《宋詩精華録》卷四,頁693。其經典作品如《題李愬畫像》,歷代衆口一詞,推崇備至,清錢謙益稱此詩“佛子之忠義鬱盤,揚眉努現火頭金剛形相者也”,(19)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卷四九《題南谿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610。張宗柟稱其“有豫章風骨,通體氣亦清遒,是能不以禪寂自縛者”。(20)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下)卷二案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頁588。《竹尊者》一詩,黄庭堅極稱賞,“以爲妙入作者之域”,(21)《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卍續藏經》(79),頁563上。後世士大夫和僧人追步其韻唱和者甚多。《上元宿百丈》詩,也膾炙人口,惠洪在世時就爲禪僧所喜,雖受胡仔譏評,然方回《瀛奎律髓》稱“詩未嘗不佳,故取之”。(22)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623。《鞦韆》詩,明徐《徐氏筆精》卷四稱“詠鞦韆詩以洪覺範之作爲最”。(23)《徐氏筆精》,《四庫提要著録叢書》(55),頁204。《舟行書所見》一詩,宋趙蕃分别敷衍該詩四句每句爲一詩,(24)《淳熙稿》卷一七《用洪覺範詩爲首作四絶》,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71。足見其爲人喜愛。至於惠洪的《瀟湘八景》詩,首次將宋迪《瀟湘八景圖》的“無聲句”轉换爲“有聲畫”,開啓了後世瀟湘八景詩的寫作傳統,對南宋以降的中日禪林書寫影響深遠。(25)周裕鍇《典範與傳統: 惠洪與中日禪林的“瀟湘八景”書寫》,《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71—80。此外,惠洪的名句也頗爲歷代詩話所欣賞,如“方收一霎挂龍雨,忽作千林攧鷂風”、“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一川秀色浩淩亂,萬樹無聲寒妥貼”等等,被譽爲“奇句”,“古今人未嘗道”,(26)胡仔纂輯,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384。“句意俱工”。(27)《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頁170。
韓駒曾見過惠洪寫詩的情景,“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于覺範,覺範斯須立就”。韓勸他“詩當少加思”,惠洪笑答:“取快吾意而已。”(28)《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頁384。這種快意的書寫與詩僧的苦吟傳統形成鮮明對照,然而這種寫作態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其詩氣韻流行,無晦澀艱難之病,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詩因過分隨意而難免顯得粗糙。惠洪將自己的寫作比作“決堤”,然而在滔滔滾滾的同時,也往往挾泥沙俱下。尤其是他的應酬詩,命意布置,遣詞造句,幾成套路,句意多有重複互見之處。
惠洪之文文體多樣,據《石門文字禪》目録就有贊、銘、詞、賦、記、序、記語、題、跋、疏、書、塔銘、行狀、傳、祭文等等。其文深受北宋古文運動影響,以意爲主,擅長議論,不拘一格。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稱惠洪“其文俊偉,不類浮屠語”。(29)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52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北磵集》提要指出:“第以宋代釋子而論,則九僧以下大抵有詩而無文,其集中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最著。”(3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北磵集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405。稱惠洪文“多宣佛理,兼抒文談,其文輕而秀”。(3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北磵集提要》,頁1405。大抵直齋所謂“其文”乃就詩文統稱,且偏重於其詩,故言“俊偉”;四庫館臣則但指其文,而不含詩,故稱“輕而秀”。惠洪之文由於宣揚佛理,所以在禪門裏比其詩評價更高。清道霈禪師《聖箭堂述古》甚至説:“往歲讀東坡《赤壁賦》,既愛其文之敏妙,又愛其理之精深,以謂世無有過之者。後讀覺範此記(《畫浪軒記》),以畫浪説法,傾盡佛祖底藴,且其文縱横浩蕩若此,不知其胸中已吞吐幾《赤壁》也。此豈文人才士之所能爲哉!”(32)道霈禪師《聖箭堂述古》,《卍續藏經》(73),頁446下,447上。這個評價或許並不公允,但也足見惠洪文的成就不容小覷。明僧達觀真可特别欣賞其《邵陽别胡强仲序》,稱讚文中表現出來的“居縲絏,濱九死,而飲食談笑如平時,死生不入其懷”“超然而自得”的人生態度,從其文中看到惠洪“洞徹自心,圓用自心”的禪悟境界。(33)《紫柏尊者全集》卷一五《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别吴强仲敍》,《卍續藏經》(73),頁275上。又如《題華嚴十明論》,以勾踐、伍員雪恥復讎之事作對比,喻破滅無明煩惱之決心,其智勇也深受真可的推崇。《石門文字禪》中一些傳敍性質的文章,具有佛教史料價值,如《潭州大潙山中興記》、《五慈觀閣記》、《潛庵禪師序》、《題光上人書法華經》、《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鹿門燈禪師塔銘》、《嶽麓海禪師塔銘》、《花藥英禪師行狀》等,皆爲明釋明河撰《補續高僧傳》所采用。
《石門文字禪》中有三種文體在禪林書寫史上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其一是疏文,在惠洪之前,雖有九峯鑑韶禪師曾作疏請大覺懷璉住明州阿育王山之例,但就現存僧疏作品而言,第一位大家非惠洪莫屬。《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八收疏七十一首,其中含山門疏、諸山疏、升座疏、藥石榜、茶榜等各種請疏,又有浴佛、抄經、化藏、修造、祈謝雨晴、長生、化供、設粥、酬經、薦經、追薦、設水陸等諸種功德疏。這些佛事四六文具有宋代新體四六文的特點,不事華藻,謝絶雕琢,文筆流動自然,對仗靈活,善用宗門公案,間使經史故事,樸實而不失典雅。這種注重應用功能的疏文,隨着《石門文字禪》在僧人羣體中的廣泛傳抄,爲南宋禪林的四六文書寫作了很好的示範。後來如釋大觀《物初賸語》中三卷一百四十多篇疏文,應間接受其一定影響。而南宋江湖疏這類四六文流播至日本,更成爲五山禪林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是題跋,在惠洪之前,契嵩《鐔津文集》題跋僅有六篇,四篇題史傳,一篇題文集,一篇題影堂。《石門文字禪》則有一百五十九篇題跋,開拓疆域,蔚爲大國,内容既包括佛教經論、語録、燈録、僧史、偈頌,又涉及儒家史傳、筆記小説,更涵蓋僧人和士大夫的詩詞、文稿、書法、繪畫等。其議論感慨,評騭玩賞,佳作甚多。以至於明毛晉刻《津逮秘書》,於僧人只收録《石門題跋》,以與蘇軾、黄庭堅、晁補之、陸游等文章巨公題跋並置。特别是他在書畫方面的題跋,傳達出禪林中人與士大夫審美趣味相投合的新傾向。後來有詩文集傳世的禪僧,如寶曇、居簡、善珍、大觀、道璨等等,例有書畫題跋,與惠洪如出一轍。其三是字序,也稱字敍、字説,申説爲他人的人名取字的理由。惠洪之前,僅天台僧智圓寫過一篇《敍繼齊師字》,(34)《閑居編》卷二七,《卍續藏經》(56),頁905下。禪門契嵩寫過兩篇,其中一篇《與月上人更字敍》,(35)《鐔津文集》卷一一,《大正新修大藏經》(52),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頁706中。爲僧人而作。《石門文字禪》中則收有九篇,皆爲僧人而作。衆所周知,北宋蘇氏父子的字説非常有名,如蘇洵《仲兄字文甫説》,其中表達的“風行水上涣”爲“天下之至文”的文學觀念,(36)曾棗莊、金成禮《嘉祐集箋注》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412。對惠洪影響很大。惠洪仿效蘇氏父子,將此文體移植到禪林中,通過對字義的闡發,宣揚其佛教觀念。從此以後,在南宋和日本五山禪林文學中,爲僧人作字説蔚然成風,成爲最常見的文體之一。
在《石門文字禪》以外,惠洪嘗試借鑑北宋古文運動的成功經驗,來撰寫禪林高僧的傳記,其《禪林僧寶傳》不僅打破了歷代僧傳由義學律師壟斷的局面,而且改變了《續高僧傳》、《宋高僧傳》“户婚按檢”的撰述風格,完全采用儒家史傳的敍述方法,以至於被譽爲“宗門之遷、固”。(37)侯延慶《禪林僧寶傳引》,《卍續藏經》(79),頁491上。此後僧人撰述的《續禪林僧寶傳》、《僧寶正續傳》、《南宋元明僧寶傳》皆遵其體例。而他的《林間録》,則借鑑東坡《志林》的書寫方式,開出禪林筆記一途。南宋以降,《宗門武庫》、《羅湖野録》、《雲卧紀談》、《叢林盛事》、《人天寶鑑》、《枯崖漫録》、《山庵雜録》等,大抵仿效《林間録》之撰述風格。無盡居士張商英一見惠洪之面,便稱讚他爲“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38)本集卷二九《答張天覺退傳慶書》。若從惠洪在佛教文學的貢獻方面來看,這個讚譽並不過分。
三 歷代士林和禪林對惠洪其人其書的主要評價
惠洪在文化史上是個頗富爭議的人物。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無論是禪林還是士林,人們對他的評價都有毁有譽。其師友如黄庭堅稱他“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煙”,(39)《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贈惠洪》,《四庫提要著録叢書》(11),頁40。賞其高格和文章。謝逸稱他爲“體道之士”,“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兼有“妙思”“美才”。(40)《洪覺範林間録序》,《卍續藏經》(87),頁245中。許顗稱他“其人品問學、道業知識,皆超妙卓絶,過人遠甚”。(41)《智證傳後序》,《卍續藏經》(63),頁195中。侯延慶稱他“嘗涉患難,瀕九死,口絶怨言,面無不足之色”,故所著書“其識達,其學詣,其言恢而正,其事簡而完,其辭精微而華暢,其旨廣大空寂、窅然而深矣”。(42)《禪林僧寶傳引》,《卍續藏經》(79),頁491上。
惠洪才華過人,性格外放,身爲僧人,卻“與士大夫遊,議論衮衮,雖稠人廣座,至必奪席”。(43)《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卍續藏經》(79),頁563上。這是很容易招致人嫉妒甚至討厭的性格,所以他的朋友一再規勸,如韓駒“嘗戒之使遠禍”,(44)《寂音尊者塔銘》,《永樂大典》(9),卷八七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9070上。徐俯怪罪他“作詩多,恐招禍”。(45)本集卷一二《徐師川罪余作詩多恐招禍因焚去筆硯》。後人更批評他:“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己,不能全身遠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46)《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卍續藏經》(79),頁563中。同時,就禪林而言,惠洪所提倡并履行的“文字禪”,賦詩作文,疏經造論,違背了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别傳”的祖訓,因而甚至與他關係密切的靈源惟清禪師,也斥責他箋注《楞嚴經》是“依他作解,塞自悟之門”。(47)釋惟清《靈源和尚筆語》,《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39),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頁392。就士林而言,惠洪平生所尊崇或所結交的士大夫如蘇軾、黄庭堅、張商英、陳瓘、鄒浩、李之儀等人,多爲蔡京政敵,入元祐黨籍,所以史稱惠洪“于士大夫則與黨人皆厚善”。(48)《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頁521。惠洪屢次下獄或被人誣告,多少與此政治立場相關。韓駒在《寂音尊者塔銘》中稱他“好文致憎,友賢招怨”,(49)《寂音尊者塔銘》,《永樂大典》(9),卷八七八三,頁9070上。可謂相當準確地概括了他平生在禪林與士林的真實處境。
南宋以後,無論是士林還是禪林,對惠洪的評價更出現高下相懸的兩極分化現象。一方面,推許他的人品詩品的不少,如曾紆謂其“豪放之氣塞乎宇宙,故能蹈禍不慄,老當益壯,暮年詩語高古如是”。(50)《鳳墅帖·續帖》卷三《與蕭郎論詩》附曾紆跋,《中國法帖全集》(8),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頁133。劉辰翁也將他引爲同道:“覺範者,豫章公之無本,鉢盂後之王何也,今亦豈易得哉!使吾及此老,與之夜話,證寂音,續僧史,豈非山間世外之一快。”(51)《須溪集》卷二《小斜川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29。清宋長白稱“寂音於宋僧中,吟詠有絶佳者,不僅《石門文字禪》也”。(52)《柳亭詩話》卷五,上海,新文化書社,1935年,頁62。翁方綱認爲惠洪詩中不僅《題李愬畫像》可與黄庭堅並驅,而且“其他篇亦有氣格近山谷處”。(53)《石洲詩話》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76。盧世喜歡惠洪,是因“東坡、山谷二老,乃石門所皈依者。夫既皈依坡、谷矣,其文安得不佳,其人安得不佳”。並自稱“閲鈔《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録之”。他特别欣賞的是“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烈處,輒見其涕出淚流,肩摇骨涌,蓋尊宿中一片有心人也。披誦之餘,肅然起立”。(54)《尊水園集略》卷七《鈔書雜序》,《清代詩文集彙編》(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71,272。另一方面,惠洪因詩文“不類浮屠語”,在某些士人眼裏便成爲一種罪過。胡仔指責惠洪:“忘情絶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55)《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頁385。四庫館臣也指出:“身本緇徒而好爲綺語,《能改齋漫録》記其《上元宿嶽麓寺》詩,至有‘浪子和尚’之目。”(56)《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石門文字禪提要》,頁1331。在《石門文字禪》之外,一些士人因學術或道德的立場,也對惠洪多加貶斥,如宋吴曾稱“冷齋不讀書”,(57)《能改齋漫録》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68。吴坰説他“荒唐不學,世無其比”。(58)《五總志》,《知不足齋叢書》(7),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661。晁公武評惠洪諸書:“著書數萬言,如《林間録》、《僧寶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於世,然多誇誕,人莫之信云。”(59)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034。陳振孫評《冷齋夜話》十卷“所言多誕妄”。(60)《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頁331。甚至也有惡意詆毁者,如孫覿對惠洪尤爲痛恨,並誣陷惠洪僞作黄庭堅贈其詩。(61)《鴻慶居士集》卷一二《與曾端伯書》,《四庫提要著録叢書》(17),頁122。其後陳善《捫虱新話》、朱熹《朱子語類》、方回《瀛奎律髓》、四庫館臣皆不加考辨,接響傳聲,認定黄山谷《贈惠洪》詩爲惠洪僞作,山谷外甥徐俯誤收,而洪芻、洪炎信以爲然。關於黄詩的真僞,我已在拙著《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崇寧三年”下詳加考辨,兹不贅述。
在禪林中,堅守以心傳心祖訓的正統禪師,對惠洪的各種撰述甚爲輕視。如上藍長老説:“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62)《臨濟宗旨》卷一,《卍續藏經》(63),頁169中。惠洪的一些論禪的文字,也屢遭後世禪師的質疑甚至痛斥,如僧祖琇作《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反駁其説。(63)《僧寶正續傳》卷七,《卍續藏經》(79),頁582。至於者庵惠彬著《叢林公論》,多處針砭惠洪著述,評《禪林僧寶傳》“傳多浮誇,贊多臆説,謬浹後學”,(64)《叢林公論》卷一,《卍續藏經》(64),頁767上。評《冷齋夜話》“以是知寂音曾不悟宗門之旨”,(65)《叢林公論》卷一,《卍續藏經》(64),頁766上。評《智證傳》,更詆毁爲“蟊生於禾,害禾者蟊也,寂音尊者似之”。(66)《叢林公論》卷一,《卍續藏經》(64),頁772上。然而,惠彬之説未必爲禪林真正“公論”,宋釋正受便指責“近有作《公論》者,肆筆詆訶,多見其不知量也”;(67)《楞嚴經合論》卷一《統論》,《卍續藏經》(12),頁94上。明釋無愠也説《公論》“斯其論之過當也”。(68)《山庵雜録》卷二,《卍續藏經》(87),頁133上。降至晚明,達觀真可將惠洪“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69)《紫柏尊者全集》卷首釋德清《達觀大師塔銘》,《卍續藏經》(73),頁142上。這些著述一時風靡禪林,頗爲禪僧及習禪士人所喜愛。達觀真可平生於《石門文字禪》“稱之不去口”,(70)《紫柏尊者别集》卷末附顧大韶《跋紫柏尊者全集》,《卍續藏經》(73),頁432下。以至於時人稱其爲“覺範後身”。(71)《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録》卷五《答孝則車公》,《嘉興大藏經》(2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頁681中。其後憨山德清、漢月法藏、覺浪道盛、山翁道忞、蕅益智旭等禪師及錢謙益、陳繼儒、馮夢禎等士人,都對惠洪讚譽有加。當然,也有永覺元賢、俍亭淨挺等禪師對其説禪的文字提出批判和商榷。
平心而論,惠洪詩文受人譏評也是事出有因。所謂“浪子和尚”之説,固然不足以評論其《上元宿百丈》的内容,但他作品中的確有不少對“紅粧聚看眼波俊”場景的艷羨,(72)本集卷一《次韻寄吴家兄弟》。有對“我有僧中富貴緣”身分的津津樂道,(73)本集卷四《郭祐之太尉試新龍團索詩》。流露出與出家人身分不符的世俗趣味。此外有部分與達官貴人、官宦子弟的應酬祝壽之作,格調不高。然而古人全集往往有此弊病,未足深責。至於禪門内部對惠洪的指責與詆毁,則屬於禪學觀念和禪宗派别之間的衝突,是非難以遽定,可以存而不論。
四 《石門文字禪》的流傳和刊刻情況
惠洪的詩文,在他生前就被傳抄,這從本集卷二六《題所録詩》、《題弼上人所蓄詩》、《題言上人所蓄詩》、《題自詩》等文中就可看出。甚至尚未最終編定的《石門文字禪》已在他生前被好事者抄録,如本集卷二六有《題佛鑑蓄文字禪》,卷一六《與法護禪者》更記載了僧人“手抄《禪林僧寶傳》,暗誦《石門文字禪》”的行爲。有的僧人抄其詩文甚至不擇真僞,“飯沙俱一吞”,全部照抄。(74)本集卷六《送瑫上人往臨平兼戲廓然》。
本編《石門文字禪》是惠洪弟子覺慈所編,覺慈,初字敬修,後改字季真,比惠洪小三十歲。南渡後曾在袁州仰山寺當書記。建炎二年五月,惠洪卒於同安寺,卷一三有《夏日同安示阿崇諸衲子》詩,當爲其絶筆。所以本編應是覺慈於惠洪死後編成的。據韓駒所説,與惠洪相别十年,覽其遺編,本欲删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然而“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於書肆,每以爲恨”。(75)《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頁385。可知《石門文字禪》在惠洪死後不久就已刊刻印行,晁公武、陳振孫著録的《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與覺慈所編卷次吻合,或許就是韓駒所説的刊本,然而最初的刊本可能因飽受批評而流傳未廣。祝尚書《宋人别集敍録》稱:“宋代各本皆久佚,刊刻情況不詳,疑由僧寺印行。”(76)《宋人别集敍録》卷一四《石門文字禪敍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679。其説可從。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最早刊本,是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浙江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徑山寺)募緣刊刻的版本,即收入《徑山藏》支那撰述的《石門文字禪》三十卷,由明釋達觀(真可)作序。原書每卷下題“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門人覺慈編録,西眉東巖旌善堂校”。每卷末長方框中刊刻施主、校者、書手、刻工的姓名,如卷一末框爲:“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刻此卷,了緣居士對,徐普書,端學堯刻。萬曆丁酉仲秋徑山寺識。”各卷刻工不同,卷二末爲“建陽鄒友刻”,卷三末爲“上元李刻”,卷四末則爲“溧水芮一鶚刻”,如此等等。這個版本是今存最古老的版本,也是唯一傳本,中國和日本皆有著録。今日通行的各種《石門文字禪》,皆出自這一版本系統。《四部叢刊初編》即據此萬曆本影印。《四庫全書》著録内府藏本,提要稱“此本即釋藏所刊也”。所謂釋藏,即萬曆《徑山藏》。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錢塘丁氏嘉惠堂將此書刊入《武林往哲遺著後編》。民國十年(1921)常州天寧寺刻本,也出自萬曆徑山寺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於一九七三年影印此刻本,並將其納入新文豐影印出版的《嘉興藏》。天寧寺刻本將萬曆本所闕之文字全部補上,可惜所補皆無依據,多爲臆測,實不可信。
《石門文字禪》傳入日本時代已不可考,但至遲在室町時代初期,虎關師煉撰於康永元年(1342)的《禪儀外文集》中就已收有惠洪的疏文數首,皆置於山門疏、諸山疏兩類疏文之首,這正可坐實其疏文在南宋和日本五山禪林的示範意義。其後五山禪林諸文集中,還能看到不少對《石門文字禪》中某些詩文的徵引評論。遺憾的是,日本今存的版本,仍然都出自萬曆本系統。如寬文四年甲辰(1664)二條通鶴屋町田原仁左衛門的刻本,版式與萬曆本全同,只有幾處句子旁夾注異文,略可供校勘。元禄二年(1689)京都堀川小林半兵衛刻《筠溪集》單卷一册,見於積翠文庫,又爲駒澤大學收藏。該書正文首頁二、三行靠下分别題有“宋石門比丘釋德洪著”,“明石倉居士曹學佺閲”。該書並非像學者蕭伊緋所説爲“海内孤本”,而其實是明末曹學佺《石倉十二代詩選·宋詩選》中的《筠溪集》。該書晚於萬曆徑山寺本,而且作爲詩選,在文字上頗有改動删節,校勘價值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寶永七年庚寅(1710),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門貫徹費時二十年的《注石門文字禪》刊刻問世。其注本的底本雖依然出自萬曆本,極少量文字小有差别,然而該注本是迄今爲止《石門文字禪》的唯一注本,承載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因而意義重大。《石門文字禪》注本的出現,似是惠洪著述自室町以來深受日本禪林推崇的必然産物。二一二年,張伯偉、郭醒、童嶺、卞東波等人整理校點的《注石門文字禪》由中華書局出版,嘉惠中國學林,爲功匪淺。這個注本在版本學、校勘學、注釋學上的價值,張伯偉已在該書前言裏詳加評述。可以説,日僧廓門注在中國的出版,對於宋代文學、禪學、域外漢學、中日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廓門的注釋受制於其時代、地域、知識結構的局限,多有紕繆之處,其於儒釋的“古典”尚有會心,而於兩宋士林、禪林的“今典”則多付諸闕如,因而頗顯粗疏。而中華書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標點斷句方面,尚存在着不少訛誤和可堪商榷之處,未能盡愜人意。
爲了推進中日兩國宋代文學與禪學研究的發展,以一個中國學者的身分與日僧廓門貫徹展開相隔三個世紀的對話,同時也爲了使惠洪詩文集的價值更清晰地展示給讀者,十多年前,我爲自己設定了重新全面校注《石門文字禪》的任務,以期利用自己長期研究宋代禪宗文學與校注《蘇軾全集》的經驗,利用當今大數據時代帶來的古籍檢索的便利條件,盡可能給讀者呈獻上一部更爲完善、更便於閲讀的新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