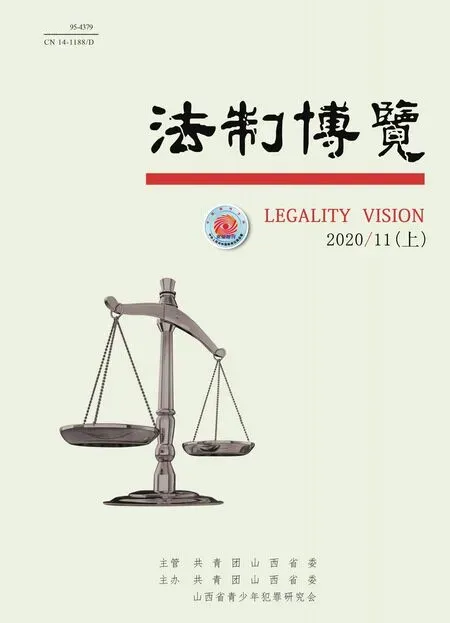司法社会工作介入监狱矫治的探讨
——以C市某监狱罪犯矫治为例
杨 倩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610500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罪犯逐渐增多以及不少国家意识到行刑制度应趋于人性化,推动犯罪矫治工作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职业群,而司法社工则是实现此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实务领域。中国长期采用国家司法模式,20世纪末开始对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局部性探讨。如今中国逐渐向以恢复性司法为主导模式、协商性司法为辅助型模式、传统国家司法为兜底模式的刑事司法制度结构探索,且在我国港澳、上海等地区的社区矫治、监狱帮教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但是内陆对司法社会工作介入监狱罪犯矫治的实践尚浅。
二、司法社会工作介入监狱罪犯矫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推动我国司法模式由国家司法模式向恢复性司法模式转变,权龙曼认为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引进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司法效率[1];袁权将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引入归为社会发展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2];石先广基于实践的基础,也认为恢复性司法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各方的矛盾,并且恢复性司法和我国“以和为贵”的文化基础相适应[3]。恢复性司法模式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我国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区进行了实践探索。
(二)罪犯再社会化的要求
罪犯在监狱进行集体改造是为了认罪悔错,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在刑满释放后能重新回归并适应社会,这样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4]。而目前监狱对罪犯矫治的范围限于在狱内的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后的再社会化是否成功达成,则难以掌握。社会工作关注对服务对象的完整评估过程,追踪评估为验证罪犯监狱矫治是否成功、是否再犯乃至预防再犯提供了可能。
(三)提供新的工作思路
针对罪犯的不同特征,社会工作擅长运用个案、小组的工作方法在罪犯需求基础上提供合理合适的矫治服务,以“柔性”协助罪犯更好地认识错误、重新做人。监狱的监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刚性”管理,对罪犯趋于严肃冰冷的改造与矫治。两者方法存异但目标具有一致性,社会工作的“柔性”与监狱系统的“刚性”结合,为进一步达成、巩固罪犯矫治提供可解之路。
(四)创新相关司法政策
目前社会工作介入监狱在我国港澳地区、沿海城市和北京等地区逐渐增多,内陆极少部分监狱开始摸索实践,但是我国整个司法社会工作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缺乏相应法律政策的支撑,实务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面临不少客观问题,监狱和犯罪矫治社会工作也不例外,因此司法社会工作在监狱矫治实务的开展为相关司法政策制定与创新提供实践支持,为之后的监狱和犯罪矫治扫除一定的政策缺位障碍。
(五)防止罪犯相互感染
监狱对罪犯实施封闭监禁矫治,产生正面效益的同时负面影响同样存在,由于监狱内罪犯构成复杂性、监狱生活单调性、罪犯进出的流动性及罪犯活动空间特定性等客观因素和罪犯自身思想观念和人际关系等的主观因素,使得监狱内罪犯交叉感染的情况无可避免。姚红梅曾提出为避免监狱罪犯交叉感染,应加强管理,为罪犯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注重个别教育,使改造的质量得以提升[5]。这种改造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与方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
三、对C市某监狱罪犯矫治的现状分析
(一)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
近年我国对司法社会工作的关注度逐渐增高,对司法社会工作的实践也开启先河,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出台,但监狱与犯罪矫治社会工作仍然缺乏法律政策支持,对该监区的制度安排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该监区仍然以原有的传统管理模式为主流,很难在现有制度安排下针对不同罪犯的不同问题做出个别化的矫治,也使得监狱部分的安排缺乏法律法规、政策的支持作用,怯于做出有法律政策依据的创新。
(二)现有矫治呈碎片化状态
除了劳动改造,该监区在休息日进行不定时的精神学习和心理辅导等活动,这些活动虽然有提前的安排计划,但如果劳动改造未达标,则直接影响了精神学习和心理辅导等活动。由于该监狱罪犯众多,每次的介入活动参与人数有限,大多数是随机抽取。再者,针对罪犯特殊情况的一对一服务比较欠缺,并且缺乏成效评估,无论是团辅活动还是学习活动等,对效果的评估不具有一个完整的配套体系,成效难以考评。从总体上看,活动的频率、参与的对象和成效评估尚未形成有立体化系统。
(三)对社工的认知度和接纳度比较低
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我国仍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无论政府、社会还是司法体系对该领域的认知度和接纳度都不高,该监狱存在相同问题。从形式上看,该监狱相比于C市其他个别监狱发挥了心理咨询的优势,开展了针对罪犯的不同形式的活动,普遍认为狱内社工的存在就不具有必要性。再者,社工等同于义工和志愿者的思想观念仍未消除,甚至社工就是为监狱做劳务的观念明显存在,社工介入监狱罪犯就显得不那么举足轻重了。
四、司法社会工作在监狱罪犯矫治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法律、政策制定
社会工作属于民政部管理,监狱属于司法部管理,两个不同领域自身有其运行体系及政策制度,监狱与犯罪矫治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监狱的融合,融合运行的法律、政策制度目前比较空白。由法律、政策制度方面引起的歧义是监狱与罪犯矫治社会工作自身无法改变的,必须从源头上解决,发挥法律与政策制度在社会工作和监狱之间的牵头作用。
(二)加强跨部门合作
监狱与罪犯矫治社会工作涉及的部门之间应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工作机构与监狱系统内部要加强沟通协调、协同合作,融合“社工一条龙”和“司法一条龙”,推动“两条龙”形成合作机制,使共享、共担、共商贯穿于合作机制的始终。监狱设置专人和社工机构对接,促进服务的开展。社会工作机构承担的职责不仅包括对罪犯的专业化矫治和帮教,更要对结果成效负责,接受监狱的指导与评估。
(三)明确矫治内容
社会工作者在系统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专业的独特性,将服务重心集中于罪犯问题分析与矫治。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进行分类辅导,针对个别化问题进行个案辅导;适当建立罪犯情感支持网络,发挥家庭情感支持作用;关注罪犯狱内生活状态,避免罪犯相互感染;重点关注成效评估,重视罪犯出狱后的跟踪服务,减轻罪犯再社会化障碍。内化矫治是为解决问题不是流于形式的正确理念,在和监狱的配合下,形成对罪犯“两条龙”立体化的有效矫治。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逐渐职业化,但司法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还处在探索阶段,监狱与罪犯矫治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难以系统化建立,因此要加强对监狱与罪犯矫治社会工作服务的购买,提高准入门槛,防止监狱对监狱与罪犯矫治社会工作者的错误理解。同时,监狱与罪犯矫治社会工作者不仅要精通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知识也要具有法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并且有必要进行定期的学习与培训,为司法社会工作机构介入监狱罪犯进行矫治储备合格的人才队伍。
五、总结
如今的社会变革与进步要求对罪犯的改造从“报复性”向“恢复性”的转变,要达成质的飞跃必须使得社会工作与监狱克服障碍,进行合作并融合。如果要使罪犯达到良好的矫治效果并重新回归社会,最大程度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要从加强法律、政策支持,加强跨部门合作,明确服务内容,强调专业特性,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思路探析,发挥司法社会工作个案与小组以及评估的优势,实现司法社会工作与监狱的结合才能使得监狱对罪犯的矫治达到最大效益化,维护社会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