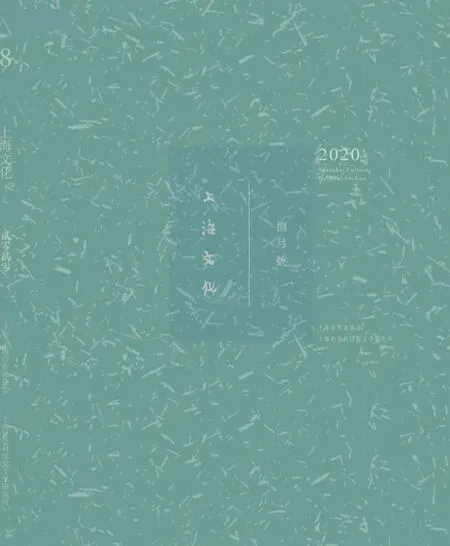论阿尔茨海默症的文学书写
——兼及“医疗叙事”的维度
曹晓华
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简称AD),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系统退化性病症。这种由德国精神病学家在1901年首次发现的疾病,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曾经这种病症被直截了当地称作“老年痴呆症”,人们后来意识到其中的“歧视”意味,逐渐倾向于用“阿尔茨海默症”替代。然而,音译的符码虽然带来陌生化的效果,却丝毫没有减去疾病本身的残忍。即便在国外的相关叙述中,和“痴呆”同义的“dementia”,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来自18世纪末拉丁语的“dementia”,是被“Alzheimer”放逐的能指,但它令人绝望的所指却保留下来,延续在“阿尔茨海默”里,注入到不同的文本语境中。阿尔茨海默症由于病人发病过程中的“遗忘”和“错乱”,使一种病态的“叙事时间”成为可能。这种意识流的记忆紊乱经过文学文本的处理,成为一种刺痛人心的情节张力。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DI)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超5000万,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52亿。①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9: Attitudes to dementia, London: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2019, p.13.失去记忆、意识混沌的病人和消瘦但热切的肺结核病人、脸色苍白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白血病人一起,化为诸多“疾病隐喻”中的一部分。漫长告别中的人性撕扯,出现在国内外多部当代小说中,用不同形状的“记忆碎片”搭建起别样的叙事世界。其中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对语言与心灵的追寻、对伦理与疾痛的拷问,病榻旁和病榻上对生死爱憎的凝视,形成属于“记忆之殇”的“医疗叙事”。
一、疾病书写的文学脉络
在阿尔茨海默症进入大众视野前,疾病书写已是我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20世纪之交的文学作品中,“疾病”的表现方式不再只是“相思泣血”、因果报应的情节呈现,而是进一步从个体经验上升为国家隐喻,暗含着国人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的价值判断。西风东渐影响下的医疗卫生话语,促使“疾病”凝结成一种文化表征。疾病书写关乎社会认知变革,也深刻影响着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范式。通过对“疾病”的命名、发现和反思,各类文学作品开始了“强国保种”框架内的“改造”叙事。五四最有代表性的“疾病的隐喻”,如鲁迅通过“投枪和匕首”完成的国民性“疗救”。同样是审视社会痼疾的“横截面”,鲁迅、郁达夫、冰心等五四作家笔下的“疾病隐喻”,是一种内省式的自我剖析,与世纪之交的黑幕哀情大有不同。对于不同时代疾病书写背后文人的精神特质,有谭光辉、许子东、姜彩燕等学者的论述珠玉在前。①谭光辉10多年前便使用词频统计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认知线索。他对诸多文学文本中的“病”字进行的统计虽然详实,却没有对“病”的概念进行词源学考证。在中国近现代小说中,即便“病”字出现的概率很高,也有可能不是西方医学观念里的病症,而是中国传统中悲秋惜春的心病,所以仅仅通过“病”字的数量统计而不考证不同文本对“病”字的认知和使用情况,就无法重现近代中国人对“疾病”隐喻的恐惧。参见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百年五四的文学“疗救”传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全新时代背景下的修齐治平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20世纪70年代,罹患乳腺癌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追溯了肺结核、艾滋病、癌症等疾病隐喻的变迁过程。尽管通过疾病隐喻的分析,她希望人们能够“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②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7页。然而事实上疾病隐喻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不同疾病的价值判断以及文化层面的各种想象,如同肺结核病人一样,带着病态的热切。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变形为与病症和病因相联系的判断和阐释,而病症和病因成为一种文本象征层面的抽象认知。桑塔格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
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做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①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67页。
桑塔格将犯罪行为以及对犯罪行为的约束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借以分析外界对病人心理施加的压力。“病人”遭受的病痛不再是治疗那么简单,还包括“病人”自身的抵抗能力和具体的疾病种类以及特定疾病的诱发因素。换言之就是一种对病人无意识的诘问:“为什么是你得了这种病?”是“你”而不是别人,必然意味着“你”出离常规的行为或者是比别人更为薄弱的意志力,“得病”成为一种惩罚;是“这种”病而不是别的疾病,这种特殊性的强调具有更为明确的指向性,唤起病人的“内疚感”。疾病隐喻在文本和社会中实际运作的时候,还会对“病人”许诺治愈的可能,成为一种话语规训。
对于病症的抽象把握和疾病隐喻社会属性的提炼,成为一种特定的写作范式。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小说”也在“疗救”话语的延长线上。近年来,随着医疗史研究的兴起和深入,同时因为医学的发展,大众对于一些疾病的认知也与以往不同,当代文学敏感地把握住了人类对于疾病的全新感知,并将其与自身对已知世界的反思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融入到创作之中。文学中的疾病主题是普遍的文学现象,反观己身的疾病探求在不同的文学语境中搭建起相互沟通的桥梁。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将自己罹患睾丸癌接受化疗的经历写成了一篇病中札记。托宾用调侃的语气,不紧不慢地报着流水账——就诊、进一步检查、确诊、化疗、转移……每轮化疗间隔两星期,但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病情急剧恶化,于是两个星期的恢复期被取消。渐渐的,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具不吃不喝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内在的那个我(inner self)不见了,不会自省,也不再会交流;只有那个外在的我(surface self)活着,它只会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其他什么也不会”。②Colm Tóibín, Instead of shaking all over, I read the newspapers.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I had my lunch, https: //www.lrb.co.uk/v41/n08/colm-toibin/instead-of-shaking-all-over-i-read-the-newspapers-i-listened-to-the-radio-i-had-my-lunch, April 18,2019.食欲锐减,失眠,脱发,看不了书,听不了音乐,也写不出小说,还有各种随之而来的疼痛和精神压力,每一天都是一种“纯粹的空白”(pure blankness)。尽管托宾最后挨过了化疗,却被告知身体有多处血栓。但作为一个癌症病人,他感觉血栓已经不那么可怕了。他甚至仔细比较了两者的区别,“在文学中,血栓是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作品,暴烈、不羁、才华横溢;癌症则是莎士比亚的作品,面具重重,可靠的、狡猾的,都令人难忘”。③Colm Tóibín, Instead of shaking all over, I read the newspapers.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I had my lunch, https: //www.lrb.co.uk/v41/n08/colm-toibin/instead-of-shaking-all-over-i-read-the-newspapers-i-listened-to-the-radio-i-had-my-lunch, April 18,2019.
托宾与癌症正面相遇,最后幸存下来,尽管已经筋疲力尽,虚弱到差点无法自理,但还有机会回头整理病中经历写成文字,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然而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病人来说,尽管他们身体机能尚可,却要面对另一种“纯粹的空白”。“纯粹的空白”在他们身上,一开始表现为一种意识尚清醒的自我告别,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自我意识逐步削弱,病人的意识和生活被强制性的“失散”吞没。21世纪以来,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文学书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作品中,它关涉的伦理关怀和人性追思成为当代疾病书写中的重要构成。在王周生、薛舒、于是等作家的笔下,这种特殊的疾病与主人公正面交锋,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
二、疾病引发的记忆转化与个体认知
人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个体的存在方式,失忆则意味着个体身份的消解和个体认知的紊乱。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主题的小说,避不开“失散”的起点——失忆,也就是所谓“发病”的前兆。由于疾病最初的表现形式较为隐蔽,而病人又大多是老年人,病态的“健忘”往往潜伏在波澜不惊的生活细节之中。该病症目前的文学呈现,多以病人家属/陪护人作为叙事者。鉴于国人对于疾病护理与亲缘关系两者间天然的认同感,讨论中国作家笔下的阿尔茨海默症和病人,也离不开特定的医护空间和疾病认知。病人的失忆过程恰恰构成了陪护人的痛苦记忆,这种记忆转化使叙事者对自身存在的思考和质询更为锐利。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病人来说,“失散”,首先是与正常生活脱轨,远离亲人和生活常态,仿佛是计时的响铃,预示着之后的倒计时。在于是的《查无此人》(2018年)中,“失散”的起点是子清接到的电话,再婚的父亲突然不知所终。身处古罗马竞技场,烈日当空,生活的血口在不经意中向子清张开。子清回国之后,为了父亲的护理绞尽脑汁,最后她和父亲、保姆3人组成了一个面对病魔的“堡垒”,但这个堡垒最后还是无法抵御父亲逐渐消失的“时间”和“生命”,子清第一次开始打捞父母的过往,将自己的生命编织进家族的谱系。在薛舒的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2015年)中,“失散”的起点是父亲骑车去领免费乘车卡,他在家门口迷路。那张最终由妻子领回家却没有被使用过的乘车卡,成为了“远去”的一部分。在王周生的《生死遗忘》(2010年)中,肖子辰的“失散”以一种戏剧化的“归来”呈现。这位已经发病一段时间的老先生忘记了20年前的离婚,不由自主回到了前妻凌德磬的家。退休的护士长凌德磬,得知肖子辰再婚的妻子已经去世,经过重重考量,她决定将患病的前夫接回家中照料。然而肖子辰对亡妻的情感还是伤害到了凌德磬,伤痛欲绝的她突发中风,最后为了救忘记关煤气的肖子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三部作品,是我国当代文坛疾病书写的别样呈现,而疾病通过病痛和共情成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文学交流的纽带。2008年,美国作家史蒂芬·梅里尔·布洛克(Stefan Merrill Block)出版了处女作《遗忘的故事》(The Story of Forgetting),小说将“失散”处理为“出发”。亚伯(Abel)和塞斯(Seth),一位是步入暮年、讲述个人史的老人,另一位是沉浸于虚无主义的少年,他的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他便出发探寻母亲的家族史。亚伯和塞斯的个人旅程由Isidora的故事连接起来,这是一片没有记忆、也没有遗忘的乐土。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Isidora城有着镶满贝壳的螺旋形楼梯,出发曾是少年,抵达却已是老年,“广场上有一堵老人墙,老人们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当初的欲望已是回忆”。①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页。就布洛克的亲身经历来说,他和祖母娜娜(Nana)“失散”的起点是那张单程票——“我的外婆买了张单程票,搬到德克萨斯和我们同住,而那时12岁的我在家自学,渴望交到朋友”。①Stefen Merrill Block, A place beyond words: the literature of Alzheimer’s, https: //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placebeyond-words-literature-alzheimers, August 20, 2014.“单程票”也可以是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失去记忆的比喻,不可逆的遗忘,解开与世界的万千勾连,像是断裂散开的线头。
在小说中,阿尔茨海默症对病人记忆的剥夺,可以培植出盘根错节的情节线索,也可以将看护的个体经验投射在自我认知的焦虑中,进而对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进行高强度的精神拷问。随着大脑斑块的沉积,神经元大片死亡,神经纤维绝望地缠绕在一起,暗示患者的生命和记忆是一个“死结”。到了疾病后期,病人同时失去了“内在的自我”和“外在的自我”,自然也无法“自省”。由此,文学作品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观察和叙述,多从观者的角度出发。美国画家威廉·尤特莫伦(William Utermohlen)于1995年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他坚持每年给自己画一幅肖像画,5年后他已经忘记了如何作画,画面从具象到抽象,阴影过渡变成抽象的色块,最后只留下模糊的轮廓。如果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试图坚持创作,文字和语句的拿捏也大抵如那画作变化,大段语言最后变成毫无关联的字词,直至纸上不留一点墨迹。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将记忆的连续复制视作“持留记忆”的呈现,但是每一次记忆的复制都会经历某种程度的弱化,而个体决定了时间对象在意识中的显现,这就是胡塞尔所谓的“内在时间”。②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学说”参考了布伦塔诺的时间分析。参见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1-57页。如果说胡塞尔借助音乐说明内时间意识,音符的串联和乐曲的呈现意味着前一个音符并未消逝,而是“余音绕梁”般留在了接下来的乐曲片段中,那么尤特莫伦的画则用不断“蒸发”的笔触和色块呈现出意识消逝后时间尽头的空白。这种过程在小说家的人物身上,表现为个体精神残缺后语词的“消散”。
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失散”,不仅是遗忘周遭的世界,也是遗忘自己。洪堡特说,语言是人类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③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页。在这个“失控”的过程中,个人和家族的记忆都被抛掷到病魔的黑洞中,转瞬即逝,只是偶然散落下没有逻辑的只言片语,那是记忆和自我剥落下的残片。阿尔茨海默症病人语言功能失调,不仅是表达性言语活动受到影响,病人对语言信息的接受也在退化。这种双重的退化使“流射”出的精神主体易变而残缺。子清父亲王世全突发奇想的“快走”背后是游子归乡的残面,老薛对金钱非同寻常的珍视背后是艰难的成长环境以及成年后压抑心中的遭际闪现出的残迹,还有肖莹父亲肖子辰有意无意吐出的英文。在不同的医疗空间中,作为看护者和观察者的叙述人和他的观察对象——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亲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悖论,无限接近至亲的同时,至亲却在飞快地远离共享记忆中的角色,疾病导致的亲密关系和疏离感交织并行。这种情感的悖论促使作者开始反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终极哲学命题。面前的至亲仿佛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但记忆剥夺使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模糊。
三、“病态”时空的“错乱”与“重置”
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依然爱丽丝》(Still Alice)中,大学语言学教授爱丽丝一生都在研究语言,却不曾料想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自己50岁的时候突然面目狰狞。小说用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爱丽丝视角,将语言紊乱后日常生活的“失控”和“脱轨”表现得丝丝入扣。当这些“遗忘”的细节聚拢在一个病人的身上,无论是柔和还是炸裂的笔触或是镜头都难掩“失散”后的记忆之殇。《依然爱丽丝》的结尾处,已经失智到无法自杀的爱丽丝失去了掌控自己命运的最后机会,但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面对女儿的问候,爱丽丝依然表示“感到了爱”。对于这个“爱”的处理,《遗忘的故事》的作者布洛克虽然感到心碎,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现了另一种“爱”与“遗忘”的和解。如何面对已经不是那个他/她的他/她?“这些天我的母亲告诉我,我应该学会融入她(Nana)的世界,和她一起大笑,把握住现在,不再去寻找那个曾经的外婆。”①Stefen Merrill Block, A place beyond words: the literature of Alzheimer’s, https: //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placebeyond-words-literature-alzheimers, August 20, 2014.当年12岁的布洛克面对外婆,尽管知道她是个病人,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在孤独的人生阶段有一个一直陪伴自己的玩伴——“我必须羞愧地承认,在十二岁天真烂漫又自私的我看来,外婆智力退化有时候还挺好的,她会因为我那些小孩子的玩笑话开怀大笑,看我打几个小时的游戏,和我一起去Kriss Kross的热舞派对,跟着《狮子王》的伴奏一展歌喉。”②Stefen Merrill Block, A place beyond words: the literature of Alzheimer’s, https: //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placebeyond-words-literature-alzheimers, August 20, 2014.布洛克的母亲觉得这才是外婆的“真我”(true self),一老一小正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汇合。文学作品对阿尔茨海默症做的一种诗意处理,是将不同人生阶段在护理时期的重合染上黄昏暮色,夜幕终将降临,但没有人愿意抹去疾病肆无忌惮爆发之前的人情温热。肖子辰的外甥魏乐,一开始对外公住到自己家里并不满意,因为外公会占据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私人空间。但是他很快发现,外公的记忆碎片还没有将其撕扯成一个无趣的人。时间长了,外公支离破碎的句子里居然也可以找到些许的生活智慧。魏乐把外公带到公园的英语角,在这里病魔似乎放缓了脚步,因为周遭环境的刺激,外公的病症没有加速恶化。魏乐和外公的温馨相遇,是阿尔茨海默症相关叙述中的暖色一刻,正是因为这样的灵光乍现,总让看护的家属产生昔日的那个“他”依然还“在”的错觉,对病患的感情愈发难以割舍。
海德格尔曾将“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视为“流俗时间”,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91页。这种机械钟表规定的精确时间无法反映人的真实生存样态。人对于未来和现在的把握建立在对过往的追溯中,但是定位现时的坐标在阿尔茨海默症病人身上发生了偏差。老薛患病之后的记忆错乱,也打碎了作者自己的生活秩序。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不是人们惯常认知中的线性时间,阿尔茨海默症的时间是发散性的,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使过去的某些片段“闪回”。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未能找到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机制和发病原因,但是临床病学认为脑外伤很有可能是这种疾病的诱因,父亲的发病让作者不由自主地联系到父亲年轻时候的一场车祸。父亲受伤住院,重重绷带让他在女儿眼中“面目全非”。当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去医院探望父亲的时候,她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曾经的父亲可以体贴默默抠冰凌花的女儿,但是现在的父亲却会怀疑妻子子虚乌有的出轨、一次又一次的日夜颠倒、吵嚷着“回不了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陌生人。薛舒在小说的引子里写到:“他叫我‘小姑娘’?他的记忆已经退回到我的少女时代了?”①薛舒:《远去的人》,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4页。“年幼”的薛舒与父亲再次“相遇”,但是父亲却把她当做了别人的女儿。记忆消失的同时,阿尔茨海默症病患从失智到成为植物状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表现出一种让人心碎的“返老还童”,成为不断倒退的“老小孩”。如果遇到恰好在不断成熟的少年,两个人生阶段的交叠便会映射出难得的“光彩”。《查无此人》中的子清,因为父亲的病而开始追溯父母结合的来龙去脉。去哈尔滨寻亲的线索明晰起来,仿佛独立的水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河流。在这顺理成章的回溯之前,她艰难地调适着自己的生活,对奥托说,“我不再是我”。②于是:《查无此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8页。与薛舒的非虚构不同,于是笔下的子清,制造了另一种“重逢”,与父母的过去相逢,重新审视曾经被否认的自我。这种疏离又陌生的“病后”追认,并未给父女情添上暖色,而是平添了些许中年的无奈和苦涩。子清原本自由随性、甚至有一些慵懒的单身生活,让她一度以为人生只需要对自己负责,然而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强行将一种病态的时间表嵌入女儿的生活。子清在照顾病患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抽离”,试图对自己全新的生活样态进行形而上的审视。然而到了小说后半段的“寻亲”之旅,“抽离”变成了“相遇”,只不过这种对人事亲情的“贴近”并不是子清主动寻找的。子清将对“我”的寻找,与寻找父母的历史重叠起来,如同布洛克笔下的塞斯。父母的疾病成为子女发现“真我”的契机,尽管对于患病的双亲来说,疾病是遗忘“真我”的噩梦。在子清的寻亲之旅中,她把父亲的近况放在苹果平板电脑Ipad里,向亲戚展示,代父亲向这些亲戚道别。这个过程中的子清看似在为父亲的影像做旁白,实际上在为自己的人生做脚注。她对实际情感的剥离,如同与Ipad中的父亲影像相伴相随,却从未想起打一个电话问候父亲。
除了发散的时间轴,阿尔茨海默症的文学书写还离不开医疗空间的转移和变化。病人与亲人们“失散”,与“自我”的疏离,与“家”渐行渐远,一切不再由自己掌控。《查无此人》的终章是“送别”,将父亲王世全送到护理院的新家,却没有丝毫回家的欣喜。子清和保姆给父亲造就的“家”,已然不是父亲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地方。而护理院的结局,也是阿尔茨海默病和病人家属互相撕扯的结局。病人记忆的空洞,变成亲人的情感伤痛,病人失去”自我”的过程,是病人精神的“流浪”。《远去的人》中,父亲从家里的主心骨,蜕变成多疑、贪财、时而狂暴时而胆小的“看门人”。他已经不能分辨自己守护的“领地”是否还属于自己。他那“乡下的妻”正在等他,而现实中的妻女成了阻止他“回家”的雇主。他身处家中,心却开始流浪,对一旁家属的嘶喊置若罔闻。这是另一种“失散”,“家”的周围是他的整个世界,偏偏世界从“中心”开始垮塌。《生死遗忘》中的肖子辰,这个分不清前妻凌德磬和第二任妻子柳沁的人,分不清母爱和性爱的人,将清醒时的犹豫和徘徊变成了病发后匪夷所思的“回家”之旅。他在失去柳沁后无意识地进入了前妻的家,作为护士长的前妻左右权衡,收容了他,却无法阻止他再一次回到自己和柳沁的家,并在那里怀抱亡妻的相片入睡。这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背叛”,阿尔茨海默症病人无法刻意隐瞒自己曾经的记忆,心偏向哪里,回到那里就像本能一样自然。也正因为这种不加隐瞒的“真实”,他们的行为“伤人”而不自知。离婚前夕面对凌德磬追问的肖子辰,推心置腹地表示无法在柳沁和凌德磬的爱之间做出区分,“肖子辰越是坦诚,凌德磬越是无法忍受。正是这种坦诚,这种触及灵魂的困惑与忏悔,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①王周生:《生死遗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7页。如今神志不清的肖子辰用同样的“坦诚”再一次伤害了凌德磬,而老护士长终于在焚毁了所有情书后中风不起。同样伤人的“真实”还出现在薛舒的父亲老薛发病后喃喃的“还是我做主”,不由自主的语句隐藏着他对自己婚姻的基本认知,而这种认知一直以来隐藏在他的潜意识中,所有郁积的矛盾经过β淀粉样蛋白(β AP)的改造,要么成为陷落的漩涡,要么成为喷发的火山,让家属心力憔悴。阿尔茨海默症作为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病人自述成为一种逐渐“不可靠”的维度,主体记忆的削弱将会导致语句间逻辑关系的“失联”与“瘫痪”,最后成为存在但无法自证的叙述主体。当叙述者是病人的亲人时,无法将观察者的视角与血脉亲情的悸动完全剥离开来。情感的投射过于强烈将会影响文本的张力,但情感的抽离又容易使叙述浮于表面。但是意外的,在这场胶着的“告别”中,文字获得了不同于病人自我剖析式叙述的力量,一种“凝视深渊”时最为直观的感触,以及“被深渊凝视”时的惊惧与迷茫。而随着大脑神经系统的完全退化,病患与家属陪护情感疏离,在他们陷入无尽的空白和混沌之时,大脑意识的告别将肉身与精神的哲思彻底留给了观者。
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日益凸显,阿尔茨海默症越来越为人熟知。阿尔茨海默症不仅将记忆和认知作为医疗叙事的拓展维度,其遗传的特性更让叙述者有一种“预见”性的危机感,反过来加强了精神锤炼的力度。值得一提的是,与桑塔格疾病论说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西方“叙述转向”,“把人的叙述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尤其明显);用叙事分析来研究对象(在历史学中尤其明显);用叙述来呈现并解释研究的发现(在法学和政治学中尤其明显)”。②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口述史、非虚构、叙事话语等纷纷进入叙述学研究,但此时的跨学科还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叙述转向直到2001年才与医学邂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丽塔·卡伦(Rita Charon)在这一年正式提出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并开始担任《文学与医学》杂志的主编。然而与文学中的医疗叙事不同的是,“叙事医学”通过培养医生理解、把握病人病痛的“叙事能力”,来改善医患关系。“病人则期望医生能够理解他们所经受的痛苦,见证他们的苦难,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在;医生也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使他们能够反思自己的实践、认真而坦诚地与其他医生谈论自己对医疗实践的反思和困惑、尽可能准确地理解病人、特别是危重病人所经受的苦难,并感知死亡对人的意义等。”①郭莉萍:《从“文学与医学”到“叙事医学”》,《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3期。也就是说,目前西方文学与医学的结合实际上具有实验性,侧重于临床医学的可操作性。然而,中西方医学护理观念的差异导致疾病中的共情体验不同。家庭成员居家对病人进行看护在中国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住院治疗直到清末民初才开始为国人接受。②杨念群认为西方医疗现代性的重要体现在于将病人托付给医院看护的“委托制”,这种“不近人情”的护理方式在清末西医东传时饱受中国病人家属的诟病。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122页。回想爱尔兰作家托宾化疗的经历,在治疗过程中他与医护人员的直接沟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医生的病情判断与用药计量。在西方现代医院的“委托制”看护制度下,“医学叙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桑塔格所谓的“疾病隐喻”也找到了话语权力的源头。但卡伦担心的“叙事能力”在中国的医护语境中借鉴意义有限。血缘、亲情伦理、赡养等关键词是中国人情社会的重要构成,医患关系不仅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还关乎病人家属。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护工”和“护理院”为何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作家“疾病叙事”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护工”在这些作品中已经不仅是一种职业,患者家属希望他们能把病人当做亲人对待,通过一种超越雇佣关系的情感培养,使自己患病的亲人在自己不在场时得到细致的护理。一旦这种情感培养失败,或者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病人与医护人员的矛盾就会演变为病人家属对整个医疗系统的指摘。另一方面,医院或者护理院与患者的“家”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其中的人伦纠葛充斥着病患家属的“内疚”。正是亲情伦理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异,使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乔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展望医学与文学的“邂逅”后的风景,认为人文修辞融入医学叙事或改变“专业的医疗叙事声音”,而“就像多胞胎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不只有一个故事想要冒头”。③Hartman, G, Narrative and beyond,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004 (Fall).文学与医学,这种生死离别间绽放出多种人性书写的维度,值得更多的观照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