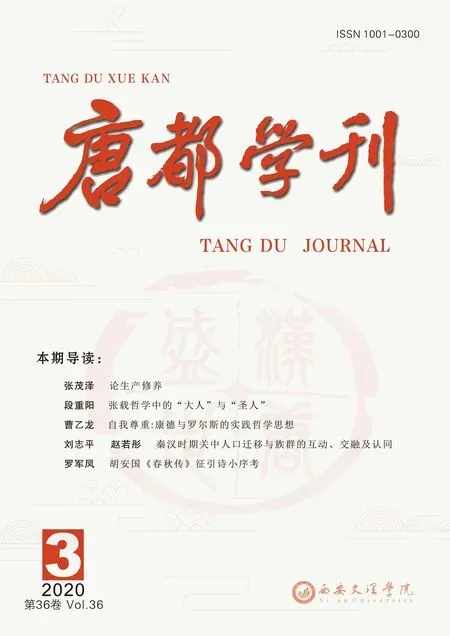汉代区域历史研究的新收获
——读贾俊侠《两汉三辅研究:政区、职官与人口》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汉代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作为国都所在,三辅地区对汉帝国而言,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而高度重视三辅区域,自然是汉代区域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贾俊侠所著《两汉三辅研究:政区、职官与人口》(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三辅研究》)一书,堪称汉代三辅区域历史研究的里程碑。于汉代区域史而言,亦是一项非常值得关注的新成果。
一、《三辅研究》的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
《三辅研究》分上、中、下三编,共九章。上编为“两汉三辅政区研究”,由前三章构成。首章“文献所见两汉三辅之政区”,展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当中包含三辅及其属县名称的史料,以静态呈现为主。第二章“两汉三辅政区沿革及其属县”,对三辅政区形成、治所更动、辖县增减进行了动态梳理。第三章“两汉三辅地位的变化及原因”,通过政区变动判断政区地位升降,进而分析导致地位变化的原因。
中编“两汉三辅职官研究”包含第四章至第七章。第四章“文献所见两汉三辅之职官”,勾稽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当中出现的三辅长官及属官。第五章“两汉三辅长吏之职掌”,以“一般职掌”“特殊职掌”的两分法,对三辅长吏的职权进行了归类。第六章“两汉三辅长吏的选任与迁转”,分西汉、东汉两大时段,考察了三辅长吏的选任、迁出、任期等关键问题,并对相关人事政策的原则性、规律性做了归纳。第七章“两汉三辅佐官及属吏”,将长吏以外的三辅官员分为佐官和属吏两类,对其官称、职掌分别做了稽考。
下编“两汉三辅人口研究”由第八章、第九章构成。第八章“两汉三辅地区的人口数量与分布”,分西汉、东汉两个时段,对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人口数量与分布分别进行讨论,并从中发现东汉相比于西汉所发生的变化。第九章“两汉三辅地区的宗族与学术文化”,首先分区域搜集文献所见两汉三辅的宗族大姓,然后以大量实证展示两汉三辅地区的学术文化成就,由此发现三辅学术文化水平在两汉之间的变动,以及三辅区域内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章节设置来看,《三辅研究》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特点(《序二》第6页)。不过,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该书内容设置更为系统、考察更为深入。在政区沿革方面,《三辅研究》力图扭转以往三辅研究中重京兆而轻左冯翊、右扶风以及县级政区的取向。在职官制度方面,除了将三辅长官的职掌与一般郡守的差异揭示出来,还通过对三辅长官一般职掌与特殊职掌的分别归纳,使两汉三辅长官作为地方官与中央官的双重身份明朗化。此外,该书详细考察了三辅长官在选拔、迁转、任职时限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以及三辅佐官与属官的设置、职能,有助于全面了解三辅政府机构的运转情况。在人口构成、分布及社会文化方面,《三辅研究》注意到宗族势力对三辅地区历史发展的强大影响,并将三辅区域内部发展进度的差异揭示出来,显著提升了三辅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层次。
在研究方法上,《三辅研究》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重视传世文献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认识到考古材料证史、补史的积极意义,尽可能全面占有相关材料。在分析史料时,坚持信则传信、疑则考析的原则,力争全面、完整、准确地挖掘材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为提升研究效率及成果的可靠性,作者还大量采用统计方法、表格形式,通过图表比较,揭示两汉三辅地区历史演进的过程。这种做法的好处,正如作序者所指出的,“寓繁于简,不仅能使人把握全局,而且又可以从全局中把握局部,对于分析研究问题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序二》第8页)。
二、《三辅研究》政区史的亮点
读者的问题意识、知识背景不同,学术收获自然有别。就笔者个人而言,《三辅研究》的政区史部分有两点尤为印象深刻。
1.西汉内史的左右分化,以及右内史再分为京兆尹、右扶风
汉代三辅由秦及西汉前期的内史演化而来,内史地左、右分化的时间问题,学术界以往有三种观点,分别为“景帝二年说”“武帝建元六年说”“景帝之前说”。作者注意到,《史记》《汉书》晁错本传或曰“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或曰“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由此推断“景帝之前说”“似乎不能成立”。余下两说,就史料而言,各有所本。《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孝景元年,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可为“景帝二年说”之证据。因为景帝即位次年改元,所谓“孝景元年”,正是晁错本传“景帝即位二年”。而《汉书·地理志》曰:“右扶风,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则为“建元六年说”张本。对于两处记载的冲突,作者认为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两说并不矛盾,关键是要意识到,“内史官和内史地的起源和分化过程是不一样的”,应当“分别对待内史官的分治和内史地的分置时期”。(29页)也就是说,汉景帝元年分置左右的为内史官,而内史地到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
在分析右扶风之置时,作者坦承,“在正式分置内史政区之前,对它的管理已经进行了分工,这对我们讨论主爵都尉与右扶风的关系有极大的启发。”又说:“笔者鉴于内史政区分左右是先分官管理,然后再分开政区的启发,认为在太初元年以前,主爵都尉已经治土管民。即其与右内史分管右内史政区,并且主爵都尉分管的部分正是后来的右扶风政区。正因为主爵都尉事实上成为了右内史西部地区的长官,所以武帝太初元年才将右内史政区开置,并将主爵都尉更名为右扶风。”(42-43页)至此,内史左右分置,左内史最终演变为左冯翊,右内史最终析置为京兆尹、右扶风,三辅形成的过程得以明晰。
2.三辅政区变动背后的政治含义
东汉时期,原属京兆尹的华阴、湖、船司空三县改属弘农郡,而京兆尹则从弘农郡接收了商、上雒两县,又从左冯翊接收了长陵与阳陵两县,《三辅研究》认为,“这种政区调整的政治寓意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包括两点:“其一,东汉皇室出自汉景帝之子长沙王刘发一系,其对于高祖长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将长陵、阳陵从左冯翊划入京兆尹应当是从国家祭祀方面的考虑。其二,将华阴、湖、船司空三县划归弘农,又从弘农将商、上雒划入京兆尹,当是从关东本位的思路考虑”。那么,东汉王朝关东本位的政治思维究竟如何体现呢?作者分析:“华阴、湖、船司空三县划归弘农使关中丧失了天险,从弘农将商、上雒划入京兆尹使得京兆尹与弘农犬牙交错,有利于东汉政府控制关中”。而之所以强化对关中的控制,“从根本上讲”,“是东汉政权防范重点转移的必然结果”,因为东汉王朝“防范的对象由西汉时的关东豪强转向了关中豪强和西北羌人”(68页)。
除了较早发生的京兆尹辖区的变动,东汉末年,右扶风政区被析置。《续汉书》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中平六年,省扶风都尉置汉安郡”,领右扶风西部五县。(1)《后汉书》志19《郡国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3408页。《三辅研究》认为,此次析置“是当时中央政权崩溃、武将擅权、地方叛乱的产物。”“汉安郡设置于中平六年十二月,此时距汉献帝即位已三个月,距董卓出任相国已一月。设置汉安郡很难说不是董卓的决定,但无论是谁的决定,笔者认为汉安郡的设置更多是因为凉州边章、韩遂等的叛乱。韩遂等的叛乱起于灵帝中平元年,董卓与皇甫嵩、张温等均被派往镇压,但数年未能平定。中平六年东汉中央政权崩溃后,这股地方势力更得以坐大,其对关中地区的威胁无时不在。故笔者认为此时省去右扶风都尉而设置汉安郡意在建立安全缓冲区以保护长安,其属县全部在原右扶风政区的西半部便可佐证。”
另有新平郡,《后汉书·献帝纪》载,兴平元年(194)十二月,“分安定、扶风为新平郡”。该郡只领二县,其一便是原属右扶风的漆县。对于新平郡设置的背景,作者注意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皇帝政令不出宫门,各地割据势力往往自领郡守或州牧”,“新平郡的设置极可能是出于对地方势力的承认,即因存在地方势力而被动设置新郡”。作者还认为,对设置新平郡一事,可以结合汉灵帝中平五年(188)以来汉阳郡先后析置南安郡、永阳郡的记载来理解。“凉州汉阳等郡在灵帝中平六年以来一直处在战乱割据之中,何以能陆续开置为数郡?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兴平元年设置新平郡两者具有共同性,即他们设置极有可能是出于对割据势力的承认或者安抚。故建安十九年,曹操派夏侯渊平定盘踞在陇右的马超、韩遂及诸羌氐势力后,便省并了安东与永阳两郡,这侧面反映出这种设置新郡现象是非正常的。”(122-124页)《三辅研究》采用的这种全盘考虑、横向比较的思维方式,说服力很强。
三、《三辅研究》职官、人口史的亮点
《三辅研究》在涉及职官、人口史方面也有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知卓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对曾任三辅长官者的细密考证
《汉书·百官公卿表》未载汉宣帝五凤二年至甘露三年(前56—前51)何人出任右扶风。但《文献通考》载“陈万年、郑昌皆以守相高第,入为右扶风”,对于这个记载,《三辅研究》按:“陈万年在宣帝神爵元年至五凤二年(前61—前56)间出任右扶风,加之《文献通考》载两人均是由郡国守相政绩优异者迁入,则郑昌应该是西汉之右扶风。并且其出任右扶风应该在陈万年之后,但不知其出任右扶风的具体时间段。”为了确认这个时间段,作者注意到《汉书·刑法志》曰:“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于定国自地节元年至甘露二年担任廷尉,郑昌担任涿郡太守,必在此期间。而“在这十八年内,右扶风先后有尹翁归、陈万年”,陈万年于五凤二年既已卸任,曾担任涿郡太守的郑昌,以故两千石而出任右扶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三辅研究》认为,“《文献通考》所载右扶风郑昌与宣帝时涿郡太守郑昌为同一人,他在宣帝五凤二年至甘露三年内担任右扶风”,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对于右扶风傅干,《三辅研究》亦做足了考证工夫。《后汉书·傅燮传》载,中平四年(187),叛军攻汉阳郡,傅燮时任汉阳太守。“时北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素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子干年十三,从在官舍,知燮性刚有高义,恐不能屈志以免,进谏曰……干知名,位至扶风太守。”从中平四年傅干十三岁的记载推断,“其主要的活动时间应该是在汉献帝及曹魏时期”。考虑到“在两汉,尤其是东汉史书中,将右扶风称为扶风太守的情况比较常见,而曹魏时期将右扶风去‘右’改称为扶风郡,称其长官‘扶风太守’”,作者坦承了一个断代的困难,即傅干任扶风太守“不知是指东汉之右扶风还是曹魏之扶风郡太守”。不过,作者并不放弃,“又查傅干事迹不见载于其他史籍中,唯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九州春秋》载建安十九年有参军傅干,其‘字彦林,北地人,终于丞相仓曹属’。清代严可均认为这两人是同一人,故其《全后汉文》载:‘傅干,干字彦林,小字别成,燮子,官扶风太守,终丞相仓曹属。’笔者认同此观点,且此丞相当指曹操。由此,笔者认为傅干为东汉时期右扶风可能性更大,且时间在汉献帝时期。”(150-151页)
2.对三辅长官迁转之政治背景的认知
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作者发现,“西汉元帝以前三辅大多久任,而成帝及以后任期变短,尤其在哀、平两帝时期三辅更换更为频繁,几乎一年一任。”而宣元时代任期较长意味着“中央吏治稳定、选举清平”。成帝以后任期短暂,“三辅长官的更换如走马灯一般,这也是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吏治选举不平的反映。”(248页)
至于东汉时代,统计结果表明,东汉“中央官迁入京兆尹共有13人”,而包括侍中、尚书令在内的中朝官有10人,“占迁入京兆尹的中央职官的76.92%”。作者认为,“东汉朝廷任命中朝官和尚书台官员出任京兆尹有两重涵义:一是提升亲信官员的秩级;二是利用亲信官员加强对三辅的控制。”另外,“屯骑校尉、讨虏校尉、匈奴中郎将出任京兆尹,则是东汉朝廷应对西北边患的具体表现。”(268-269页)
3.对西汉长安城人口问题的讨论
以往不少学者认为,《汉书·地理志》载汉长安城“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户均刚过三人,不符合五口之家的常规,因此怀疑记载的真实性。有的学者从漕运规模逆推西汉长安城容纳的人口应在四十万以上。作者认为“学者的观点仍有商榷之处”,“《汉书》的记载是有一定道理的”。理由在于,“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汉长安城布局来看,宫殿建筑占据了大半的面积,其余主要为列侯、关内侯、官员的府邸,北部为市场,真正能留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区域极其狭小。”民众生活空间有限,此其一。针对以漕粮规模估算人口数量的做法,作者辨析道:“从漕粮来讲,主要运往太仓,其作用主要有三:一是满足宫内人口的需求;二是给官员发俸禄,如《史记·平准书》所谓‘以给中都官’以及‘诸官’等;三是供给军队、实边移民及战略储备,如远征匈奴、西域的军队后勤供给,被迁往边关地区和充实陵县的民众的口粮和奖励都需要从太仓拨给。”(310页)漕粮不可能都用来供应长安居民,以漕粮逆推长安人口,是不科学的,此其二。总体来看,所论合情合理,堪称卓见。
4.对三辅区域内文化差异的辨析
通过制作“士人分布情况表”“所出书籍数目表”“私家教授籍贯统计表”“五经博士籍贯分布概况表”等表格,《三辅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对三辅学术文化发展所做的判断:“两汉时期三辅内部学术文化发展水平也不统一,京兆尹、右扶风学术水平发展迅速,左冯翊则相对迟缓。”而在京兆尹与右扶风两区的比较中,作者进一步指出,“西汉时期以京兆尹为中心的形势得到了改变,右扶风后来居上,成为三辅地区学术文化的中心”。
除了揭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三辅研究》还从“五经博士家法”“私家教授”“世代习经”三个方面,展示了右扶风经学文化的“繁荣和发达”。而对文化发展的另一极——左冯翊日趋式微的原因,作者注意到扶风茂陵后来居上,吸引了大批强宗大族,从而对左冯翊长陵、阳陵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东汉将长陵、阳陵划归京兆尹,则使左冯翊“失去了涵养士人的土壤,严重影响到左冯翊地区文化的长期、持续发展”。以这样的方式对文化面貌进行描述,对文化演进做出解释,离不开对史实的全面把握,对辩证思维的良好运用,对理论深度的自觉追求。
四、对《三辅研究》的几点建议
《三辅研究》值得改进的地方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对“三辅尤异”的理解似乎过于宽泛
著者认为,“三辅尤异”“是指三辅在行政方面的一部分特权:一是三辅地方长官任命无籍贯限制,无需回避;二是‘汉代只有三辅长官可以自行任用他郡人’;三是可直接上名尚书调补属县令长;且属吏的秩级高于一般郡国。”(202-203页)这个理解似乎过于宽泛。
《汉书·循吏传》载黄霸为左冯翊“二百石卒史”,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三辅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独二百石,所谓尤异者也。”(2)参见《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628页。乍看此注,可能会认为,三辅“尤异”有两个表现:一曰“得仕用它郡人”,二曰“卒史独二百石”。与《三辅研究》所列举的三辅行政特权第二项和最后一项“属吏的秩级高于一般郡国”相对应。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三国时期注家的解释,未必符合西汉实情。再说,如淳注本身在注文中用了一个“而”字,此字虽有并列用法,但也常有转折意味。“所谓尤异者”有可能仅指“而卒史独二百石”为言,在这个意义上,“尤异”仅指三辅属吏秩级高于一般郡国。
而在另外一处注文中,如淳显然是以秩级高来解释“尤异”的。《汉书·张敞传》:“勃海、胶东盗贼并起,敞上书自请治之”,“天子征敞,拜胶东相,赐黄金三十斤。敞辞之官,自请治剧郡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壹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对于其中的“三辅尤异”,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史秩百石,又《循吏传》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谓尤异也。”毫无疑问,在如淳看来,三辅属吏比其他郡国属吏秩级高,这就是“尤异”。
有学者认为,如淳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首先,虽然三辅长官与卒史秩次确较它郡为高,但赵广汉须‘奏请’,才得到‘长安游徼狱史秩百石’的待遇,恰说明从制度上说宣帝之前长安县属吏秩次与它县相同,我们由此可知三辅所属官吏并非都比它郡秩高。其次,从《张敞传》本文来看,张敞要的‘比三辅尤异’的待遇,不是普遍提高胶东国官吏秩次,而是‘破格提拔’在追捕盗贼过程中有功的官员”。在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郡县属吏以‘尤异’除者共5例,皆与捕盗有关。这种低级属吏以‘捕格群盗尤异’而越次升迁的例子,正是张敞所言之‘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一切比三辅尤异’。”(3)参见李迎春《秦汉郡县属吏制度演变考》,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5页。
总之,所谓“尤异”,原本仅指表现突出。从尹湾汉简来看,“尤异”并不局限于三辅,三辅以外的郡国在行政过程中也会出现尤异者。按照考课的一般规程,此类人员或优先提拔,或“破格提拔”,依情理而言,任何地区莫不如此。如果各地“尤异”待遇相同的话,那么张敞特别请求“比三辅尤异”似乎无此必要。从这个角度考虑,“三辅尤异”必定有其不同于普通郡国“尤异”的地方。不同之处很可能在于,三辅属吏的秩级原本就高于普通郡国,同样是因“尤异”而提拔,三辅属吏提拔后的秩级要高于普通郡国,张敞要求“比三辅尤异”,应当是欲使胶东属吏尤异者被提拔后达到与三辅尤异提拔后相当的秩级。“三辅尤异”的实际效果仅仅是秩级高于普通郡国,紧扣这一点,不难发现,《三辅研究》对“尤异”的理解超出了西汉实际。尽管所列“尤异”的几个特征均符合三辅管理的实态,但“尤异”概念已被悄然现代化了。
2.对个别史料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313A14云:“甘露二年十二月丙辰朔庚申,西乡啬夫安世敢言之:富立薛兵自言,欲为家私市张掖、酒泉、武威、金城、三辅、太常郡中。谨案:薛兵毋官狱征事,当得以令取传,谒移过所津关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围绕这条简文,作者说“三辅百姓私下的走私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162页)。这个推断可能是对简文中“私市”一语的理解。然而,肩水金关汉简可见大量的“私市”简文,书写格式大同小异。就简文来看,其大意为:某人汇报“欲为家私市”,官吏审查后,如果该申请人“毋官狱征事”,没有司法方面的纠纷,就会向上禀报,使申请人不被“苛留止”,一路畅行,最终实现“欲为家私市”的愿望。可见,对于“私市”,官府并不禁止,只要其人无司法纠纷即可。这种情形绝非“百姓私下的走私活动”。
关于“两汉三辅的荐举职掌”,其中一项为举孝廉。举证时,作者引《后汉书·贾琮传》:“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有政理迹。”细思文义,所谓“举孝廉”,是东郡举贾琮为孝廉,与京兆尹无关。这条记载不能作为三辅举孝廉之权的例证。不仅如此,对于这条记载,作者说“‘京兆令’在《后汉书》中只出现此一次,且历代均无此官。”并且“判断此处‘京兆令’有可能是‘京兆尹’之讹误。”(190页)今案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贾琮本传,原文作“再迁为京(兆)令”,据《后汉书》整理规则,“凡是应删的字用小一号字排印,并加上圆括弧”(4)《后汉书》“校点说明”第5页。。这就意味着,《后汉书》原文只有“京令”,京县属河南尹,与京兆尹无涉。作者还认为,三辅长吏有举“经行”之责,例证出自《后汉书·韦彪传》:“(韦)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大将军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车备礼征,至霸陵,称病归”。对于其中的“不应州郡之命”,作者理解为“京兆尹受命征韦著,但其辞不应征。”(191页)但这段文字讲的似乎是京兆尹如其他郡国一样,行使自辟属吏的权力,并非奉朝命而举士。另外,举“经行”似非汉代固有制度,文中仅言韦著“经行知名”,即便因此被举,亦应有“明经”“孝廉”之类固定名目。所谓“举‘经行’”的说法不够规范。
3.有些表述不够严谨
在说明“东汉前期,三辅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十分明显”时,说“出自陵邑的贾逵、杨震、马融、班固皆是一代儒宗”(68页),杨震籍贯弘农,并非出自陵邑。又如“关于汉代诸侯封地的情况”(105页),汉代“诸侯”常指诸侯王,实际上,作者讨论的是“列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