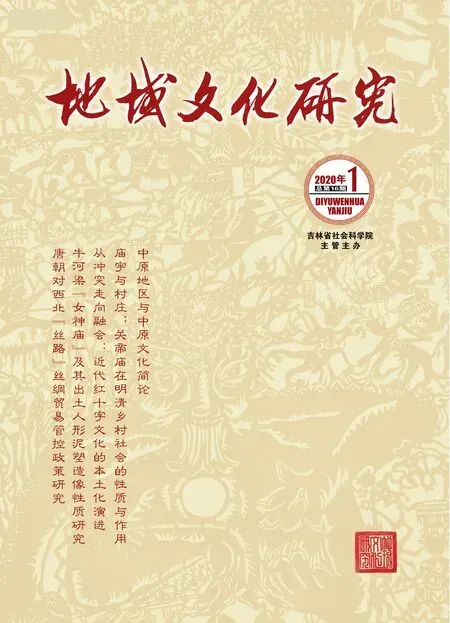五代十国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之比较研究
赵春昉
王建于891年攻占入据成都,903年,唐昭宗封王建为蜀王。907年三月,唐昭宣帝“禅位”给朱全忠,朱全忠称帝建立后梁。蜀王王建号召天下兴复唐室,无人响应。同年九月,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蜀,史称前蜀。王建称帝在位12年间,蜀中百业兴旺,民众安居乐业,是当时乱世之中的一方安稳之地。前蜀成都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繁盛大都会,人文荟萃、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是成都城市历史发展中的一段鼎盛时期,而前蜀高祖王建正是开创这一繁荣历史局面的重要人物。
同一时期,位于两浙地区的吴越钱氏,在藩镇割据战争中逐渐崛起。后梁开平元年(907)封钱镠吴越国王,后唐同光元年(923),钱镠称帝。从吴越国建立到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存在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安定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开创者吴越王钱镠则是一位传奇人物。平民出身,发迹于行伍之间,从唐乾宁三年(896)钱镠击败董昌占有两浙十三州算起,到后唐长兴三年(932)卒,钱镠在位近四十年的时光里,忠君睦邻,惜兵爱民,礼贤下士,兴修水利,发展农桑,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江浙两省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
五代十国动荡纷乱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政权更迭,前蜀王建据蜀和吴越钱镠控制两浙之地的过程,显示了两位平民英雄人物在纷乱的历史时代,乘农民起义之机投身行伍,通过政治军事实力成就大业,成为一方节帅的相似人生。
本文从人生轨迹、治国方略、宗教思想、家训家风四个方面力图全面阐述展现两位英雄人物。
一、人生轨迹惊人相似
王建生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初八,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一个世代饼师之家。家境贫寒,未受教育。《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记载王建本人隆眉广额,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后弃盗从军,唐僖宗乾符元年(874),27岁的王建投忠武军为卒,乾符二年(875)十二月,王仙芝攻沂州(属河南道,州治临沂,今山东临沂),王建在这一年参加了镇压王仙芝起义军,因军功被提拔为列校。乾符五年(878)二月,王仙芝牺牲后,共推黄巢为起义领袖。黄巢率军渡过长江淮河,进入河南境地,攻陷洛阳,突破潼关,直捣关中,攻克长安。唐僖宗溃逃之余,纠集各藩镇兵力前去镇压。而王建作为“八都头”之一在参与围剿起义军的战争中成为一名悍将,跻身将领之列。光启元年(885)三月,唐僖宗流亡后回到长安,王建为禁军神策军将领,成为僖宗的亲近卫士。后僖宗又流亡凤翔,出奔逃难途中,王建保护僖宗冲过燃着的栈道,夜宿“上枕建膝而寝”,僖宗脱袍服赐予王建,并赐以金券,深得僖宗信任。①杨伟立:《前蜀后蜀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3页。光启三年(887)被任命为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他采用谋士周庠之计,放弃了交通便利但易受攻击的利州,进而攻占地方偏僻但较为富裕的阆州(今四川阆中)。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踏上了割据称雄争取“豹变”之途。大顺二年(891)王建攻下西川(治今成都)。王建占有富庶的西川,拥有近二十万庞大兵力,并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武将和善于谋划的人才。期间不断发动夺取东川和山南西道北部各州,到天复二年(902),三川之地,均被王建占领。天复三年(903)王建被唐昭宗加封为蜀王,天祐四年(907)三月,朱全忠篡唐建后梁,王建传檄四方试图讨伐朱温,兴复唐室,但无人响应。同年九月,王建在大臣士卒的拥戴下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政权,疆域为今四川大部、陕西之南、甘肃之东南及湖北西境一隅之地,面积位居十国第三。王建于60岁登基,918年病逝归葬永陵。在位11年,也是五代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主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发展措施,百业兴盛,民众安居乐业,是乱世当中难得的一方富饶之地。
钱镠,字具美(852—932),杭州临安县人,《十国春秋》记载,镠于唐大中六年(852)二月十六日出生。贫寒家庭,世代以务农为业。七岁修文读书,《旧五代史》中记载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年少喜武厌文,后喜读《春秋》,兼治武经诸书。②钱文选:《钱氏家乘》卷5《武肃王年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14-115页。青年时卖过私盐,后习武练兵,而钱镠在从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为将风范,“临安里中有大木,镠幼时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指挥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惮之。”③欧阳修:《新五代史》67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钱镠二十一岁“入军”,散家财在乡间组织“义师”,建立起自己的小支武装队伍,成为钱镠发迹的起点。④杨渭生:《略论东南雄藩钱镠》,《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年第8期。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据《新五代史》记载,浙西裨将王郢作乱,唐廷敕本道征兵讨伐,石镜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逆贼。钱镠率领自己的武装队伍投奔董昌参与到讨贼行动中,骁勇善战,一举将王郢攻破,逐渐得到董昌重用。乾符五年(878),寇盗蜂起,江淮盗贼聚众,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闾里,董昌聚众,令钱谬率兵参战,剿灭义军。在击退黄巢军的过程中,钱镠以“临安兵屯八百里”的奇袭战术和出色指挥才能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军事声望。是时,唐廷镇压黄巢起义军的都统高骈召董昌与钱镠到广陵(今扬州)会面,高骈表董昌为杭州刺史,昌乃以钱镠为“杭州八都”都指挥使,成为靖江都将。钱镠在战争中建立培养起自己的一支武装力量,并逐渐在军中树立起威望。随后,在中和二年(882)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杭州刺史董昌争夺浙东浙西两地的战争爆发,昌以军政委镠,率八都之士进攻越州。钱镠全程指挥了这场长达四年的争霸战,最终于光启二年(886)在会稷斩杀了刘汉宏。钱镠于是奏请董昌代汉宏,自居杭州,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地盘。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拜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从唐乾符二年(875)王郢之乱到光启三年(887),钱镠一直跟随董昌,立下赫赫战功,而彼时,钱镠与董昌一个占领浙西一个占领浙东,已形成龙虎对峙的局面。这也成为钱镠立足建立吴越军事生涯的最初阶段。
光启三年(887),淮南大乱,六合镇将徐约攻取苏州,润州牙将刘浩叛变,浙西节度使周宝仓促逃奔常州。润州发生兵变,钱镠挥戈攻苏州、常州、润州。昭宗封钱镠为杭州防御使,这场战争进一步巩固了钱镠在浙西的军事地位。同年,占据扬州的杨行密与孙儒争夺淮南,钱镠审时度势参与到这场争战之中。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正月,董昌反,称帝,给了钱镠讨伐董昌的极好机会。钱、董战役发生一年后,钱镠占据两浙十三州,至此吴越国的版图初步形成。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授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金书铁券,恕九死。天复二年(902)钱镠被封为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钱镠吴王。梁太祖即位,开平元年(907),朱温封钱镠为吴越王。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钱镠建立吴越政权,称吴越国王。到后唐长兴三年(932),钱镠病逝,享年81岁,葬于安国山(今太庙山),赐谥号武肃。
纵观王建与钱镠成长、发迹、崛起的人生轨迹,会发现他们都出生成长于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期,王建比钱镠大五岁,二人幼时家境贫寒,了解民间疾苦。青年时代因缘际会受到道士点拨,武当僧人处洪见王建“骨相甚奇”劝他投军,以求“豹变”。27岁参加忠武军后攻打王仙芝起义队伍有功而得到提拔,随后又因黄巢起义唐僖宗流亡入蜀,王建护驾有功而被擢升。少年钱镠则遇善术者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遂激起钱镠奋发向上之心。钱镠21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一支乡间武装。黄巢起义,唐廷征兵讨伐,钱镠率自己的义军投奔董昌,后因参加镇压和阻击黄巢起义军有功,逐步提升,实力愈加雄厚。仔细分析王建与钱镠的人生成长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诸多相似之处:同处割据、分裂动荡的朝代和时期,一介布衣投身行伍,机智拳勇,有过人的才能和风范,同在镇压唐末农民起义中发迹,开始军事政治生涯。又在藩镇割据中异军突起,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实力。戎马一生,王建于907年,60岁这一年即帝位,建立前蜀政权。923年,钱镠71 岁建立吴越政权,受封为吴越王。王建在位12年间,励精图治,为达“永致清平”。钱镠在位近10年,“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二、治国方略几近趋同
王建、钱镠二位藩雄的施政思想和治国方略如何呢?有何相似之处呢?
钱镠唐乾宁三年(896)受封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据有两浙起到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钱镠统治控制两浙36年。钱镠建立吴越政权后,疆域极盛时,拥有十三州、一军,包括今浙江全境、苏南、闽北一带地方,东濒大海,西邻歙州,南连漳、泉,北达常、润。①杨渭生:《略论东南雄藩钱镠》,《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年第8期。唐末以后两浙地区长年征战,《资治通鉴》卷282记载,“自黄巢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吴越建国,战火平息安定以后,钱镠为巩固政权统治,着手整顿秩序恢复经济社会发展。钱镠治国期间,重视人才,礼贤下士,招揽贤能之人为其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项事业,并采取系列措施,治国理政。
史载王建本人宽宏大度,知人善任、重视人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锦里耆旧传》卷五中记载开国大赦召文:“诸州府或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达于教化,明于吏才,政术精详,军谋宏远,韬光待用,藏器俟时;或智辩过人,或辞华出格,或隐山林之迹,或闻乡里之称,仰所在州府奏闻,量材叙用”。在用人政策的感召下,王建身边汇聚了一批来自各地的贤能之士,各有所长,在王建的礼遇与重用下,励精图治,为前蜀政权的巩固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后梁纪一》评价道: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一)息兵安民,以文治世
“保境安民”是钱镠治理吴越国的基本国策,安民和众事中朝。钱镠作为吴越开国之主,志向远大,曾与淮南杨行密抗衡并有兼并藩镇之志,但钱镠也深知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吴越的北面是吴、南唐,南面是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经》卷89中载“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钱镠始终以吴、南唐作为其制定军事战略的首要因素,吴越尊奉中原王朝为正统,联姻闽楚,睦邻藩镇,对契丹称臣。钱镠“保封疆”施政用兵的基本思想,为吴越国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欧阳修在《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中描述了吴越时期,杭州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说明,当时杭州这座都城日益成为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的中心。
与此相似的是王建为民利政“以文治世”的主张。藩镇割据,三川地区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前蜀立国后武成元年,王建颁布大赦诏:革弊从新,去华务实,有利于民者,不得不用;有害于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于民安,富庶自成于国霸。恩虽不吝,法且无私。赫宥者各迎自新,厘革者皆宜共守,俾从荡涤,永致清平。②(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前蜀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前蜀立国后,蜀地安宁的社会局面。前蜀王建据蜀,与后梁保持友好关系,前期与歧王李茂贞修好,结成姻亲。不与邻国为敌,巩固边防,谨慎用兵。王建本人虽然目不识丁,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前蜀开国之初,就设国子监,学校教育按唐朝旧制把京城和各州的学校与孔庙加以恢复。永平元年(911),修建新宫,储存四部书籍。宰相王锴上表劝高祖兴文教,选用名儒专门掌管图书。通正元年(916)八月,起文思殿,购置群书存放在里面,用清资五品正品官管理,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从恢复庠序、崇饰孔庙到两次集中图书来看,前蜀王建在兴复文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前蜀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③杨伟立:《前蜀后蜀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30页。而这也正是王建推行以文治世的政治方略,蜀地重视文化典藏的收集与整理,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整治水利,重农兴商
唐末,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江浙海塘失修,钱塘江水患严重。钱镠据两浙后,积极兴修水利,治理潮患,发展农业。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平四年(910),镠定两浙,就开始从六和塔至艮山门,修筑瀚海石塘”。后梁贞明元年(915),积极治理太湖水系,并组织人力整修浙东诸湖,包括东府南湖(绍兴鉴湖)。后唐天成二年(927),钱镠派遣士兵数千人,日夜割草、清除淤泥,疏浚西湖,以利航运和灌溉。据史料记载,吴越国86年中,只发生过一次水灾。而在吴越国之前的唐朝,却是每隔九年一旱灾,每隔36年一水灾。吴越国之后的北宋,因为缺乏水旱治理,平均每七年半受旱灾一次,五年半受水灾一次。①卢仁江:《钱镠对吴越国的积极贡献》,《浙江档案》1995年第9期。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钱镠对吴越国水利工程的重视,通过设置专门的治水治田机构“都水营田使”,整修水系,设闸治水,修筑堤坝,既可防洪又可灌溉,且利于农渔业发展。开垦农田,耕地面积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增产,蚕桑丝织业发展。吴越江浙一带,农业发展的同时,丝织品、茶叶、冶炼、造船、盐业、越窑青瓷等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的增加,进一步促进贸易的繁荣。吴越都城杭州也一跃成为东南繁荣大都会,商贾云集,《旧五代史》卷133 中记载:“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在钱镠和其继任者的治理努力下,吴越逐渐成为富庶之地。
而王建着手整顿社会秩序,通过减免赋税,赦免犯人,劝课农桑,整治农田、水利,发展农业,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等系列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扭转生灵涂炭混乱的社会局面,以达“永致清平”的政治目的。前蜀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农业粮食增收,手工业当中,丝织、茶叶、蜀刻印刷、冶炼制造、陶瓷等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都城成都出现各类集市,《五国故事》记载前蜀王建时期:“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商业的繁荣,贸易往来不局限于境内州县,与后梁、后唐、吴越、南唐、南汉等割据政权以及海外诸国都有贸易往来。前蜀武成三年(910),后梁遣使通聘前蜀,前蜀高祖王建获赠大量珍贵礼品,其中产于域外的即有“金香一十斤,麝香五十剂,犀一十株,琥珀二十斤,玳頊二百斤”。另有新罗人参、羚羊角等一些域外药物,被后梁国书称为“或来从燕市,或贡自炎方”。②陈玮:《唐五代成都外来文明研究》,《唐史论丛》第二十八辑,第198页。可见其物丰货足,市场繁荣。
(三)发展贸易,对外交往
钱镠尊奉中原王朝,通过频繁而丰厚的奉贡来维系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下》介绍了钱镠时期的924年,“王遣使钱询贡唐方物……秘色瓷器”。朝贡的同时,经济贸易往来也日益增多,《十国春秋》记载,“梁时,江淮道梗,吴越泛海通中国,于是沿海置博易务,听南北贸易”。吴越国与周边割据政权吴、南唐、南汉、前蜀、契丹等经济贸易往来不断。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钱币3,400多枚,其中铸于五代宋初的有41 枚,南唐14枚,后周8枚,北宋5枚,前蜀11枚,南汉2 枚,后晋1枚。①黎毓馨:《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钱币》,《中国钱币》2003年第1期。另据《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载,墓中发现收口圈足青瓷小碗六件,敞口青瓷小碗六件,花式口平底青瓷小碗二件、青瓷小碗二件,另有青瓷器皿的残片。陈万里先生考证这些青瓷均属越器。该墓出土的墓志,刻有“应历九年(959)”字样,证实了这是五代时期的墓葬。墓中越器,应该是从吴越输入的。②孙先文:《吴越钱氏政权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钱镠治理吴越时期,由于大力整治疏浚航道,海陆畅通,造船业兴盛,扬帆远航,与日本、朝鲜半岛、印度等诸国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海上外交关系。《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十曰“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云烟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此时,吴越国明州、湖州、杭州等杭州湾及长江沿海城市港口一带,已成为吴越国海上贸易的重镇,明州港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日本成为明州港的主要商品贸易国。《吴越史事编年》记载924年,钱镠遣使日本,船舶往来。据《吴越备史》卷三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桶发之”,这里说的火油指石油。大食(阿拉伯帝国)石油从吴越时期开始输入,要比郑和下西洋早400 多年。吴越海外贸易及对外交往东到日本、新罗,北至契丹,南到海南,西到波斯、大食。史书记载,“航海收入,岁贡百万”,吴越富甲东南。
在内陆的蜀地,王建打通盆地阻隔,以政治家的深远谋略发展对外贸易。南汉刘涉时,“西通黔、蜀,得其珍玩。”荆南高从诲“东通于吴,西通于蜀,皆利其供军财货而已”。后晋“天福初,蜀犹与中国通”。后周“听蜀境通商”。③武建国:《论前后蜀经济发展及其原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另外,蜀国还从海外输入众多香药,成为蜀地商品市场上特殊的一类海外物产。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蜀地钱币流通到外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例如在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曾发现一枚五代十国前蜀钱“永平元宝”,该钱币始铸于王建公元911年。而王建在位期间,还铸有“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等钱币。④杜国禄,董秉义:《赤峰出土前蜀永平元宝》,《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1期。可见,前蜀经济的发展与王建开放的治国理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通过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治国理政分析,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两位平民帝王的相似之处:宽宏大量、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忠君睦邻、重视民生,积极恢复生产发展,采取诸多政策与措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使杭州与成都商业兴盛、城市繁荣。
三、崇佛信道出自心性
唐朝是我国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尤其在唐玄宗时期,崇道活动达到高潮。但唐朝末年,经过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的战乱冲击,道教的发展由盛转衰。进入五代,战火纷飞、社会动荡,前蜀政权,众多唐朝皇亲贵族文人学士入蜀,“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前蜀王建不仅优礼士人,也沿袭了唐代崇道风尚。⑤尤佳、周斌:《杜光庭与蜀地道教—兼论其咏道诗的思想内涵》,《中国道教》2011年第2期。
杜光庭(850—933),唐末五代著名的“道门领袖”,黄巢起义爆发后,唐僖宗为挽救唐王朝的颓势,求助于圣祖老子,崇奉道教,多次下诏赐封道士。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杜光庭由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郑畋推荐进京:“郑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道门领袖。”僖宗在长安时因杜光庭弘道有方已嘉奖重视此人,而到中和元年(881),黄巢军攻占长安,杜光庭随僖宗入蜀避乱,越发得到皇帝的信任。从光启元年(886)到天祐四年(907),杜光庭留在四川隐居青城山。①栗品孝等著:《成都通史》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61页。907年,西川节度使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后,杜光庭投靠王建,因其有经国理政之才,得到王建的尊重与赏识,官爵至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后又除户部侍郎。王建赞曰:“昔汉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②(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0,《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30页。
杜光庭在前蜀王建的信赖与支持下,对道教自开创以来的重大理论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成为晚唐五代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进一步壮大了道教的组织规模,提升了道教的社会地位,扩大了道教在蜀地的宗教影响。其中,前蜀时期,在王建、王衍父子的大力支持下,杜光庭参与了众多斋醮科仪活动,为王建和许多人写了斋醮词,系统规范化整理了道教的斋醮科仪。道教的斋醮科仪活动在蜀地得到充分发展,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既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教的传播与发展。
前蜀皇帝王建所葬之永陵,在地宫后室石床上放置有王建石质圆雕坐像,石像坐北朝南,通高86厘米,在墓室中放置墓主写真石雕像,是五代十国时期川西地区非常流行的一种葬俗,反映了道教文化对丧葬习俗的影响。③张勋燎:《前蜀王建永陵发掘材料中的道教遗迹》,《中国道教考古》第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1033-1041页。王建之后,其子王衍也大力崇道,尊老子为圣祖,道教在蜀地继续发展,宫观众多。
同一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吴越国也是一个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家。重视宗教,道、佛并重,是吴越国自始至终贯彻执行的一项宗教政策。吴越国钱鏐对道教高度重视,延请礼敬名道,不惜花费巨资修整战乱破坏的道教宫观,使道士云集,令一度衰落的道教得以振兴,道教对吴越国的历史产生重要的影响。唐光化三年(900)七月,钱镠重修大涤山天柱观,使一度衰落沉寂的道教得以振兴。钱鏐还在吴越境内兴建了不少道教宫观,比如在金华建广润龙王庙,建上清宫于绍兴泰望山,建灵德王庙于浙江。明万历《金华府志》、清雍正《浙江通志》及清光绪《金华县志》等历代方志,都有“吴越钱武肃王(钱鏐)重修”金华赤松宫的记载。为了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扩大道教的影响,钱鏐还奏请中央朝廷给境内高道颁赐封号,礼遇道士。④曾国富:《道教与五代吴越国历史》,《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钱镠在崇奉道教兴建宫观的同时,也对佛教文化倍加推崇。吴越从开国者钱镠到末代钱俶,他们都与禅僧来往密切,尤其是创建寺院、刻印佛经、延请高僧,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活动中心,为佛教文化在吴越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宗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在今天杭州以灵隐寺、净慈寺、六和塔、保俶塔、白塔、雷峰塔、临安功臣寺、功臣塔、海会寺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遗存,实际上与吴越国时期宗教文化的繁荣和钱氏家族的推崇密切相关。唐末五代,整个文化呈现向南转移的态势,佛教文化的中心也向南转移,其标志就是禅宗的南迁。这种宗教文化南移的大背景,对于吴越国来说是发展宗教文化的机遇。①薛正昌:《钱氏家族与吴越佛教文化》,《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钱镠及其继承者“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②任继愈主编:《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2页。
经过发掘的杭州雷峰塔、金华万佛塔、东阳中兴寺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黄岩灵石寺塔中,出土了众多造像、阿育王塔、经卷等礼佛精品,极具时代、地域特色。在举国上下崇佛氛围中,从王室至民间,佛教盛极一时,吴越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③浙江省博物馆:《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日,第4版。
王建和钱镠对道教、佛教的尊崇,既是那个时代宗教之风传布使然,更是他们作为一国之君为维护统治利益和使内心价值平衡所不得不强力推动的治国安民、行善修心的宗教文化举措。由于他们的倡导和推动,道教和佛教得以广泛传播。
四、注重家训家风传承
从907年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到钱镠孙钱俶纳土归宋(978),吴越立国72载,历三世五王。钱氏政权继任者都遵从“善事中国”的家训,对中原政权恪尽臣礼,纳贡称藩。坚守“关切民生、经营和谐”的家训,偃息兵戈,发展生产、保境安民,江浙富庶,甲于全国。像钱镠这样一位影响钱氏后世发展的历史人物,他所树立的家训家风,有其传世价值。
912年,钱镠曾作《武肃王八训》,932年三月,81 岁高龄的钱镠写下《武肃王遗训》,《武肃王遗训》是在《武肃王八训》的基础上修订而来,二者基本内容一致。在《武肃王遗训》中,钱镠回顾了自己从初出江湖到戎马执政的岁月,将自己处于五代乱世中的成功经验传给其后继者,并以忠孝作为基本的道德信条,重视家族的伦理教育,提倡忠孝思想。④耿宁:《钱氏家训及当代价值研究》,合肥:安徽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钱镠对唐朝末年上层统治者道德趋于沦丧的现象有深切的感受,希望子孙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唐室之衰微,皆由文官爱钱,武将惜命,托言讨贼,空言复仇,而于国计民生全无实济。”钱镠《武肃王遗训》所列十训,涉及忠孝、民本思想,确立“保境事大”的基本国策。告诫子孙要以臣子的身份效忠中原故土,对臣民多施加恩惠,爱惜子民。嘱托诸子要“兄弟相同,上下和睦”,强调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钱镠希望子孙勿忘祖先,不要抛弃自己的家乡,需念祖先创业之艰辛。遗训中,钱镠还谈到了对婚姻的看法,希望子孙婚姻嫁娶选择同样家风家教良好门当户对的家庭。钱镠十分重视钱氏家族的门风,具有较强的儒家宗法思想,重家教,尊家训,《武肃王遗训》的最后一条:“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⑤钱志熙:《〈钱氏家训〉体现的现代思想》《,学习时报》2018年第5期。
《武肃王遗训》由先祖钱镠所作,可以说是钱氏家训的始创者,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强调治国齐家的重要性。《武肃王遗训》这一古老的钱氏家训,到近代民国初年,经钱文选重新整理而成《钱氏家训》,为后人研究学习提供了范本。
钱镠晚年病危之时,召诸将议立嗣王。“诸将立下,皆曰:元瓘从王征伐,最有功,诸子莫及,请立之”。长兴三年(932),钱镠弥留之际,以印、钥授元瓘。镠卒,元瓘嗣立。钱元瓘继位得到了诸将和一些兄弟的广泛支持。①孙先文:《吴越钱氏政权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前蜀王建以“恭俭畏惧,勤劳慈惠”作为家训,告诫儿孙们“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必须“早暮诫勖,恐汝遗忘”。王建称帝时60岁,他有11个儿子,因长子宗仁先天残疾,立二子宗懿(元膺)为太子。元膺多才多艺,却因王建不察宗懿与枢密使唐道袭的紧张矛盾关系,造成二人皆在宫廷武装冲突中被杀。元膺死后,太子人选未定。王建有宠妃徐妃,因受宠幸,专房用事,干预朝政,王建未能制止。徐妃为使其子王衍立为太子,拉拢朝臣,合力密谋,王建被蒙骗而不知,永平三年(913),王衍被册立为太子。王建虽立幼子为太子,然而内心清楚王衍不堪大任,心中始终忧虑,却未能及时更改,另立贤者。《资治通鉴》卷270 曾记载“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乎!?”王建病逝,王衍喜爱声色、宴游,不理政事,咸康元年(925),前蜀被后唐所灭,耽于享乐的王衍葬送了两朝基业。王建曾在《诫子文》中提到的殷殷期盼终幻化于空,留下诸多遗憾:“吾提三尺剑,化家为国。亲决庶狱,人无枉滥。恭俭畏惧,勤劳慈惠。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故百官吏民,爱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贵,不知创业之艰难……察声色之祸,然后能保我社稷,君我臣民。吾早暮诫勖,恐汝遗忘。当置之几案,出入观省。”
从钱镠和王建在家风育化和继承者培养方面相比较,可见钱氏家风比王氏家族要规范系统得多,具有家族制度性约束机制和传承方式,一代一代地遵循着钱氏家风,至今还鲜明地体现在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钱学森、钱大昕、钱钟书以及钱其琛等大家名人身上,而王建后裔则消失在历史的沙石之中。
综观五代十国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的史迹,二人的人生和从政经历颇多相似,这种“历史共生现象”值得深思。历史共生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身处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和个人因交通环境阻隔,缺乏交流沟通而产生的相似的同时性历史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难解之谜。钱镠与王建的惊人相似性,既表明身处大变革时代有抱负的平民一旦把握机遇就可助推历史的进步,也证明一个朴素的真理:不管是君王还是百姓,只要“为民向善”就能书写历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这就是钱镠与王建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