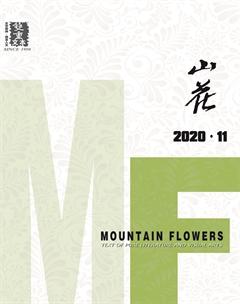两人对酌山花开
甫跃辉
2019年3月15日,《山花》老主编何锐老师走了。我写了一篇怀念何老师的短文,一个月后,作为“纪念何锐先生小辑”中的一篇,发表在《山花》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上。我在朋友圈转发的时候说,“何锐老师过世,李晁兄约稿,写了《文学人生——纪念何锐老师》一文。昨晚在贵阳和《山花》各位朋友喝酒,李寂荡老师坐身边,说起我写的这篇东西里何老师喝酒的细节,说何老师喝酒之所以小口抿,不是为了省酒,是因为酒量不好。”
世间常有误会,也多有巧合。这里说的“昨晚”,是2019年4月14日,我因参加“中国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题采访团”,途径贵阳,李晁兄和《山花》诸位同仁约小聚,我和雷默等几个一起去了。几年不见,李晁仍然穿得干练潇洒,说话举重若轻。我们几个随了李晁,在贵阳的街头走着。说实在的,到过贵阳多次,却对贵阳一点儿不熟悉,但熟悉的李晁在前面呢,这就够了,仿佛和这城市也熟悉起来了。
快到饭店时,我们停在一树繁花底下,等后面走得慢的人。
一棵高大葳蕤的染饭花,在一处小区门口。染饭花在我老家云南很常见。村子和村子后山路边不少,多是不及一人高的小灌木。常说云贵川是一家,想必贵州也不少,然而这样远远高于人的染饭花,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花树底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奶奶摆着个小摊卖东西——具体卖什么却忘了,大概是卖点儿小零食吧?当时全然被染饭花吸引住了,没注意看。老奶奶旁边,站了个农民工模样的中年男人,踮起脚尖,一手够树上的花枝,一手拎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已经鼓鼓囊囊地装满了。老奶奶抬头看看,又低头看着自己的小摊。没人觉得这个男人摘一些花枝有什么不好。只是他摘了花枝做什么呢?是送给妻子,还是送给女儿?或者纯粹自己觉得好看?当然,也有可能会用来“染饭”。但还不到端午节,按云南不少地方的习惯,端午节包粽子才会用染饭花染饭。
想着这些时,花香一阵一阵飘来,而要等的人也赶上来了。《山花》的朋友们和我们几个外来者,又往前走了几步,上了二楼,坐了满满当当两桌。
自然,喝酒吃饭,都是寂荡老师自掏腰包,我们这几个家伙,很理所当然的样子。席间,不由得说到刚刚过世的老主编何锐。于是,和坐在身边的李寂荡老师有了开头那番对话。
记得我和寂荡老师又絮叨了些我和何老师的交往。
何老师是我的第一位责编,我在他手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少年游》。小说完成于2006年5月底,发表于当年《山花》杂志第9期。五年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做“少年游”。然而,发表在《山花》上的《少年游》和收录在书里的《少年游》不一样,区别在于结尾。记得那天从图书馆跑到复旦光华楼张新颖老师办公室拿的样刊——《少年游》是张老师转给何老师的,所以样刊寄给了他。刚拿到样刊时候,我走在细雨纷飞的路上,一面走一面翻开看,看到最后,忽然愣住了,最后一段呢?怎么没了?记得那时候小说写完,我自己很喜欢这最后一段。然而,竟然没了。刚刚的欢喜,转眼变成了失落。那时候自以为会有很多人看到杂志,似乎一个词一句话都会有人关心,更何况是一整段呢?
原文的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我站在那棵香樟树下,香樟树不知生长了几千几百年,但它的叶子很年轻,每一片嫩绿的叶子都是一个年轻的生命,阳光照耀着它们,它们很年轻。我忽然很兴奋,说不出地兴奋,我搓着手,想,我二十岁了,我才二十岁,我应该到地球上走走,我应该到远方认识一个人,我应该真实地走入一场斑斓眩目的青春和流浪。可这时候悠悠拐出了小镇,看不见了,踮起脚尖也看不见了,我的兴奋穿过了一条窄窄的隧道,不可遏止地刺痛了一下。
我不可遏止地想起了十二岁那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出走。我莫名其妙地觉得离家出走能为我争取到成为大人的资格。我在离家三里地的一棵树下饿了整整一天。当爸爸找到我,当爸爸对我笑笑,当爸爸头一回像对待朋友一样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这一招奏效了。我和爸爸不慌不忙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爸爸搭在我肩膀上的手始终没放下来。暮色昏黄,我低头注视着地面上一长一短两个影子,仿佛看到了电影放映结束后,冷暗的银幕上映出的散场的人群。
我拿着样刊,回到之前看书的图书馆。这时候,我看到对面一直坐着的低头看书的女孩,脑袋一热,写了张纸条给她,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请你吃饭啊。我忙低下头。女孩大概抬头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一张纸条推过来,只有两个字,好啊。
后来和那女孩去了复旦南区步行街(现在已经拆了)二楼的阿康烧烤,点了一堆肉串和一个什么锅,吃得油星四溅。女孩穿的是白色连衣裙,裙子上都溅了好几点。两个人聊得很开心,最后,在细雨朦胧中,我把女孩送到了公交站。这时候才想起来,忘记问女孩叫什么名字了,当然,更不可能想起来留什么联系方式。
回去后,我又想起《少年游》被删掉的最后一段,脑袋不知道怎么运转的,就把这些事情一股脑儿搅合搅合,加了一些虚构的面粉进去,新烘烤出炉了一篇新的小说,又投给了何老师。过不多久,小说发表在了《山花》2007年第1期,叫做《金色》。《金色》成了我发表的第二篇小说。我想,虽然经过了重大整容,何老师应该还是看得出来,这篇小说写的小说结尾被删的事儿,正是他和他的杂志干的。然而,他还是给发出来了。现在回头看,这小说写得实在不大好,当时是何老师为了鼓励新人,才发表的吧?
《少年游》对我来说自然意义非凡。不仅因为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还因为它为我带来了第一次约稿。2006年底,我收到厚厚一封信,里面是两本《长城》杂志,杂志里有一封信,写信人我不认识,叫做“王志新”。他在信中说,看到我发表在《山花》上的小说了,打电话到《山花》,问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写信给我,希望我有新小说给他。那时候,我不知道志新和我是同龄人,想着是老前辈呢,回信喊他“王老师”,同时,寄了一个短篇给他。没过多久,回信收到了,小说竟然被退了!我以为,约稿嘛,自然是要发表的,怎么还有约稿又退稿这种事呢?然而,现实是如此不以我的想象为参考。我又打印了一篇小说,再次寄过去,然后,过了段时间,王老师的信又来了,小说又被退了!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写作了。然而,我没气馁,或者说是气馁了一阵子就恢复了,又寄了篇小说过去,这次,發出来了,彼时,已经是2008年底,这便是我发表在《长城》上的第一个小说《雀跃》。几年后,这小说同样收进了小说集《少年游》里。——而我见到志新兄,是十年后了,2008年8月8日,我到石家庄参加活动,我和志新兄一起去了赵州桥。那时我才知道,那个我一直喊“王老师”的人,年纪并不比我大。
在《山花》投稿的顺利,算是被《长城》杂志扭转过来了。我想,原来投稿是这么不容易的事儿啊?后面的向更多杂志投稿经历还真是如我所想,很多稿件泥牛入海,不由得一次一次怀疑自己。然而,《山花》一直对我很好,我写小说十多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在上面发表小说,还发过散文。当然,《山花》也是退过我稿子的,只是我选择性遗忘了,不记得退的是什么稿子了。倒是有个事儿,和当初何老师对待《金色》一样,让我记忆深刻。
这是前年的事儿,我投了短篇《夜眼》给李晁。李晁看了,提了些意见,让我改一改。我改了,也就改动了十来个字吧?过不多久,《夜眼》在《山花》2018年第6期发出来了。《夜眼》随后被《小说选刊》第7期转载。《小说选刊》需要我写个创作谈,还需要李晁兄写个编辑手记。李晁兄写了《打开“夜眼”去阅读》一文。我是在《小说选刊》微信推送时才看到这篇文章的。文章开首是这样的:
初读《夜眼》,给人留下的是一幅乡村图景,以一个惯常的少年视角去捕捉世界一隅的光亮和暗影,依托白马与驴到阿胶的转化,透视出一段亲情,自然,这一过程带着一种纯朴、朦胧的感受。……这是初读的印象,可仍不大满意,不满意的来源或许是小说的舒缓节奏和对事物细微的描摹多少遮蔽了小说的内核——那应是由人物关系组建起来的生命场——伤感的挽歌式的作品在当今机动如“闪电战”的短篇里已淹没了位置,所以曾提出疑虑,疑虑之处是“物象”之外的人生应给予与“物象”相应的关注,从而贯穿小说,达到一种平衡。跃辉兄说,那我改一改吧。然而,第二次读到《夜眼》。奇妙的是,这一稿和前一稿几乎没有区别,字数也几无浮动,完全没改啊!也許是我的记忆出现偏差,抑或时间间隔,其中的细微变动未能被及时察觉,可这一眼到底不同。
我在一段时间里思考这前后阅读带来的感受差异,是阅读状态的调整,还是期待视野里探照灯的再度亮起(与初读的照射不同,这是一次有准备有标底的再次巡查),从而找见了此前被遮蔽的部分?……
李晁兄真不容易,没嫌弃我这作者偷懒,反倒怀疑自己,调整自己,重新读了一遍稿子,还读出里面的“好”来。其实呢,也不能说是我懒。我自己也做编辑,知道有些意见,提得是没错,可真要改起来,谈何容易?而作为编辑,又总希望稿子能好些,再好些。李晁兄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只是我功力欠缺,没能好些再好些。
除了何锐、李寂荡、李晁这老中青三位,见过面的《山花》编辑,还有谢挺、杨打铁、郑瞳、李世成等。比较熟悉的,还有在《山花》实习过的肖江虹。有一年我到贵阳,江虹兄开车,我坐副驾驶座,到一个叫做“甲茶”的地方去,美其名曰“看外景”。那时候,江虹兄的《百鸟朝凤》正在筹拍。后来,外景地并没选在甲茶,但那一整天的时间,我们花得并不冤,我们看到了极好的山极好的水,还吃到了刚从清江里打上来的极好的鱼。
之前在《山花》待过多年,后来离开了的冉正万,我也很熟悉。犹记得读万哥《洗骨记》《纸房》等小说时候,我还在复旦读书,是在教室里读完的这些小说。有一年到贵州——那是我第一次到贵州,如今已经记不得怎么会飞到贵阳转机了,抑或是坐火车到的贵阳?完全不记得了。但记得万哥来接我,记得那次我喝了不少酒,记得住在万哥家。
此时回想起来,和《山花》的朋友们碰面真不多,和何锐老师有限的几次碰面,我在《文学人生——纪念何锐老师》一文里写过了,在此不赘述。和李晁兄碰面,除了在贵州,是在上海碰过?我和他、曹永去了田子坊,大白天的,喝了个晕晕乎乎。和寂荡老师在贵州外的碰面,是在绍兴,我们一起参加《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的活动,在自助餐厅同桌吃饭。李老师吃了会儿,站起来端着空盘子去加菜,走了两步,回过头,手往虚空里一按,嘱咐我,“帮我占好位子啊,不要让别人给占了。”很是可爱。
和《山花》的情谊,都在稿件往来里了。我争取写出满意的稿子,投给他们,他们看中了刊登,看不中了退给我,刊登也好,退给我也好,大家见面了,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喝一杯,这就足够了。前文提到的去年四月份在贵州和《山花》的朋友们聚会,算是和《山花》“建交”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了。《山花》能来的人都来了。酒自然是喝了不少,第二天我说,“感谢李晁兄约酒。”李晁说,“感谢甫兄不剩,我们讨厌剩酒的。”我说,“昨晚又变身酒桶了。”李晁说,“放心,风度不倒!”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紧,昨晚怕是早没什么风度了吧?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头天晚上,寂荡老师和我说过,真想弄个“山花酒”,《山花》的作者们来了,都喝“山花酒”。新酒面世,自然得有个广告语。寂荡老师说,广告语就是李白的那句诗: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想起饭店附近那一大株高大葳蕤的染饭花。虽不是多么金贵的花,却在漫长岁月里一天一天长得壮大,开得繁盛,散播无尽馨香。而我们喝酒的地方,离它不过几步之遥。而《山花》杂志,正如这一大株罕见的染饭花,开了一年又一年,香了一年又一年。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单可作为至今尚未面世的“山花酒”的广告语,亦可作为至今已面世七十周年的《山花》杂志的广告语。“两人”,既可以指《山花》的编者和作者,也可以指《山花》这本杂志和它的所有读者。七十年《山花》烂漫,一代一代编辑和作家和读者在此耗尽青春岁月,也留下了自己的生命记忆。人生苦短,七十年何其不易。此时此刻,怎可不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