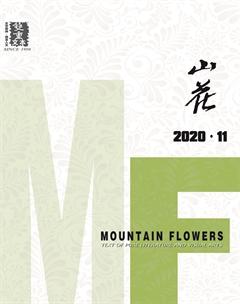译记三则
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的“朝向”
被很多论者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英语诗人的史蒂文斯,由一个并非诗人的译者来翻译,不止一次,并且不止是翻译,还要谈论,即使译者本人都觉得是一件有点过分的事情。幸好我无意也无资格进行任何批评或“导读”,以使史蒂文斯在任何人手中变得不那么艰深,而只想整理一下我对史蒂文斯的认识,以供对我的译文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在我第一次翻译史蒂文斯时,我将他的最重要诗篇之一的题目译为“最高虚构笔记”,并以此作为那本诗选的书名[1],这应该是这首译诗诸多错误之中最大的一个了。原诗题为“Notes Toward A Superme Fiction”,在我第二次翻译的版本[2]中改成了“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至少在字面上更准确了一点,同时也标注了我对史蒂文斯看法的改变。(注:以下所述都是我毫无根据,亦无法论证的一孔之见,为图方便一律省略“在我眼中”四字。)
“朝向”(Toward)在这里是一个不可省略的词[3]。史蒂文斯的诗是一种投射,将自身投向一个作为至高虚构的中心,同时它本身也作为投影呈现在文字构成的诗篇之中,“如其所是”,也许这可以用柏拉图的洞穴投影来类比。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诗都是如此,一种抽象的诗的投射,但史蒂文斯把这一点变成了他诗歌的目的和每一首诗最终的主题,而非仅仅是一种(在诗歌自身以外的)诗学或哲学的诠释。换句话说,史蒂文斯的诗就是它的诗学本身,同时又是通向其诗学理想中的诗歌的途径——它通过朝向至高虚构的无尽上升来呈现它所不可能抵达的至高虚构,而这一呈现又反过来成为它由之而来的诗学(亦即诗歌本身)的理由和证明。至高虚构须以诗宣示其存在,而诗也正因其“朝向”的动作才成为其自身。史蒂文斯的诗正是这样,从自我否定和自我诠释中完成了它的自我肯定,如 “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这首诗之所为。
把这首诗的三个段落(“它必须是抽象的”“它必须改变”“它必须提供快乐”)读成史蒂文斯为诗歌设立的坐标线,用以在想象的地平线上定位他的至高虚构,或是他根据理想中的至高虚构,划出诗歌的疆域,都无不可。重要的是,它让我们隐约看到了史蒂文斯诗歌的一条轨迹:一,世界,现实,或无论我们叫它为什么,并无意义,它必须从自身中被抽离,指向别的,更高的事物,比如一种理念或一种虚构;二,没有什么永恒的存在,心的行动(想象)始终改变着现实,生成新的现实,注入新的意义;三,为一切意义带来价值的是人的情感,诗的至高虚构之所以值得追寻是因为,它是情感所投射的方向,一种精神之极乐的所在。史蒂文斯在划出了这条诗之轨迹的同时写成了这首诗。
事实上,史蒂文斯曾经讲过“诗人是一个神或青年诗人是一个神。老诗人是一个流浪汉”[4]以及“诗人是不可见者的传道士”[5];而在《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的献词中,史蒂文斯“催迫”的是那个“就在我近旁,日夜隐藏于我体内”的“最智慧者”;此外,“高贵的骑手”,“必要的天使”[6],“至大的人”[7],“喜剧演员”[8]等等也曾被史蒂文斯拿来指称诗人。诗人对于史蒂文斯来说是至高虚构这一世界的探寻者、创造者、信息传递者和表述者,一个具有神性的多位一体者,寻求“在个人内心中将美学缔造为一种比宗教更无限广大的事物”。[9]
这个多位一体者的角色从来是游移不定的,在史蒂文斯的每一首诗中都有所不同,因为他所朝向的中心是未知并无可企及的,我相信史蒂文斯在心怀最大的信念的同时也无时不在经历着最大的困扰,因此他才如此看重诗人“阳刚”与“力量”的属性,并时常将崇高与怀疑和反讽的调性同时汇入诗篇之中,如一个置身荒野走向他看不见但却始终确信的目的地的人,在辨识、体验并且享受此时此地的每一种感觉。我猜想对于史蒂文斯来说,创造也就是发现,想象也就是知识,至高的虚构也就是至高的现实。
史蒂文斯研究的大师海伦·文德勒曾经提到,在一次读诗会中,一位听者抱怨说他不理解史蒂文斯的诗歌,史蒂文斯的回答是“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是否理解它。”[10]海伦·文德勒对此的诠释是,诗歌将随时间而自我澄清。但我更倾向于把这解读为,史蒂文斯只是道出了自己对于诗歌的迷惘,迷惘正是领悟的一部分,也是诗歌在其中行进的空间。
我把史蒂文斯的诗歌视为芝诺的箭,它们每一首都是静止的同时又朝向一个目标而去,它们每一首都自成一篇又连成一道朝向一个目标的轨迹。阅读史蒂文斯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正如你抓不住那支箭,或者说你抓住的必定不会是那支箭,因為它已经不再是在那个空间,那个时间,出自那个射手,射向那个目标的箭了。或许重要的不是那支箭而是那个目标,或许射向那个目标恰恰就是那支箭的目标。
当我们看着箭的投影之时,我们能做的是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射手在射出那支箭,想象那支箭所朝向的那个目标,甚至想象自己成为那支箭,朝向那个目标而去。也就是说,每一首史蒂文斯诗歌的读者都必须成为史蒂文斯来写下那首诗。
那么,翻译的工作是否更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我仅仅是将文字(也就是箭的投影)从一个表面(英语)移到另一个表面(汉语)之上,尽管这并非易事,但最难的部分依然是属于读者的。
注释:
[1]《最高虚构笔记》(与张枣合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2]《坛子轶事:史蒂文斯诗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3]这个词亦有“关于”“对于”等义,按此原译并无不可,但只有现译能够完整呈现我理解的诗题含义。
[4]史蒂文斯:《箴言录》(Adagia)。
[5]同上。
[6]史蒂文斯:《必要的天使》(The Necessary Angel)。
[7]史蒂文斯:“一名年轻上尉的重复”“乡民编年史”“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运往夏天》)。
[8]史蒂文斯:“作为字母C的喜剧演员”。
[9]史蒂文斯:《箴言录》。
[10]文德勒:“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声音是‘拯救生命的(Wallace Stevens' Voice Was ‘Life-Saving)”。
“夜晚的光线”与“云中的路”
——史蒂文斯诗全集译后记
苏珊·桑塔格[1]写过一部书[2]来诠释“反对诠释”,史蒂文斯的每一首诗(每一个诗人的每一首诗)都在做这件事。因为构成诗歌的物质:想象,它是非理性的,而作为诠释这一行为基础的理性,对于诗歌而言并无必要。诗歌先于诠释,正如非理性先于理性,甚至理性的最中心也还是非理性的“秩序之狂”[3]。此外,对史蒂文斯诗歌的诠释之多,事实上也已令诠释变得不可能。在史蒂文斯本人的论文、演讲、书信中有关诗歌的理念阐述之外,每一页史蒂文斯诗歌都有一百页的评论文字,于是我们有了道格特[4]的、布鲁姆[5]的、文德勒[6]的史蒂文斯,太多人的史蒂文斯……但所有这一切是外在于诗歌的事物,对于史蒂文斯来说诗歌是自足或“自为之物”[7],它与“不会宣示它自己”的“老歌”[8]全然不同,证据是在史蒂文斯的每一部诗集里,除了诗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文字[9]。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试着诠释过一两回(或许根本谈不上诠释,仅仅是诠释的动作)[10]之后,这篇译后记将仅限于谈论我作为读者和译者对语言和翻译的一点想法。
史蒂文斯的语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一个英语诗人的英语(我们完全可以加上“最好的”这个形容词,有没有“之一”无关紧要)。一种“现代”英语,一种质疑,否定,分裂,聚合,反转,延伸,增殖,突变,湮灭与新生的语言,无论是这语言之于它的时代,还是之于它的存在空间,还是之于它的使用者(史蒂文斯),都是如此。即使没有资格,我也可以不负责任地拿莎士比亚时代最好的英语,莎士比亚的语言来作个比较:如果说莎士比亚的语言精美而又机智,流畅而又悦耳,令人愉悦而又启人心智,史蒂文斯的语言就是简练而又晦涩,平静而又深邃,出人意料而又难以索解的。莎士比亚以国王般的自由来驾驭和享受英语,畅游于英语之中,有那么多没有言说过的东西,即使言说过却还可以言说得更好的东西,言说随世界的延伸而延伸;而史蒂文斯以药剂师般的精确来调配英语,尝试每一种可能,以致分解,重组,颠覆,重新发明英语,重要的已不再是言说什么,言说什么都不如言说的方式,或言说本身更加重要,世界延伸之处就在言说之中。
换句话说,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诗人用语言呈现世界,在史蒂文斯的时代,诗人用语言呈现语言,语言就是世界。再简化一下:如果将诗人等同于他的语言,那就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诗人呈现世界,史蒂文斯的时代诗人呈现语言,即诗人自己(因为诗人等同于他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呈现的就是自己,这话依然可以套用在任何诗人头上。诗人的语言——“那千丝万缕的 / 一团乱麻就是自己的脸相”[11]。但我希望前面的比较已经足够表明我的心目中,莎士比亚与史蒂文斯,也就是前现代诗人与现代诗人的不同——当然这种区分必定是武断的,或许并没有所谓前现代与现代两种诗人,而只有两种读者,即两种阅读方式的不同。
再多引用博尔赫斯一回:“一切阅读都暗示着一场合作,几乎是一次同谋。”[12]莎士比亚的读者如同剧场里的观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也确实是观众),他们看到并且知道自己面前是一座舞台(他的语言)。这时读者与诗人合作的方式是想象舞台就是世界的呈现,而他与诗人都在这个被呈现的世界之外,谁都可以随时抽身离去。在史蒂文斯的时代,诗人和读者都没有了舞台(舞台已经专属于另一门艺术),但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剧场,他自己,自己的世界;读者与诗人合作的方式是想象自己就是诗人,想象诗人的语言是出于读者自己,读者与诗人的自我/语言/世界合一。而在这合作——这想象的另一端,诗人也必须想象自己是在为这样一个读者在写作。当一个诗人说自己不为任何读者写作,或只为自己写作时,他说的其实是:他为一个与他的自我/语言/世界合一的读者写作。显然这是一种比莎士比亚时代更紧密的合作方式,你都无法确切知道合作是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同时这也是更困难,更不可能的合作方式,你甚至无法肯定你是否真的在合作,合作的双方是否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诗歌缺少读者是一件必然的事,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少。
无论如何,总有人想要尝试成为这少数,完成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事:阅读现代诗歌,阅读史蒂文斯的诗歌。这场合作的用时不会很短,但前期准备却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需要:開始想象即可(难易因人而异)。忘掉诗人和你,想象书页上的分行文字,每一首的每一句,每一个词的每一个字母,那些排列与组合,分断与延伸,拆解和生造的语汇,入微的细部与“至大的抽象”[13],就是你的存在和你自己:“如我所是,我说话和行动”[14]。总之,这个“没有身体的读者”[15]要用一个词语的自我重构一个世界,逐字逐句地经历诗人经历的行程(我相信,无论是史蒂文斯对其诗歌信仰的探寻,还是诗人数十年长达万行的写作,或是阅读史蒂文斯写下的全部诗篇这件事,用行程两字来形容都无比贴切)。
而这不可避免是一段充满困扰的行程:我们有的只是晦暗的想象和晦暗的悟性,走的却是一条“云中的路”[16](为清楚表达我必须拿史蒂文斯的词语来作我的比喻——有一些评论者认为史蒂文斯的诗就是由比喻构成的)。在诗人/读者合一的史蒂文斯/我脚下,词语的岩石坚硬地承托着“事物的直感”,但语义的云雾将视线完全遮挡,仅有一种难以界定,或许为知,或许为觉,或许是力与信心(史蒂文斯多次提及的“阳刚”?),或许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冥冥中连接了不同的时空与种族,让诗得以为诗的东西,一道“夜晚的光线”[17] ——像“秋天的极光”一样浩大,但不需要那样玄奇瑰丽,更平静也更平凡,仿佛是理所当然——在指点着方向,将路径导向下一个“合适的瞭望点”[18],于是自我/语言/世界便会再一次显现,尽管诗人/读者每一次都会“发现自己更真切也更陌生”[19]。
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没有人能告诉我是否真有这样一场合作,我是否真的在阅读史蒂文斯,但我愿意相信它的确发生了。而将这个动作拉长数倍时间,增加若干步骤(比如查更多字典),就是本书的翻译过程了——只是这场诗人与读者的合作是反向的,一次颠倒过来的想象,是要将史蒂文斯/我在英语中走过的路径,以我/史蒂文斯的方式在汉语中再走一遍,行对行,句对句,词语和意象的序列也力求对应,除非遇到在英语中是一个通道的地方,在汉语中是一堵墙或一道深沟,这时才会尝试不得已的绕行或跳跃,或“挪动岩石”[20]以便迈步,总之,语言上的变通被尽可能地压制,译者本人(从未有过)的诗意与灵感也从未前來打扰,因此纯熟而流畅的美妙步法或悦耳之音也无从产生。一个有利条件是,英语和汉语都有足够的空间,像史蒂文斯和我所在的国度一样,可以各自容纳如此广大,几乎是远不可及的诗歌行程,尽管地形、地势、地貌全然不同。但愿前文所述的某种超越语言的东西,那道夜晚的光线依然存在,能够将两种语言导向同样的海拔,再一次铺开那条云中的路。我的期待与惶惑仅仅是,同样遮没视线的语义的云雾,同样仅在脚下方才坚硬的词语,和必定无法再现同样远景的瞭望点,是否能给汉语的我/史蒂文斯(或是本书的读者)一个英语中前所未见的视野?
注释:
[1] 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作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
[2]《反对诠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年)。
[3]史蒂文斯: “礁岛西的秩序理念”(《秩序的理念》)。
[4]Frank Aristides Doggett(1906-2002),美国文学批评家。
[5]Harold Bloom(1930- ),美国文学批评家。
[6]Helen Hennessy Vendler(1933- ),美国诗人,文学批评家。
[7]史蒂文斯:“哦,佛罗里达,交媾之地”(《簧风琴》)。
[8]史蒂文斯:“一个显贵的若干比喻” (《簧风琴》)。
[9]绝无仅有的例外是诗集《一个世界的各部分》的末尾,附在“战时对英雄的检视”之后有一段散文体的说明,或许是因为那首诗既是“宏大的战争诗歌”又是“作为想象之作的诗歌”吧。战争中的世界具有将想象拉回现实的力量,此刻诗歌的破坏与否定与世界的破坏与否定合为一体,或者说,有赖于后者方能存在,后者成为前者存在的前提与理由,乃至剥夺前者存在的可能。在我看来,显然,仅仅在这个时候,史蒂文斯才认为对诗歌的阐释或辩护是必要的。
[10]陈东飚:“坛子轶事的轶事”(《坛子轶事:史蒂文斯诗选》;“史蒂文斯诗歌的‘朝向”(本书附录)。
[11]博尔赫斯:“总和”(《密谋者》)。
[12]博尔赫斯:“前言”(《为六弦琴而作》)。
[13]史蒂文斯:“朝向一个至高虚构的笔记”(《运往夏天》)。
[14]史蒂文斯:“弹蓝色吉他的人”(《弹蓝色吉他的人》)。
[15]史蒂文斯:“西方的一个居民”(《岩石》)。
[16]史蒂文斯:“取代一座山的诗篇”(《岩石》)。
[17]史蒂文斯:“山谷之烛”(《簧风琴》《尤利西斯之帆》《晚期诗作》)。
[18]史蒂文斯:“取代一座山的诗篇”(《岩石》)。
[19]史蒂文斯:“胡恩宫中饮茶”(《簧风琴》)。
[20]史蒂文斯:“取代一座山的诗篇”(《岩石》)。
“El Hacedor”:博尔赫斯的作者与读者
这篇小文谈论的不是博尔赫斯的诗集El Hacedor,也不是它的第一篇“El Hacedor”[1],而仅仅有关“El Hacedor”这个词的翻译,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想法。
翻译博尔赫斯诗歌前后已有三十年了,期间不断修订译稿并扩充到译完《博尔赫斯诗歌总集》,但直到2018年在为一部博尔赫斯对话集写译后记的时候,我才想到其实我要做的最大一个改动就是重译这个词。
在博尔赫斯与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2]合译的《阿莱夫及其他故事1933-1969》[3]里“The Maker”这篇的注释中,博尔赫斯说“一位早先的译者担心‘El hacedor这个词,我的西班牙语标题,没有严格对应的英语。我只能告诉他‘hacedor是我自己对英语‘maker的翻译,像邓巴尔在他的‘挽歌(‘Lament)中使用的那样。”
博尔赫斯所说的邓巴尔是苏格兰诗人威廉·邓巴尔[4],他的“挽歌”即《诗人的挽歌》(Lament for the Makaris),英语“maker”对应于中古苏格兰语“makar”,意为“诗人(作诗的人)”,源自(直译)古希腊语“ποιητ??”(创造者,制作者,写作者,诗人),而后者又是基于动词ποι?ω(制造,创造,写作,发明……)。
显然从古希腊语到中古苏格兰语再到英语,再到博尔赫斯西班牙语“hacedor”,以“创造,制作,写作”这一动作来界定所指的人这一点是一脉相承的,我的观点是这个动作是这些词语共同的内核。这个内核使得“hacedor”这个词(以及maker / makar / ποιητ??)既容纳了“诗人”的涵意,又大大扩充了它的外延,令它囊括了人类所有创造性的职业(哪些职业,哪些人类行为是非创造性的呢?)。
在汉语中有几个词可用来翻译“hacedor”。“诗人”是最先被我排除的,尽管此译并非错误,但它在字与词的构成上与前述的这个内核全然无关,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约等于不翻译的“正确”翻译,因为如果仅需传达“诗人”这个意思的话,原文标题尽可使用“poeta”而不需要费心翻译英语的“maker”。何为诗人——我想这应该是“hacedor”这个词旨在呈现的东西吧——就好像,如果谜底是“诗人”,它就不应该出现在谜面上。
我原先翻译“El hacedor”时用的是“创造者”这个词,同样并没有错,甚至比“诗人”更正确一点,现在弃用的理由是它带给我的印象约等于“造物主”,与“创造物”或“造物”相对,因此就有了强烈的神学色彩,一个强大、全能、终极、无上、荣耀、创生万物与人的存在,跟“El hacedor”以及博尔赫斯的全部写作中所说的诗人距离太远,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在博尔赫斯这里,我猜想,写作与做梦同义,是一件被幸与不幸的因果强加给他的赠礼,一份无限而不可让渡的财富,一种神秘和一个魔法,一个无可破解的宇宙布局的一部分,一场痛苦,偶然,虚妄,短暂,扭曲,希望与失望兩者皆有的过程(“啊,多么无能!”[5],“我才艺的工具,惟有耻辱与痛苦”[6]),诗人是“用无常,用危险,用失败”[7],“把岁月的侮辱改造成 / 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8],其来源是无可捉摸,仅仅“吹拂它嘱意的所在”的“灵感”[9],其形式是贫乏的“计算音节”[10]。因此我希望翻译这个词所用的汉字能够剔除宗教的崇高、骄傲、夸张意味,博尔赫斯绝不是在用“El hacedor”神化诗人与他自己。
最终我采用的词是“作者”。在我的认识中,这是一个现代的词,简洁朴素,直接呈现语义——相比之下“创造者”是典型的“现代”汉语,用两个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取代的词“创”和“造”叠加以形成华丽装饰的效果,这种效果将它的意思稍稍遮蔽了一点——在“El hacedor”里为诗人写下明确无误的定义,同时(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其包容的范畴远远不止是诗人,而是所有的行动者、发明者、写作者、构想者、制造者。
“创造者”一词在人的身上渲染神性的光辉,“作者”一词将神降格至与人同一高度。
在《戈莱姆》[11]中那个巨大的人型玩偶戈莱姆的“作者”犹大·莱翁[12]因失败(教不会它说话)而痛苦与恐惧,在最后一节里博尔赫斯暗示莱翁自己的“作者”上帝也有同样的无力之感;在“棋”[13]中可以读到套娃般的多重“作者”(棋子——棋手——上帝——“在上帝身后,又是什么上帝”);又如“Everything and Nothing”[14]中莎士比亚的“作者”上帝:“我也不是我;我梦见了世界就像你梦见了你的作品,我的莎士比亚,你是在我梦幻的形体之中,你像我一样,是众人也是无人”。
以更近于“作者”而非“创造者”的hacedor这一身份,一个或多个人格化的“上帝”被去神化了,奇怪的是在此观照下的世界忽然有了一点泛神论的意味(我们通过语源回溯的古希腊人看世界的眼光);与此同时一个可以说是专属于博尔赫斯的词——“读者”,几乎是自动地与它形成了基本的对应。这时我想到,或许博尔赫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破解宇宙布局的方法(在此低调地借用一下博尔赫斯的语汇,即使它并非博尔赫斯的理念,至少是来自我对博尔赫斯的阅读)。
量子物理学试图用它的方法解释“万物之理”,我确认它对我毫无意义,因为不但无法理解,强行去理解它也无法让我得到丝毫的乐趣,因此我只能满足于下面这样的伪思路:
这个方法就是把世界看成一个“作者——读者”的二元结构。万物皆有其作者,即使宇宙创生于无物,也可说无物即是其“作者”,而“读者”即是诞生于“作者”的存在,没有“作者”就没有“读者”,同样没有“读者”就没有“作者”,若有因而无果则因也不会有。意为“读者”的西班牙语和拉丁语“lector”——源自拉丁语动词“lego”,后者源自古希腊语“λ?γω”(排列,收集,选择,言说,命名)——是接受作者之“作”并将其改变而化为己有的存在,而这些动作(即广义的“阅读”)本身同时也是一种创造,制作,写作。换句话说,“读者”同时也是“作者”,宇宙间没有一件事物不是既为“作者”又为“读者”的。
很难说这是博尔赫斯的宇宙观,但我仍可断言它是博尔赫斯式的——别忘了博尔赫斯直接发明了“宇宙(别的人把它叫做图书馆)……”[15]。由此再说回诗人既是“作者”而又是“读者”显得顺理成章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诗也可以说是宇宙向人投射的一个幻象,同时也是人向宇宙投射的一个幻象。而博尔赫斯本人早已将自己视为读者,不止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读者,其次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散文作家”[16],更因为“你是这些习作的读者而我是它的编写者这一情形是微不足道和偶然的”[17],作者、读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分别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他们归根结底是一体:“那些沉湎于莎士比亚的热情读者难道不就是,真实的,莎士比亚?”[18]。
在“圆型废墟”[19]中,主角,那个以梦造人的“作者”,事实上正是以他的写作(存在与做梦)在阅读他自己的“作者”,同时也为他的弟子即“读者”所阅读。多年来这个短篇重读了许多次,我已经可以直接跳过前几页铺垫加最后转折的完整情节,只需要末尾几行——他发现自己像梦中的弟子一样滔火而不死,从而领悟自己是另一个人梦中的作品——就可以品尝到这篇杰作之所以为杰作的精华所在:就是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宣布无论作者与读者出现多少回,他们都只是诗与世界之中,同一个倏忽而无尽的幻影。
由此可以理解“在‘实际语言和对话所由来的猜想性特隆‘ursprache[20]中并无名词:有无人称的动词……”[21],在特隆(博尔赫斯的星球上)“作者”与“读者”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动作——“作”与“读”——前面有关“读者”语源的时候已经说过,不妨把两者看作同一个动作的前后两段,或者仅仅是两种诠释的分别(或无分别)即可。
总之,我将自己原译为“创造者”的“El Hacedor”改译成了“作者”,并引申出“作者/读者”的观点,最后将“作者/读者”抹掉。我不知道这些解读是否合乎博尔赫斯的本意,不过“hacedor”一词在博尔赫斯的诗中仅仅出现了两次(在其他文体中也极少出现),都是作为诗题,在《作者》和《秘数》[22]两部诗集里;我感觉博尔赫斯真正在意的,不是他为诗人和他自己找到的那些无关紧要而终将消失的名字,而是那份永不消失的(直到“他沉入最后的黑暗之际”[23]),“我是谁”[24]的困扰。
注释:
[1]在2011年之后的西班牙语版《博尔赫斯诗歌总集》(Poesia Completa)中这一篇及其他若干篇散文诗被删去。
[2]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1933-2017),意大利裔美国翻译家。
[3]The Aleph & Other Stories,1970年。
[4]William Dunbar(1459/1460-约1530)。
[5]“Dreamtigers”(英语:“梦虎”),《作者》(El Hacedor,1960年)。
[6]“诗人表白他的声名”(“El Poeta Declara Su Nombradía”),《作者》。
[7]“Two English Poems” (英语:“两首英语诗”),《另一个,同一个》 (El Otro, El Mismo,1964年)。
[8]“诗艺”(“Arte Poética”),《作者》。
[9]“另一个”(“El Otro”),《另一个,同一个》。
[10]“短歌”(“Tankas”),《老虎的黄金》(El Oro de los Tigres,1972年)。
[11]“El Golem”,《另一个,同一个》。
[12]Judá León(约1520-1609),犹太教学者,哲学家。
[13]“Ajedrez”,《作者》。
[14]英语:“一切与全无”,《作者》。
[15]“巴别图书馆”(“La biblioteca de Babel”),《歧路花园》(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1941年)。
[16]“序言”(“Foreword”),《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923-1967年诗选》(Jorge Luis Borges: Selected Poems 1923-1967,1971年)。
[17]“致读到的人”(“A Quien Leyere”),《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Fervor de Buenos Aires,1923年)。
[18]《对时间的新驳斥》(Nueva Refutación del Tiempo,1947年)。
[19]“Las Ruinas Circulares”,《歧路花园》。
[20]德语:“原始语言”。
[21]“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Tl?n, Uqbar, Orbis Tertius”),《歧路花园》。
[22]La Cifra,1981年。
[23]“作者”,《作者》。
[24]“阴影颂”(“Elogio de la Sombra”),《陰影颂》(1969年);“一个盲人”(“Un Ciego”),《深沉的玫瑰》(La Rosa Profunda,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