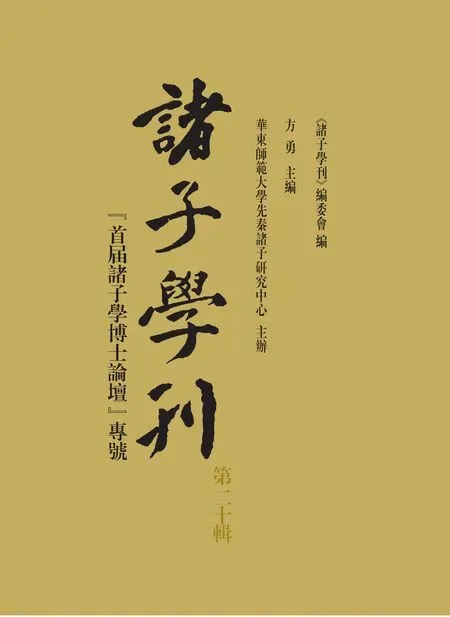論章太炎“以佛解莊”的致用理路
——以《齊物論釋》爲中心
王英娜
内容提要 近代以來,由於西學傳入,傳統儒學的權威地位發生動摇,佛、道思想出現復興契機。章太炎對莊子内聖外王的認同及佛學現世致用的近代轉向,促使其通過“以佛解莊”建構致用理路。他將唯識論的“阿賴耶識”作爲致用的終極預設,目的是實現俗中求真和由真返俗的致用融合。其中,突破我執、法執是回歸“藏識”的路徑,以“兩行”對治是非“成心”;以能詮、所詮消解是非名相;將齊同是非擴展到萬物平等;在眇契中道中隨順俗情;以會通之法呈現真諦等,是圓融致用的具體方法。他對莊子的闡釋與古人不同,所呈現的致用理路是對文化價值重構的有益探索。
關鍵詞 章太炎 以佛解莊 致用 《齊物論釋》
“以佛解莊”是莊學研究的一種常用方法,多集中於莊、佛義理在精神領域的互釋與貫通。時至近代,由於西學觸動了我國本有的社會文化結構,莊、佛思想在致用層面也被發掘出潛力。梁啓超説:“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爲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1)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90頁。這一“新國土”即是其所開拓的致用内容。章太炎“以佛解莊”包括真與俗兩個方面,求真是致用的目的,返俗是真以致用的圓融。他以莊、佛建構致用體系,是對傳統文化“返本開新”的探索,其旨歸是以固有文化唤起民族的自信與自强,以傳統思想爲内在邏輯開發時代新意。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經世致用”觀念多與儒家孔孟相關,章太炎爲什麽選擇莊、佛作爲致用理路的文化資源?他設想了怎樣的目標、路徑及方法?他對莊子的理解與古人有哪些不同?兹不揣淺陋,試作論述。
一、 以莊、佛構建“致用”理路的動因
近代“經世致用”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歷史背景下,知識分子通過歷史反思所選擇的救國圖强的道路。梁啓超認爲“經世致用”一派的根本觀念傳自孔孟(2)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04頁。,李澤厚則指出實用理性是“中國傳統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儒、墨、老、韓等均從不同角度展現了實用理性中歷史意識的發達,它們不重視短暫的成敗利害,而是從久遠、系統的角度來考索事物(3)李澤厚《新版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頁。。如以韓非爲代表的法家提出了以“法”治世的思想,以老子爲代表的道家提出了“無爲而治”的安邦方略。也就是説,“致用”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品格,它不僅僅發生於儒家。先秦諸子學説雖有後人所謂“入世”“出世”之别,但其根本目的均是爲了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在濟世安民方面可謂殊途同歸。從漢代獨尊儒術後,儒家積極應世的倫理思想成爲致用精神的主導,道家、佛學等“出世”思想常被儒者批評爲不能致用的對象。即使道、佛在魏晉和隋唐時期達到繁盛,它們也仍多處於附庸儒學的地位。宋明以來,除經學外,其他學説均遭遇了長期貶抑。時至晚清,西方的堅船利炮不僅打開了國門,隨之而來的西方思想亦撼摇了儒學千年的權威地位,此時諸子、佛學才出現真正的復興,開始對社會文化結構的變化發出積極回應。章太炎將莊、佛思想引入經世致用,即是在傳統儒家致用原則被質疑後的新探索。
儒學地位的動摇是使莊、佛思想成爲致用資源的動因。致用理路的建構關涉文化選擇,面對不得不變的時代必然,中國文化面臨中西古今的揚棄與抉擇。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文化從未停止變化的步伐,從諸子争鳴到儒家一統,從今古文經之争到道、佛興起,再到三教合一,從漢宋之争到乾嘉考據的鼎盛,可以説,文化發展正是在矛盾與統一的張力中不斷碰撞、更新與推進。這種變化並非完全斷裂,而是具有承續性的開拓,因此,每一次變化總能溯源到文化的源頭。對於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界的變遷,梁啓超説它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4)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頁。。明末清初之際,顧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抨擊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之弊,主張運用考據方法研究儒家經典,以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他們開啓了樸學考據之風,至乾嘉而鼎盛。但古文經派章句的繁瑣僵化,失卻了本有的致用旨趣。於是以莊存與、劉逢禄爲代表的今文經學派引領了新的致用學風。清末龔自珍、魏源等憂時之士則“以經術作政論”,再倡“學以致用”精神,但此時之致用則由考據轉向了義理。廖平有經學“六變”之義,康有爲有托古改制之説,“今文經學家以先秦諸子並起創教、托古改制之意,貫穿經子;……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思想的指引下,客觀評判諸子哲學,甚至從倫理學的發生,統論經學與子學”(5)麻天祥《中國近代學術史·前言》,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他們給予了經、子以平列的地位,同時亦開啓了質疑古文經的風氣。儒學致用漸失傳統的權威地位,這從客觀上促進了道家、佛學等其他學説在致用方面的興起。
對於“殘明遺獻”的繼承,主要表現在“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6)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頁。,這些晚明學者可謂後世疑古派的先驅,他們提出了傳統文化自身嬗變的依據。這種通過求是求真以救世的致用理路給後人以啓發。可以説,晚清諸子等學説的復興不僅是西方外因帶來的改變,亦是傳統文化内在邏輯發展的結果。中國文化所走的一直是在復古中開拓未來的路徑,其新變與發展從未脱離傳統文化的本位立場。但當面臨西方文化的挑戰時,傳統儒學遭遇了從未有過的被學術主流重新評估的命運。作爲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學不僅失去權威,而且被普遍認爲是消極存在意義的引導。章太炎在提倡國粹時,甚至還要强調他“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7)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頁。。可見,當時如果没有其他學説的復興,那麽,中國文化除了選擇西方,幾乎被置於無路可走的地步。然而,千年的積澱使中國傳統文化早已形成儒、道、釋一體的特色,它具有多元包容的優秀品質及同化異質文化的强大能力。當儒家主體遭遇重創,子學、佛學的復興便彰顯了時代的生命力,它不僅擴大了學術探究的領域,突破了傳統思維模式的局限,而且在批判吸收西方文化理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章太炎雖爲古文經派,但從他對當時文科之弊的批評(8)章太炎批評當時文科的五種弊端,即“尚文辭而忽事實”,“因疏陋而疑僞造”,“詳遠古而略近代”,“審邊塞而遺内治”,“重文學而輕政事”。(參見《救學弊論》,載《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03頁。),可以看出他尤重學以致用。在諸子中,章太炎對莊子的評價頗高,如“《齊物論》者,内外之鴻寶也”(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漢微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頁。,“莊周方内之聖哲也”(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國故論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頁。,“經國莫如《齊物論》”(11)同上,第106頁。等。又,“自莊子之説流行,不啻爲研究佛法者作一階梯”(12)章太炎《諸子略説(下)》,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1014頁。,因此章太炎以莊、佛爲主導的致用思想既有歷史緣由,亦是應時代之需的産物。
佛學現世致用的近代轉向使其成爲學者們救國的文化資源,亦是章太炎“以佛解莊”的動因。佛學自從漢代傳入,至近代已有千年歷史,它早已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且具備廣泛的民衆基礎。對於佛學義理而言,它對傳統文化具有補充作用。傳統儒家文化重在關注現實生活,並建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和秩序。道家亦關心當下,但它提出了與之不同的處世態度,其側重於人作爲個體存在對自由的追求。佛學的“三世説”則爲我們打開了一個新視域,它將現世的存在放置於與前生、後世具有因果關係的體系中,也就是説,現世的存在不是單一而孤立的,三世因果爲生命存在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緣由。因此,它也成爲人們價值信仰的依托之一。如果説,儒學是入世的,道學是出世的,那麽佛學則是超世的。不論在治世,還是亂世,在官場,還是民間,作爲對未知世界的追求與渴望,佛學豐潤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即使在佛學被壓抑的時期,它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裏也仍占據一席之地。正如梁啓超所説:“中國之有佛教,雖深惡之者終不能遏絶之;其必常爲社會思想之重要成分,無可疑也。”(13)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96頁。
明清以前,佛學主要在精神領域解決人們的來世問題,但到近代,它已出現明顯的入世轉向。也就是説,近代學者在運用佛學的三世體系時,其重點已發生變化,由以往對超世的關注轉向對現世的關懷。他們認爲,佛學不但要解決來生問題,也要發揮其現世部分的效用,這使佛學在近代出現了“人間佛教”的時代精神。爲挽救近代危局,佛學也成爲學者們經世致用的文化資源。龔自珍、魏源引領了“今文學家”對佛法的兼治,楊文會以“法相”“華嚴”擴大了佛學在學術界的影響,譚嗣同以佛學義理著《仁學》,康有爲“以己意進退佛説”,章太炎則認爲“佛法本來稱出世法,但到底不能離世間法”(14)章太炎《佛學演講》,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156頁。。可以説,晚清以來的新學家,“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15)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95頁。。蔣方震認爲,新佛教是我國未來新機運開拓的必要之途,梁啓超亦深韙其言(16)同上,第96頁。。從近代學者對佛學的致用來看,他們主要借中學嬗變、西學東漸之歷史契機,闡揚佛學的現代意義,通過儒釋結合與道釋結合的路徑,發揮樹立文化自信與重塑道德價值的功能,從而創造新的文化氛圍。與譚、康不同,章太炎選擇了道釋結合的道路,他的“以佛解莊”即是以佛學的濟世情懷和理性思維發掘《莊子》的深層内涵,並試圖將佛、道的出世思想轉化爲入世致用,他要爲中國文化尋求一個在延續中更新的道路,從而應對文化秩序重構的時代需求。
二、 “齊物”與真如目標的預設
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儒家傳統思想定式被打破,近代知識分子不得不尋找構建新的價值信仰與意義世界的文化資源。西方的理性認知與中國傳統經驗式的描述呈現了中西文化明顯的思維差别,但唯識學的邏輯體系與西方科學有相似之處,正如章太炎所説:“逮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縝密矣。是故法相之學……於近代則甚適,由學術所趨然也。”(17)章太炎《答鐵錚》,載《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頁。他借鑒唯識理論闡釋莊學,順應了時代需要,一方面,它可以滿足人們對科學邏輯的渴求;另一方面,通過佛學他建立起理性思維與傳統文化思想的銜接。他認爲佛教不是宗教,因爲佛理非心外求佛,其“自貴其心,不依他力”的特質,恰可用於艱困危難之時。在他看來,佛法真、俗二諦的最高處是“理論極成”與“聖智内證”,其目的是求取真如智慧。因此,在世俗中明悟真如是章太炎致用理路所預設的終極目標。對於真如,他亦有多種表述,如畢竟平等、藏識、阿賴耶識、種子、真君等。
在讀《莊子》過程中,章太炎深感郭象注與莊子之意不合,他説:“爲諸生説《莊子》,間以郭象敷釋,多不愜心,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觀,而釋《齊物》,乃與《瑜伽》《華嚴》相會,所謂摩尼見光,隨見異色,因陀帝網,攝入無礙,獨有莊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18)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漢微言》,第69~70頁。從這段自述中可知,章太炎與郭象的主要不同即是其以佛釋莊。在對“齊物”的闡釋方面,他尤重人心齊同萬物的探討,但其並未局限於對是非的判斷和辨析,而是從人之本心入手,從物相追溯至心性之本根,從而提出了明悟真如的路徑。
章太炎以“平等”釋“齊物”,提出了“畢竟平等”的最高境界,這是他依佛理預設的真如狀態。又,因“世間法中,不過平等二字”(19)章太炎《佛學演講》,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157頁。,因此,以“平等”爲釋,亦可與生活實踐建立關聯。對於“齊物”的理解,歷代有不同詮釋,如郭象注:“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20)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44頁。這種闡釋主要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從彼此間的是非、美惡角度來談論“齊物”問題,他重在强調人與人之間的齊等,不可以己意判斷他人。憨山則從“物論”出發,指出是非不齊之象。他説:“物論者,乃古今人物衆口之辯論也。……若不執我見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脱卻肉質之假我,則自然渾融於大道之鄉。此乃齊物之功夫。”(21)釋德清《莊子内篇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他指出若去此是非,須了悟“真宰”,不爲肉體之假我迷惑,而脱卻假我是齊物功夫。王夫之則説:“物論者,形開而接物以相搆者也,弗能齊也。使以道齊之,則又入其中而與相刃。唯任其不齊,而聽其自已;……則無不齊矣。”(2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三册),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93頁。他認爲“物論”由“形開”與“接物”互相碰撞而生成,是在個體自我與外在世界交互中生發的具有差異性的認知,“不齊”是它本來的存在狀態。若以“道”齊之,則會呈現與本然“相刃”的情狀,是對存在本身的破壞。因此,從物與世界的關係看,順應萬物各自的本性差異,是真正之“齊”。較之於前人,章太炎則以“平等”釋“齊物”。
關於“平等”一詞,本見於佛典,而西方平等思想的傳播使時人對其更爲關注,他以“平等”釋“齊物”不免時代之影響,但其義理非西方之“平等”,亦非古人之“齊物”。與西方不同,他所言平等並不囿於“人人平等”的單一領域。與郭象相較,他的齊物平等突破了“有情”範圍,其内涵具有超越價值判斷的更廣闊外延。與憨山的佛理釋莊相比,他的“齊物”遠超出泯滅是非的一隅。對於“真宰”的了悟功夫,他提出了具體的抵達路徑和方法。王夫之的“齊”以肯定多元主體爲存在方式,章太炎則將“齊”收納於人之本心,通過主體的非對象性實現“齊物”之義。同時,萬物的本性不是差異的存在,而是具有同一性。可以説,在前人闡釋基礎上,他將“齊物”從人與人之間的“無所優劣”擴展到人與物、人與世界的關係,並建構了一個具有場域感的齊物體系,其中畢竟平等是“齊物”的最高境地。
章太炎的“齊物”理念直指人心。在他看來,心之所起,不外乎對相、名、分别三事的執取,因此,他提出要“離言説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從而達至“畢竟平等”。對於這一理念,他第一章釋義即言:“齊物本以觀察名相,會之一心。”(23)章太炎《齊物論釋》,崇文書局2016年版,第9頁。對於子綦喪我,章太炎依佛法將之分爲人我、法我,這較之於前人僅爲形體之我的理解而言,將“我”辨析得更爲精細。對於地籟、天籟之喻,他指出了兩者不同的喻旨,他認爲“地籟能吹所吹有别,天籟則能吹所吹不殊”(24)同上。。在郭象注中,天籟與地籟、人籟之間具有能、所關係,但在章太炎的釋義中,兩者是相對獨立的存在狀態。他指出:“地籟中風喻不覺念動,萬竅怒呺,各不相似,喻相名分别各異。……天籟中吹萬者,喻藏識,萬喻藏識中一切種子。”(25)同上。在這裏,地籟是名相分别的代指,天籟是佛學中的“藏識”。天籟的“吹萬不同,使其自己”,非郭象所理解的“自然”,而是“意根自執藏識而我之也”。章太炎指出,對外境持情執而生“自内我”,即爲妄執,是人我範疇;若執藏識爲真我,則是“法我”。名、相、分别不過是“自心還取自心”。他認爲名相的存在是意識分别所成,因此並非外有,而是自心現影,由此説明名相假有。可以説,他没有將事物作爲一個客體看待,而是從主體認知的角度分析客體在主觀的呈現,以此將外在名相轉化爲主體内心的取捨。客觀名相是相分,消解其存在分别是對“人我”的突破,内心的執取是見分,消解其作用分别,是對“法我”的突破。“吾喪我”即是“心不起滅,意識不續,中間恒審思量,亦悉伏斷”,這是對本體藏識存在狀態的還原,“吾喪我”即可證得心之本體。由此可知,“齊物”齊在藏識本體的同一。如果説郭象對“吾喪我”的理解是由主體推知宇宙萬物存在的齊一,那麽章太炎則是以萬法唯心爲根本,從人自身尋求可使萬物齊一的心體。也就是説,真如不必外求,人人平等,它就是自我的内在澄明。
在闡釋《齊物論》時,他以“八識”詮解“成心”,預設了名相分别可回歸本體真知的具體路徑。所謂“八識”,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與阿賴耶識。在八識中,第六意識是追隨前五識而生的意識了知,五識的直覺對象是色、聲、香、味、觸等感覺要素,意識是對這五識的直覺材料進行思慮、綜合、分别的産物,也可以説是妄想。末那識是第六識意識所依之根,又被稱爲“意根”,是我、法二執的根本。它以第八識爲我,且我執成見很深,並由此發生我癡、我見、我愛、我慢四個根本煩惱。前六識所變現的是外物映現於心的物像,被稱爲我執;第七識末那識以阿賴耶識爲我,是謂法執,而第八識是能變現這些對象的本根,它含藏萬有,又稱“藏識”,亦即“阿賴耶識”。瑜伽行派認爲,“阿賴耶識種子是一切現象的本原,是現實世界一切事物的最直接原因,它也涉及生命個體的起源和解脱。”(26)方立天《佛教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頁。佛學立“八識”説的動機是“居於無我説的立場,欲對萬有諸法作一番合理的説明”(27)釋聖印《佛教概論》,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1頁。。佛學的“無我”與莊子的齊物“喪我”有相契之處,這也當是章太炎以“八識”體系詮解“成心”之因。章氏説:“成心即是種子,種子者,心之礙相……成心之爲物也,眼耳鼻舌身意六識未動,潛處藏識意根之中,六識既動,應時顯現,不待告教。”(28)章太炎《齊物論釋》,第19頁。他認爲,成心是以隱性種子的形式存在於八識之中,它呈現的狀態是前六識未動,潛處於第八識藏識與第七識意根之中。此成心種子可化藏識無形真如智,如果在順應成心種子的情況下化隱爲顯,它則具有“解紛”的作用。在此,“隨其成心而師之”具有“齊一”的正面價值,或者説,以“成心”爲師是實現齊物平等的方法。章太炎將“成心”分爲三個層次,“第一明種子未成,不應倒責爲有;第二明既有種子,言議是非或無定量;第三明現量所得計爲有實法實生者,即是意根妄執也”(29)同上,第25頁。。這種詮釋是依“三性”(30)三性,即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圓成實自性。章太炎釋遍計所執自性是“由意識周遍計度刻畫而成”;依他起自性“是阿賴耶了别所行之境。……末那唯以自識見分,緣阿賴耶以爲相分。即此相分,便執爲我,或執爲法,心不現行,境得常住。……即依此識而起見分相分二者,其境雖無,其相幻有。是爲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是“由實相、真如、法爾(猶云自然)而成,亦由阿賴耶識還滅而成”。參見章太炎《建立宗教論》,載《章太炎全集》(四),第403~404頁。説所作的劃分,已超出了郭象、成玄英等以個體偏私爲“成心”的限定。在章太炎這裏,“成心”既有可追索“藏識”隱静狀態的終極目的,亦有順“成心”而“解紛”的應對顯動狀態的方法,這種多層次的解讀展開了一條真如本體與外在世界相通的道路,或者説,他爲名相分别的世界指出了可回歸本體的路徑。
章太炎將唯識論的理論基石“阿賴耶識”作爲致用的最高追求,並認爲莊子所言“吾喪我”是回歸的必須之途,但他“以佛解莊”所釋的“無我”而至真如境界,不是欲人脱離世間,而是爲更好地利益衆生。正如他所言:“非説無生,則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非示衆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31)章太炎《建立宗教論》,載《章太炎全集》(四),第418頁。可以説,了悟真知亦是爲了更無畏、更堅定、更圓融的致用。
三、 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章太炎“以佛解莊”思想並不是以明悟真如爲歸宗,而是以由真返俗的圓融致用爲根本目的。對於佛法“藏識”妙境,他給予高度肯定,同時亦指出其“不應用於政治社會”的遺憾,對此,他以老莊思想進行了彌合。正如他自己所説:“唯有把佛與老莊和合,這才是‘善權大士’,救時應務的第一良法。”(32)章太炎《佛學演講》,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159頁。熊鐵基先生曾評價章太炎“使莊學染上了現實的功效色彩”(33)熊鐵基《二十世紀中國莊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頁。。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的“以佛解莊”之致用重在改造人心,以此達到變革社會的效用。那麽,他提出了哪些具體致用的方法呢?
第一,以妙有非有對治是非“成心”。關於對治是非“成心”,莊子提出“兩行”之法。郭象注“兩行”爲“任天下之是非”(34)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2頁。,成玄英從情與理相悖逆的角度闡釋了其緣由(35)“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可不可皆妄也。”(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9頁。)。與之不同,章太炎則從名相的義界入手,闡釋名不可拘、是非不可斷的道理。他提出三點理由: 一、 名的義界爲依我執、法執而起;二、 責其因緣,其根極處仍是依我執、法執而起;三、 尋其本相,終至意根,亦不外依我執、法執而起。“諸説義界,似盡邊際,然皆以義解義,以字解字,展轉推求,其義其字,唯是更互相訓。”(36)章太炎《齊物論釋》,第26頁。可見,名相從其發生處,即是我執、法執的産物。因此名相是非的消解不能從情與理的轉换中得到調適,而應從消除我執、法執處着手,這是取消是非的根本,以此亦可達至“成心”的第一個層次。但問題是,在世界中生活,人有認知萬物之“質”的需要,而“質”不可言又不得不言,所以必然是“成毁同時,復通爲一”,言中有“毁”,亦含其“成”。“一語一默,無非至教,此之謂兩行”。(37)同上,第29頁。此處,“兩行”不是任是非之意,而是融通是非與是非的言外存在。因此,對治是非不是以消除是非的判斷爲方法,而是以隨順是非“成心”來消解是非。“狙公賦芧”變“朝三暮四”爲“朝四暮三”,即是隨順衆狙以消解是非的“兩行”應用。順世是借天鈞爲用,表現爲隨順他説以和是非;無言則是休乎天鈞,它是離言説而觀天鈞自相。因此,在章太炎看來,以“兩行”妙有非有的圓融心境看待世界,才可對治是非成心。
第二,明能詮、所詮消解是非名相。在莊子看來,是非在有形世界中無法消解,是因爲其没有恒定的標準,所謂“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對此,莊子提出了“一”的概念,此處之“一”强調的是物我一體,正如郭象注:“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38)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9頁。章太炎在闡釋是非名相差異時,没有延續前人是與非關係的探索,而是從言與義的能詮與所詮角度給予分析。在他看來,是非的原由是言不盡義,能詮與所詮不相稱。章氏所采用的不是回溯方式,而是對具體問題的展開説明。或者説,他不是從是與非的名相對待中討論,而是就事物之名本身揭示其存在的矛盾。他認爲,凡事均有本名、引伸名、究竟名三種。“本名”之立,本無所依,“一所詮上有多能詮”,如初、哉、首、基,均可釋爲始,但其各“始”之所以爲始有異,可知“本名”能詮非一。“引伸名”是依“本名”爲據,在“一能詮上有多所詮”,多所詮爲引伸之名。佛典將所詮的引伸之名分爲密詮與顯目兩種,其中密詮爲名之本義;顯目爲累名之現義。如言苗裔,苗本嘉穀,裔本衣裾,此爲苗裔密詮;苗裔顯目則爲遠孫,可見顯密之義相距甚遠。引伸名與顯目之義一致,則多與本義相違,因此言義不齊。引伸名的另一情況是外來翻譯之名,其能取意念、所取事相均奥博無窮,因此名義亦難相稱。“究竟名”是於所詮中遍一切地,如言“道”“大極”“實在”“實際”“本體”等,但能詮之究竟名與所詮之究竟義,仍不能相稱。因此,轉譯殊言,雖覺彼此之意相同,亦不免錯繆。有時指物雖同,現相也不乏各異。章太炎説:“隱顯無礙者,無過十之一二。”(39)章太炎《齊物論釋》,第36頁。從色相上見,言義多有不齊,即是能詮與所詮不相應的結果。因此,章氏之“一”不是物我對待後的融合,而是其自身法藏的無盡緣起。《華嚴經》云: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可以説,明瞭能詮、所詮才可消解是非名相的對待差異。
第三,將齊同是非擴展到人與物及萬物的平等。他指出物與人齊同,表現在物也有識、有意根、有自體。以金爲例,章氏認爲人有識,金亦有識,金有其自身的物質特性,這是它的業識;在一定條件下,它可能變化形狀,或者與其他物質化合,這是轉識;依轉識它呈現了一種新的表相,這是現識。就識性言,其他無生之物均與此相類。此外,金亦有意根,所謂“成此小體,即是我見,有力能距,依於我慢”,也就是説,它之所以能够呈現一種形態是其意根的作用。金分子可分析無盡,其以金塵攝金微塵,以金微塵攝金極微,“一有情者,必攝無量小有情者。是故金分雖無窮盡,亦得隨其現有,説爲自體”(40)同上,第42頁。。這與人有相同之處。此外,他甚至認爲世界萬物都齊同平等,因爲,他們可以更互爲種。以人爲例,人體“含有無始以來種種動物形性,至單細胞而止,依此人力又能生起各種細胞,而彼細胞唯是細胞果色”。又,人因食牛羊雞及菜果穀麥等,這些動植物種性便化入人體,與人合一。“下逮金石,既亦含於人體,或啖雲母,或餐鐘乳,悉可攝受爲人身分。”(41)同上,第44頁。因此,人的身體是無量異性生命集成。“虎豹蚊虻,食人嚼人”,亦是如此。在他看來,欲普度衆生,就不能執取、分别衆生的差異之相,而應“以一切衆生,及與己身,真如平等無别異故”(42)章太炎《俱分進化論》,載《章太炎全集》(四),第394頁。。可以説,以“真如平等”度脱衆生是他覃研萬物平等的最終用意。章太炎從無盡緣起的角度闡釋萬物平等,他認爲萬物的呈現均是意根所執的幻有,是依藏識而起,因此,“實”是“諸心相構,非有外塵”。對於莊子所言萬物與我爲一,前人的理解均是以幻相爲前提,而章氏則提出了與“幻”相對之“實”,即圓成實性。章太炎所釋萬物平等,已超出了物相及理相的範疇,直指性體,“一”即是無見無相。可以説,以“藏識”視角對待萬物是“齊物”致用的根本。
第四,眇契中道,還順俗情。對於齊物之理的應用,章太炎主張要能够眇契中道。中道的方式是内持寂照,外利有情,而利益有情的途徑即是任物之自然。以“堯欲伐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之事爲例,在舜看來,這是德日進的表現。宗、膾、胥敖雖處蓬艾草野之間,但其亦有自若之處。物本應當暢其本性,各安其所安,堯若奪其蓬艾之願而攻伐,使三國順從己意,則違背了事物本有之理,所以才有不釋然的感受,此即“齊物”之德。章太炎借此分析世情,他指出人間世物相不齊,文野有異,但各自所尋之本均爲一,所以相異而質同,當各安其所適,則爲不齊之齊。若以高義之名破壞“質”同而欲得其“相”同,則破壞了齊物中道。物有自量,不可强行增益,否則亦是毁傷。章氏亦聯繫社會現實深入探討其中之理,他説:“觀近世有言無政府者,自謂至平等也。國邑州閭泯然無間,貞廉詐佞一切都捐,而猶横著文野之見,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勞形苦身,以就是業,而謂民職宜然,何其妄歟!”(43)章太炎《齊物論釋》,第52頁。這是針對當時西方以文明自居,欲侵蝕中國文化,而國人多隨其鼓吹、唱和的情況所發出的覺醒聲音。章太炎認爲西方所謂平等只是無實的表相追求,終爲無本之木,虚妄之形,不可因飾西學美名而全盤西化,以西代中在表面上看是追求平等,但其所行實爲不平等,因爲它破壞了中西文化“物有自量”的平等存在。章太炎“應物之論,以齊文野爲究極”的文化多元論,在其所處的歷史語境中可謂深意無窮。因此,真正的平等在應世中還需“還順俗情”,要以無歧相的一如視角分析和解決問題。
第五,會通而見真諦。莊子提出應對世間萬物不齊的方法是“和以天倪”。郭象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44)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03頁。章太炎認爲,以“聖教量”(即聖者之言)爲評判是非的天倪或標準,雖可止息争論,看似可行,但不能被智者所服。對於“自然之分”的釋義,他以爲亦不恰切。他説:“自然之分,即種種界法爾而有者也,彼種子義説,爲相名分别習氣,而與色根器界有殊。”(45)章太炎《齊物論釋》,第62頁。在章氏看來,相名分别與色根器界存在差異,自然之分非天倪之義,因此,他提出更具本體性的概念“種”,並以此統攝無盡緣起、色根器界、名相分别,“種”即爲天倪義。他認爲世情中的各種知見,不論淺深,均依於此種而現世識、處識、相識、作用識、因果識,乃至我識。因此,這種知見雖不圓滿,但亦有真知的一部分。對於這種情況,他提出,應當“一種子與多種子相攝,此種子與彼種子相傾,相攝非具即此見具,相傾故礙轉得無礙,故諸局於俗諦者,觀其會通,隨亦呈露真諦”(46)章太炎《齊物論釋》,第63頁。。在此,章太炎提出了“會通”以和天倪的應世之法。他指出,世俗不得真諦是因不用會通,而以一己之見遮蔽對方的光明,從而不得其正,若能將自悟與他悟會通,則真諦自然可呈,這與古人主張道統攝萬物的的思路明顯不同。在他看來,一物有一藏識之種,或者説一物有一物與“天倪”相和之道,物與物之間彼此交互,真諦之道即在關係交融中呈現。因此,獲得真諦的關鍵在於會通萬物。他的“以佛解莊”融通古今中西,應是這種會通理念的實踐,亦是對文化真諦的彰顯。可以説,會通方法亦打開了莊、佛思想積極致用的入世維度。
結 語
在近代文化轉型的歷史境遇中,傳統的儒家致用原則受到質疑,這從客觀上激發了道家、佛學的致用潛力。章太炎雖爲古文經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尤重學以致用。應時代之需,他通過“以佛解莊”的致用理路,展開了建構新價值體系的探索。在學術史上,他以傳統文化爲本位立場,主張以内在更新爲主的文化發展道路,在楊仁山“以佛解莊”的基礎上,他系統論述了莊、佛思想的致用理念及方法,體現了近代經世致用的新風貌。他以“平等”釋“齊物”,以唯識學的“八識”邏輯預設“藏識”的終極目標,旨在實現人間世的“畢竟平等”。其中,“藏識”的設定指向本體人心。他以佛學的理性邏輯預設真如,使之成爲人們的精神追求與依托。同時,他亦通過對莊子文本的闡釋,提供了突破我執、法執達至“真諦”的路徑。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則包括以“兩行”對治是非“成心”;明能詮、所詮消解是非名相;將齊同是非擴展到萬物平等;在眇契中道中隨順俗情;以會通之法而呈現真諦等,這些均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他通過融貫莊、佛所構建的具有目標、途徑及方法的致用理路,雖然文字艱深難懂,但在重拾民族文化自信、重塑國民價值體系方面,做了積極而有益的嘗試,這對當時乃至後世的文化建設,均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