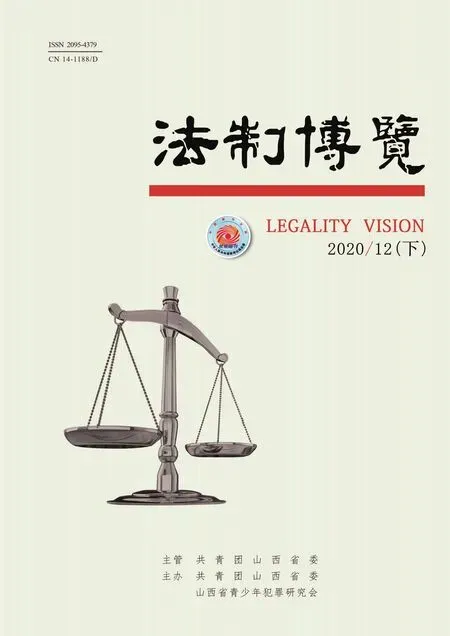继承合同制度初探
姚 遥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公证处,江苏 南京 210000
继承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享有重要的地位,是财产流转的主要形式之一。随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断增多以及法制观念的普及,通过个人意思对扶养、身后财产分配及相关事宜进行安排的需求也不断增多,甚至成井喷之势。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对此提供了三种方式供当事人选择,分别是遗嘱、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但是,遗嘱、遗赠均属死因行为,于继承开始后才发生效力,且立遗嘱人生前可以单方修改、废止,不具有稳定性;遗赠抚养协议虽然于订立时生效,且被抚养人生前不能单方任意修改,但只能和被扶养人的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订立。在司法实践中,许多被继承人会在生前与继承人签订协议,内容大多包括对被继承人的扶养事宜的安排和对遗产的处置。但因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法院对于上述协议的效力认识各不相同,因协议被判决部分无效导致尽到赡养义务的继承人无法取得约定的财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基于此种现象,我国可借鉴相关的外国立法例中的相关制度,建立继承合同公证制度来满足社会需要。
一、继承合同的概念
继承合同在国外也被称为继承契约,目前国外对于继承合同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肯定立法、否定立法、折中立法。由于继承合同起源于日耳曼法,故受日耳曼法影响较深的国家如德国、瑞士、匈牙利均对继承合同抱持肯定的态度。而受罗马法影响较深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以及禁止共同立法的国家如日本、捷克、西班牙,均对继承合同予以否定态度。折中立法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其与肯定立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在肯定立法模式中,继承合同可以直接作为继承的依据,而在折中立法模式中,继承合同无法作为遗产继承的依据,如果要继承遗产还需被继承人依照继承合同的约定另行订立遗嘱。
目前我国学界对继承合同并无统一认知,而对继承合同持肯定观点的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德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可以以继承合同的形式设立遗嘱、遗赠以及继承财产的条件,并且受益人可以是合同的相对人或第三人。匈牙利的法律则规定,被继承人可以通过继承合同指定合同相对人为继承人,相对人负有扶养继承人的义务。瑞士有关继承合同的规定则与德国类似。通过分析可知,以上各国虽然对继承合同的立法各不相同,但对于继承合同应当充分实现被继承人处分遗产的自由及发挥扶养功能的理念,则基本一致。因此,笔者认同部分学者的观点,即:继承合同应是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就继承人、受遗赠人的指定,遗嘱、遗赠负担的设定及继承权抛弃等内容所订立的合同。
二、继承合同的法律特征
根据上述继承合同的概念,继承合同应当具备以下特征:(1)继承合同是双方或多方民事法律行为。(2)继承合同具有诺成性,虽然涉及遗产继承的内容无法立即执行,但不影响继承合同自各方民事主体达成合意时成立。(3)继承合同可能是双务合同,也可能是单务合同,这要由继承合同的内容来决定。(4)继承合同是要式法律行为,即继承合同只有在符合法定形式和程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5)继承合同的效力具有优先性,即同时存在遗嘱、遗赠、继承合同的情况下,继承合同的效力优先。
三、继承合同与遗赠抚养协议的区别
继承合同目前在我国并无法律规定,不过我国现行《继承法》中的遗赠抚养协议与继承合同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已经规定了遗赠抚养协议,不需要引入继承合同制度。但笔者认为,继承合同与遗赠抚养协议还是有相当的区别的。其一,继承合同的合同主体没有限制,而遗赠抚养协议的扶养人只能是除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民或集体。其二,继承合同的内容包括设立遗嘱、遗赠,为合同各方设立权利和义务,放弃继承权等等,可以涵盖被继承人的生养死葬及遗产处置的所有事宜;而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仅包括扶养人负有对被扶养人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同时享有受到遗赠的权利。其三、继承合同的收益人可以是合同的相对方或第三人,而遗赠抚养协议的受益人只能是扶养人。其四、继承合同可以是双务合同,也可以是单务合同,而遗赠抚养协议则必然是双务合同。纵观上述比较,遗赠抚养协议制度完全可以被继承合同制度所取代。
四、我国建立继承合同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在从业过程中,大量遇到这种情况:在多子女的家庭里,由于各个子女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条件好,有的条件差,有的住在外市、外省,对老人扶养不便,有的与老人共同生活照顾方便,不可能做到每个子女都尽到相同的扶养义务。而《继承法》中所规定的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制度无法解决此类问题。首先,由于扶养人系被扶养人的法定继承人,不适用遗赠抚养协议制度;其次,由于遗嘱、遗赠系单方法律行为,其修改、废止无需经过受益人同意,在受益人尽到扶养义务的前提下,一旦被扶养人修改、废止遗嘱,受益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基于这种情况,老人与子女就签订协议,内容是由某位条件较差的子女与老人同住,老人的生活起居主要由其照顾,其他子女辅助,而等老人去世以后,遗留的遗产则由这位扶养较多的子女继承。然而,相应法律规范的缺乏导致法官对于继承合同的认知也不相一致,相关判决中,有些继承合同被认定无效,有些继承合同被认定是一般民事协议,有些则被认定为遗嘱。如此既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也阻碍了法律的指导、预测与化解纠纷职能的实现。笔者认为,继承合同制度在我国应当存在与否已经不值得讨论,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继承合同制度,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对现存的大量继承合同予以司法层面的定性,并对潜在的签订继承合同需求给予法律层面的引导和规范。
五、继承合同与公证
继承合同所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基本涵括继承中的一切问题,一旦成立对合同各方都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普通民众大多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订立的继承合同内容往往漏洞百出、不具备可行性,最终导致合同相对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进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因此在肯定继承合同的外国立法例中,无一例外都对继承合同的成立作出了严格的形式要求,确保继承合同形式规范、内容严谨、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德国、瑞士的法律均规定,继承契约必须经公证方可生效。在我国,公证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具有预防纠纷、化解矛盾、保障法律实施、维护法律秩序的作用,经过公证的文书具有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和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效力。由于继承合同可能变更继承关系,涉及利益重大,由公证机构对继承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进行审查,才能最大程度保护继承合同各方的利益,发挥继承合同应有的职能。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一旦建立继承合同制度,也应当严格限制继承合同的形式与成立要件,即继承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且必须经公证后生效。
六、结语
随着我国民众的私有财产不断增多,通过个人意思对扶养、身后财产分配及其他相关事宜进行安排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现有的遗嘱、遗赠、继承抚养协议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通过新设继承合同制度满足需求,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如何设计继承合同的相应规范,如何让这项舶来的制度在我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将是我们法律人即将面临的下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