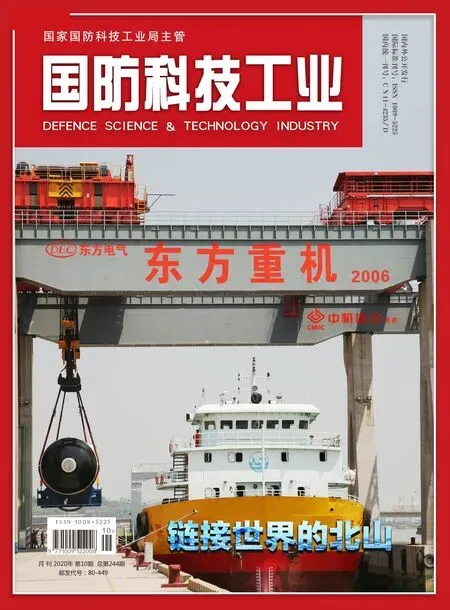无人区的火种
——绘影中国北山高放废物处置研究团队

从北京出发,3 小时飞到嘉峪关,4-5 小时汽车开到北山无人区,这是现在从北京到甘肃北山最快的交通方式。进入甘肃省肃北县后,广袤的戈壁很难再看到村庄,崎岖的山路满是黄沙,一路烟尘伴着天地间被压得渺小的越野车。经过最后一个多小时越来越剧烈的颠簸之后,终于到达北山新场——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的最终场址。
这样的路途,北山地下实验室项目总设计师王驹和他的北山团队,已经走了近30 年。
从1996 年初入北山搭下孤单的第一顶帐篷,到如今北山新场的生活区和国际交流中心初步落成,他们的住所经历了单帐篷——棉帐篷——寝车——彩钢房——宿舍楼;他们从北京地研院到北山的路程时间,从最初的四天,缩短到如今的一天。

2018 年10 月,院领导野外检查并进行“安全生产党员先锋队”授旗

北山团队的科研外围条件已经在大大改善,但如今的北山,生活条件依然是恶劣的:从90 公里的绿洲拉来的生活用水成本很高——每立方米88 元,为了节省科研经费,他们不敢洗澡,脸盆和水桶里总是存着洗漱用过的废水;彩钢房里3 个上下铺床睡着6个人,入秋后的北山早晚很冷,他们需要在被子上再搭一层自己的衣服;更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手机不能离手的时代,这里没有手机信号,中国移动在北山不“移动”,我们在这里采访的三天,基本是与世隔绝的三天……
就是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无人区北山,却被北山科研团队里的每一个人热爱着:
他们在生活区养了两只狗,黄狗是小二,黑狗是老三(老大前年去世了,11 岁时无疾而终)。他们说,狗在门口一蹲,汪汪一叫,荒漠就有了家的感觉。
他们在漫长的工作间隙,拍下了北山所有呈现着土黄色的、紧紧伏在地下的植物,居然有30多种,他们拍到了北山的十几种鸟类,最终做成了一本既科学严谨又生动有趣的《北山常见动植物野外识别手册》;
他们在科研压力大、睡不着的漫漫长夜,看着北山的璀璨星空,在光秃秃的山顶找了一块石头,上面刻上了北山星空图。
他们拍下北山的日出和夕阳,在短短长长的散文和打油诗里,抒发着他们对大漠无边的热爱。
……
从1996 年第一次进入北山开始,到如今的近三十年里,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动(采集样品),一片戈壁一片戈壁地丈量,干着最脚踏实地的事,坚持着与“仰望星空”一样伟大的理想。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那些年,北山人吃过的苦亏欠家人的情
出野外:曾经吃长蛆的肉,曾经用泡着死兔子的井水,也曾一路颠簸中抱回完整的蛋糕
1996 年当王驹带着陈伟明他们一行5 人,挺入北山,开展场址筛选和评价工作时,他们只有一顶帐篷为伴。
荒无人烟的北山,方圆百里就他们四五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着远方传来的阵阵狼嚎,不能不让人有点心慌。一天半夜,他们感觉到有什么动物在拱他们的帐篷,力气还挺大的。几个人都惊醒了。后来发现是一头野驴,才长出了一口气。从那以后,他们每天晚上睡前都要在铁桶里点一串鞭炮,希望噼里啪啦的声音能给北山的野生动物们一点儿警示。

2003 年,北山野马泉营地

2001 年,北山项目人员野外午餐
白天,一个人在驻地看帐篷、做饭,其他四人出去工作。有一天轮到团队科研人员金远新留守做饭,那天的饭大家都说分外地香。结果吃完以后,金远新实在忍不住告诉他们:“咱们带的肉已经长蛆了,可是舍不得扔掉,我就洗了洗给大家炒了,你们就当吃了些高蛋白的‘肉芽’吧。听完金远新的话,几人的胃里都一阵翻腾。”
那时候,从北山到玉门市区的交通不太方便,为了节省来回路上的时间,他们尽可能多地带足生活用品进山。然而北山常年干旱少雨,中午温度异常地高,要保持肉不变质,几无可能。为了吃上一点新鲜的肉,他们想了各种办法。还曾试着在帐篷里养鸡。结果鸡粪太臭,弄得帐篷里都没法睡人;把鸡放到帐篷外,鸡又会在四周跑来跑去,每天为了找鸡也是大费周章。
北山团队地质调查主力科研人陈伟明还记得一开始在北山调查的时候,要从山上拉牧民水井里的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全来自一口深4、5 米的水井。有一次不经意往水井里一看,里面居然掉着一只死兔子,不知道掉进去多少天了,回想这么多天喝水、刷牙,就是用泡着死兔子尸体的井水,五脏六腑又是一阵翻腾。
这样的事例并非少数。在北山现场待了10 年、如今是北山地下实验室项目部副总经理的王锡勇说,在北山这些年,我们都已经练就了强大的“西北胃”——烂掉的蔬菜、发霉的水果、过期的牛奶,团队里在北山住过的人,几乎没有没吃过的!
虽然条件艰苦,但却无法阻挡北山人的浪漫。陈伟明还记得,2000 年6 月5 日他下山去市区拉给养的时候,正好赶上金远新的生日,为了把一个完整的生日蛋糕带回驻地,陈伟明在一路的颠簸中,坚持在怀里抱着这个大蛋糕,没敢松一下手。照片记录下那次生日的场景,驻地简陋的帐篷,那样完整的生日蛋糕显得分外扎眼,而更让人动容的,是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留在北山团队成员脸上那灿烂而质朴的笑容。
搞科研:一次次地辜负家人,
因为家国之爱终难两全
中国的高放废物处置研究,起步于1985 年,有实质性推进也是在21 世纪初,明显晚于世界上其他核电大国。为了追赶世界水平,也为了中国的高放废物处置问题尽可能早地得到解决,北山团队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挤了又挤。团队每一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忙得顾不上家。


团队成员季瑞利高级工程师是水文组的负责人,为了获得完整的北山地质水文数据,他不得不长期守在北山钻孔旁,获得一手数据资料。他曾经45 天没有下山,这就意味着他有45 天不能洗澡。
“为了北山的科研,亏欠家人太多了!”季瑞利的右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色的镯子,与他常年在野外搞科研的黝黑肤色并不相衬。他说:“我从来不爱穿金带银,但这只镯子,我戴上了再没摘下过。”那是一年春节前,先是家里的老大得了甲流,得在家里隔离看护,妻子一直守着照顾孩子,直到孩子病好;紧接着老二得了肺炎,跑医院输液、吃药看护,都是妻子一人忙碌。好不容易俩孩子好了,妻子又得了甲流。这期间,季瑞利没能抽身回过一次家。妻子为了隔离自己的病情,不传染给孩子,那一年的春节,一个人在北京过的。病好后,妻子一个人跑到了商场,买了一个镯子,让季瑞利戴上,希望家人能够平安健康。说到这儿,40 多岁的汉子哽噎了,他要使劲地仰着头,才不让泪水流下来。
赵星光,北山团队里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博士,岩石力学组的负责人,2010 年加入团队。有一年夏天,他夫人带着孩子在小区里玩,遇到了地研院一位同事,聊天的时候,对方说他家高温假的时候带孩子去了哪儿玩。赵星光的爱人才后知后觉地反问了一句:“他们还有高温假!”直到那个时候,妻子才知道赵星光他们这些科研人员,不仅有高温假,还有出野外的假!后来妻子埋怨他:“为啥瞒了我这么多年!”有些尴尬的赵星光才回答:“反正我也休不了,告诉你了不是徒增烦恼?”
陈亮,北山地下实验室项目的副总设计师,北山团队的后起之秀。2011 年他辞掉法国南特中央理工大学副教授的职位,从法国来到了戈壁科研一线。2015年以后,陈亮不仅要负责科研,还要兼顾地下实验室工程立项、项目管理等事务。家在通州,离单位太远。他索性直接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行军床,工作晚了就在办公室里睡下。同事们给他做过统计,最长的一次,他居然有近两个月没有回家。家人说他,在北京和在北山,没啥区别。
王锡勇,现在北山现场事无巨细都需要他管起来。来北山10 年了,每年有半年多都待在山上。结婚前跟妻子承诺,现在出差有点多,以后就好了。结果,结婚后,去北山的时间更长了。
王驹30 年扎根戈壁搞科研,他从来只讲北山的好,从来不提他曾经因为赶路在北山越野车侧翻,腰部摔伤,住院很长时间;陈伟明2005 年评正高级工程师,但因为北山项目现场他是核心人员,他走了,项目推进就会受影响,他请别人代他在答辩会上念他的论文,评审会认为他太不把评职称当回事不予通过,他也只能一笑置之。
从60 后到90 后,北山团队里的这些科研人,早已“身在苦中不知苦”。王驹说,套用范仲淹的诗句,我们这些搞地质处置的“地下工作者”,为了高放废物的处置,先天下之忧而忧;同时,每当打出新的岩心,获得新的地质数据,发现完整性极好的花岗岩体,那份欣喜就是“先天下之乐而乐”。
北山的“科学家”与“民工”
因北山的召唤而回国的科学家
从法国攻读博士开始,陈亮就一直致力于高放废物处置研究,他深知该项研究对每个核工业国家的重要意义,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进展。2009 年5 月,他在香港参加中国岩石力学大会期间,听到了王驹副院长关于高放废物处置研发规划的报告,他感到了一种祖国科研事业的召唤,不由心潮澎湃。会议结束,他第一个冲上讲台,表达了自己要回国参与高放处置研究的意愿。回法国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北山团队的故事,深深地被团队几十年如一日扎根戈壁、拼搏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确信,在这个时代,依然有那么一批人为了真正的科研理想和国家需求在默默奋斗,这也是他的归属所在。
加拿大留学回来的赵星光,谈起他的岩石力学研究,眼睛中充满了点点星光。当被问及他为什么选择回国,选择来到荒凉的北山开展自己的项目时,他说,我之前在加拿大留学时就在关注北山项目,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这个项目一定能干成,而且能做成世界顶尖的高放处置地下实验室。他诉说这个信念时的坚定,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为了两弹研制而回国的元勋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农民工不错!”
曾经有一位领导调研北山时,发现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农民工正用力地用铁锹修复因头一天暴雨冲毁的土路,感慨说,“这个农民工不错,干得挺卖力”。王驹赶紧解释:“他是我们的水文组专家季瑞利!”
除了黝黑的面孔,过早靠后的发际线和他沉默寡言的性格,穿上工作服,混迹钻孔施工现场,任你眼光再独到,也无法把季瑞利从钻井工人的人群中辨认出来。
与他毫不起眼的面容形成反差的,是季瑞利能操控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钻孔水文试验系统,而在芬兰,这个系统是由多个专业团队组成的技术公司来统一操作的。他在芬兰进行学术交流时,芬兰同行曾经羡慕地对他说:“一个这么复杂的机器系统,你一个人走完了全程,太了不起了!”
季瑞利代表了整个北山团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北山现场,你分不清他们是科学家还是农民工。


北山团队现有员工58 人,其中29 位博士,20 位硕士,5 位是海外归国博士。这些成员,除了辅助成员外,几乎全部参加过国际交流和培训。这些成员,几乎常年奔波于北京和北山之间,有的是常驻北山。
正如北山地下实验室项目部总经理苏锐所说,既然选择了在无人区开展科研,就需要做好干基础工作的心理准备。所谓的基础工作,就是在没水、没电、没手机信号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条件,开展高放处置这样的世界级科研课题。说具体一点,就是搬石头、修水管、挖沟渠、做饭、搭帐篷……
年轻的国际顶尖科研人才
王驹说,北山团队里几乎所有人的英文水平都很好。因为高放废物处置是世界性难题,也是全世界科学家致力于共同解决的问题,因此国际学术交流非常开放和频繁。现在团队成员写邮件或学术论文时,不仅使用英语,而且思维表达也完全转到英语频道了,这是为了国际交流的便捷和高效。王驹本人就是国际高放处置学术大会被邀请的常客。
陈伟明当年读大学时,考英语四级的人还非常少。为了苦练英语,他用10 年时间潜心研究音标,直至最后把每一个音标都能标准地发出来。陈伟明是浙江人,他的普通话至今带有浓浓的乡音,难怪他的老师陈璋如说他的英语比汉语好多了。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高放处置科研团队相比,北山团队最大的特点是年轻。
80 后赵星光博士就是一个优秀代表,学术能力强,英文好,会说也能写,特别受国际高放处置学术交流论坛的欢迎。
马洪素,北山团队的破岩专家,2012 年从瑞士博士毕业后回国。这位看起来文弱沉静的80 后女生,现在正在研究的方向,是使用岩石掘进机(TBM)开挖北山地下的花岗岩斜坡隧道。她的研究方向,决定了北山地下实验室将拥有世界上首条用TBM 开挖的螺旋隧道。
马洪素的本科同学中,女生大多都转行了;上到研究生,她的女同学就更少了;待到博士选定具体研究方向时,更是几乎就没有女生了。当时她只觉得这个方向还没有人研究,而且北山项目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TBM 进行螺旋隧道挖掘的项目,她自己觉得会非常有价值,因而毅然选择了这个方向。本来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何特殊之处,但等到因为研究需要而去一些隧道工程调研时,有的施工方提出女生不能下隧道,她才发觉性别给她的研究带来了麻烦。
但在去年在武汉举行的国际隧道大会上,她作为研究方向上唯一一位女性研究员发言,不仅赢得了在场所有与会者的目光礼赞,更赢得了大会的奖项。


他们在北山种下精神的火种
年轻的理想在北山经受历练
2002 年,从北山现场回到地研院的季瑞利,只剩下70 天的时间用来准备复习考研。他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只有晚上12点以后才是留给自己的复习时间。一天晚上,他再次准备去往5 号楼复习的时候,站在黑漆漆的大楼前,他也曾感慨万千:所有的人都睡了,却正是他要开始奋战的时候。那时候女朋友也刚刚因为他工作太忙而分手,他真的想过,自己是否应该离开。如果他走了,中国就少了一个操纵双栓塞钻孔水文试验设备的顶级专家。
2011 年,29 岁的陈亮一回国就在北山一线连续待了100 多天。他发现,按照北山项目需求,他需要暂时放弃原来的科研方向,要从一节岩心一节岩心测量、一条一条数据编录开始,以获得场址岩体的基本特征数据。他说,这些基础性工作尽管枯燥,但这些第一手数据是最宝贵的,是开展深入分析之前迈不过的重要一环。基于现场的科研数据,陈亮与团队后来提出的花岗岩场址适宜性评价方法发表到了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在地下实验室候选场址适宜性评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亮说,他之前发的所有文章都比不上这一篇,因为这项成果真正助推了国家在这一科研领域的进程。
2016 年8 月,北山团队筹办第六届废物地下处置学术研讨会时,恰巧爆发了连云港事件。提前1 年就已经启动的会议筹备工作要做颠覆性调整,此时距离会议召开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周,为了应对这项突发情况,北山团队几乎调动了全部力量。清华毕业的岩土工程博士张海洋,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因为她刚刚入职一个月,就切身感受到了北山团队中的每个人在困难面前都能勇于承担,出现问题时是互相补位而不是推诿逃避。
研讨会的后半段,第一次来到北山的张海洋,陪同台湾专家代表团一起参观考察了旧井的坑探设施,并在寝车围成的营地上吃了简易午饭。第一次上北山的她,不仅感受到了北山的苍凉和雄浑,更感佩于长期在野外工作的同事们的艰苦。北山对新成员的第一课,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北山精神的构筑
从70 后苏锐、季瑞利,到80 后陈亮、赵星光,再到90 后张海洋,还有很多北山团队的优秀队员,他们的故事,刻画了北山团队中的新鲜血液是如何一点点融入,又一点点渗透,最后也变成了北山精神火种的历史轨迹。
在这中间,北山团队的核心人物王驹,始终起着不可忽视的精神领袖的作用。20 世纪90 年代,王驹把研究方向从核工业前端的地质专业,转向后端废物处置时,特别是1993 年第一次进入北山时,大约并没有想过这条路,他们会走得如此漫长和崎岖。


然而,1964 年出生的王驹身上,除了科研人员的钻研执着,更有中国文人的热情浪漫。他的父亲是历史老师,受父亲影响,王驹热爱中国古代历史。王驹的导师杜乐天,也是中国地质科研领域的先驱,他在开课前,曾用三天时间跟核地研院的研究生漫谈中国文化与治学之道。这些都对王驹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他对北山、对科研的热爱,渗透到了点滴。
30 年来,北山的营地换了许多次,钻孔就打了近100 口,但是每一次在一片戈壁扎下帐篷或寝车,王驹都坚持让大家在驻地先竖起一面国旗。当大家从四面八方的野外回到营地,远远地就能看到红旗招展,仿佛就能读出祖国事业的召唤。
从甘肃肃北县进入北山,无人区之前没有路,北山人来得多了,就趟出了很多条路,王驹用汉朝的历史人物命名这些路:汉武大道、卫青路、霍去病路、李广路……北山人走在这些路上,时刻感受到历史的豪情。
王驹本人的微信名,就叫“北山游侠”。跟他一起参加过培训的中核工程公司董事长徐鹏飞曾聊起王驹:课间他总是热情洋溢地给我们所有同学看北山的照片,在我们眼里看来毫不起眼的北山,在他眼里,有无限魅力!
正是因为王驹对北山的热爱,对他所从事的高放处置事业的执着,影响了北山团队的每一个人,使得北山团队不仅做科研精进,做基础工作踏实,更可贵的是总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岩石力学组的刘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为人幽默,所有的困难让他以诙谐的语言说出来让人感觉不算什么事儿。他的口头禅是“没问题”和“好着嘞”。北山人就是这样:虽然工作繁重,但是能笑着工作。
北山精神向周边辐射
如今正在北山新场施工的三家施工单位,分别是中核集团的四院、七院以及甘肃第一建设公司。在北山已经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三家单位的项目经理脸膛被晒得黑红,但还带着真诚的笑容。他们说,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北山是他们遇到的最苦的工地了。去年带着新招的工人来到北山,有的工人一下火车就跑了,有的到了北山工地看一眼扭头就走。但三位经理却都留了下来,一待就是大半年。冬天的北山气温零下30 度,穿的棉袄都得12 斤重,去年施工队愣是元旦后才回的家。
问及原因,四院项目经理尹力生说,王驹带着他的博士生、研究生在这个地方待了20 多年,我们只是待一两年,又有什么待不下去的呢!七院的项目总监董海增说,我回家会告诉我的女儿,爸爸在做一个特别伟大的工程。
2013 年,美国核学会主席给王驹颁发了一个“感谢状”,感谢他作为第13 届国际高放废物管理大会名誉主席为会议作出的贡献。王驹、陈亮参加了那次国际大会,在会后得到来自国家原子能机构的同行如此评价:
“此次美国之行,深刻体会到了你和亮对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从你们的参会实践,感受到荣誉与尊严,这是以前出国很少体会到的……王博士,中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事业在你的推动下,刚刚拉开了帷幕……期待着你和你的团队尽快有很好的提议……我想只要像你们一样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现在还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是7 年前的信件,但从字里行间,都不难感受到王驹带领的北山团队,带给国际大会的影响力和带给周围人群的精神感染力。
北山团队,用他们30 年的执着科研,正在形成一种精神感召。这感召如同北山的一串火种,一直还在燃烧、传递。
北山人想在北山建一片胡杨林。胡杨属于戈壁,它可以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烂。胡杨是千年万年的坚韧,而北山团队,为了突破高放废物处置这一难题,解决祖国千年万年的高放废物处置难题,其所映射出来的精神,与胡杨有一种高度的契合。
有一天,北山所有为高放废物处置工作过的人,都将拥有自己的一棵胡杨树。它们将站在戈壁上,无惧黄沙与狂风、干旱与孤寂,默默守护着北山的高放事业。

结语
作为北山地下实验室项目的副总指挥,地研院院长李子颖,多年来领导、见证了北山团队在高放废物处置科研领域的艰苦跋涉过程。他说:从1985 年徐国庆研究员提出高放废物处置研究的初步想法,彼时各界对高放废物处置研究的重要性认识非常不足,当年地研院的高放废物处置研究也只能从5000 元起步,到如今项目每年能够争取到上千万元的研究经费,20 多年过去了,高废处置项目从小到大,科研团队也从一两个人,发展到如今拥有50 多人,学科也从地质扩展到岩土工程、环境安全等多个学科。这其中一直贯穿着科研人员对理想的坚守。
“北山团队将承担国家战略研究需求的责任和担当,与自己对科学问题的探索和追求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从事事业的热爱和忠诚,而这热爱给了他们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动力。我想,这就是北山精神——扎根戈壁,团结奉献,争创一流,永久安全。”李子颖说,“北山精神就是新时代的核工业精神在地质科研人身上的具体体现。”

——纪念刘章先生(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