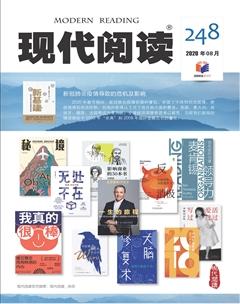祖孙三代66年三战洪水:“守护家园,我们没有退路”
1954年、1998年、2020年,是武汉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大年份”。对于洪山区青菱街菱湖美景社区的祖孙三代周松林、周红胜、周家河来说,也是他们战洪水的日子。
7月14日凌晨,22岁的周家河换上迷彩服,拿着电筒,站上武金堤首次夜巡。夜色如墨,江水滔滔,背水坡上,周家河和4名队友一字排开,5根竹竿向前探出,拨开草丛,仔细寻找堤岸上的渗漏点。
菱湖美景社区居民原住杨林村,那里距离长江1公里左右,地势偏低。从空中俯瞰,杨林村头枕长江,背靠青菱湖,与水有着天然的地理纽带。平日里,长江是温柔的母亲河,滋润着两岸平原;汛期时,它又是狂野的巨兽,等着人们去驯服。
数日前,长江水位高涨,在杨林村村集体企业工作的周家河,接到防汛“招募令”,主动递交了报名表,成为一名参与抗洪的志愿者。上堤时,他没忘父亲周红胜叮嘱的防汛“法宝”:雨靴、竹竿。1998年,周红胜曾亲测“法宝”有效。
1998年,周紅胜第一次发现“坐在堤上就能洗脚”。远处江面上,几艘满载碎石的轮船正在待命,预备随时“破釜沉舟”,紧急填决口。
“保卫大武汉”期间,40多度高温的炙烤下,他一天巡堤超过12个小时,2天后脚丫开始溃烂。巡堤间隙,他还要照料自家被雨水淹没的三口鱼塘,阻止鱼儿逃逸。
数月防汛工作结束后,周红胜给襁褓中的儿子上户口。原本设想叫“周家和”,希望“家和万事兴”,为了纪念抗洪的这段经历,改为“周家河”,意为“保卫家园,守护江河”。“只有保卫好了江河,家才会存在。”
这也是众多青菱居民的夙愿。1998年之前,每逢大汛,大家只能到邻村避灾。
周家河的爷爷周松林,记忆中最大汛情发生在1954年。彼时长江全流域洪水,武汉关水位推上29.73米,至今未被超越。当年武金堤约有现在的一半高,堤上仅能并行两人。洪水一个浪头都能过堤,身后的家园已然没顶。
30万武汉人奔赴一线,与漫天江水殊死搏命。时年18岁的周松林报名成为抢险队员兼潜水队员,与父亲、弟弟一道,并肩抢险。
他们拿起铁锹和扁担,赤足奔走在黄土堤上,抢运麻袋,务必“水高一寸,堤高一尺”。他们潜入浑浊的江水中,一寸寸探摸大堤,查补漏洞。
那段日子,解放军战士的歌声成为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他们上工和轮休下工都会大声唱着军歌,好听。”他清楚记得,那些战士的后背几乎满是脓疱,白白的溃口一片片相连。
日夜驻守4个多月后,周松林荣立抗洪抢险三等功。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很多人永远留在了那一年,成为防洪纪念碑上的一个名字。
66年来,周家从茅草屋搬进了楼房,伴随洪水、内涝威胁,地基陆续垫高了1米多,但他们从未想过远离长江。
平日里,周松林是远近闻名的游泳好手,周红胜把长江当自家“泳池”,周家河从小听着祖辈与长江的故事长大。洪水期间守护长江大堤,是周家流淌在血液里的使命。
去年底,祖孙三代搬进了高楼林立的改造小区。周红胜每天都要拿着望远镜,站在28层的窗边,看江水起落。
这个7月,面对波涛汹涌的万里长江,周家河握住了“接力棒”。“以前父祖保护我们,现在我来保护大家。”他循着祖辈的足迹,再度站上武金堤。
7月14日,周家河向家人讨教防汛经验,三代人想法一致:“守护大堤,就是保卫家园,我们从来就没有退路。”
(摘自《长江日报》 本文作者:杨菁 龙京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