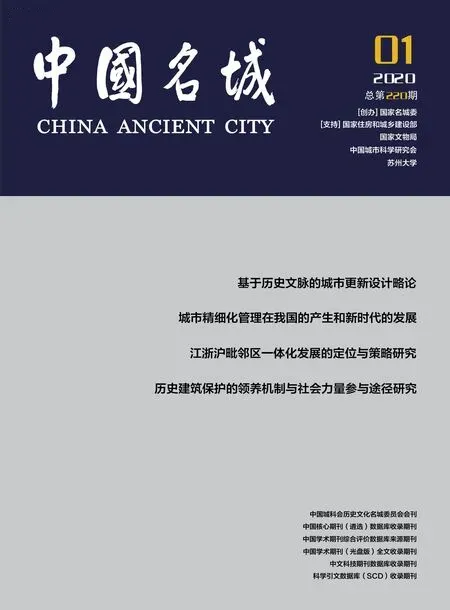传统村落中景观基因的价值与保护*
祁嘉华 靳颖超 张宏臣
导 语
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起始于2012年。截止到2018年12月,住建部公布了第五批评选出来的2666个村子,加上前四批评审出的4153个,全国入围国家级保护名录的村落共有6819个。从最初的给名分,到后来的给资金,再到后来的建立警示和退出机制[1],传统村落保护经历了一个由务虚到务实的过程。在文化旅游产业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传统村落在保护中如何发展的问题依然是一个热点。在工作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村落因为过度旅游开发而变味,出现了只见村落不见传统的现象,很像生物学上所说的“基因变异”。为了保护传统村落原有文化的纯粹性,2016年底,国家七部委制定的《中国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暂行规定》中,明确将出现上述情况的村落予以退出,凸显保护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
基因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认为基因不仅能决定生命的基本性质和形态,还决定着生命的遗传情况。于是,对于一些重要的生命现象,人们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基因的纯粹性。在生物学的视野里,传统村落不只是一个社会单位,更是一个生命的集合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凝结着中华文化的不少优秀品质。村落中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隐含着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也创造出了独特的空间形态,并以景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依照这样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村落,大到村落的周边环境,一家一户的院落布局,小到建筑装饰和生活习俗,都隐含着居住者对当地自然和历史的理解和适应,折射出村落存在的生命品质。于是,借助生命科学的原理来研究传统村落保护,对于我们准确理解村落中的核心价值,并对这些价值进行活态传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 生命基因的启示
基因遗传规律发现于上个世纪中期的西方。中国民间虽然没有这个词,但早就知道父母双方诸如高矮、肤色、体魄、甚至性格等特征都会传递给下一代,而是“混血儿”,则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血缘遗传的结果。基因遗传规律是经过长达八年的豌豆培育发现的,奥地利人格里高利•孟德尔把开红色花的豌豆和开白色花的豌豆进行杂交,得到的结果不是介于红色和白色之间的粉色花,而是全部开出了红色花。孟德尔发现,如果把开红色花的豌豆后代再相互杂交,其后代中又重新出现了红白两种颜色的花朵。这一实验说明,决定豌豆花色的不是两种要素的混合,就像红墨水和蓝墨水倒在一起混合成紫色那样,而是不同“因子”(也译为基因)的作用。至此,在民间久有流传的“遗传”之说终于得到了科学证明。后来,孟德尔把这一发现以《植物杂交实验》[2]之名进行了发表,成为遗传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孟德尔的伟大体现在对生命遗传现象的关注,开启了基因研究的先河;同时,孟德尔的伟大也体现在对遗传规律的揭示上,它对我们理解生命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基因组合是生命延续的根本。一般而言,只有同质量的基因组合才可能形成新的生命体,质量不同的基因即使结合,也不可能生成新的生命。比如,孟德尔的基因实验始终围绕豌豆进行,不管是高大型还是矮小型,开白花还是开红花,结合到一起的基因始终来自豌豆,如果是拿豌豆与茄子结合,两者的生命也会因为基因的风马牛不相及而终结。
其次,基因的多样性决定了生命的多样性,也决定着生命体的外在形态和寿命长短。在生命繁衍中,基因也因先天或后天的影响出现进化或者变异,或者进化出更加优良的品质,或者变异出各种疾病。不过,不管是进化还是变异,最终都会遗传给下一代。可见,基因的科学配置是保障一类生命体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手段。避免近亲繁殖,讲究门当户对等等习俗,都是人类为获得良好基因的纯粹性而采取的措施,是保障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有效经验。
再次,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基因复制,从而保持遗传基因与原基因的相同性,并且衍生出更多的生命体。《西游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孙悟空在紧要关头能拔出一根猴毛变出一群猴子。其实,基因复制技术已经可以将这样的神话变成现实。从理论上讲,猴毛含有的DNA完全可以进行复制。克隆技术对保护物种,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来讲是一个福音,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克隆技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基因与农村之间具有某种特别的关系。发明者孟德尔是从奥地利的一个叫海因策道夫的普通农村走出来的,是地道的“农村娃”;变幻莫测的基因遗传规律是他在乡村一次次的豌豆种植过程中发现的。若干看似偶然的现象,恰恰给孟德尔研究发现基因活动规律提供了条件,不仅使这位“农村娃”成为“现代遗传学之父”,也将基因科学与农村结合起来,给我们运用基因科学的基本原理,研究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2 传统村落的生命转换
当然,用生物学的基因理论来研究传统村落保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基因理论属于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传统村落是历史的遗存,属于一种古老的人居空间;传统村落保护属于一种国家政策,提供的保护思想中并不涉及生物学。这样看来,基因理论、传统村落、传统村落保护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其次,由于所属学科不同,三者之间所运用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甚至思维方式都会有很大不同,很难在传统村落保护上融会结合。也就是说,由于是跨学科,从基因理论来研究传统村落保护所产生的难度,显然要远远大于从空间角度展开的研究。不过,由于研究角度的独到,得出的结果也会别有意义,不同凡响。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在生命科学与传统村落之间找到连接点。
与西方建立在航海与狩猎基础上的外向型文化不同,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则主要是在内陆环境下形成的。 航海的目的地与狩猎目标,都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能否到达目的地或获取到猎物,取决于对客观对象的准确捕捉,需要通过精准的认定与分析来克服重重困难。与此不同,适宜的内陆气候与肥沃的土壤条件,使中华民族的衣食之需都可以在自然中得到满足。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熟悉与适应。[3]不同的生存理念,不仅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到人们的理论与实践,也就是说,即使是从事同样的活动,设计相同的产品,也会体现出迥异的风格和追求。以经典建筑为例,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建筑是教堂,那拔地而起的尖顶直指苍穹,大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架势;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建筑是宫殿,偌大的屋顶向下延伸,左右张开,犹如俯向大地的双臂。从功能上看,两种建筑的屋顶都具有很好的排水性;从技术上看,两种建筑的屋顶都是整个建筑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从花费上看,两种建筑的屋顶造价都几乎要占到整座建筑的一半……也就是说,避开建筑形态,从功能、技术和造价上看,我们几乎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差异。
其实,教堂和宫殿最为重要的差异还是集中在文化上。教堂是神灵的化身,宫殿是权力的体现。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便有更深的发现:神灵和权力都有至高无尚的一面,但是,神灵居住在彼岸世界,权力则是身边的事情。走向神灵需要离开原点,超越自我;拥有权力则需要拥有实力,完善自我。这样的指向,形成了西方喜欢解析问题的思维习惯,追求一种向理想进发的精神状态,而中华祖先“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喜欢保持一种与自然万物和平共处的生存心态。于是,依照西方的思维传统,认定基因理论与传统村落是属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分属于两个学科门类,很难相提并论,而按照中国的思维传统,基因理论与传统村落虽然有着不同的属性和形态,但可以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关照下获得有机统一,殊途而同归。在这样的思维视域下,传统村落既是一种空间存在,也是一种生命存在,各种村落景观要素便折射出古老的生活方式,具有了文化意义。当我们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审视村落——村落里的山水环境、街道布局、建筑样态、装饰美化时,便会发现,它们既是一种景观,同时也是村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体现,更是村民当初选址建村、起土造房、营造环境、民风民俗等等生命活动的一种物质呈现。
经过这样的转换,传统村落中的各种景观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存在,它们还因为承载了前人的生活观念、风俗习惯、审美爱好等等精神要素而具有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节点都印刻着前人的生产和生活烙印,成为不同形态的文化符号,像基因那样起着“记录和传递生命信息”[4]的作用。
与生命的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不同,传统村落的基因则只能转化为文化要素,并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来呈现。这些要素与村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在年深日久中成为村落中的文化景观。那么,传统村落的大小景观中可能蕴含哪些文化基因,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呢 ?
首先,传统村落蕴含着历史信息方面的基因,是特定时期百姓生存方式的空间体现。这里所说的“历史信息”,包括村落中前人留下的一切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老物件,以及街道、房屋、码头、桥梁、牌楼、围墙、水井、田地、拴马桩等等人造的东西,也包括古树、河流、山体、巨石、旷野、沙漠等自然景观。人造物的历史性主要通过造型、材质、工艺、用途等来体现,折射出当年村民对自然的态度和生活水平;自然形成的东西虽然没有直接打上人的烙印,也是村民当年根据生产和生活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其中包含着“我看江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词《贺新郎》)的某种默契,属于间接被人化的结果。
在现代化无处不在的今天,这些人造的老物件显然已失去了实用性,却是一个时期百姓生存方式的最好证明;那些纯自然的东西显然不具备规划设计后的靓丽规整,却很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百姓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水平,可折射出村民们历史上曾经的生存能力。而正是这些带有本源性的历史文化基因,构成了传统村落中的各种空间景观。
其次,传统村落承载着营造观念方面的基因,是特定地区人们营造水平的经典展现。建筑在任何环境中都是最显眼的景观,体量大,工艺繁,用途多。需要说明的是,“营造”属于中国传统建造活动的总称,在过去,所有土木工程都可以称之为营造;“技艺”则是一个广义词,贯穿在所有加工制造的过程中。与现代建筑的机械化生产不同,传统村落中的建筑从选址到选材,从尺度的确定到房屋的朝向,从砖石垒砌到大小木作,每一步都是纯粹的手工制作,体现着一个地区百姓的建造水平,也很能体现当地人某个时期的营造观念。比如说,在中原文化核心区的传统村落中,祠堂、庙宇、戏楼等公共建筑,一般会建在村落的核心位置,方位朝向、选材用料、建造工艺也最为讲究,体现出这里人们对祖先的重视。处在历史边关、多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村落,往往要选择险要之处,周边有高高的围墙作为屏障,体现出当地百姓对安全的期盼。建在边远山区的传统村落,往往背山而建、临水而居,体现出务实方便、随性不羁的营造取向,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的家园,在选址、尺度、工艺上占尽优势,丝毫也不掩饰与众乡亲的不同,体现出当年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对权贵的畏惧……
村落中的任何营造活动都会受到观念的影响,在折射出当地百姓对社会与自然理解的同时,也印刻着人们之所以这样营造的心路历程。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从村落遗存的各种建筑景观中,领悟出这里的人们曾经敬畏过什么,喜爱过什么,有过怎样的信仰和追求。
再次,传统村落凝聚着生存智慧的基因,是特定人群认识和利用自然的经验结晶。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事情同样会出现在传统村落。目前存留下来的传统村落多有百年以上历史,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的摧枯拉朽,战争匪患的血雨腥风,社会变革的除旧迎新……都会给这些村落以巨大的影响,或者毁灭,或者淘汰,或者面目全非,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村落躲过了无数劫难,步履维艰地走到了今天呢?从村落的某个方面发现些端倪,得出环境隐蔽易于躲避战乱、选材精良适合当地水土、工艺讲究建造结实等等答案,也确实可以将这些视为村落历经风雨而不灭的原因。这些村落都是按照传统理念营造的,其中隐含着中华祖先在年深日久积累的生存智慧。表面上看,这些智慧与技术无关,而实际上却给村落带来了巨大的实惠。比如选址,大凡能留存下来的村落多处在“后有靠,前有绕”“左青龙,右白虎”[5]的环境之中。这样的选择确实找不出多少技术方面的理由,却为村落巧妙地解决了诸如抵御寒风、用水方便、美化村庄环境等实际问题,不仅有效地提升了村落空间环境的安全性与舒适度,还大大降低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成本。
在实际勘察中,我们看到许多出类拔萃的传统村落。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村落在建造和设施上确实没有多少科技含量,但是,真正走进村子,走进一家一户,亲身感受那井然有序的空间布局,细致入微的功能设计,尤其是冬暖夏凉的居住效果,我们不能不佩服前人营造之精心,尤其是尽量少消耗能源而借助自然之力的巧思妙想,对前人凭借自然循环规律安排生产生活的聪明而敬佩,也让我们悟出了这些村落所以能生生不息走到今天的某些必然。
经过这样的转换,在审视传统村落的时候,不只仅仅是那些古色古香的外表,还要去寻找其中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营造理念和生存智慧。于是,那些老物件、老房子以及凝聚着聪明才智的各种景观,就成为一种带有生命属性的历史存在 。也就是说 ,传统村落中但凡能够承载历史信息、营造理念和生存智慧的大小空间形态,都可以视为留有传统文化基因的景观。
3 文化景观的生命价值体现
与只有借助仪器才可能发现生命基因的存在一样,发现传统村落景观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同样也要借助多学科的知识。以村落中大量存在的老房子为例,要想知道其中的历史价值,我们不仅要懂得历史,还要懂得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以及所达到的水平,以确定这些老房子的历史价值;要想知道其中的营造理念,我们不仅要对当地的乡土建筑特点有所了解,还要懂得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以体会这些营造理念的合理性。而要想深入体会房屋中的营造智慧,我们不仅要懂得当地百姓的民风民俗,还要尽力寻找到这种民风民俗在顺应自然中所获得的奇妙效果,发现其中科学与文化的精义。
经过多学科的介于入,我们才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局限,对传统村落中某个特定的景观形成多角度关照,站在当时人们的立场上去体会他们是怎样认识外在世界,处理生存与发展关系,从而发现这些景观中的生命价值。
3.1 对大自然的务实态度
自然山水是村落中最大的景观,有自然天成的一面,也有人为选择加工的成分。与现代人对自然山水的欣赏态度不同,古人所以选择在某个地方建村,往往对自然山水有着更加实际的考虑。比如之所以喜欢依山建村,是因为山可以对气流形成遮挡,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在给人安全感的同时,也可以阻挡冬日严寒;之所以喜欢在植被茂盛的地方建村,是因为植被丰富与否,直接关系到有利于人们生活的自然资源的多寡;之所以喜欢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建村,是因为山是依靠,水是滋润,山水相依才最适于休养生息。也就是说,传统村落的先民们当年并不是把自然山水作为观赏对象,而是把它们作为长久生存的物质依靠,它不仅关系到日常生活的方便与否,也关系到周边四邻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子孙后代是否能衣食无忧地生活下去。
与现代人从村落的山水景观中看到“诗和远方”不同,传统村落的先民们更是在给自己和子孙后代选择安身立命的场所。当然,在真正受到大自然带来的实惠后,村民们会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一些精神上的依赖,形成丰富多样的信仰和民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就将山、水、树木作为图腾顶礼膜拜;汉民族的村落中,几乎家家院落里都有供奉土地神的龛位,尤其是在婚丧嫁娶的重要时刻,至今还把“拜天地”“敬土神”作为重要的仪式……这里当然包含着村民们对大自然的感恩,更有一种敬仰态度,这充分体现出漫长农业时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的古老哲学思想。
3.2 无处不在的秩序讲究
传统村落所以能够长久地留存,说明这里的生活不仅自给自足,而且井然有序。与现代人习惯跟着感觉走不同,古人安排生活内容往往更加看重自然节律和历史传统。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不仅是村落安排生产活动的节律,也是人们安排日常生活的依据。具体而言,春天万物复苏,既是春耕大忙季节,也是喜结连理最佳的时候;仲夏北方有麦收,南方有插秧,同时也是瓜果蔬菜生长旺盛的时候;秋天金色的庄稼,累累的硕果,收获的喜悦使人们很少待在家里;冬天果实入仓,牲畜入圈,回家过年也成了人们的最大愿望。在遵循自然秩序的同时,传统村落还十分重视人伦礼常,营造体现礼仪规矩的景观,以求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引导作用。比如宗祠,既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也是家族共商大事、扬善抑恶、弘扬祖训的之地,更能彰显一个宗族的兴衰状况;而庭院匾额,虽三四个字,便能简明扼要显示出一户人家的门第层次、道德修养、处世哲学、生活理想,常见的“太史第”“孝悌慈”“耕读传家”“大岳屏藩”等等,是一个家庭精神追求的集中表现。其实,仔细观察村落中的院落布局,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规矩的重视,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四面围合的院落中,最好的位置、最大的房屋,肯定是长辈的住所,小辈的住所分布两侧,体量也要小些,将家庭秩序与友善亲和有机地统一成一体。
3.3 有序的生活都离不开规矩
与现代社会带有强制性的法规制度不同,传统村落中所体现的规矩并没有特别强调,但又无处不在,告诉你是否遵循这些规矩所产生后果的巨大差异——是否按照时令进行耕作,很快会体现在秋后的收成上,影响来年的生活水平;祠堂的大小,匾额的内容,院落的布局,不仅会体现出家族的兴衰状况,还会关系到一家一户在村落中的实际地位。因此,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人们会自绝地按照自然秩序和民俗习惯安排生产和生活,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避免稍有不慎可能带来的“报应”。与条文性的法规制度不同,传统村落中的生活秩序是人们在遵循自然规律和家族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并通过自然或人工的景观来表现,让人们在日常的劳作中都可以有所体察,有所领悟。
3.4 追求自然的审美情趣
审美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却是决定一件事物能否保存并留传于世的重要条件——谁也不愿意将丑陋的东西传给子孙后代。也就是说,当年人们未必是为了美而建造村落,但是,能够历经风雨存留到今天的传统村落肯定留存着大量美的信息,并以景观的形式呈现,告诉我们当年人们对美的种种理解。从村域空间上看,传统村落中民居的高度均没有太大的差异,偶尔出现的牌楼、祠堂、风水塔等高大建筑都属于公共建筑,反映出当年人们营造村庄时的环境观念:民居建筑追求平等,公共建筑突出规格,使村落的整体空间在自然中呈现出主次。从建筑布局上看,传统村落由一个个院落组合而成,并不杂乱,院门与院门相对的地方距离较大,形成街道;院子侧墙与侧墙之间则比较紧窄,形成巷道,从而使村落的街巷布局井然有序。从色彩上看,江南水乡粉墙黛瓦,中原地区夯土瓦屋,云贵地区的石墙草顶,黄土高原的土色窑洞,等等,它们构成了各地村落的主色调和天际线,在高天厚土的掩映下产生了生动的画面感。从装饰上看,木砖石雕往往是传统村落中最为精彩也最具美感的所在。木雕一般出现在大小木作上,大木作是指木构架建筑的承重部分,尤其是建筑正立面的梁柱,往往是木雕装饰的重点,最为常见的雀替造型就有回纹、鱼形、骑马、葫芦纹等等十几种之多;小木作制作包括门、窗、隔断、栏杆、外檐装饰、地板、天花、楼梯、龛橱、篱墙、井亭等,工艺更加精细。砖雕大量出现在屋顶、墙面、墀头和照壁上,是房屋主体最为醒目的装饰。石雕多出现在柱础、护栏、护墙、门鼓石等部位,集装饰和加固于一体。三种雕饰大多保持原材料的本色,表面看并不张扬,但工艺却十分细腻讲究,圆雕、浮雕、透雕、隐雕、多层雕等等不一而足,从而使每一个部件都极具艺术气息[7]。
不难看出,传统村落中的空间营造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有着明确主题,从而在整个村落上空形成了主次分明的天际线。传统村落中的民居建设也很有人情味道,道路的宽窄按照人流量安排,形成了动静有序的大格局。传统村落并没有忘记色彩的重要,在自然山水的底色上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效果。装饰是传统村落的点睛之笔,也最能证明原住民当年的审美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环环相扣,从上下左右构成一个浑然融合的整体,水乳交融地统一在村落空间里,形成氛围,构成村落独有的风貌。
综上所述,从生命的角度观照传统村落,我们得到的就不只是一些“小桥流水人家”的外在体现,还有形成这些外在客体的内在原因;不只是“绿树村边合”的自然景观,还有形成自然环境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切折射出来的,恰恰是历史上村民们对大自然的务实态度、对生活秩序的渴望以及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审美情趣。
4 景观基因的保护
古人早就有“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8]的总结。然而,在经济至上的社会环境,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往往把满足欲望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而将这种欲望可能给天地(环境)带来的影响置之不顾。这是今天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所以重视传统村落研究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村落中还比较完好地保存着“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大格局,它对天地人之间微妙的生养关系给予了定格与展示。
在这样的语境中研究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其根本的目的是将村落视为一种古老的生命存在形态,发现村落各种景观中的核心价值,进而制定出既可以使村落保持天生地养状态的方案,也可以使古朴的村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1 依照生命只有在相同基因组合中延续的原理,在保护中尽量遵守与村落原有生态相匹配的原则
要在村域环境整治上保持原生态,不仅新增添的植被要与村落原有的环境相匹配,新增加的如道路、卫生、电力、服务等设施,其造型、色彩、材料、摆放位置,也要尽量与村落原有风貌相匹配,使这些景观成为村域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村内老建筑维护上保持原生态,不仅所用材料要尽量与原材料一致,而且加工工艺、尺寸大小、数量增减等环节要有严格的遵守,不能随心所欲地改扩建。需要强调的是,当今对危老房屋主体和屋面进行加固,最常用的是钢筋水泥或金属构件,为了避免与老房子的原有风貌发生冲突,进行上述施工时要尽量采取一定的隐蔽措施,避免钢筋水泥或金属构件的外露。为了给村落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保护过程中要适当增加一些新业态,这样既可以给村落带来活力,也有助于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不过,新业态一定要与村落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联系,使之深深地扎根于村庄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村民生活的组成部分。
村落保护中最难处理的是新与旧的关系,新材料、新技术、新业态的进入可以极大地提升村落的质量,但是,也会使原本已经很脆弱的村落脱胎换骨,发生质变。因而,依照相同基因组合才可以使生命得以延续的原理,要强调村落保护过程中在环境整治、建筑维护、业态设计等环节上保持原生性,也就是确保村落原有文化基因不发生蜕变。从近年来的保护实践看,那些在传统村落中开设“咖啡屋”“酒吧”“歌厅”等做法,由于与村落原有的文化基因没有任何关联,无异于给村落移植了并不匹配的新基因,虽然因新鲜而可能产生一时效果,却因为不接地气而很难长久地持续下去。
4.2 为了保障重要生命体的健康成长,必须坚持基因配置的科学性
在生命科学的语境中,能够“健康成长”的往往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所谓“科学的基因配置”,一般是指为了保障生命体健康成长而采取的符合生命规律的人为干预。这样的理念对于传统村落保护具有极大的启发性。经过严格评审入围国家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无疑是众多村落中的佼佼者,既在某个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也因凝聚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而显得珍贵,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品种”。然而,现有的评审和保护工作主要针对的是村落风貌、古建筑数量、历史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几个方面,缺少村落文化特色方面的指标。这导致了传统村落评审过程中只注重村落外观,尤其是古建数量多少,而直接导致了村落保护过程中以外观修缮好坏作为评价标准的情况。这种只重其形、不重其神的做法被专家指责为只做“表面文章”,反映出对传统村落价值研究的轻视。近些年传统村落中之所以出现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的问题,说到底是因为主持村落保护工作的人,对村落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把握不准。每当面对多种选择时,由于没有“主心骨”,在多种文化信息、多种价值取向、多种可能性存在与交集时,很难做到心中有乾坤,手里有规矩,保障村落固有的文化基因不受到冲击,不发生变异。
这样的坚守是保住村落景观独有魅力的根本,也是保住村落文化竞争力的根本。探寻国内外著名村落保护案例,都会发现一些代表性的景观,因为表现出某种纯正性的文化基因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日本岐阜县白川村虽寒冷而偏僻,却因为拥有“极端合理的传统庶民建筑”合掌房而闻名于世;奥地利哈尔斯塔特村位于哈尔斯塔特湖与达赫斯坦山脉之间,两千多年的历史和如画的风景使这个小山村名声远播;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西递宏村,其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大观园,使得遐迩皆知……这些村落所以闻名天下,固然离不开当地优美独到的自然环境,但更与各自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有关,以及当地人强的村落维护意识。可以肯定,历史上这些村落曾经有过无数次的修缮和改造,但是,不管怎么修,怎么改,“合掌屋”和“马头墙”的形制没有变,古老的村落格局没有变,悠然自乐的生活方式没有变。以往我们常用“修旧如旧”来解释这种情况,外观形式的古色古香确实也是这些村落的价值所在,然而如果运用生命科学的观点来审视,我们则可以透过现象发现本质:那些成为村落标志性的景观,其独特的造型所以长久留存,正是因为契合了当地气候,满足了当地人的某种生存需要,于是才可能在年深日久中固定下来,具有了文化属性,成为生生不息的生命基因。这些地道而纯正的景观,无疑是村落最值得保护的所在,也是这些村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理由。
4.3 像基因复制那样对待村落更新,使新景观保持原有的文化品质
在研究传统村落保护时,村落更新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社会发展会对村落产生影响,村民对新生活的渴望也会给村落发展提供动力,并最终造成村落空间上的变化。可以肯定,那些完好保存下来的村落,历史上都曾经因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地位升迁等原因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改扩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现在的问题是,以往的改扩建,村民们遵循的是老传统,使用的是老材料,选择的是老工艺,建造出来的空间并不会发生质的变化。然而现在的改扩建,村民们遵循新的时尚,使用新的材料,选择新的工艺,建造出来的空间很可能会与传统风马牛不相及。加之传统村落中的房屋属于私产,怎样改扩建完全由村民自己说了算,当地政府无权干涉。这是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遇到的又一难题,而且带有普遍性。
其实,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依据村落传统风貌,制作具有仿古效果的建筑材料并不是难事。除了砖木等大料外,像仿古的门窗、瓦件、装饰等等都可以量身定做,批量生产。在村落修缮和改扩建过程中巧妙地使用这些材料,既可以满足村民实用方面的需要,又可以与村落传统的空间和谐统一,犹如基因复制那样完成村落的改扩建。这里关键是要提高村民保护传统风貌的意识,让村民知道,正是因为传统风貌的整体完好,才使自己的家园以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进入了国家保护名录,为提升村落的社会声誉,改善生活水平提供了可能。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除了当地政府要制定相应政策,还需要具有古建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帮助村民在改扩建中准确把握自家环境的文化特色。
在生命科学的语境中,传统村落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空间形态,还是一种悠久的时间记忆,这里的每一个景观都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反映着不同时期人们的生命状态。保护传统村落中的文化景观,说到底是对农耕时代某种生活遗存的保护,跟其他历史文物的保护并无二致。加强村落原生态文化的挖掘,是为了延续村落在千百年中形成的文化根脉;坚持文化基因的纯正性,是为了保持村落的核心价值,凸显其魅力;像基因复制那样对待村落更新,是为了拓展村落的使用价值,满足村民的生活需要,最终达到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的双赢。
5 结 语
在生命科学的视野下,传统村落不再只是一个古老的环境空间,而是一种悠久的生命存在。这里所有的景观因为凝聚着优秀的文化基因而获得超长的生命力,所以也显得越发珍贵。这些基因决定着村落的基本性质和形态,还决定着村落的未来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传统村落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多种选择,是以随行就市的态度肆意改造,还是以科学的态度保护其“基因”的纯正性,考验着我们对村落的认识水平,也考验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通过村落的风貌格局、古建老屋、生产方式、民风民俗等要素,研究其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在传统村落下一步保护工作中追求文化的原生性,体现文化传承的科学性,达到新旧文化要素的有机更新,是传统村落保护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这代人将传统村落原汁原味留给后人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