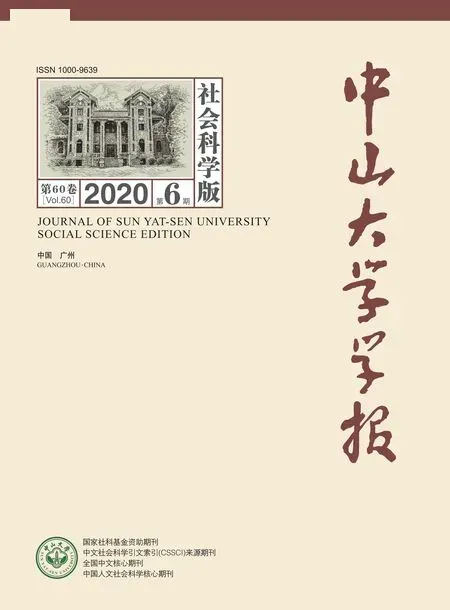城市变革、边缘社群与地方社会*
——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进路
黄晓星
中国社会学形成和发展之初受西方社会学影响,也有本土的思想渊源(刘少杰,2009)。在引入及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学蕴含着较强的价值诉求,如民族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等(刘少杰,2006)。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对社会学史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陈树德,1991;韩明谟,1992;景天魁,2017;林闽钢和李保军,1999;刘祥和周慧,2013;阎,1990;应星等,2006;周晓虹,2012)。社会学从引入中国开始就带着经世救国的应用导向(韩明谟,1986),以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寻找社会出路为目标。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学史的关注从大处着眼,如中国社会学史的阶段划分(陈树德,1993;韩明谟,1986;韩明谟,1991;郑杭生,1999),或者对重点历史阶段、标志性学者及研究的回溯(陈新华,2003;刘祥和周慧,2013;马戎,2012;孙庆忠,2012;王炳根,2014;周晓虹,2012)。社会学史的书写更多像大传统的写作,即对中国整体社会学发展的素描,是对“国家”的关注与分析。近期的社会学史研究在宏大的进程中也关注影响中国社会学进程的大事件,如燕京学派、乡村建设运动等。
本文力图转换视角,以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学发展,尤其是岭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为研究文本,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讨论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的价值关怀与地方视角。华南地区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展现了“中心”与“周边”的时空转换(麻国庆,2006)。在区域上来说,岭南区域处于国家中心的边陲位置,其社会学的发展受到全国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如社区研究;但相对于华南其他区域以及东南亚来说,岭南地区又属于“中心”,尤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经商口岸,并且在清末、民国时期广州在政治上亦具有重要的位置。岭南地区社会学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断裂及转型(城市与农村,抗战与稳定),也反映了岭南地区作为地方社会的逐步解体。在该情境下,社会学的发展以边缘社群为主要研究对象,切换研究的视角,呈现出与全国社会学不一样的特征,生产出社会学的地方知识,同时也丰富补充了全国的社会学研究。岭南地区的社会调查开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涉及内容包括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劳工群体、特定村落等等,截止到1950年,包括调查报告与论文成果共有80份左右①根据《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经济政治学报》等过刊及校史资料整理。。本文选取1930—1950年代由岭南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师生完成的部分调查报告和毕业论文作为分析文本,讲述社会学的地方叙事,以作为中国社会学史宏大叙事过程中的补充。
一、知识脉络:中国社会学与岭南社会基础
知识和思想的发展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总体状况相关联(罗伯特·K·默顿,2006)。岭南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两个重要基础:其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燕京学派、综合学派、乡建学派等的发展;其二,岭南地区本身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当时广东在全国发展中的位置、岭南的文化基础。
(一)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下的社会学发展
1949年前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时代,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实现中西双方的并轨发展(赵旭东,2017)。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发端于制度结构急剧转型的时期,旧的制度结构迅速破坏,原先一体化的乡村结构迅速解体,中国不得不打开国门,进入世界格局。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带有较强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引入西方社会学的观点以期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学以“群学”之名从西方引入,从甲午海战清王朝战败开始。康有为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从事社会学教学的学者,首先提出“群学”一词,并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设置“群学”科目,将“群学”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韩明谟,1986)。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将其界定为“合群立会”(刘祥和周慧,2013),而非所引入的社会学概念。相对有共识的是,严复1895年首次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学说,作为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开始(阎,1990)。清末的社会学引入是一种功能性的引入,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在于如何回应社会问题、建立新的社会结构,如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的兴起是一种政治,1918年陶孟和在《新青年》发表的《社会调查导言》像是一篇社会调查的政治宣言,给社会调查注入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特征,强调对传统的批判与倾听民众的声音,而后李景汉、吴景超等学者期图使用社会调查认识中国、建设中国(何祎金,2018)。
社会学的课程设置从清朝政府创立的京师政法学堂、京师大学堂等已经开始;到了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任第一任校长,文科中均设有社会学课程(韩明谟,1996)。在后续的社会学发展中,燕京学派成为重要的支柱,尤其是在1930年代之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倡导的社区研究(侯俊丹,2018)。在1920年代,燕大已经开始了社会调查,采用问题表的调查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朱浒和赵丽,2006)。早期燕京大学的社会调查也蕴含着由传统调查向吸收人文生态学中有关生态组织化分析方式的转变,如甘博和步济时的北京调查、李景汉对平郊家庭手工业发展的调查等(侯俊丹,2018)。吴文藻于1935年发表了《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提出“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通过社区来研究中国,具有极为鲜明的功能学派和人文区位学色彩(吴文藻,1935)。吴文藻还邀请派克、布朗两位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以及将学生送往国外留学,培养了一批知名的社会学家,如费孝通、李安宅等人。在吴文藻等人大力倡导下,社区研究成为1930年代社会学的主流范式。燕京学派的诸多学者大多有海外的学习经历,西方社会学的引入与对中国经验的分析,这也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站在一个前沿的高位上,如《江村经济》采用了与国际社会学界一脉相承的社会现象描述逻辑、竞争冲击分析逻辑、均衡功能分析逻辑、因果关系分析逻辑、制度条件分析逻辑等研究方法(张静,2017)。
1930年代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另外一个重要枝干,它希望以农村复兴的农村改良运动来取代农村土地革命(韩明谟,1996)。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1933年7月晏阳初在山东邹平召开的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做报告,指出农村建设四大问题为愚、贫、弱、私,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需要从事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解决农村问题需依靠乡村自身力量(晏阳初,2010)。梁漱溟与晏阳初同样将乡村问题的解决诉诸社会的力量,强调社会自身的改善以及问题的解决。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从政治入手,目标在于解决政治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应坚定社会运动的立场(何建华,2007)。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步走的方式探讨中国民族的前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梁漱溟,2005)。
如果说燕京学派是从社区出发去认识中国,那么乡建学派则更强调将外在的结构断裂作为乡村建设的前提,结构与功能、区位与文化等的分析是共同的特征。梁漱溟分析乡村建设运动原因时,重点强调乡村的破坏,以及在此背景下乡村自救的运动以及重建新社会构造的要求(梁漱溟,2005)。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社会结构处于断裂的状态之中,“愚、贫、弱、私”等问题只是社会秩序崩溃的体现。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下,民国时期的社会学是一种“拯救中国之学”(韩明谟,1986),如孙本文强调社会学报国为民、追求社会进步的精神(孙本文,2011)、言心哲对现代社会事业的探讨(言心哲,2012)等。
在赵承信的《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中,赵氏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分为文化学派(综合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两大主流(赵承信,1948)。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重要学派,是学院派社会学的主流学派(郑杭生和李迎生,2000)。孙本文是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对1920—195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孙氏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社会学著作近20部,对社会学理论体系做了较多探索,从社会学研究问题(社会行为)到社会问题都有详尽的研究(郑杭生和李迎生,2000)。综合学派和前述燕京学派、乡建学派都是中国本土化的努力,吴文藻等人的目的在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孙本文等学院社会学家则着力于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周晓虹,2012)。综合学派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正宗”,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极大问题,如对社会主义思想、唯物史观的排斥,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忽视对中国的实地调查等(郑杭生和李迎生,2000)。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各派社会学家不同的看法,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许德珩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学者(郑杭生和李迎生,2000)。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为己任,如毛泽东对旧社会结构采取阶级分析,对中国的革命方向进行分析。
(二)岭南社会学的发端与发展
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构成了岭南社会学发展的情境,后者虽然包含于前者,但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岭南社会学的发展更基于岭南地区当时的社会情境,强调城市变革中不同社群的生存状态,尤其是边缘社群的生存状态,并且力图为边缘社群发声。
从社会学的设置上看,1920年代有1所学校创立社会学系,1930年代有2所,1940年代有5所,学生在校人数也逐年递增(李文波,1994)。由于北方长期军阀割据、战乱,岭南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1928—1937)给社会学者提供了持续积累的优势,尤其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岭南社会学迎来较大的发展。从黄文山、周谷城、言心哲等部分教授的履历可见,这段时期除了原有的教授之外,不同的社会学者从北方高校流动到南方,推动了岭南地区的社会学发展。
教授的流动使岭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融为一体,但更能体现岭南社会学传统和特色的是长期任教的教授,如伍锐麟、陈序经、岑家梧及1940年代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杨庆堃等多位教授。他们研究的本土化程度非常高,同时国际化程度也较高,如陈序经、伍锐麟的疍民研究,杨庆堃后来围绕鹭江村的著名研究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力(Yang,1959)。从结构特征上看,广州是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同时,在1930年代中期以前,广州相对于北方来说远离军阀战乱等。这些社会结构特征使社会学者能够持续地进行经验研究,岭南地区的社会学者对当时岭南区域不同的边缘社群进行了深度调研,反映了这些社群在结构变动情境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其所联结的地方社会基础。由于结构变动的滞后性,这些研究也力图对地方社会结构进行干预,而从改变稳定的结构入手,寻找社会变革之道。

表1 部分教师履历体现出民国时期社会学者的流动(尤其是1927—1937年北方向南方流动)
二、结构断裂与社区转型:岭南地区的边缘社区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岭南地区虽然未处于战乱,但也面临着区域城市变革和旧社会结构解体的双重影响,城乡结构的解体导致城市和城郊的急剧变迁,传统社会的宗族礼教习俗等在努力维持的同时,也被逐步打破,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结构解体的滞后性,边缘社群的道德基础相对稳定,维系着原有的秩序。
(一)城市边郊农村:旧凤凰村、下渡村与鹭江村等
岭南地区的底层社区研究包括了两个不同阶段,其一是伍锐麟在岭南社会研究所所完成的旧凤凰村、下渡村等调查;第二阶段当属20世纪40年代杨庆堃所主导的鹭江村研究。前者受芝加哥学派影响更大,强调经验导向;后者则引入了系统的社区研究范式,形成了对鹭江社区等的不同功能结构的剖析。
1930年代,社区研究成为了解民族兴亡之所系的课题,这也反映在岭南地区的社区调研中。这些调研将乡村的溃败归结于大结构的战乱、国外列强的入侵,同时也将城郊村落置于城乡结构的变革中来对待。如伍锐麟在下渡村研究的序言中提及:“但自鸦片之役后,帝国主义者藉其资本势力,吮吸我脂膏,荼毒我民族……农村衰落,不仅是农民本身厉害问题,实是整个民族兴亡之所系。”(伍锐麟,2005A)1938年,区阃奇的《下渡村调查》也提到:“中国农民受这种蹂躏,农作技术无从改良,农业经济无从发展,农村社会渐形衰落,农业经济破产,因而牵动到中国整个社会之不安,到了现在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区阃奇,1938)
同时,也将城乡结构变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影响变量,如1935年对于旧凤凰村的特点的概括,主要有人口的外流与减少、经济方面以商业和雇工收入为主,“凤凰村是由农村社会而变为城市化了,即是说此村已成为广州市的附属无疑……农村破产可见一斑”(伍锐麟和黄恩怜,2005);又如下渡村的报告中:“下渡已不是纯粹的农村,大概是接近广州市,受各种影响而起变化。我国工商业日趋发达,都市亦一天天地发展。”(伍锐麟,2005A)报告充分反映了伍锐麟等人对于该社区生存状态的担忧,农村的破产导致凤凰村的村民生活无依,没有出路,而村民大多进广州城做佣工,生活较为困难。报告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当时贫苦原因的看法,如底层农民不寻求农业的改良。下渡村、凤凰村都是城郊的农村,村民往返于城乡之间,区阃奇提到佣工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农村社会处于崩溃的状态,原因既受农业生产技术问题的支配,也受农村生产关系的影响;前者是自然的原因,而后者是社会的;社会学欲图救济的方法则在于村民的教育(区阃奇,1938)。

表2 岭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社区部分调查报告目录
在1940年代中后期之后,岭南地区的社区研究开始转向引入在国内外更为成熟的研究范式。1947年夏,杨庆堃留美归国,被聘为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开展了鹭江村的系列研究。据杨庆堃的学生刘耀荃记叙(刘耀荃,2005),杨庆堃想要开展社区研究的原因有:
(一)“社区研究”是美国社会学界中最流行和最吃香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在中国也是大有前途的;(二)抗日战争前,赛珍珠的丈夫贝克教授在金陵大学主持一项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计划,从而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现在搞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就是要在贝克调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三)费孝通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搞的社会调查也是采用社区调查的方法,写出了两本书,而杨先生是费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过去在华北和费合作也搞过一些农村社会调查,有经验,有成功的把握;(四)岭大社会学系在抗日战争前也曾在附近的农村(凤凰村)进行过社会调查,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可供参考,也可说是继承岭大社会学系过去的传统。
其中提及对于国外社区研究范式的引入、中国社区研究传统、岭南大学社会学社区研究传统的多方面继承,但与原来岭大较为注重全方面的经验研究不同,杨庆堃所主导的社区研究将社区进行功能结构的划分,也有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刘耀荃在《鹭江村的权力结构》中使用了区位学等分析方法分析社区权力结构,将社区权力结构置于大的范围之内(刘耀荃,2014):
(一)研究一个社区的政治生活,从权力结构入手要比单是注意政治制度的问题获得对事实更深彻的了解。(二)权力结构是社区一切生活得以有秩序地进行的依据。它不但是生活的必需,也是生活所造成的事实。把权力结构孤立在政治范围之内的看法,难以更周详的看待问题。(三)一个社区的权力结构是不会“消灭”的。它只有解组和重组的变迁,这种变迁是指社区内各种权力成份间地位的升降,或新的权力成份的出现。(四)权力结构既是社区生活的事实,而生活又是社区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每个社区都有“它自己”的权力结构。社区特有的自然、历史、社会条件造成了权力结构方面的特色。(五)权力结构是社区权力的配合,而配合的方式和原则,受到社区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最为重要,而且往往是推动权力结构方式变迁的原动力。
另外5篇学位论文从儿童家庭、家族与祭礼、阶级及职业的流变、娱乐活动等不同的角度对鹭江村进行了不同部分和角度的分析,将社区各个部分进行剖析。虽然不同的师生将研究对象置于农村,但都选择了城郊的农村,而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连。
(二)稳定与动荡:礼教维系与社会解组
系列的社区调查报告反映了结构断裂下民不聊生的状况,但其问题意识却在于原本的封建意识形态的维持,并将何以维持的原因作为下一步社会改造的出发点。礼教维系与社区权力结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原有社区结构稳定的基础,维持了以往的阶级关系。岭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社区研究对礼教、习俗等做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强调礼教的维系与功能,以及在社会结构断裂冲击下的变动。
伍锐麟在关于旧凤凰村、下渡村的研究中,细致地梳理了两个村的婚俗、宗教信仰等,但仅将其视为“受传统思想的蒙蔽,保留了原始和幼稚的信仰”(伍锐麟和黄恩怜,2005),从经验事实的角度进行描述。其中保留了对于岭南地区年节、人日、清明、蒲节、乞巧节等节日如何祭拜的详细描述。岭南地区的礼教在相对稳定的维系中也在变化,如《鹭江村家族与祭礼调查》论文一开始就谈及文章的研究问题(正宝杰,2014):
中国家族组织之所以能够维系和能够延绵持续,拜祖的丧祭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家族生活的中心离不开寺庙丧祭。本文的目的就是根据这一个假设,去研究鹭江村的家族组织系统及其祠庙丧祭的体系,借此追寻这两个社会因素的关系,研究二者最近的变迁,希望从鹭江村的例子中,观察华南现在社会组织及其变迁的一面。
正宝杰对鹭江村氏族结构、氏族成员的约束等做了全面盘点,如其中所列《车氏合族公约》指出族员需要遵守的孝悌及个人德行,“以上规例在必行,轻则集祠警责,重则官间究治,永远革胙,不许入祠”。父老为族中长老,负责执行族中事务,祠堂在鹭江村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宝杰指出祠堂与祭礼对于维系家族的关键,其中车族、莫族等维系了原先的祭礼,而王、何、伍三族人丁逐步稀落,难以维持。礼教的变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如鹭江村中的祠堂在战争中多次遭劫,人口减少、变动,如伍、何两族的祖祠抗战期间则被拆卖、族田等也被变卖,这直接导致礼教的难以维系(正宝杰,2014)。
礼教的维系和教养成为社会落后的象征,也成为变革的阻碍。在《鹭江儿童家庭教养调查》一文中,简慕贞、谈文焕明确提到(简慕贞和谈文焕,2014):
乡人对儿童教养意识既如此低下,为了要矫正彼等对儿童错误的观念,提高儿童地位,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工作者便应深入乡村,实际调查,务必明了乡民之实际情形、风俗习惯及各种困难所在;实地对症下药,以收实效。故此次调查……更有一深远之目的,就是如何能灌输父母以正确之育儿知识,明了儿童教养之重要;如何破除迷信,引起他们对儿童卫生、习惯、食物及营养等等之注意;在可能范围内举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在今中国重建声中,产生重建之新国民。
在家庭中,原有的婚姻习俗也备受批判,旧式家庭制度逐步解体。马纨素的《广州市旧式家庭制度研究》、刘春华的《广州市五十件离婚案》、刘国香的《广东不落家婚俗的研究》、陈慧贞的《广州市已婚妇女与职业》等对广东已有的家庭制度以及妇女的地位展开了研究。“不落家婚俗”是珠江附近广府地带原有的一种特异的婚俗,即嫁娶之后女方在娘家居住,与之相关的有“违夫教”和一些巫术。刘国香论文指出这种习俗与妇女地位低下及少数民族的婚俗相关,而这种婚俗在新文化及抗战的影响下开始改变(刘国香,2014)。陈慧贞一文则讨论了妇女职业解放运动与中国女子对职业觉悟的觉醒(陈慧贞,2014)。
国立中山大学的系列社区调查将研究触角伸至更广阔的珠三角区域,但同样带着对结构断裂的判断与社会改造的学科情怀。袁伟民的《东莞员溪农村社会之调查研究》将调查动机界定为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急剧变化,了解农村中抗日战争、内战中的创伤,其结论中提及(袁伟民,2014):
今日中国农村社会的问题,并不是自然的、静的技术问题;而是人为的、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以农村土地经济为内容的。它决定整个农村社会的诸现象。
……土地私有制实是中国农村社会改进的唯一阻碍。
调查报告立足于对社会结构改造的目的,原先的社会结构解体、崩溃,新的社会结构尚未建立,从而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这些社会调查报告基于对原先农村社会组织的详细了解,从社会学的观点提出重建社会组织的建议,如林纬的《龙村社会调查》,对龙村的经济、人口组成、社会关系、社会控制等做了全面盘点,以了解抗战后天灾人祸及封建形态屹立不动的原因。郭文榜、夏新民等同样就农村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等展开调查,了解农村社会的剥削情况,为新社会的建设留下宝贵的调研资料。这些社区研究除了维持岭南大学社会学对底层社区的关怀之外,刘榘教授等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投身革命,指导学生对阶级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为革命提供详实的调查报告。
两个学校的社会学师生聚焦于如何重构新的社会结构、推动旧结构的解体,研究的目的则在于政治实践。如刘耀荃在其论文的引论中直接指出“除旧布新”的问题(刘耀荃,2014):
我们研究中国的基层权力结构,主要是希望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加速一个旧有的权力结构的解体,和帮助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更快地建立和巩固起来;也就是怎样使广大的人民,能够过上现代化的政治生活。
可见,民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区研究聚焦于岭南社区的特色,充分揭示了底层社区的文化与结构,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学的价值关怀。这与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联系在一起,也呈现出社会学师生对于岭南地区社会学的地方性知识的生产。
三、城市变革与漂泊的群体:岭南地区的底边社会
1928年至1937年是广州市规划及发展的高峰。1928年,广州市城市设计委员会成立(邹东,2012)。陈济棠主粤期间(1929—1936),主持制定《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救济广东农村计划》,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民族工业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对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做了大规模的规划改造(周兴樑,2000)。原有的城市规划难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但规划的改造使底层群体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同时,在1920年代开始,中国各学术团体对底层群体的关注日益突出,中国社会学学者组织、主持的大规模对于社会底层群体包括人力车夫、乞丐和工人等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内容涉及人口、劳工、风俗、教育和社会概括等各方面(陈映芳,2004)。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师生在1930—1950年代对职业妇女、人力车夫、乞丐等同样展开了调查,对于疍民的关注也成为岭南社会学的特色。
(一)城市的边缘群体
1920至1930年代,广州的农村日渐衰败,城郊农村逐步城市化。但城市工业一蹶不振,底层群体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底层人群是经验研究关注的对象,强调底层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研究的特色也体现在岭南地区的调查中。这些调查报告大概可以分成底层劳工(包括女工及妇女职业、人力车夫等)和乞丐研究。
伍锐麟自己及指导学生完成的人力车夫的调研报告是其中的一个系列。在社会调查课,伍锐麟率领学生对广州市人力车夫进行调研,对其面临的城市交通变革的背景下的生活困境进行全方位的描述。“自机器的运用发达以来,长途汽车满布全市,便捷价廉;人力车乃大受影响,况年来世界不景,农村破产,贫民挤拥于都市,多藉拉车以谋生。他们受着社会经济的恐慌,公共长途汽车的增加及路线延长的影响;于是车夫生活日渐困苦。”(伍锐麟,2005B)人力车夫处于社会底层,操手车业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农村经济崩溃、天灾人祸等原因,生活也较为困顿,如居所不卫生、容易患病、健康状况差,伍锐麟认为在逐步淘汰人力车的同时应该早做准备,培训人力车夫等有新的技能,从经济、卫生、教育等多方面介入(伍锐麟,2005B)。李蕴碧于1937年以同一个调查的资料写成学位论文,也是希望借以“将广州市的车夫的痛苦生活向社会人士作一个简略的报告,俾他们对于这一万多的比牛马不如的同胞加以援助和拯救”,人力车夫的困境除了受到社会整体经济的恶化影响之外,还受到城市政府制度的多种剥削,包括政府、车公司、夫目的三重剥削(李蕴碧,2014)。他们又将人力车夫置于全中国的情况中看,“人力车夫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低卑而下贱的,似乎是多数人们的劳奴一样,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给少数的钱来临时雇用他去代步,故他的社会地位是被一般人所轻视的”(伍锐麟和白铨,2005)。

表3 岭南地区的边缘群体研究
乞丐群体是城市最底层的群体,与贫穷紧密相连。张天佑在其学位论文(1938)中对该群体进行研究,以回应当时对乞丐研究较少的补充。“乞丐则不能不专恃慈善赈恤以过活。倘若得不着人们的赈济,便有立成饿馁的危险。即就其平日生活而言,也已经够是非人的生活了。”(张天佑,2014)他采用了调查表对乞丐的状况进行细致地调研,包括分布地、年龄、籍贯、性别、婚姻、经济收入、教育、疾病、社会状况等,最后分析乞丐的成因及救济方式。在该论文中,张天佑将乞丐与其他城市底层群体(如工人、沙南疍民、凤凰村村民等)的收入、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其将乞丐视为增加社会负担、犯罪、影响市容、影响子女等的社会问题,而需要预防和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张天佑对乞丐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分析,广州市乞丐的组织多以某某堂为名,如“同庆堂”“旺相堂”等,聚集地方也多有组织,由乞丐头来管理指挥,乞丐行话中有“包爷”(乞丐头)、“拉马”(离去)等(张天佑,2014)。在1950年,何肇发趁广州市人民政府对乞丐救济之时,对收容的乞丐进行调查,完成了《广州市乞丐的个案研究》,认为乞丐是社会解组和生活方式解组的结果(何肇发,2001)。1940年代至1950年代是社会结构动荡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崩溃带来的冲击直接反映在乞丐等群体上。
(二)“河上城市”:疍民的研究
疍民具有很强的岭南地域特征,充分反映了岭南特色,相对应的疍民研究也成为岭南社会学在民国时期独树一帜的研究。同时,该研究还充分体现了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对底层群体的关怀。表4是部分较为出名的疍民研究目录。

表4 疍民研究调查报告
伍锐麟将疍民群体居住的水域描述为“河上城市”:“假使我们把广州市这10万左右的疍民来当做一个特别城市看,那么广州这个河上城市,简直是中国40余个最大城市中之一了。不但这样,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找出一个很特别的世界。”(伍锐麟,2005C)这个群体生活在河上,正如陆上人生活在陆上一般正常,并且有商业、娱乐等船艇。疍民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社会:“除了他们自己喜欢,他们用不着跑到陆上来寻找他们的日常或是特别的需要。总而言之,他们是自成一个世界,别有一个天地。”(伍锐麟,2005C)
疍民人口众多,从而生发出不少问题,如船艇之间的治安问题、环境问题、疍民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由于珠江两岸的交通改善,通过疍民运输过江的需求减低,疍民的收入来源急剧减少,进而引起学者的关注:“船只若是减少,这些没有教育而世世代代以舟为生的疍民的前途,又怎么样呢?这是一般为社会谋幸福的人所不能不注意的。”(伍锐麟,2005C)疍民具有与陆地居民不同的职业和生活特征:其一,经济收入相对低下,“凡疍必贫”。《沙南疍民调查》梳理了13种职业的平均收入数目,收入最高的是机器工人,每月得47.8元;其次是航业、做醒婆(迷信);但操盐务、棹艇、商业的、佣工的、接生妇等从11元到19原不等,做田工的平均每月9元。“贫穷的沙南人,只求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要能够保证便已足矣,哪里还有什么奢望呢?”(伍锐麟,2005C)。伍锐麟、陈序经等在三水河口的疍民调查也同样得出疍民贫苦的结论(伍锐麟,2005)。其二,与陆上人家有着不同的宗亲关系,多姓氏,少宗族。从1930—1950年代的疍民调查报告中反映,疍民群体多以职业聚居,姓氏较多,《三水河口疍民调查》指出191家疍民家庭共有27个姓氏,宗亲关系较为淡薄。疍民群体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家,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中指出水路与疍民之间的关系,疍民通过水路到处迁移,较为分散。同时,船艇也难以容纳大家庭形成大家族,大部分都是小家庭模式,三水河口的疍民家庭以4人家庭最多,生育率也比较低。其三,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关于疍民的社会调查报告都提及陆上居民对疍民的蔑称,如“疍家佬”“疍家婆”“疍家濑”“密毛”“水底鸭”等,疍民被贴上了下贱族群的标签,被“污名化”。
通过详实的调查,这些报告将事实揭示出来,同时立足于为疍民正名,以疍民的真实情况破除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固有偏见:(1)民众认为疍民性格凶暴,有“疍家贼”之称呼,但根据调查发现,这个群体却是非常安分守己;(2)有人认为疍民妇女多数卖淫为生、不讲道德,但调查发现沙南疍民700余户,有不正常行为的找不出二三位,“受了旧礼教的束缚,沙南妇女是很注重道德的,她们咸是安分的人,在家庭上作良妻贤母,服从翁姑,若果其中有一个做不道德的事,即如盗窃或者奸淫的事,她们便觉得很羞耻”(伍锐麟,2005D)。因此,社会学者的意图在于还原事实的真相,使人们首先认识到这个群体的现状,再就改善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进行努力。《粤东疍民社会调查》提出了涵盖疍民生活各方面的建议,包括政治权利、健全渔民组织、对疍民新村的建设、文教和卫生的改善、处理渔贷问题等。同时,疍民与汉族的关系、内部的团结问题等也是社会学者希望政府要关注及解决的。
结语:地方社会的社会学范例
关注社会学的早期发展,能够关照现阶段社会学的境况。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应该具有自己的历史担当(李培林,2016)。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学术话语权(郑杭生,2011),岭南地区对于底层社区和群体的关怀反映了社会学的态度,一个学科发展初期所力图建构的学科谱系从根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学科自信。这提供了社会学对于地方分析的一个范例,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综合学派、燕京学派、乡建学派等形成了互补。
社会学的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具有强烈的社会重构的价值关怀。从民国时期岭南地区所处的情境来看,既是革命发源地,同时又是偏安一隅的地方。在1920、1930年代,虽然也受到军阀割据的影响,但相对于国内其他地方来说又暂时远离战乱,从而给广东的城市变革提供了较好的机会。这些政策变迁直接反映在城郊的农村以及城市底层的群体中,对于他们来说则是生活危机的积累及困境的应对。在这样的结构变迁情境下,社会学研究形成了国家命运、城市变革、地方社会、边缘社群四个层次的研究进路。从社区及人群的研究上看,这些研究同样带着对国家命运关切的视角,改造社会结构成为若隐若现的价值关怀,如旧凤凰村、下渡村及鹭江村等一系列的研究。与国家相对的是地方,社会学藉其深入的触角,对地方的权力结构、礼教伦理秩序、文化等进行了深入剖析,留下了社会学对地方的深度知识。在国家命运、城市变革、地方社会的变迁情境下,底层人群的生命历程也发生急剧转变,其生活所积累的危机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大的社会结构背景下被裹挟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将民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学发展置于全国社会学发展的情境之中来看,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岭南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性提供了城市变革的持续性,岭南社会学更加关注城市地区、城郊村落等的变迁及城市底层的民生问题。结构的变迁给岭南的社会学提供了实验的土壤,广州及周边作为城市实验室,成为社会问题的滋生地,成为观察地方、国家甚至世界的窗口。岭南社会学更多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相联系,强调经验分析,而与北方社会学对功能理论、区位理论的杂糅等不同(李文波,1994)。除了本文所梳理的三个系列的研究之外,岭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在社会事务上也进行了较多研究,如叶息机《广州市社会局管辖之慈善事业的研究》(1934年,岭南大学学士论文,指导教授:伍锐麟)、陈继明《私立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之社会事业》(1938年,岭南大学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指导教授:伍锐麟)、黄碧云《一个社会儿童教养机构——岭南儿童工艺所膳食与营养问题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指导教授:容筱韫)、李希旻《广州市儿童福利事业概况调查》(1949年,岭南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指导教授:黄翠峰)等,这些论文也呈现出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状况。
其二,民国时期岭南社会学的发展彰显了较强的地方社会学特色,提供了一个地方社会学理论关怀的范本。岭南的地方社会文化从明中叶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直到18、19世纪趋于普遍(叶汉明,2000)。地方是一个有意义感和认同感的空间。民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群研究充分体现了这种地方社会在面对结构急剧变迁下的维系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广州作为地方社会的逐步解体:一方面,广州作为重要的城市,被纳入世界的范围以及成为革命的起点;另一方面,政治家及学者们也力图于改造社会结构,使其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城郊农村逐步被纳入城市范围;在1950年代之后,疍民群体上岸,“疍民”成为一个历史现象,“河上城市”也走向终结,而沙田疍民登陆后融入汉族,修建祠堂、修订族谱。对于他们来说,原有的文化符号是一种歧视性的符号,而需要改除(黄向春,2008;张银锋,2008)。这些社会学者关注特殊文化形态的社区,如疍民群体、边缘村落等,突出岭南地区的文化,同时也关注海外华侨社区(李文波,1994)。
其三,从方法论上讲,民国时期岭南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充分糅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采用整合视角的文献分析与田野研究相结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相互融合借鉴,并注重实用的传统(王传,2012),如伍锐麟的调查时间长、跨度大(何国强和温士贤,2009),陈序经的《疍民的研究》则从历史的角度去谈社会学(郑朝波,2008),同时还有一系列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本文仅分析其中城市(城郊)底层社区研究的进路,而未将这些系列研究同时纳入文中,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整合视角有助于克服割裂及碎片化的学科对社会的把握,与综合学派有点类似。同时,强调社会学的客观分析的科学态度与平等眼光、同情的态度相结合(郑朝波,2008)。社会学者转换视角,关注底层人群,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务实的情怀,如伍锐麟、陈序经等人的研究则充分转换了视角,避免从“陆上”看“水上”的状况,充分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不得不设身处地把自己当做沙南社会里的分子。要是我们是这个社会里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调查他们的情况,也犹如我们调查自己的状况一样。”(伍锐麟,2005C)这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来说比较有价值和意义,也是社会学科的初心所在。岭南地区的社区研究从伍锐麟等人开始,1940年代以前注重经验研究的持续积累,而在1940年代后期逐步成熟,与北方的社区研究进一步接轨(李文波,1994),逐步融入到全国的社会学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