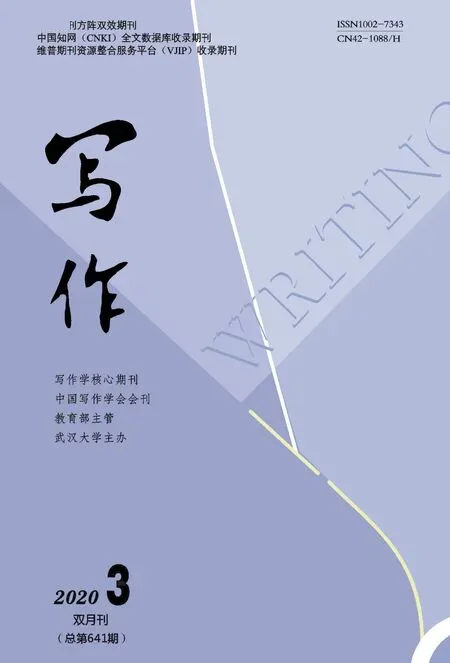创意写作与新媒体:基于四个维度的观察
刘卫东
1880年以来,创意写作从早期以小说、诗歌为主要写作类型的教育为起点,随着媒介技术、教育理念与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其课程、学位方向与实践路径不断扩展,先后经历了多次转向。近20年来,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写作不断涌现,与创意写作教育不断融合,构成了当前创意写作教育领域的突出现象:“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一些课程,使学生过渡到新的数字时代的写作,一些大学现在要求至少有一种数字叙事作为创意写作课程组合的一部分。”①Dianna Donnelly and Graeme Harper.Key Issues in Creative Writing.Bristol:Multilingual Matters,2013,p.22.这种与新媒体的应用紧密结合的创意写作课程、学位的出现,对既有的教学与研究模式都提出了新挑战。
从创意写作的学科史视域观察,创意写作研究学者唐纳利(Dianna Donnelly)论及的这一现象,正是科勒尔(Adam Koehler)所说的创意写作数字转向(creative writing’s digital turn)的结果②Adam Koehler.Composition,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7,p.18.。这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创意写作,具有与传统印刷媒体时代不同的数字化、虚拟化和非线性叙事等诸多特点,对创意写作既有的理论与实践都有相当的影响。其中,作者身份的跨产业重构、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是创意作者与新媒体融合的直接产物,教学方式的数字化改造随之成为常态,创意写作研究也开始更多地聚焦数字化创意写作活动的教学规律与理论问题。这一方面使得创意写作能够在当前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推动创意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开始新一轮的自我更新。与当前国内注重通过创意写作教育“摆脱自我的平庸”③张定浩:《文学的职业与业余——兼论创意写作》,《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从新文科建设的视角推动“创意写作的社会化实践”等研究热点相比①葛红兵:《创意本位的新文科何以可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从作者身份、文本类型、教学方式与理论研究四个维度出发,探究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融合问题,尚需进一步展开②[美]迈克尔·迪安·克拉克等编:《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杨靖、张晓东、苗英婷、罗昶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一、“作者”身份的跨产业重构
与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平面印刷媒体占据主流的时期相比,当前的创意写作实践与新媒体技术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文学与数字叙事技术的改进,游戏写作与为数字视频撰写各类脚本等都成为常态。这些现象导致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在这些跨产业链的文学实践中,“作者”的身份和种类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多元。小说家可以扮演游戏脚本写作者的角色,诗人可以跨界成为数字视频创意文案的作者,而表演艺术家也可以借助新媒体进行复杂的超文本形态的视觉叙事。这些分布在文化产业不同领域的创作者,频繁地介入不同形式的创作活动,作者从某种类型的文本生产者向更为复杂的、多元身份的创意型“作者”。
当前文化产业领域涌现的自媒体作者、数字视频脚本写手以及众多的网络写作者,他们的创造活动频繁跨越多种产业和职业领域,这种创意型作者从事的创作活动也与传统的“作家”或“作者”存在较大差异。新的活跃于该领域的创意型作者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新媒体技术影响,写作方式、传播路径和生产模式的全方位变化所致,而并非创作者本人的标新立异,或刻意为之。随着新媒体不断地用于写作实践,基于不同文本类型写作的“作者”活跃在出版、展览、动漫、广告、电影等不同的领域,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不断地从事各种各样的写作活动,“作者”开始被用来指称更大范围的写作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包括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等,与新出现的“动漫脚本作者”“数字广告创意作者”、自媒体平台的非虚构作者共同构成了以创意实践为共通品格的“作者共同体”③叶炜:《作为文学教育共同体的创意写作及其实践品格研究》,《写作》2020年第1期。。总体上,这些新型作者都是“互联网经济与创意写作”的融合产物④刘海玲:《纵论中国创意写作的新机遇、新理念、新对策——2018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暨创意写作高峰论坛综述》,《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1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39页。。而从创意实践的角度,又可以把他们都视为数字时代的“创意作家”⑤葛红兵、王冰云:《创意写作学本体论论纲——基于个体的感性的身体本位的创意实践论写作学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如果回顾文学史上关于“作者”研究的诸多观点,可以看到“作者”其实并没有死亡,纯文学领域的作者虽然总的基数在减少⑥叶炜:《创意写作视域下的作家系统化培养——对鲁迅文学院文学新人培养的学科化路径思考》,《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但是新兴的利用新媒体写作、从事文化生产的“作者”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作者的身份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同样,为了适应文化生产活动的需要,新的以新媒体为写作基础的创意写作课程与学位也在不断增加,在注重小说家、诗人与非虚构领域精英作家培养的同时,能够熟练利用新媒体、数据库以及掌握多种写作文体的“作者”也在被不断地培养出来。在这种教育过程中,从事新媒体创意写作学习的学生们,主要的学习内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构思方面的训练,而是包括了习得当代创意技术(contemporary creative technologies),接受包括注重文学素养、媒介素养、写作素养等在内多元化的写作教育。这种以文学教育为基础,以写作训练为具体方式,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综合训练,培养了大批新型的具有写作能力的创意人才。
在新媒体与创意写作融合发展的语境中,随着写作应用场景的增加与变化,写作不再是文学创作人员的专利,而是文化生产中的一种常见的劳动形式,学员可以是熟练使用各种新媒体技术的艺术家、具有程序编写技能的设计师,以及其他领域的能够运用新技术进行书写的专家,也可以是来自传统人文学科或交叉学科的人员,这主要是由当前文化生产活动对新型复合型创意人才的需求决定的。例如,在世界文学之都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文学创作与新型媒介传播高度融合,文学原创价值可以借助新媒体得以进一步实现,相应的创意写作人才因此受到欢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开设的“新媒体与创意写作”(New Media and Creative Writing)课程,即是创意写作与新媒体技术结合研究的典范。这类创意写作课程注重创作者的创造潜能 (creative potential)与各种前卫的艺术(avant-garde)、跨类型(cross-genre)的写作形式结合。新的视觉叙事领域包括了电视写作、播客写作(serial storytelling including TV writing and Podcast writing),以及面向表演和新媒体的写作(writing for performance and new media)。这些科目的设置都是以经济活动不断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升级对内容创作提出更为细致的要求为前提的。
总体而言,新媒体与创意写作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新的不同于传统小说家、诗人的作者涌现成为可观测的显著现象,这是创意写作实践不断与文化产业融合,在跨产业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结果。这种跨产业的作者身份重构一方面是文学不断产业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新媒体技术与创意写作融合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但是,新媒体与创意写作的融合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否定既有的小说家、诗人与非虚构作家的地位。相反,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融合为文本叙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到社会文化生产的产业链,数字化叙事对小说叙事、诗歌创作方式及文本呈现都提供了新的契机,文学的多模态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其影响而言,“文学多模态实践的发展和多模态理论研究的兴起,为反思文学意义理论的语言学范式和观念论传统提供了契机,对重估文学与媒介的关系、重审先锋实验文学的思想指向提供了启示。”①张昊臣:《多模态:文学意义研究的新维度》,《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以新媒体与创意写作融合为基础,从事文学多模态实践的“作者”群体不断增加,也为文学写作赋予了新的可能性。
二、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
新媒体技术带给创意写作的第二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它主要是指数字媒介技术在不断被运用到文化生产活动中之后,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形态的新型文本。布朗温·威廉姆斯(Bronwyn T.Williams)在《数字技术与创意写作》(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reative Writing)中已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数字化创意写作的实验催生了很多不同的文本及类型”②Alexandria Peary,Tom C.Hunley.eds.Creative Writing Pedagog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15,p.247.。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新的数字叙事技术不断演进,传统的线性叙事不断拆解,新的多模态叙事兴起,语言的形体、声音和意义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加以创造性地组合,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就成为自然的结果。这种跨文本类型和媒介领域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across genres and media)实践,以其非线性、视觉化、多媒介的创作、传播与接受为突出特点,是新媒体为代表高度技术化的、以文本为主要生产价值载体的创意实践的伴随产物。
除了媒介技术层面的影响之外,文本类型跨媒介衍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文化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正是得益于高度发达、活跃的文化市场,新的文本类型被不断生产出来。在跨媒介的创意写作实践过程中,随着“创意作家”参与的写作活动越来越多元化,更多的基于应用场景而生成的新的文本类型不断被创造出来。如今,这些新型的作者除了从事诗歌、小说、非虚构写作等方面的创作之外,也开始尝试新媒体叙事,借助数字技术展开新的创作探索。例如,基于动态图形展示与有声诗歌混合的文本,非线性的游戏情节设计与拥有开放式结局的超文本小说,还有以虚拟人物讲演为呈现形式的口语诗歌创作,这些新的文本类型都是在跨媒介叙事实践中不断被创造出来的。与传统的有限的文本类型相比,新媒体与创意写作融合而衍生的文本类型可谓难以计数。
在当前的文化生产活动中,作者的活动实现了创意写作与出版、娱乐、媒体和表演等行业的跨专业、跨产业链的高度融合,而新媒体则为这些融合提供了技术基础,技术、市场与创意写作实践呈现出空前的高度一体化。新媒体技术使得创意写作的跨媒介实践成为一种新的可能,书写过程中的语音、图像和文字操纵都呈现出高度的技术化、智能化。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这种融合,写作类型随着社会变迁不断扩展与媒体技术不断迭代,演进成为写作与文学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创意写作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文学教育的框架,文本类型也开始从原有的小说、诗歌等常见的经典体裁溢出。创意写作借助新媒体的力量与文化产业中的广告、影视、动漫、游戏等注重创意文本生产的行业在价值链、产业链层面得以衔接起来,而这些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与当前英语国家开设的面向影视、游戏和表演等领域的创意写作课程、学位是互为前提的。
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学者对于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现象,目前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写作活动与媒介技术关系演进的角度来说,新媒体技术带给创意写作的影响并不是特有的:“书写始终涉及技术形式,无论是笔,打字机还是计算机。”①David Morley,Philip Neilsen.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eative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02.20世纪早期的印刷媒体高速发展过程中兴起的新闻写作、长篇报道等细分的文本类型,与当下的数字化时代跨媒介衍生的文本类型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与20世纪初新闻写作领域细分的文本类型涌现相比,书写技术催生了新的写作方式、文本类型,多样化的文本类型是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而实现的。而在新媒体与创意写作融合的过程中,诸多文本类型的产生,其中共通之处则在于它们都具有“文本性”(textuality),包括书籍、杂志、电子文学作品以及视频等②[美]迈克尔·迪安·克拉克等编:《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杨靖、张晓东、苗英婷、罗昶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不过基于新媒体的特殊语境,这种“文本性”又可以视为可以不断流通、重新编码、转换形态的数据流,可以被存储和复制,文本类型可以被不断编码、塑造,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些都与传统的创意写作涉及的文本类型具有差异性,同时也使创意写作各类数字化的文本在新媒体技术时代获得了新的内在共通性。
总体上,新媒体对创意写作的影响和创意写作对新媒体的运用,彼此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二者不断互相塑造、互为支撑。例如,新闻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天然联姻,对新兴媒介的敏感性、依赖性,以及文学写作对传播媒介的需求,使得新闻写作、文学写作和各类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原创内容写作之间产生了交叉、渗透和融合。不过,创意写作对新媒体的运用也并非特例,这是数字时代整个人文学科领域都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何理解创意写作实践中不断衍生的文本类型,对其中的共性与异质性进行研究,是创意写作研究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这些跨媒介衍生的诸多文本,既是创意写作实践的活力所在,也对创意写作的基本形态与研究提出了挑战。而面对不断模糊的文本边界、不断衍生的文本类型,创意写作的未来教学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方式,又如何与不同的写作教学方法和传统对话、融通,则是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
三、教学方式的数字化改造
目前,英语国家在创意写作教学方面,已经开始尝试以新媒体技术为基础的创意写作课程设计:“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创意写作教师已经运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教学实验并引起广泛关注。”①[美]迈克尔·迪安·克拉克等编:《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杨靖、张晓东、苗英婷、罗昶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然而,相关教学与研究人员也已经意识到,目前的探索还处于初步阶段,对于其中的教学原理尚缺少深入的阐述。当代的媒介融合和产业的融合式发展,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的进一步扩张,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媒介的兴起的多重张力,构成了新型的创意写作文类、学科的基础。相应地,如何在现在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改造,引入数字叙事等多种新媒体写作实践,成为当前创意写作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学乃至广义上的文化其书写模式和表达、传播媒介都在发生变化,文学文本的多维度呈现以及影像叙事,使得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内涵更加驳杂,如何清理并就其学科基础和教学框架进行搭建,成为当前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例如,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创意、专业写作与媒体”学位,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教授从广播,电视和报纸到多媒体平台和移动电话等各种媒体的写作艺术”②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BA (Hons) 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and Media,https://www.wlv.ac.uk/courses/ba-hons-creative-and-professional-writing-and-media/,2019-10-12.。这些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创意能力培养与专业化的写作技能并重,对教学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对传统的侧重业务流程与专业理论的教学理念也带来了冲击。
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也对当前的文学教育、创意写作课程设计等带来了挑战。同样,创意写作数字化转向背景下,新媒体写作也为创意写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这个方向衍生的各种课程与学位的教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与传统的写作不同,新的基于新媒体和视觉技术的动画诗歌(animated poetry)、交互式虚构作品(interactive fiction)以及计算机生成文本与装置(computer-generated text and computer-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在文本形式、创作方法和传播途径、阅读体验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这使得创意写作学科可以继续保持自身的活力,在跨媒介、跨产业与跨学科的实践中寻求新的认同。以写作与数字媒体学士(B.A.in Writing and Digital Media)为例,这正是典型的跨专业的学位设置,媒体领域的专业训练与高级写作能力的结合。
另外,传统的学科转型也为新媒体创意写作课程提供了机会。例如,面向出版的新媒体写作(new media writing for publication)、面向表演艺术的新媒体写作(creative writing for performance)、面向虚构写作的新媒体写作(creative writing for storytelling),正是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具体例子。例如,在查特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创意写作课是数字人文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背景下观察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涌现,对相应的问题域就会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新媒体与创意写作的融合背景下,创意写作的课程数字化改造的跨媒介特征也非常突出。例如,在休斯顿浸会大学(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电影、媒体艺术和写作系(Department of Cinema,Media Arts,and Writing),其教学的重点在于发展学生们跨媒介的叙事、综合运用媒介技术进行艺术创作的能力,为未来的多媒体制作工作做好准备。这种数字讲述一方面是创意写作以其创作实践对既有叙事模式的发问,一方面也是其学科转向的结果,体现了创意写作与文化研究、媒介理论的跨学科综合。
正是在这些现实基础之上,新的作者的身份问题、叙事模式问题以及新的批评观念和创作伦理问题随之浮现。显然,这是一种基于新的语境的教育,它以新的媒体生态为基础,产生了一种基于新媒体生态的写作教学(teaching writing in a new media ecology),这要求教学与研究人员不断据此给出回应,基于当前文学教育面临的数字人文转型的契机,推进创意写作学科的数字化改造。不过应该注意,在强调数字化技术操作的时候,如何减少出现“有了创意,丢了诚意”,作品沦为毫无韵味的粗制滥造之作的情况①许峰:《“2.0时代”地方院校创意写作学科构建路径与误区——以广东财经大学为例》,《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则是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像科勒尔这样的学者认为,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化已经出现,而且肯尼斯·戈德史密斯《非创意写作:数字时代的语言操纵》与凯瑟琳·海尔斯《写作机器》也表明数字化创意写作的教学法已经形成。中国也有多位学者在立足于新媒体设计创意写作课程,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于新媒体的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仍旧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课程设计尚需进一步展开。这主要是因为创意写作作为学科与数字化的一系列融合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另外则是由于师资力量跟不上,有的创意写作教师认为这些数字工具的应用过于复杂,难以掌握,对数字叙事所依存的产业环境没有支持的话,也是难以为继的,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四、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理论研究
随着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不断融合,作家身份在跨产业的实践中被不断重构,以及文本类型的持续衍生以及创意写作教学的数字化改造,相应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对这些现象加以回应,这就需要创意写作研究走出既有的领域,直面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克拉克等学者在《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中也把它分为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数字化创意写作的理论研究一方面为数字时代的写作实践提供学理层面的支撑,另一方面则是直接从现有的数字化的课程出发,在教育教学的层面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具有突出的以实践为中心(practice-led)的特质,即把数字化工具作为创意实践使用。
鉴于目前新媒体与创意写作的不断融合,跨产业的新的作者共同体涌现、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以及数字化的创意写作教育不断推进,英语国家包括唐纳利、哈珀、科勒尔、克劳斯(Nigel Krauth)、阿德斯特(Janelle Adist)等学者在内都在对创意写作的数字化问题进行研究,克拉克等学者所提出的“数字化对创意写作研究的影响”(digital influence on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已经成为新的焦点。不过,虽然整体上创意写作研究领域已经有不少著作在研究这一现象,但是新媒体对创意写作的深层影响研究尚需要进一步展开。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对于新媒体影响下创意写作所涉及的价值问题,学界也已经有了相关研究。如 《写作新媒体:写作教学扩展的理论与应用》(Writing New Media:Theory and Applications for Expanding the Teaching of Composition)所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和时代,写作是构成和理解自我,身份以及与他人生活和合作能力的众多活动之一”。②Anne Frances Wysocki,Johndan Johnson-Eilola,Cynthia L.Selfe,Geoffrey Sire eds.Writing New Media:Theory and Applications for Expanding the Teaching of Composition,Logan: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p.2.
在具体的研究层面,提出“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的学者科勒尔也已经展开了细分领域的研究。科勒尔在《数字化技艺:创意写作研究与新媒体,一种提议》(Digitizing Craft: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and New Media:A Proposal)已经主张对数字化环境中的创意活动进行研究。他认为,数字环境提供了沉浸式的多模态和世界化功能,它们依赖于声音、图像和文本的情感环境世界的集成,每个部分以及相关的理论都需要整合①Adam Koehler."Digitizing Craft: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and New Media:A proposal."College English.75.4(2013):379-397.。在国内则有研究从新媒介语境下文艺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展开,指出:“其数字化生产力将创意写作的‘文学性+商业性’转变为一种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具有“自指性”的合法性存在。”②王宇阔、朱国华:《新媒介语境下创意写作的文艺生产力》,《写作》2020年第2期。也有青年学者指出:“创意写作应聚焦游戏、动漫、人工智能写作等新文体的理论探索,在多媒体、VR、AR等新型媒介语境下探索工坊的教学、创作体系。”③高翔:《西方创意写作工作坊研究热点梳理——兼谈中国化创意写作体系建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具体的教学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国内学界对此都已经有了初步的回应。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的融合研究与当前的媒介、传播研究也密切相关,涉及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就像克拉克所说:“除了创意写作,商业和创意媒体研究也为这种教学设计提供了理论来源。”④[美]迈克尔·迪安·克拉克等编:《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杨靖、张晓东、苗英婷、罗昶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不过,随着国内对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视,以及在网络文学研究逐步得到认同的情况下,跨学科的研究也具备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创意写作的学员来自社会科学、商业、科学等不同的专业,课堂上的诸多训练也就成为他们未来在其他行业工作的拓展训练。
总体而言,数字化对创意写作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既蕴含了挑战,也提供了契机。从教学方法层面看,新媒体创意写作对既有作家障碍的克服和突破,也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路径⑤葛红兵、高尔雅、徐毅成:《从创意写作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意本质论及其产业化问题》,《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从此出发,我们可以借助新的数字技术进一步完善并解决这一问题。而对于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创作主体的虚化、文本边界的模糊、写作伦理的含混等突出的问题,这些引出的正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与重新定义文学本质的话题,需要在学理层面作进一步的探究。这些问题既是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产物,也是当前文学与文化研究交叉领域的焦点之一,同时从学科内部来说,又构成了当前创意写作研究兴起的现实基础。
五、结语
乔治·加勒特在《创意写作项目的未来》(The Future of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一文中曾指出,对于创意写作的未来发展而言“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将来需要适应新技术和时代的变化”⑥Joseph M.Moxley eds.Creative Writing in America:Theory and Pedagogy.Urban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1989,p.60.。回顾创意写作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经历了多次转向,每一次都从时代发展的前沿汲取自身需要的资源,成功地完成了多次自我更新,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活力。尤其是当前新媒体与创意写作融合发展过程中,作者身份的跨产业重构、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教学方式的数字化改造以及数字化对创意写作研究的影响成为突出现象,这都要求创意写作逐步走出学科的自我封闭,与数字叙事、多模态写作等创作实践结合,以便更好地迎接新一轮的数字转向。
从2009年至今,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与研究的历程已有十余年,其间已经形成多元化的不同发展路径,创意写作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在这一态势背后,除了文学教育改革、文化产业这些宏观背景,还存在创意写作的数字化这一重要问题。可以看到无论是之前北京大学强调的“培养具有高水平写作能力和创意才华的应用型写作人才”①《北大中文系设创意写作专业,揭何为“创意写作”?》,《人民日报》2014年2月13日第12版。、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创意写作与新媒体”方面的课程、学位,还是上海大学开设的网络文学方向的创意写作学位、浙江传媒学院“媒体创意”“网络文学”专业、温州大学“创意中文”专业对创意写作能力的重视,都不能轻易脱离这个背景。新的创意写作课程设计、新的专业打造,无论是强调网络文学人才培养,还是提高创意型作者的多媒体写作能力,都需要将新媒体这一因素纳入考量范围。
考虑到当前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作者身份的跨产业重构、文本类型的跨媒介衍生、课堂教学的数字化改造以及对这一现象的理论研究的增加,创意写作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尤其是在“文学的创意化转型”②葛红兵、高翔:《“创意国家”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文学的“创意化”转型及其当代使命》,《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这一层面,对新媒体与创意写作融合发展的研究,对寻求数字时代创意写作中国化发展的新路径都有重要意义。以新媒体与创意写作融合发展为契机,推进创意写作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带动创意写作与既有学科资源、理论话语的进一步整合。这既是当前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与海外展开前沿对话需要做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