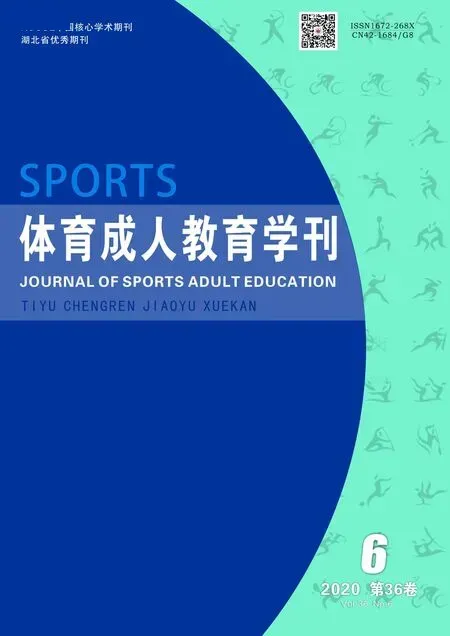生态补偿理论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以天等打榔为例
王成科,宋晓宇,胡江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近年来,“文化生态学”中的生态补偿理论思路初步运用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马冬雪(2018)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永续发展的内部机制为调试机制和补偿激励。通过打造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转换项目传承、传播的形式和社会功能,建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补偿激励机制,能够实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1]。唐大鹏等人(2014)提出要将传统文化、地域民俗、生态理念有机结合,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生态元素,传承和发展中原传统文化精髓,拓展体育文化内涵,构建和谐生态健身路径,以提升体育文化软实力[2]。
1 天等打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构成与环境要素
天等打榔主要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县内不仅具有完整的打榔舞蹈队伍,同时设有天等打榔民俗馆,笔者深入天等县展开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定性观察、地方县志研究、实地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式,从特征点入手全面了解天等打榔的核心构成与环境要素。
1.1 核心构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构成主要以其诞生之初的本性为研究重点,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天等打榔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探究其在特定文化与社会结构下的起源与发展。天等打榔已经有1 300多年的历史,2007年被列为天等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8年入选崇左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10年,天等《打榔舞》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18年,崇左市在“魅力中国城”勇夺冠军,天等《打榔舞》也在城市魅力的展示环节中大放异彩,为全国观众所熟知。打榔舞道具木榔是用一根长约六尺、直径二尺的大木凿制而成的大木槽,表演者不分男女老少,有二人对打、四人对打、多人交错对打等多种方式。当《打榔舞》的音乐响起后,每人用一米多长的木杵有节奏地敲击榔壁、榔底和榔边,动作欢快有力,节奏稳重,声调若鼓,闻于数里,以此表达壮族人民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幸福吉祥的祈求和渴望。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天等打榔这项体育舞蹈的核心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祈福,他们迫切希望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期望带来更愉悦的精神享受。
1.2 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延续的外部影响因素总和,其中包括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及民间制度等,同时也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组成等要素[3]。人类的行为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与支配,原生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符合其初始的社会价值观[4]。在通过对当地民众和传承人的访谈中发现,自然环境等生态要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当地民众张佳佳认为,天等打榔具有较强的文化基础,不仅壮族居民会参与到打榔活动之中,当地各个民族的群众均愿意参与表演和观赏。民众宋德霞认为,天等打榔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及民俗活动,更是人们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向往与追求的重要方式,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够参与到打榔活动之中,这也使得天等打榔具有了更强的吸引力。而民众刘林则认为,天等打榔由一种民间体育舞蹈活动逐渐转化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其从现实意义先符号意义转变,虽然打榔依然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环境也迫使其必须顺应社会发展做出调整和改变,保证天等打榔能够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俗专家张爱天在访谈中表示,广西天等地区的历史环境、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共同塑造了打榔这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环境要素发生变化,天等打榔的保护在保持与时俱进的同时也要逐渐回到原生态状态,真正将原生态体育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保留和继承下来;天等打榔的文化传承人刘武久表示,原汁原味的天等打榔是我们必须要继承和发扬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风土人情等因素直接影响到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现行状态下的环境并不是最优环境,保护措施与保护政策并不能够完全契合天等打榔文化遗产继承发展的需求。
2 天等打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2.1 基于社会环境变化的文化加工模式
不同内容与形式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天等打榔利用民众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元素和方式展开体育舞蹈,表达舞蹈者内心的情感。随着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天等打榔中的很多内容已经不再符合当前的表演需求。例如一些封建迷信残余及不符合精神文明的内容应该进行适当调整,但与此同时也要保护天等打榔的民族性与主体性,将传承的要素始终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使其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文化加工模式不仅能够强化天等打榔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能够有效利用生态补偿理论对内在核心进行整合与重塑,真正还原呈现原生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憾[5]。文化加工模式不仅需要传承人与当地居民的参与,更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效介入。
2.2 基于文化内核转变的文化移植模式
天等打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丢失现象,某些舞蹈动作和舞蹈节拍的含义无法得到准确认定,同时配乐方式及舞蹈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当地政府与传承人可以在相关资料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天等打榔的表演模式,将民俗文化全面重建,在保持旧有元素的同时也要适时引入新元素,这也可以视为同源文化的移植。文化内核的转变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天等打榔在传承过程中并未发生显著的文化内核改变,而如何在原有文化内核缓慢改变的情况下对文化遗产做出调整和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高校、传承人及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我们开展文化移植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为了有效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围和力度[6]。
2.3 基于全面培养重塑的文化重建模式
文化重建是一种彻底打破固有文化表达模式的构建方式,天等打榔的传承较好,当地居民对打榔拥有非常全面的了解,但是很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却出现了断层情况,广大民众对其缺少了解,不知道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全面重建是这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的首选方式,当地政府要积极鼓励探索和整理相关文化元素[7],拨付专项资金并组织人员重新排练,同时引入传统体育文化元素和现代体育文化元素,将核心构成与环境要素展开整体性的重建,使其重新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旅游产品,确保游客与参与者均能够产生较强的兴趣与认可度,进而吸引游客融入体育活动之中,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构建更加优质的环境。
3 天等打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启示
3.1 准确把握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与边界
原生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与边界,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重要内容,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定位在原始的、静止的文化范畴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认知范畴。文化的生态应该是当今的、交互的、发展的、变化的并且聚焦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现在及其未来的价值[8]。原生态体育的概念容易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臆构成“少加工或不加工”的凝固态文化思维形式,违背了文化发展变迁的基本规律,使文化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成为无生命活力的呆板文化,最终走向消亡的命运。而生态补偿理论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强调的是文化的活态性、生态性及多样性,而主动、积极、创新的保护思路是与其相适应的。
3.2 树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生态观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及发展大环境受制于经济贫困、人口迁移、社会分工、社会发育程度等综合因素,并非是单一影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最终综合产物。传统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容易误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导向政府扶持、财政补贴的单一取向,造成一味追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状态,从而让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停滞不前,造成文化遗产本身一直“贫困”发展这一难题。生态补偿理论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其保护和传承是微观的目标,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是中观的目标,促进其拥有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宏观的目标。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摒弃传统封闭守旧的原生态思维理念,树立与时俱进、开放共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观,从而构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发展模式。
3.3 围绕市场需求构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模式
现代社会,人们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异文化更加关注,贴着原生态标签的各种身体运动文化十分流行,这些构成了原生态体育商业推广的首要前提。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环境恶化、工作压力、身体健康等问题,使城市人非常向往尚未现代化的农村。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有观赏性、参与性、情感性、趣味性等要素,构成了原生态体育商业推广的基本条件。基于生态补偿理论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充分了解和把握市场需求脉搏,迎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使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够产生更为显著的效果。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