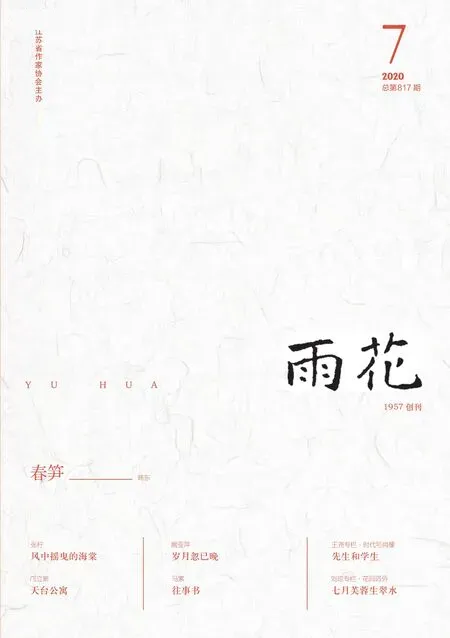董先生
董老师,董幼卿,字德庸,号蕉窗,又号燕堂。幼承家学,苦志吟哦,积古风词曲等三百余篇,辑为《燕堂吟抄》一集,已刊行矣……什么乱七八糟的!董老师今天想来,这真是一堆垃圾,一文不值;还有什么字呀号的,统统都不要,他只要“老师”这两个字,可是熟识他的人却似乎不这么理会他。
“董先生,早!”
“早,早……”
这已是一九五二年了。星期一的早晨,董老师照例早早地出门,去乘从县城开往砻坊镇的早班汽车。他是该镇砻坊中学的语文教师。从家里出来,一路上就有人喊“董先生”,董老师一路应着,心里虽不太愿意别人这么称呼他,可别人的语气中并无贬义,脸上恭敬的神色分明,董老师唯有默认自己是“先生”。至于他心里,是早有主张的:这是新社会了,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该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才对。再说,学校的领导又没有偏见,那么理解他,处处照顾他,如果身处这么好的社会环境,居然还有什么拿捏不住的事,造成不良的后果,那也只能怨他自己了。
董老师有什么难以拿捏的事么?
唉,董老师有两个老婆!
董老师逢星期一赶早班车是铁定的事,可班车发车的时间却并不准时,而且多半只晚不早。至于客车的质量,当然也难称上佳,中途抛锚是常有的事。董老师最怕的就是这一点,虽然赶不上学校的早操时间也不至于有人为难他,可因为自己的一点特殊原因,动不动迟到,总不是件理直气壮的事。经常的情形是,他人刚下汽车,额上已先急出汗来;因为,他又一次人还在路上,已听见操场上响起广播体操的口令声了。
董老师不由得连奔带跑起来。
这么说吧,董老师是砻坊中学全体教职员工中,唯一可以不在星期天傍晚到校,而延至星期一早晨到校的人。人所共知的原因,董老师不是一夫一妻,家中比别的老师多了一位太太,别的老师周六回去住一晚,董老师需住两晚,因此只能延至星期一的早晨到校。其余的日子大家都住校。做出这一决定的人是杨校长。杨校长长者风范,恻隐之心有之,为了服众,也杜绝一切有害的闲言碎语,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婚姻法,像董老师这样由旧时代造成的婚姻,如果其中一位妻子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只要到民政部门登记就行,有关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等要求,也将获得法律的支持。但如果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两个妻子都不愿解除,也可维持现状。董老师的情况属于后者。杨校长肯定董老师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学有所长,古文功底尤其扎实工作表现出色,是新社会合格的人民教师;对董老师那点特殊情况,老师们应当宽谅,为他保密,尤其要对学生保密,因为孩子们还小,不扩散超过他们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事,对孩子也是一种保护。
怎么着,事情说简单也简单,就这丁点事嘛。
董老师是一个重点生活在星期一的人。星期一对他来说是个备感压力的日子。
他经常赶不上早操时间。学生已站好队了,他才气喘吁吁赶来,众目睽睽,情何以堪。甚或,他的人到了但早操已经结束,同学们开始回教室了。更多的时候,是他一路小跑着赶来,当当当!出操的钟声敲得正急学生如一股决堤之水,呼啸而出,几乎要将他吞没。董老师站稳了,喘息着,似乎要逆着这股潮流而动,赶到自己的办公室去;这时候老师们也都出来了,就夹杂在这呼啸的学生潮流当中,有老师朝他挥起手来,意思是操场,操场!董老师愣了一下,恍然大悟似的,立马转身,也变成人群中的一员——毋宁说,他其实是被这股潮流推着走的。
“董老师,早!”
“早,早……”
这是一九五二年的春天,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董老师到校稍迟,但总算赶上了早操的时间。这时,“决堤之水”正从校门口涌出,他有了经验马上转身,也往操场而去。一旦融入这股潮流中,董老师也仿佛有了自信,开始边走边维持起秩序来,让同学们别挤,慢慢走。教师么,爱护学生,维持必要的纪律和秩序,乃是一种职责。
“大家别挤,慢点走,当心摔倒!”
砻坊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一共九个班级。学校的操场,是一块五亩地大小的场地,跑道上铺着煤渣。眨眼之间,刚才的“潮水”不见了,全校四百多名学生已站成队列,像是种在操场上的一棵棵树。这些树在等一股风——由体育老师何志仁发出的口令——一声令下,马上迎风起舞。
何志仁老师身穿运动衣,身体笔直,脸上星星点点的麻子,略显严肃。
“现在做第一套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一年多了,但学校受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扩音设备,每天的早操都由何志仁喊口令。何老师是师范学院体育专业毕业,标准的科班出身,五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还很匀称,标准的体操动作,十分中看。一年中,无论春夏秋冬,只要站在早操的队列前,他一定穿这身蓝色的运动衣,袖子和裤管上四道白杠,让砻坊中学的学生天天看不够。
这所学校的学生,全部来自周围的乡村和集镇,不少学生春夏秋三季都不穿鞋,一双赤脚什么样的路都能对付。做踢腿运动了,乌黑的脚掌朝你亮一亮,马上不见,因为双手抱膝,身子蹲下去了。跑步时,嚓嚓嚓,无数的光脚板踩着那些煤渣,仿佛这就是最好的跑道。当初铺设跑道时,董老师还担心煤渣会硌孩子的脚,提出是不是该加加工,结果不到一周,那些鸽蛋大小的煤渣,都被同学们用脚掌磨碎了。
学生做广播体操,班主任老师站在自己班级的队列前跟着一起做,其他老师在整个队列的后面做。
董老师在初二(3)班的队列前做操,已不气喘了,十分努力的样子,还时不时扭转脖子,查看后排可有站着不动,或马马虎虎对付的学生。
董老师四十不到,实际看老一些,略胖,穿一件已经泛白的竹布长衫。有同学说,董老师穿长衫、戴眼镜的样子,有点像“五四”时期的一位革命前辈。董老师听后,一副惶恐不安、愧不敢当的样子,连连摆手,让同学们千万别乱说。唉,怎么说呢,这所本地有名的初级中学,固然由他父亲长源公一手创办,但他坚持在这所学校任教,绝不是居父辈之功,坐享当一名人民教师之荣光;恰恰相反,他是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改掉身上的旧习气(例如什么古风词曲、字呀号的之类),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众所周知,董老师其实是有机会到教育局任职的,局长几次提出让他到教育局当督导员,也便于他照顾家庭,但他经过考虑,还是决定留在这所学校工作。别的不说了,父亲一手创办的学校,如果自己也离开了,怎么对得起已经故去的父亲!
董老师近时觉得,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自身体质,确有十分之必要。自己年纪不大,小跑便喘气,身体也开始发福,因此,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推出的第一套广播体操,他打从心底里拥护。但他做广播体操,因为患有颈椎病的缘故,又仿佛须处处小心。他的颈椎,平时还好;在不警觉的情况下,一扭脖子(比如身后有人喊他),会突然感到一阵晕眩,须得赶快将脖子返回到原来的状态,才能解决问题。弯腰提鞋也要小心。这不,刚才他提了一下鞋,就又出现那样的状况,不过,很快又缓和过来了。
广播体操做完了。
往回走的时候,气氛轻松多了,大家有说有笑的。也有不是初二(3)班的同学,簇拥着他走,像跟他特别有缘的样子。一个塌鼻子小萝卜头,有天对他说:“董老师,你衣服上一颗纽扣脱开了。”董老师一看,说:“啊,是的,是的。”赶忙扣上。是腋下的一颗布纽扣——他穿的是长衫——最吃分量的那颗,刚才做广播体操,受力的牵动,脱开了。可还是这个小萝卜头,另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竟在校门口拦住他,问他:“董老师,别的老师星期六回去住一晚,星期天就到校了,你为什么要住两晚?”董老师想也没想就说:“这都是旧社会害我的呀!”塌鼻子小萝卜头偏问:“旧社会害你什么了?”小眼珠望着他,像在期待一个最佳答案。董老师叹一口气,说:“唉,你们现在还小,还不懂旧社会的害处,真是说不完呀!”这时小萝卜头笑了,别的同学也都笑了他们的样子,分明像在说,什么他们还小,还不懂,嘿,懂得很呢!
事后想想,他觉得有点不对,不是说好了,学校为他保密的么?怎么弄得孩子们也知道了?是谁把这事张扬出去的?
早操之后,例行的工作是打扫卫生。这是星期一,办公室尤其该打扫一下。董老师在语文组,但这也是大致的划分,音乐老师、地理老师和历史老师也在这间。另一间以数理化为主,但其他负责劳动、图书室和花房的老师,也在那一间。教音乐的张静娟老师抹桌子,一定先从别的老师的桌子抹起,抹一张搓一下抹布;一张一张地抹,最后才抹自己的桌子。周子善老师提着个喷壶在洒水,陈菊英老师扫地,还有两位老师在擦窗子只有教初三语文的汪韵溪老师,今天像遇到紧要的事,捧着本字典,和一本打开的线装书对照着,在查一个什么字。陈菊英老师扫地扫过来,他抬一下脚,张静娟老师抹桌子抹过来他抬一下手,眼睛仍不离字典和线装书——一切都表明,汪韵溪老师今天遇到了紧要的事。
董老师也赶快投入到打扫卫生中,看中墙边一只痰盂,端出去倒掉再清洗。
董老师虽然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可是对于打扫卫生这类事,向来认真。他把长衫的下摆撩起,扎在腰间,这样干活也利索。道理很简单,共同的工作环境,每人有一份,该做的事情大家一起做。不过,有几次,汪韵溪老师的说辞,连同对他特别的照顾,让他感到尴尬。依然是星期一的早晨,董老师走进办公室,一看大家在搞卫生,立马提起一只装字纸的竹篓,要去倒。不料汪韵溪老师却说:“董老师,您歇着。”夺过了竹篓。董老师转身拎起两只竹壳水瓶,要到学校的老虎灶灌开水,又被汪韵溪老师拿下,仍说:“董老师,您什么也别忙。”那样子,仿佛董老师回家住两晚,已出尽非常之力,十分辛苦,现在该好好歇着了。汪韵溪老师说话之间,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还不忘向同事们挤一下。董老师虽然深度近视,但汪韵溪老师的表情,他是看到了的,只觉心里有股子气恼,不知道该冲着谁。汪韵溪老师嬉笑和挤眼的表情,人人都看到了,人人也都没有呼应他,但董老师心里还是感到气恼。唉!……
大概一刻钟工夫,办公室打扫完毕,老师们埋头做起了各自的工作。这时候是早读时间,从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也有老师到自己的班级去看看。汪韵溪老师忽然放下字典——他去老虎灶灌了两瓶开水,仍捧着字典细细研究——说:“明白了,明白了。”周子善老师问:“明白什么了?”汪韵溪老师环视一下其他老师,指指手边另一本打开的线装书,亮一下封皮,是后主的《李煜词全辑录》,说:“上周六的晚上,有位邻居老先生,非要来跟我探讨,后主的这首《菩萨蛮》,其实是为小周后所作。我才疏学浅,一时倒也无言以对。当晚我细读后主的这首词,又查阅相关资料,方知邻居老先生所说,完全正确!……”
老师们一愣,意识到汪韵溪老师今天事出有因,一早晨的铺垫,像是要引到一个什么话题上去。
汪韵溪老师说:“后主的这首《菩萨蛮》,明写小周后的真率之态,暗写后主的左拥右抱。后主娶有貌美的大周后,又对小周后垂涎三尺,这首词便是他和小周后偷情的自供状。你们看:花明月暗之夜,词中的这位女子,‘刬袜步香阶,手提金镂鞋’,就是说,为了和她的情郎幽会,蹑手蹑脚,把鞋子也脱下来了。紧接着,‘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恋’——露骨的表白!有现场感!前人有评,后主词乱头粗服,不掩国色,这首词便是最好不过的佐证。刚才我是查……”
这所学校的老师,倒也不是随便凑合,都是有资质的。说白了,以前,他们便是合格的教师,学问之外,也有为人师表之范儿。老师们看汪韵溪煞有介事的样子,愈加相信他装模作样的背后,必有另外的意思要表达。因为,像他这样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怎么会连后主这首《菩萨蛮》也没读懂?
汪韵溪老师五十出头,家也在县城。稀疏的头发,常年抹着凡士林。他是有些旧学功底的,也爱填几首词,因为心性和习气的关系,颇多香艳之词,同事们颇不屑。吟咏起古人的诗篇来,着重点也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这类句子,志得意满的样子,仿佛他就是周公瑾。老师们私下里说,若论旧诗方面的功夫,他连当董老师的孙子都不配。现在他提到邻居老先生的见解,被老师们选择性地忽略,大家琢磨的仍是他到底要表达什么,躲藏在他镜片后面的目光,闪烁难辨,总仿佛不独在于情色,还有他意。
汪韵溪老师说:“刚才,我是查‘刬袜’的‘刬’字,本是作‘削平’解,这里的‘刬袜’只作‘以袜着地’解。必须指出,词中写到的这位女子,固然狂野,可俗话说,一只巴掌拍不响,至于另一个……”
老师们不动,屏住了呼吸,相信汪韵溪的另一个结论快要出来了。
汪韵溪老师说:“唉,说起来也是可怜,已经是一国之君了,搞个一妻一妾还偷偷摸摸的,远不如今人来得……”
“哗!”
一声脆响,大家吓了一跳,一看,董老师捧起教本、教鞭和粉笔盒站起时,衣袖带到桌边的茶杯,玻璃杯子落地,打碎了。董老师也愣住了,像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闹出这么个差错来,竟然没有注意到手边的茶杯,又像一切终归还是自己的错,行事不慎,杯子落地,把老师们吓了一跳。
“对不起……”
董老师像清醒了,想到要打扫地上的碎玻璃和水迹。待要去拿扫把和簸箕时,却见张静娟老师早已在忙不迭地打扫了。张静娟老师声音很轻只说:“董老师你去教室,这里我来。将碎玻璃片扫入簸箕,又拿拖把来拖地。董老师望着张静娟老师忙碌的样子,又愣了一会儿,竟没有说声“谢谢”,也就走出去了。
汪韵溪老师也一愣。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
“唉,怪我,怪我,是我不好。汪韵溪老师也便做出醒悟的样子,收起那本《李煜词全辑录》,说:“看来董老师这一拂袖——如果不是不小心的话——是多心了。我无意中提到大周后、小周后,他多心了。怪我说话不慎,不及其余。嗯,少了点恻隐之心唉,都是那位邻居老先生,非要和我探讨什么后主词……”
这时候,老师们纷纷收拾好教本教鞭,起身。
董老师来到外面,并没有立即去教室,而是在一个花坛旁坐了下来教本、教鞭和粉笔盒放在旁边。这个花坛,正对着校门,显眼的是一棵五针松,一人多高的身量,却是老干横枝、历尽沧桑的样子。还种着些花草四季都开出花来。董老师选择在这里坐一坐,是想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一种不恰当的心情(可别带进教室去)。这种心情,与他人无关,多半还是自身固有的,郁积于胸久之,不知道该对谁气恼。
不过,他平时也爱在这里坐一坐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这其中有个缘故,他身后这棵五针松,是当年这所中学的奠基日,由他的父亲长源公手植。如今长源公已经去世。如今董老师是一名新社会的人民教师,在这里坐一坐,听一听满校园的读书声,能亲身感受到父亲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作为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者,自己心里也有一种安慰。
这棵五针松,教育局的领导到学校视察时见了,十分重视,指示为它设计一个花坛,加以保护。杨校长说,长源公捐地建校,罕有的大手笔,值得地方百姓和全校师生铭记。按杨校长当时的想法,似乎还应该在校园里立一座长源公的半身塑像,以彰显他对地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激励广大寒门子弟发愤读书。董老师得知这层意思后,连连摆手,说:“使不得的!使不得的!”这才作罢。他的真实的想法是,父亲虽然建校有功,但总而言之还是有些问题的,人人心里也都明白,适当的纪念可以,过分张扬万万不可。
也因为这一缘故,董老师有时在花坛旁坐久了,也会联想到自己,似乎和他的父亲长源公一样,也是有些问题的。他总觉得,这所学校的其他老师,个个称职,唯独他是不怎么称职的。他的预感也有些不好,总觉得家里那点破事,还不能算就此结束,还会发展,很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唉!……
董老师的家,在县城博爱路八号,一座私家花园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如今已搬进许多住户。把多余的房子献出来,让无房的人住进去,是父亲生前最后的心愿。那是普天同庆、万象更新之时,这位前清光绪年间的举人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长源公中举而不仕,志在耕读传家,当然所谓的“耕”,也意味着他其实是个大地主,大量田亩在砻坊镇一带,由广大的佃农“耕”,他自己不必“耕”。现在分田分地也在紧张进行中了,对于董老师来说,心理上其实并无困难。董老师写得一手娟秀的小楷,到时候如果要他帮忙填写土地证的话,完全可以,而且非常能胜任。
娶二房是遵父命。因为正房嫁过来五年未育。世上的事都一样,正房门当户对,也是有根基的人家;二房就随意些,闾巷人家出身,但年轻漂亮。二房嫁过来也有几年了,董老师至今仍未有子嗣,他一度怀疑是自己的问题。
从去年起,董老师为了退掉其中一个妻子,可说是心血耗尽,身心皆空。在他看来,退哪一个都行,抓阄也行,只要还他一个“一夫一妻”便可。可是,别说抓阄了,董老师哪怕磕头、哀告、哭泣(他是哭过的,哭得珠泪滚滚,痛心疾首),都没有用,两个妻子的不离不弃之心,坚如磐石,休想撼动。奇怪的是,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本来还有点磕磕碰碰的,自从提出要退掉一个后,竟变得和睦起来,形同姐妹(说准确点,是面对严峻的局势,变得团结了)。家务分担着做,对董老师的母亲尊爱有加,老太太的脸上时常挂着笑容。这样的变化,着实令董老师有点看不懂了。
董老太太几次说起:“幼卿,都是好媳妇呀!你看这一阵,我什么也不用忙,什么心事也没有,脸上也胖起来了。”
母亲身体变好了,董老师当然高兴,可是再一想,仿佛不对,母亲心宽体胖,是阶段性的现象,万一有一天——比如说,到了“另一个阶段”——母亲的身体不怎么好了呢?
董老师是个大孝子,在“退掉一个”的问题上,母亲的身体已然成为一个参照值,就是说,即便“退”,也要做到皆大欢喜,老太太两害相权取其轻,依然保持心宽体胖。
事情一度有所松动,两个女人高调谦让,牺牲自己,保全对方。一个说:“要不我离开吧。”另一个说:“不,还是我离开吧。”这下董老师犯难了,仿佛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一个也不愿放弃。事实是,二太太是先被他带到民政部门办离婚的,二太太签过字了,轮到董老师签了,二太太的眼泪一下涌出,董老师心软了,对民政部门的人说:“她其实心里并不情愿,还没有想通,我再做做工作吧。”收起了协议。大太太的情况也一样。总之,离“退掉一个”只差一步,否则的话,“一夫一妻”早就实现了。
两次到民政部门办离婚,两次无功而返,董老师突然想到,一向自认为有板眼的他,其实虚伪得很。斩钉截铁的誓言,清坚决绝的口气,仿佛统统是用来表演给别人看的,而他自己早有主意,早有设计好了的方案到时候轻轻一笔带过。
不知怎的,这些有关家庭秘事的消息,又不知是谁、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传到学校,引发对他个人品质的质疑。如果传到学校的消息说,留下的是大太太,马上有舆论说:“贪财罢了。”如果消息说留下的是二太太舆论又说:“贪色。”如果事实证明最终一个也没有退掉,那当然是,“既贪财又贪色”。
董老师贪财么?贪色么?
事态发展到最严峻的阶段,董老师曾横下一条心,发下毒誓,两个妻子的房间一个也不进。你们看着办吧董老师说到做到,从贮藏室搬出一张钢丝折叠床,架在母亲的房间,从此就和母亲合住一个房间。至于老太太的脸色,好看不好看,他也顾不得了那些日子家里冷冷清清,几乎一整天也听不到说话声,但似乎正朝着他心中的目标接近。
意外出现在一个月之后,二太太病了,持续高烧。上门诊病的是附近诊所一位有资质的医生,与董家长期交好,相当于董家的私人医生。药开了,挂水要挂好几瓶。董老师是发誓不进她们房间的人,当然是由他的母亲去照顾。董老太太去照顾儿媳妇不是在那里倒一杯水、坐一刻的问题挂水需要人看护着,水挂完了,如果旁边无人,当事人又睡着了,血液回流到吊瓶内,那是要出大问题的。董老太太看护了两晚,渐渐感到吃不消白天也睁不开眼,上眼皮和下眼皮一直打架。
不能让大太太去照顾二太太么?不,大太太很快也病了,一样的病状,一样发高烧,就好像谁在什么事情上跟不上趟,落下一步的话,谁的命运都不好说。
老太太伺候两个儿媳妇,心里积了一股子不平气。二太太生病的第三天晚上,老太太发话了:
“幼卿,是你娶的媳妇,你媳妇生了病,要我上一辈的人伺候?”
董老师一惊,他听母亲说话的口气,不像一般的怪怨,而是有点声色俱厉的味道。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向来温婉大度,疾言厉色从未有过,他觉得母亲这次是发怒了。
董老师吓坏了,一声不响,马上住到二太太的房间,尽一个丈夫的责任。紧接着,大太太病了,他也得住过去,他不能照顾了一个不照顾另一个,一碗水得端平呀。
等到两位太太的病都好了,董老师想再住到母亲房间去时,却见老太太端坐不动,那张折叠床也不见了。董老师又是一吓。老太太是小脚,走路颠颠的,董老师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搬动那张钢丝折叠床,把它放回到贮藏室的。
这样,理所当然——本来规矩也破坏了——董老师又自动回到以前的生活当中,两个房间轮着住,星期六一晚,星期天一晚。
他感到奇怪,这两个女人,一前一后生病,怎么那么巧?如果是传染病,他和母亲却无恙,那几天母亲累成那样,也没有生病。而且,她们的病都不是装的。
当年的这座私家宅院,有个不大的荷花池,还有一座假山石。外面的住户搬进来后,进出不愿绕这个荷花池,大家一商量,就把假山石的土石移过来,把荷花池填了。填也填得不很严实,主要是中间填出一条路,进出之间方便。有天晚上董老师到院子里散步,皎洁的月光下,见到原荷花池残余的水塘里,竟探出两支荷花来,在斑驳的树影里明明灭灭。董老师觉得不对,这是不应该有的景象,但居然出现了。
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董老师坐在校园的那个花坛旁,依然满耳的读书声,董老师却在心里骂着,无耻啊,无耻!董老师本不会骂人,现在也开始学着骂人了,骂的是他自己。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两个妻子都怀上了,像暗中较着劲儿似的,谁也不落后谁。董老师没有别的话说,唯有在心里一遍遍地骂自己,无耻啊,无耻……
董老师离开砻坊中学,是在翌年的四月,属于病退性质的离职。这非常令人震惊,他的精神出了问题,不能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了。事实是,他后来有许多时间是在医院度过,好一点出来,过一阵又进去。一发病就说:“我是一夫一妻!我现在是一夫一妻制!……”见人就宣布。
诱因是从县医院打到砻坊中学校长室的一个电话,董老师的一个妻子,由流产引起大出血,到医院抢救,没能救过来。这是四月里的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杨校长放下电话,立即找人商量,该如何安抚董老师,以最恰当的方式,告诉他这一不幸的消息。有关他妻子后事处理等事宜,学校也打算派人全程予以协助。
有一个细节,竟然被大家忽略了。不,还牵涉到医院,医院也被蒙在鼓里,就是死去的到底是董老师的哪一个妻子。通常来说,妻子是唯一的,大出血的那位,由董老师的母亲和另一个妻子送去,医院视她们为患者的亲属(这没有错,但他们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其实也是董老师的妻子)。病人不治后,董老师的母亲和另一个妻子吓昏了,只会说死者的丈夫是砻坊中学的老师,名叫董幼卿。学校方面疏忽的原因是,既然患者不治是由流产引起,董老师应该清楚怀孕的人是谁,选择性地忽略了另一个妻子也怀孕了。是的,之前董老师一遍遍地骂自己“无耻”,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董老师在校长办公室最初的反应,符合常情,就是失声痛哭,涕泗横流。但接下来,他有一句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好人啊!……贤妻啊!……跟了我这些年,也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
他竟然没问死去的是两个妻子中的哪一个。既然没有问,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无论死去的是他两个妻子中的哪一个,一律是他眼里的好人、贤妻。
然后,他两眼发直,像要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仿佛有一种光荣,本不属于他,在高高的云端里,可望而不可即,现在从云端里落下来,落到他身上,属于他了。董老师脑子转过弯来了,以很确定的语气,说:
“我是一夫一妻!……我现在是一夫一妻制!……”
董老师一下来了劲头,猛地起身奔出去了!
关于这个星期三的下午,董老师在砻坊中学校园里的全部表现,许多人都是目击者。同学,老师,还有学校的校工。很多年后,他们还向人们讲起,当年他们就读和工作的砻坊初级中学,有一位老师,名叫董幼卿的如何如何。
董老师先奔向自己的办公室。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位老师,首先是汪韵溪老师。他奔到办公室了,冲着汪韵溪老师的办公桌喊:
“我是一夫一妻!……我现在是一夫一妻制!……”
办公室里空空如也。这时已到放学时间,老师都在班上处理班务。
另一个办公室也没有人。
他似乎想起,有个塌鼻子的小萝卜头,一副嬉笑的模样,也应该通知到他。他奔到教室的走廊上找一间一间找过去,学生突然呼啸而出,像一股决堤之水,要将他吞没“我是一夫一妻!我现在是一夫一妻制!……”他呼喊着,恍惚之间,只觉得眼前的学生个个都是塌鼻子,都是小萝卜头。
他一个激灵,奔到花坛那边,“决堤之水”不奔涌了,打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变成围住他的一汪活水,推着他,在校园里这里涌一下,那里涌一下。
活水推涌着他,渐渐到了传达室那边。他想起来,那天塌鼻子小萝卜头问他“为什么回家要住两晚”时,打铃的校工昌华,仿佛在一旁捂嘴笑。昌华也是他要找的人。
“当,当,当……”
钟声悠扬,校工昌华在一下一下地扯挂在大槐树上的钟绳。放学了。
他望着满眼的人,同学,老师,校工。太好了,不用找了,人都在。
“我是一夫一妻!……我现在是一夫一妻制!……”
杨校长和几名老师走过来,其中有两名老师,是杨校长安排他们陪他回县城的。杨校长说:“董老师,汽车票买好了,是末班车,时间还有宽余,你到我办公室再休息一会吧。”他点一点头,说:“车票买好了?”杨校长说:“买好了。”他说:“好的。”这时,他感到有点累了。
他到这时也没问死去的是两个妻子中的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