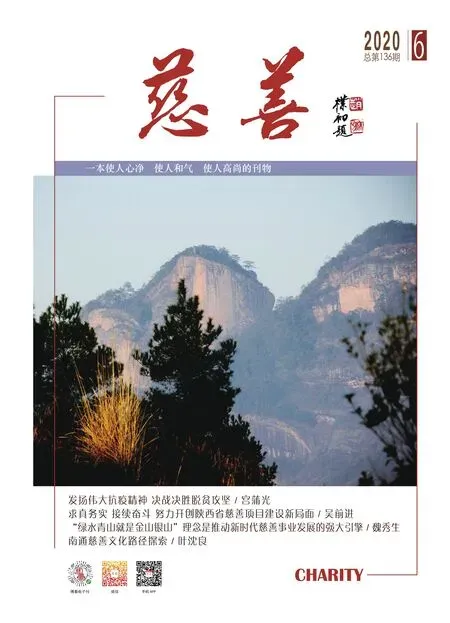半棵桑树
文/刘国林

儿时,常跟同村的小胖在一块儿玩。突然有一天,小胖装了满满一兜兜黑乎乎的东西给我看。为拉着我跟他多玩一会儿,塞给我一把。那毛茸茸的粒子,黑里透红,有半个花生角那么大。吃到嘴里,软糯糯的,酸里带甜。小胖爸爸在附近造纸厂上班。家里有钱,这东西是他爸爸去城里买的,说是叫桑粒。我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尝到,感到很新奇。
回到家,当美事跟母亲说了。不料却遭到母亲一顿责问:“在外面,可不能馋嘴,随便要人家东西吃。”我辩解说:“没有,是他缠着我玩,硬塞给我的。”母亲笑笑,没有继续说什么。
那天晚饭后,母亲心情大好。圆圆大大的月亮刚刚爬上天,我偎依在母亲膝下又提起白天吃桑粒的事。“要是咱们家有棵桑树就好了。不用花钱到外面去买,每年都能吃到。”母亲接过我的话茬儿说:“桑粒像樱桃一样,好吃,但树难栽呀!听说,要由大鸟先把桑粒吃下,消化后再便出来,落到地上,遇到合适的土壤、水分和阳光,才会长出树苗来。咱家要想长出桑树,就得碰运气了。谁知啥时候,有吃过桑粒的鸟从咱这飞过,正好把桑粒籽便在咱家园子呢?等着吧!”母亲当故事讲给我,而我却没有只当故事听。从那以后,就天天盼着有大鸟从天上飞过,正好便出桑粒籽,落在我家园子里……
说来也巧。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果真在我家后园子边上神奇地长出一棵桑树苗!那是和母亲在园子里拔杂草时,我第一个发现的。经母亲辨认,千真万确是桑树苗,就长在与邻居裴家交界的秫秸杖子里!我高兴得几乎蹦起来。自那以后,每天早晚都要看一遍,并在它周围插上干树枝,做了记号。还特意告诉家里所有人:“谁都不能随意给拔掉!”
就这样,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小桑树苗已长到2尺多高,浓绿的枝叶,很是壮实。而我担心它越冬时会被冻死,还特意用一捆谷草给它围起来。母亲见了说:“它没那么娇气。它要是不能过冬,北方咋会有桑树呢?”我相信母亲说的话,但还是担心失去这棵“宝贝”树。
又过了两年。在第3年头上,这棵桑树苗终于变成了桑树。长到一人多高,已和我们两家分界的秫秸杖子比肩了,而且穿过密密实实的杖子缝隙分出许多枝杈。更令人惊讶的是,进入6月后,竟在浓绿叶子的遮盖下长出了一串串桑粒!不知是害羞见人还是怕被鸟吃掉,藏得严严实实,反正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母亲说,桑树结果至少得3年。果真如此。虽说第一次结的桑粒个头不大,数量也不多,但成熟时还是挺好吃。这味道与几年前村里小胖送给我的那把桑粒一样鲜美,酸甜可口。
采桑粒那天,我特意把小胖找到家里来。既是向他显摆我的成果,也是作为一种回报,真心实意地请他尝尝。
短短几年间,这棵桑树,长得又粗又壮。枝杈更多了,树冠直径也差不多有七八米。夏季里遮天蔽日,人们都可以搬着小板凳在下面边唠嗑边乘凉了。那树干有小碗口粗,虽说和裴家分界的杖子在一条水平线上,但越长越偏在我家这一边。因为树冠很大,桑粒成熟时,自然会落在两家园子的地上。裴家的孩子们在靠他们家那一侧的园子里,也随时捡着吃。开始时,两家谁也没有太介意。母亲也常教育我们说:“都是吃的东西,别太小气。小孩子哪有不馋嘴的。”所以,每到采摘季节,还常打发我把桑粒分装在小筐里,给包括裴家在内的左右邻居送去尝尝鲜。
不过,我知道我们与邻居裴家关系不是很好。按村中习俗和辈分,我还向他家男主人叫大舅呢。但这户人家个性较强,平时跟谁家都很少说话和交往。很自然,我们与他家的孩子们也来往不多。前些年,记得春天菜苗刚出土时,他们隔着杖子把鸡扔过来,一眨眼工夫,就把我家园子里的菜苗吃得精光。母亲急了,心疼得直跺脚,抓住他家的鸡便找上门去理论。裴家的主人非但不道歉还蛮横地说:“牲口那东西想吃啥,人怎么管得了!”母亲回击说:“牲口不懂人懂啊。有人看见,你们是故意隔着杖子扔过去的,咋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再说,如果是鸡自己飞过去,就该把鸡膀子剪短一点,既不影响下蛋,也不会祸害人……”对方无言以对。自那以后,两家便结下了“梁子”……
该发生的事迟早会发生。一天早饭后,我们一家人正准备下地干活去,裴家的那个“大舅”气哄哄地找上门来。刚进院子就扯着大嗓门吼道:“你家后园子那棵桑树得赶紧处理,影响我园子长菜!不动,我就把它砍了!”吼罢,转头就走。这哪是商量,分明是通牒呀。还好,他没有提桑树的归属问题,我还以为他要来抢这棵桑树呢!心想,“这棵桑树也通人情,起初还扎根在杖子中间,后来越长越偏向我家这边。裴家嘛,还算明智,想抢也不占理。”
两家本来就有“梁子”,这一闹,此后会更不平静。古语说,“好亲不如近邻。”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但砍掉我是难以接受的。每年能吃到甜甜的桑粒不说,毕竟费了多年心血把它养大,人树间已有了感情!但仔细想想,乡下人生活主要靠土地,寸土寸金。园子的地就更精贵。抛开裴家矫情不说,树冠一大,罩着园子也确实影响作物生长。看来,真的要拿出个解决办法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要不,就下决心砍了吧。说不定哪一天又弄出点别的事来。咱脑瓜皮薄,惹不起躲得起。”父亲在一旁蔫头抽着旱烟,一声不吭。“有啦!我倒有个办法。既能保住桑树,又让他们说不出啥来。”说完,没等母亲问我啥主意,拿起锯子便向后园子奔去……
桑树下,我脱掉鞋子,爬了上去。不大工夫,就把靠近裴家的那一半树冠齐刷刷地锯掉了,等于给这棵桑树理了个阴阳头。
说来也怪。被我锯掉半个树冠的这棵桑树,这一年不但没有死,也没受到多大伤害,还长得挺茂盛,桑粒也没有明显“减产”。只是靠向裴家那一面,枝条不再生长了。年复一年,远远望去,这半棵桑树,就像一位把秀发甩向一边的少女,经风历雨,亭亭玉立地竖在那里。每到夏秋交接季节,桑粒成熟了,紫色的,黄色的,半红半紫的,多姿多彩。让人看了,总会产生强烈的食欲。每每这时,我都要在树底下铺上一块干净的苇席,腰间别上一根木棍,脱下鞋子爬到树上去,用棍子轻轻地把桑粒打落,又尽量不伤害枝叶。当然,少不了边打边吃。而且挑选长得又胖又长水汪汪的颗粒填入口中……吃了个水饱之后,爬下树来再收拾那落满苇席的“战利品”。那一刻,那种丰收的喜悦之情,真是无以言表。
更令人心安的是,自那以后,邻居裴家再未上门来找什么麻烦。每年打下来桑粒后,按母亲吩咐,照例给包括裴家在内的左邻右舍送些过去。不过,我发现,裴家人的态度似乎比先前有些变化。每当接过我送去的桑粒,说话客气了许多,脸上似乎也流露出一丝愧疚的表情。
不幸的是,就在我锯掉半个树冠的那年初秋,桑粒熟了的时候,裴家的男主人病了。得了一种乡下人叫不上名字的怪病,半个头疼,一卧不起。他们全家人整天唉声叹气,“阴云密布”。这一年,在那种气氛下,我们再也没有过去送桑粒。后来听说,我叫大舅的那位裴家主人,临终前,心里感到无比忏悔。每当见到去看他的人便没完没了地嘟囔:“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是隔壁她刘老姑(指我母亲),那是个明事理又能干的女人。是我做了许多缺德的事,对不住人家,对不住人家啊……”说着,还忘不了提到那棵有争议的桑树,“房后那棵桑树,其实也无……无大碍。是我故意找茬儿……告诉他们……以后别再锯了,随便长吧,半个脑袋不好看!”
裴家男主人出殡那天,母亲不计前嫌,一大早带着我去了。向这位老邻居作最后告别,我们没有照例参加吃饭,但却随了一份厚礼。
大约在1961年前后,我家这幢土坯房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于是,决定向公社申请新的宅基地,由村子前街搬到后街去重新建房。这时,我也离开居住近20年的故乡,到县城去读高中。这半棵桑树,在搬家时,不得不被砍掉了。
后来,听母亲说,在砍掉老桑树时,将在它的根部附近一棵小桑树苗又移植到新家那边去。这棵小桑树苗,是否也由大鸟吃了桑粒再便到地上长出来的,不得而知。
新房建起来以后,我的确曾见过母亲移植过来的那棵桑树。但在那之后,还没等它结出桑粒来,我已经考上大学远走他乡了。岁月沧桑。转眼间已离开故乡60年。此后,再也没吃过家乡园子里长出的桑粒。但那写满故事的半棵桑树,仍然深深地留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