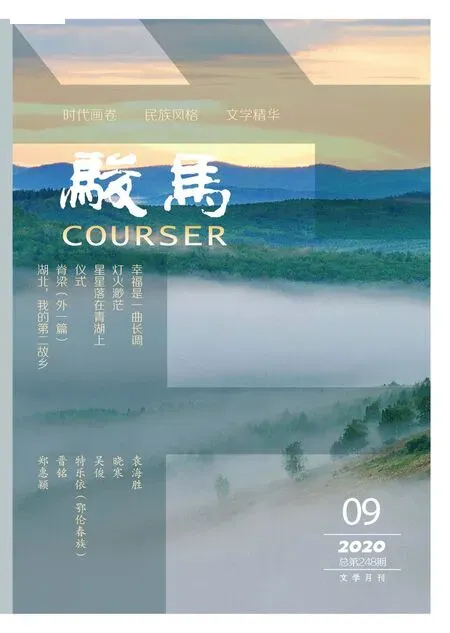星星落在青湖上
■吴俊
托娅趴在木杖子外,喊着我的名字,荒草埋没她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透露出恐慌,“你家马打滚把我家草场刨烂了,阿爸要找你们算账呢。”我蹲在房檐下无精打采地抓着泥土,佯装听不见。
母亲刚刚点起柴火,炉膛火正旺,炝锅油花嗞啦声从屋里传出来。门口吵骂,厮打声越来越大,两个男人抓抱在一起,在地上滚动,草垛被他们扑腾得一片凌乱,父亲被那汉子按压住,抡着粗壮的胳膊捶打。我拎起一截木棒冲了过去,我的腰突然被箍住,后背被狠咬了一口,是托娅,这臭丫头,甩开她的时候,看到她满眼泪水,像是水晶破碎,闪着光,装满无辜。
托娅脸蛋肉嘟嘟的,两颊布满红血丝,像云霞飘浮着,那时总是不愿跟她说话,宁肯对着空荡的天空、蚂蚁巢发呆,或者就看草丛随着风晃动,她鸟雀般叽叽喳喳,嗓门大,语速快,本来挺宁静的草地,一有她,几里内全是人一样。
“哥哥,哥哥,你看我捡到个什么。”我转身看,兴奋烧得她满脸通红。“不过是个破瓷瓶嘛。”我不屑地应和。她端在手中,泥巴沾满那碎作一半的瓷瓶,她用袖子拂去泥土,显露出流线的衣袂,纤细的手指拈着翠绿的水草,眼睛半眯着投向远方。我边说着,边要过去夺那瓷瓶,托娅连忙护住,连口说道,“她一定是有神灵的。”
傍晚的那一幕,我们真觉得天都塌下来了,见过羊和羊顶架,马和马撕咬,那么亲近的人动了刀子,真是吓人。幸运的是,当我们战战兢兢回到家门口时,淡淡的光从窗子透出,里面响起了雄浑的歌声,两个男人喝得一团火热。
第二天,再去草地玩耍时,我们说好把那瓷瓶埋在草地深处,让她永远保佑草原水草丰美,所有人都开心快乐地生活。
那时候日子总过得很慢,勒勒车在风霜雨雪中静止不动,就像天空的云让人看得厌倦,虽然不断变幻着形态,不过是填充那空白的天空。
听大人说,托娅的妈妈跟一个牛贩子跑了。我们再去找她玩时,她总是把门关得紧紧的,眼巴巴看着我们一帮一伙在疯跑、追逐、打闹,她那爱凑热闹的性子,像被按住双角的羊,只有四蹄蹬跶的份儿。如同此刻她掐着我的脖颈,我在酒桌上抖擞她小时候那些可笑事,托娅红着脸愠怒,“还说不说。”我连连求饶,过了这么多年,托娅还是那风风火火的劲儿。
这是我们相隔很多年,我带着扶贫攻坚的任务,再次来到呼和诺尔小镇,见到托娅的情景。
入驻下来,小镇一排排砖房整洁齐一,水泥街道平坦干净。当托娅来到我宿舍时,我说,“我都快认不出咱们镇子了。”她说,“没有啊,还是那样子,我不还那样吗?”她哈哈笑了起来,接着说,“你来的正好,咱这儿看个差不多的病都要去几十公里外的海拉尔,你要好好为家乡做点事儿啊……”她这话让我有些无措,支吾道,“没,没,就是工作……”
关于时间的词语,在陈巴尔虎草原说出时,总会让人感慨,浮满虚幻的浪漫与感伤,有了退却浮沉的轻松与懈怠。
接下来几日繁忙的会议和工作安排,还来不及亲近离开多年这片生养我的故土。当困意很浓,辗转不能入睡时,雨泼水般淹没着呼和诺尔小镇,简陋的宿舍,屋顶铁皮叮当作响,透进屋子浓烈的牛粪和青草的味道还是那么亲切。
托娅带着七岁的姑娘,在一处住宅改的门脸里打扫,墙壁布满霉点,地面还是土地,小姑娘收拾杂物,托娅擦洗着遍布灰尘的柜台,我站在门口好久了。
“呵,真是勤快呀,我都站了半天了,也不让进屋。”
托娅抹了把额头的汗说,“哎呀,领导来了也不说声,看这屋子乱的,都没地方下脚,蕊蕊,快过来叫叔叔,去烧水沏杯茶。”
“快别忙活了,我帮你也干点活。”我挽起袖子,端起盆子,帮她去换水。
“这不镇里鼓励自主创业,我去城里上了几期药士培训班,办下来个药铺的执照,自己找点事做。”托娅停下手中的活说道。
“挺好挺好,这个对百姓有益处,自己也有个长久的营生。”
她叹口气说道,“没办法,维持生计呗,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养牛放羊的,很多重活也拿不起来,不像你呀,城里的大医生,有知识有文化……”
我连忙打断她的话,“你这才是真正的‘脱贫’创业的典型啊。你说,我们来到这儿坐几天诊,在卫生所上几堂课,水平能提高多少,回头我得跟市卫健委好好反映下,得大力支持民办医药行业呀。”
她神采奕奕地说,“那时候咱们一起在医士班,我太不靠谱,不好好学,回到家后,学的那点东西都就着青草喂牛羊了……你说现在开个药铺,又得重新学起,这OTC、处方药、蓝帽保健,感冒消炎发烧的倒是懂,毕竟放了那么多年了,遇到问题总得去卫生所药剂师那儿,问这问那,人家都不正眼看哟,买了一堆书,学起来也费劲儿。”
扶贫工作有序地进行着,调研、讨论、基层卫生服务的完善提高,每周出三个门诊,空余的时间很多,没事时我就去托娅的药铺。这几日她的店面收拾得已经很有模样了,墙壁已经贴了白壁纸,地面用旧地板铺得那么工整,柜台整齐一排,贴着指示牌,我在心里暗暗佩服她的能干。药进了几箱,分门别类摆放上去,托娅穿着白大褂,说,“心里突突的,没底。”我说,“没事,我帮你坐镇,你会做得很好的。”看着她严肃的样子,觉得真是可爱,平时在医院忙忙碌碌,不觉得这职业有什么,托娅穿上白大褂坐在那里,既熟悉又陌生,那么亲近又那么遥远。
那年,父母带着我搬离了呼和诺尔小镇,去了一个不远的城市,那里有楼房,街上有车子,有电影院和百货商场。离开了这夏天泥水路,冬天雪窝子,牛羊腥膻,永远单调的草原时,托娅扭扭捏捏拉着我的衣角,塞给我一支蓝色的自动铅笔,转身就跑掉了。那时自动铅笔是珍稀的文具,上面的图案我还记得很清楚,她那眼睛潮湿的瞬间,就像发生在昨天。羊群拥挤着啃食青草,草叶上的脉络与水珠,阳光打下来的温度和味道,还停留在身体里……
思绪蔓延着,托娅用肘部推了下我说,“赶紧吃呀,是不是菜不可口呀,这段时间你帮了我这么多,也不知怎么感谢你,你在镇卫生院的工作够忙了,还在我这帮忙,我可没客气呀。”她哈哈笑着,端起杯子,我也端起杯子说,“祝你的药铺越来越有起色,你这么能干好学,以后肯定能经营得越来越好,听说现在有专长的医学资格考试,你可以试一试,能抓药又能看病,来就诊的才会更多。”她说,“我能行吗?”“你行的,去年第一批确有专长考试都有下证书的了,你有基础,我在这半年可以给你补补课。”她说,“真的吗?记得你小时候就爱学习,不光学习好,还爱看话本、故事书,懂得特别多。有一回,你拿家里一桶奶换了几本破话本,被你爸一顿揍,我还笑话你书呆子,打得真狠呢。”我说,“还有这事?”我支支吾吾,遮掩自己的丑事……天色黑透了,一轮暗红的月亮,沉甸甸压在窗边,离我们那么近,里面白兔眼睛的眨动,斧子砍桂树卷起的木屑都如此清晰。
我踉踉跄跄走在呼和诺尔小镇,眼前还晃动着托娅忧伤的神情,她那些年经历的不幸,针刺般扎在我心里。母亲跟人跑了后,他阿爸心情郁闷,天天酗酒。托娅虽然读了医士班,十多岁也不懂前程,被阿爸拉回家里,当做男孩子使唤,放羊、打草、捡粪全得做。一到黄昏,烧柴的烟雾漫布时,她阿爸早已经喝得大醉,趴在桌子上打着呼噜,嘴角流涎,磨着牙,她抱着双膝坐在门口,一直到风吹透身体,才回去倒头睡下。漆黑笼罩这片草地的感觉,跟她的心情那么相似,要是一直就这样,偎依在黑暗中,多好。可天总会亮,往复这无尽头的生活。
后来,她阿爸肚子胀得像个大锅,卫生所说看不了了,一次啃硬奶酪,大呕血离开了,那年她十八岁。长生天赐予人间雨露、奶汁和美酒,青草扎下根,荣枯生息,托娅也是这草地里,最卑微的一根野草,默默生息。
那天傍晚,药铺来了个五十多岁的顾客,一下栽在椅子上,脸色苍白,说浑身无力。托娅急奔过去扶住他,他说给他抓个补力气的药,再这样就不行了。托娅被这情形弄慌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我给他倒了碗水,耐心地问了起来,“大爷,你感觉怎么不好?”他说,“憋闷啊,腿像棉花一样,家里人也不给看,我只能自己来这了。”我看了下他的眼结膜,贫血。“你这是血色素低,没去医院看吗?”他说,“你是干嘛的,在这啰哩啰嗦,我就问有没有补力气的药,你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说些没用的话,解决一点儿病了吗,就知道吸老百姓的血汗钱……”
托娅被他说的话气得直抖,说道,“谁卖假药了,不买药赶紧走。”我轻轻按下她的肩膀,叫她坐在一边。
“大爷,喝口水,您别激动,现在我就给您找几个治您病的药。”我走到架子边,拿了盒参芪扶正颗粒和补中益气丸。“大爷你看看这个对你的病吗?”他接过来,看了一眼,“啪”地扔到地上说,“你们都是骗子,我就死在这得了,没人能治得了我的病。”他拍了拍前胸,“吃不下东西了,都堵住了,脖子的瘤子压得全身发麻,头疼得快要裂了。”听他说这些我大概知道了。
“大爷你是不是食管癌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对对,就是这病,活不了了。”他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我坐在他旁边,轻轻拍拍他的手,“大爷你别难过,我是市里医院来咱们这儿看病的大夫,您这病没有那么可怕,不要一听是癌症就像是被判决了似的,现在这病是多发病。你要学会跟瘤子共处,你看你发脾气,认为自己不行了,不吃饭,身体肯定受伤害,正气越来越虚,你要心情好,好好养身体,瘤子就不敢猖狂了,好好保持,肯定会好起来的。”他听着眼睛有了点光亮,拉住我的手说,“你说的这些,还有点道理。”
“是吧。”我起身把那两盒药再次放在他手里,“明天你去卫生所,我再给您好好瞧瞧,给您补补血,您就有力气了,好吧?”他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真的能好吗?”老人大口喘息着,眼神那么的渴望。
“能,你好好听医生的话,会好的。”
当我们扶着老人送出门时,仿佛他真的有了些力气,不再那么绝望了。托娅带着钦慕的眼神看着我,“你真行。”我说,“也不是,可能我说的不客观,不符合病情发展,可是咱们要给病人信心和希望,治病首先要治心。”
她打断我说,“行了,行了,城里来的大医生就了不起了,我要超过你……”托娅拉着我的手,高兴得像个孩子。
风轻轻吹动着草地,天空蓝得如一块巨大宝石,几丝云浮在中央,像托娅垂下的发丝,随着青湖的波纹,荡漾向远处。
“我也是有过爱情的。”她撕碎草叶,撒向湖水。
“那年我十八岁,从香河来咱镇一个青年,跟你一样,像个书生,说话文弱温柔,来完工站做什么考察。我在车站卖茶叶蛋,他跟我搭话,问这问那,问站东的水塔,我就说从记事起就在那。他就跟我讲曾在这里发生的战事,讲车站的来历,我哪听得进这些,看着他蹲在煮茶炉旁,鸡蛋剥了一个又一个,边说边吃,一阵阵打嗝。我实在忍不住,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就打嗝更厉害,做着可笑的表情,我就推他,说赶紧走吧,要不我就笑岔气了。”
“他说我长得真好看。”
“每天他都来买茶蛋。我跟他说,这里牛羊肉更香,奶茶喝上一口你就会忘不掉。他说,就喜欢吃茶蛋。”
“渐渐我们就熟识了,一起去草地骑马,湖边捕鱼,他还带我去海拉尔城玩。那段时光真的很快乐,后来他突然不告而别了,过了三个多月我总是吐,才知道已经怀孕了。我知道我多么爱他,他也一定那么爱我的。我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倒客车,来到他无意说过他在的那个地方,可他的态度完全变了,推搡我,踢打我,让我滚开,骂我乡巴佬,说他有老婆孩子了,说我在讹诈他,就塞给我几十块钱,气哼哼地走掉了。”
“从小到大我第一次那么难过,坐在地上号叫、哭喊,天都塌了,地都裂了,人们围了我一圈。好心的大娘拉我,我撞她,咬她,可能那些人认为我是一个疯子。我真的疯了,真的不要活了,心铁疙瘩一样掉出来了,我真想马上飞到呼和诺尔草地,把自己埋到土地深处,或是让湖中的鱼儿把我吃个精光。你知道吗,我有多么恨自己,就有多么爱他。”
“我可没他那么坏呀,还说像我。”我听她讲着,离现在那么遥远的往事,托娅咯咯笑起来,“谁能说得好呢,所有男人都一样吧……”我看到一丝虚无,从她漂亮的眼睛飘过。
来呼和诺尔小镇三个多月了,医院的扶贫支援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照例开会,帮助开展一些适合当地的医疗项目,完善相关科室的管理制度,定期出门诊,为当地乡亲诊病。
托娅的药铺也一步步走向正轨,顾客越来越多。她非常用功地学习,准备报考十月份的确有专长资格考试。很多时刻,眼前的托娅,还像儿时的那个小女孩,大大咧咧,却有着如水般的柔情,仿佛跨越过的三十多年,我们不曾离开过,还是每天一起去草地撒欢,或者想这永远不懂的世间。有时又感觉她那么陌生,我们可能从未相见过,一切只不过是虚假的想象。
她一本正经地问我,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的关系是什么,问我补液量的计算方法,总要加个老师的称谓,老师这,老师那的。我就逗她,“咱俩一点儿不像师徒,倒像相濡以沫的伴侣。”她就哈哈地笑,“想什么美事呢。”
七月的草原蓬勃盛大,无限的绿色,让人满心舒畅,呼吸着清鲜的气息,萨日朗的红艳火苗般浓烈,金莲花的澄黄沁人心脾。在草原久了,整个人就归属于大地,所有的感情同每棵草、每朵花消融在一起。
烦心的事情还是来到了,托娅日日进学,充实奋进时,区里的飞行检查,来到了呼伦贝尔。盟市镇药监部门,给了最后通告,不能出一点儿差错,正值脱贫攻坚最后的时刻,各行业都要严阵以待。
托娅坐在那里唉声叹气,像是大难临头,对着上百条条款无计可施。“经营面积加库房要一百平,咱这小门面五十平都不到;计算机系统要做到药品全程追溯,咱的电脑嗡嗡响比牛都慢,根本达不到;处方要求审方管理、处方备案,到哪里弄那么多处方……后天检查组就要到了。”
“我医治看病懂,这药监巡察真不懂呀。”我安慰托娅,“不要着急,咱们也是刚接触这行,车到山前必有路。”
托娅说,“咱们付出这么多辛苦,刚刚有点上手,要真给查封了,就全完了,你看看这些条款,一条条要求高得离奇。”
“我托朋友问问巡察的要求吧。”
“真的能问到吗,你现在就打电话。”她摇晃着我的手臂。
我斩钉截铁地说,“好,现在就问。”
很多我们所认为难的事情,当努力去做时,发现想象的困难其实都是夸大了的高山。经朋友的帮忙和指点,我们连夜做表格,补记录,建制度,设职责,把软件和资料突击做完时,天都蒙蒙亮了,腰酸背痛,写得手指生疼。
“真是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她给我捶着背。
“这也是我扶贫的任务呀。”
她咯咯笑着说,“让你‘扶贫’我来了。”
“你比我的工作还艰巨和重要那。”我说。
“你可别乱说了,咱们还得抓紧把硬件弄好,排风、空调、防爆灯、鼠夹,一大堆事情。”
“咱们会做好的。”我举起拳,做加油的姿势,托娅露出真心的笑容,“谢谢你。”
“困意来了,睡会吧。”说着她倒头趴在桌子上,细微的鼾声就响起了,我轻轻给她盖上衣服,她身上散发出馨香,让我一阵眩晕,她脸庞的宁静,看上去真美。当我轻轻关上门时,天边投射来一道刺眼的光线,这是黎明之光,希望之光,也是爱之光吧。
检查组来时,我们都紧张得要命,脑袋里全是那一条条的条款,组长是个胖胖的蒙古族汉子。
“陈巴尔虎草原是我的家乡那,草原深处也有了正规药房。”他严肃又亲蔼地说道。
柜台上摆放着一摞摞文件材料,他翻了几本,连连点头,进了里间,库房标识没条件做硬塑的,是托娅裁纸手写的待验区、合格区、不合格区、退货区,勾画着花边、有胶囊图、草叶图,还有几只简笔羊羔,组长笑出声来,我们又是一阵紧张。
他停顿了几秒说,“这才是草原特色呀,我们草原虽然没城市那么发达的物质条件,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一个多小时的检查,起初的紧张氛围全消了,端起了奶茶,聊起了家常,一片其乐融融,送出门口时,组长说,“我给你们打九十分,那十分扣在医药知识上,你们虽然回答得很好,可是草原欠缺的就是知识,要努力提高业务,更好地服务群众,我为你们,也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
当检查组车子走远时,托娅上来紧紧拥抱我,竟哭了起来。
“检查这么顺利,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还哭了呢?”托娅说,“两天两夜你陪着我,感谢你。”
“真是傻姑娘,只要认真努力,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她说,“我说的是真的。”
草原上有许多野菜,婆婆丁、车轱辘菜、马齿苋菜,刚吃的时候很苦,细细品味起来,却是香的。那种有滋味的香,就像托娅,真的觉得她不容易,可时间久了,她如车辙样的粗线条里,是金子般的光芒。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扶贫收尾总要加班,做总结报告,诊治数据统计,到嘎查义诊讲课。好些日子没去托娅的药铺了,她已经能独挡一面了,我坚信即将来的资格考试,她一定能顺利通过,也就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少去打扰她的生活了。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托娅。
车子一路颠簸,让人昏昏欲睡,路过青湖,我分明看到湖中央有无数的天鹅,洁白宁静,随着波光晃动。托娅在湖边,脚踝在湖水里晃动,她说,水的声音多好听,她轻轻咬着一片草叶,说青草的味道真香。只有这片草原,才能让人心安静,所有破碎的灵魂会重新完整,我紧闭上眼,无数的星星落在青湖上。
很多年以后,呼和诺尔小镇作为乳业、牧业模范基地,我再次参会来到这里。不多的几条街,拥挤了好多家药房,当路过托娅的门口时,一片欣欣向荣,隔窗看到她微笑着、忙碌的身影,我想停下来,可一转瞬,一片楼房遮住了我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