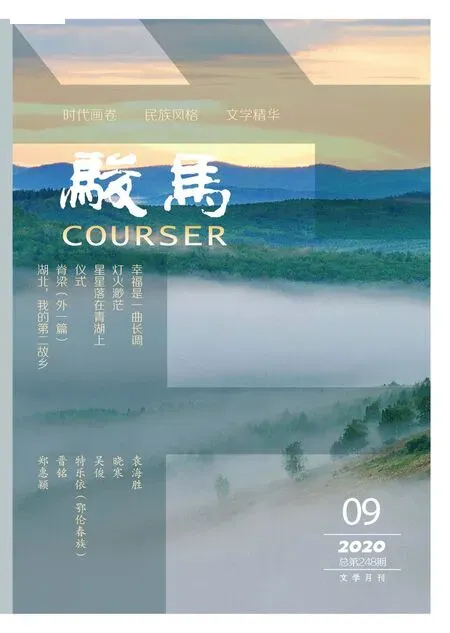奔赴和别离
■曹阳春
老李嗜酒。闲日,中午连晚上,甚至延到夜里,一顿接一顿。酒后,话题亘古不变:去远方。并非胡侃,右手还端着酒杯,左手已订了机票。这些年,湖南、甘肃、青海、新疆、泰国,皆酒桌上的一时兴起。
又在酣饮。说向往西藏。众人劝他,西宁的高反都把床睡歪了,别提入藏了。他拗了起来,阿里高,林芝低,林芝总可以吧!没直达,那重庆转机。第二天上午,他的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牦牛广场的照片,定位林芝八一镇。
他去了比日神山。在山崖下,看见了镀金的小佛像和几堆贡品;在树杈上,看见了白色哈达和刻有藏文的羊头;在寺庙里,看见了一圈转经筒和几十只鲜艳肥硕的公鸡。他去了巴松措。斜倚栏杆,穿过眼前的村落,与雪山湖泊遥遥相视;坐在白塔的光影里,煨桑炉慢慢散开的烟雾,从鼻子底下飘到了经幡顶;由观景台远远望去,粼粼水波上的湖心岛,慵懒得像个婴儿。他还去了秀巴古堡。一埋首,钻进了古堡肚子里,不为别的,只想听听历史的回响;脚一踩,是兵营的石片和城墙的残垣,屏息细闻,好像听见了将帅的号令和士卒的呐喊;寂寥与荒芜中,他一个人,站在土地的记忆里,站在生命的断层里。
老李这浪漫和高效,叫人佩服。老李说,浪漫全是自己的,高效嘛,有他人相助。他人指刘师傅,三十出头的四川男人,胖胖的,叼着烟,寡言少语。以前在老家开车,出了事,便背井离乡,一路来到了林芝。还是川牌轿车,底盘很低,与满大街的越野格格不入。挡风玻璃裂了一米多,没换,说要等下一个保险期。老李打车遇见了刘师傅,一个为了游历,一个为了养家,两人各取所需,成了临时搭档。
八一镇的暮色,来得要晚一些。内地六点就黑透了,这里直到八点,不借路灯,尚能看清酒馆招牌。老李的餐桌上,是离不开酒的。青稞酒上了,石锅鸡上了,松茸菌菇也上了。酒后的高原,睡眠极其饱满,连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雨老李都没察觉。清晨,太阳初升,刘师傅早早把车停到了门口,车里车外整理了一番,蹲在路牙上,静候老李。老李还呼着呢,刘师傅也不着急,八一镇人稀活少,碰见个大户,等多久都得等。
老李出门了。刘师傅箭步笑迎,一只小背包,也伸手去提。“今天到大峡谷吧,我想看看雅鲁藏布江。”老李坐在后排说。刘师傅一句“好嘞”,油门一加,把车开进了山间的流云。云很低,闪着清光,像一簇簇盛开的昙花,有的差点要亲吻地面,有的落到了牦牛的脊背和尾巴上。老李看着窗外,尽是新鲜风景。有佛掌沙丘。大量沙子从周围吹过来,贴山临江,越积越多,越垒越大,成了一块巨型玉佩,别在喜马拉雅山的腰上。有玛尼堆。山间、路口、湖畔、江边,到处都是,藏民不断往上面叠石子,虔诚地用额头碰触它们。有快速生长的沙洲。或是光秃秃的,白白净净,任由沙石飞走落下;或是黑森森的,茂密的树林和成片的灌木,铺满了所有肌肤。可这些,在刘师傅眼中,算不得风景。公路挂在悬崖上,感受不到最高是多高,也感受不到最低是多低,在这全世界最深的峡谷里,他唯一能做的,是认真开车,安全开车。
回到八一镇,老李第二次提出要去措木及日。昨天来晚了,票房正准备下班。此刻光照炽烈,附近的午宴还没散场,却也不能游览,说人凑不齐,开不了景交车。老李破口狂喧:“冰点的人气,罕见的凋零!”刘师傅倒心平如水,轻轻地问了句:“下面去哪儿?”老李长叹一声:“回酒店。”
又下了一整夜的雨。老李起得很早,朝后排一坐,“米堆冰川,住察隅。”这七个字,干脆。脸上的表情,一夜过来,似乎完全修复了。刘师傅乐呵呵的,一句“好嘞”,直奔海拔4720 米的色季拉山口。这是老李平生翻过最高的山口,因为时间短,也没多大反应。下了山,便是鲁朗。栅栏、牛群、田畴、民居、山冈、树木、白塔、吊桥,一切都映在湖里,水面上下清晰对称。老李喜欢这情趣,不停拍照,不停录像,满身兴奋,四处乱跑。
抵达米堆之前,还经历了通麦天险和排龙天险,亲眼目睹了四个大拐弯。老李更加兴奋了,百度以后,主动跟刘师傅聊,聊当年的艰辛,聊窗外的奇峻,聊自己的见识。刘师傅偶尔“嗯”一下,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午后,天气极好,米堆冰川的每一个细节,都向老李纵情开放。奔跑了三四个小时,回到车上,老李兴奋到了顶点,没说过话似的,一个劲儿地跟刘师傅聊。他说,看米堆冰川,得看五道。一是人道,两旁有三百多株三百多年的古杨树,黄色的叶子背后是白色的冰川,那色彩对比,强烈;二是水道,河流穿行在杨树林里,性情急,流量大,那震天的声响,隔老远依旧真真切切;三是马道,由乱石铺成,上头积了厚厚一层干粪,风一吹,山谷里都是清新的草木味;四是牧道,一条最清幽的山道,不宽敞,没形状,却是牧民和牦牛们每天必须打卡的;五是冰道,落差八百多米,自上而下,超级垂直,凝固的瀑布一样悬在冰川的胸口。每说完一道,刘师傅都礼貌地“嗯”一下,不过老李好像也没听见,只顾自己的满足了。
由米堆前往察隅,一路逆流相伴的,是帕隆藏布江。江水撞击石崖、撞击树根、撞击铁桥,每一次撞击,浊浪都翻得很高。江源在然乌湖,这湖反而文静,不咆哮,没脾气,安安稳稳地躺在几座雪山脚下。湖岸,是不加修饰的田园风光。一块块方格里,麦子已经成熟,藏民们正在收割,麦秆被堆在高高悬起的木架子上。这里的屋顶,有蓝的,有红的,齐齐整整地镶嵌在更加齐齐整整的黄色麦田里,像极了童话书里的插页。
过了然乌湖,开始翻山。海拔渐高,人烟渐稀,呼吸也觉得困难了。从3000 米,迅速攀升到4900 米,因为前后没有光亮、没有村庄、没有声响,经过德姆拉山口时,老李表现出了异常的恐惧。他说,不要赶到察隅了,一百多公里,还要三个小时呢,碰见村镇,立即投店。老李对住宿向来考究,可在恐惧面前,大概一间破旧的小旅馆,他也能欣然接受了。刘师傅没吭声,想抽支烟,换了三个打火机,都没点着。车内车外,氧气骤减了许多。
老李的烦躁,分秒激增。也难怪,无人区太长了,下坡路和上坡路也太长了。不停地有坑坑洼洼,得刹车。不停地有滚石落石,得加速。在山间盘旋,一会升顶,一会跌谷,老李真怕自己摔到悬崖底下去。他一句接一句地唠叨,埋怨这,埋怨那。而刘师傅依然不吭声,只管开车。
进察隅县城,已是子夜。本计划明日继续往前,去看珞巴族,看他们的寨子。可这么一折腾,老李突然失去了方向。电话响了,几天没动静的电话,在下半夜响了。吴超打来的。“老李,看你朋友圈,到察隅啦!我在丙中洛,正好跟你在丙察察的两头,来我这!”吴超的电话,像一场及时雨,把老李的浪漫和激情又浇灌出来了。“丙察察是经典的自驾线路,丙中洛是人神共居的地方,从丙中洛到丽江只要两三个小时”,吴超补充的每一句,都击中了老李。“体验,值得体验;向往,值得向往;出发,一早就出发。”老李自言自语,兴奋了一夜。
刘师傅却不乐意了,“这车底盘低,不能跑,再说了,出门也没带换洗衣服。”“加钱,加多少,现在就加。”老李早已迫不及待。一听加钱,刘师傅愣了下,与老婆视频后,立即改口:“跑!上车!”反向穿越丙察察,就这么开始了。
说是公路,其实只有路基。老李和刘师傅,将要共同面对的,是转圈,持续的转圈;是翻越,持续的翻越;是颠簸,持续的颠簸。前六七十公里,一直在原始森林里打转。半山腰朝下看,是清冽蜿蜒的溪河,是黄绿交错的田野,是火柴盒一样的屋舍。朝头顶看,古木遮天蔽日,枝条上缠满了白色蔓衣,像老树的胡须,像山色的胎记。老李打了个盹,海拔就抬至4706 米。森林的高度,到不了这里,它们的家园,只能在脚下很矮的地方。一圈圈绕下去,出现了牧民和村庄,出现了牦牛和草原。可刚到谷底,又抬至4498 米,人牛草木又都消失了。下了垭口,再一次,森林渐密,村舍渐稠。还没缓过神,第三次抬升已在眼前,左拐、左拐、右拐、右拐,方向盘转得更加频繁了。大部分路段缺少栏杆,离轮子一两米,就是千丈深崖。偶尔有栏杆的,也被巨石砸得稀烂。从这4636 米向下,一路都是灾难片,台风、海啸、地震,这世上最凶险的灾害都像昨日刚刚来过。峻极的山,终于翻完了,刘师傅底盘的凄怆,仍在嚎叫,大声嚎叫。老李淡定地看着窗外,看目若村的圆木房子,看让舍曲的翡翠水流,看怒江边的落单孤马。刘师傅却满腹哀叹,一句接一句:“车废了!车废了!车废了!”
晚九点多,过滇藏界。吴超在小镇上,把火锅安排妥了,白酒啤酒排满了桌子。老李见到吴超,见到这位再熟悉不过的朋友,居然久别重逢似的,在丙中洛的夜色中,深情拥抱了起来。几日劳顿,几日起伏,于这一刻,熬到了尽头。他们快意吃肉,他们用碗喝酒,还时不时地,敬一下刘师傅。可刘师傅愁容难掩,一脸心事,从头到尾,连筷子都没拿。
刘师傅问哪里能加油,吴超说丙中洛没加油站,唯一一个是军用的,民用得去县城,四十公里外。刘师傅问哪里能修车,轮胎漏气了,底盘划破了,方向盘不灵了,吴超说这么多毛病,那得去县城。刘师傅问回林芝哪条路最近,吴超说要么从四川绕,要么原路折返。刘师傅张了张口,似乎还有问题,却没敢说出来。老李早喝多了,“人神共居”重复了十几遍,桌上的对话,他一句都没听见。
第二天凌晨,星斗闪烁,刘师傅设好导航,一个人上路了。而老李,鼾声如钟,美美地睡到了十一点。下午,吴超开了辆越野,带老李畅游丙中洛。去了怒族的翁里村,去了江中的桃花岛,去了山上的普化寺,老李孩子一般,又扭又跳,各种自拍。晚宴很热闹,吴超在丙中洛的朋友都来了,大家纷纷向老李敬酒,老李特开心,说明天中午到丽江接着喝。“丽江?明天中午到丽江?”桌上忽然安静了下来。“这里没法到丽江,包辆车,也得十几个小时。”老李傻了:“不两三个小时吗?”吴超半开玩笑地说:“不这么讲,你会来?”
吴超的公司,在江苏,效益不错。这两年,他常驻丙中洛,正做一个项目,扶贫的。丙中洛的确偏远,通往外界,没一条像样的路,更不用说水运、铁轨、机场了,到最近的州市,也得十几二十个小时。老李本想抱怨几句,可看到吴超的匆忙和坚毅,看到他长长的络腮胡、满袖的烂泥巴、一屋的施工图,所有怨气,统统咽了回去。
新的霞光,系上了怒江大桥。老李坐着车,摇摇晃晃,正赶往丽江。刘师傅开着车,过了省界,正要入藏。而吴超,仍在丙中洛的工地上,与设计师一起,测绘、讨论、修改。他们奔赴和别离的,都是异乡,又都是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