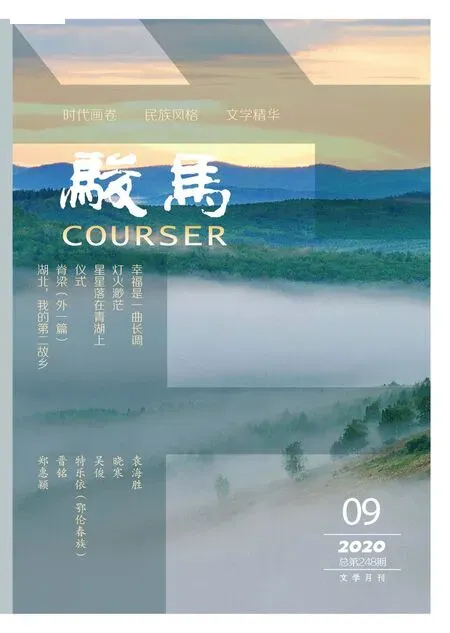灯火渺茫
■晓寒
暮色落下来,对岸亮起了灯,东一盏西一盏,稀稀拉拉的,隔着江望过去,像一段模糊的往事。这是白昼和傍晚的临界点,眼前晦明不定,湘江如一匹黑色的丝绸,沿着脚下的泥巴路铺开。涛声已经停止,夜航的船挣脱黑暗的纠缠,顺流而下,忧伤的汽笛声从江面上升起,仿佛一个长夜赶路的人发出疲惫的叹息。
右边有一片带状的树林,正是早春,光秃秃的枝丫还笼罩着冬天的阴影,在不断加深的暮色里,像老人叉开的手指。穿过林子,是一个名叫洛口的古镇,我刚刚从那里过来,这是个崛起于唐代的镇子,在千余年时光的流转里,已经衰败得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青石小路上,看不到人影,路边那一大片砖瓦房子,早已人去楼空,其中一些院子,荒草没过了膝盖,上面散落着瓦砾和墙皮,从中仿佛能听到那些冷清的长夜里,寒蛩在老木窗外低低地吟唱,雨水嘀嘀嗒嗒地跌落。
风从江的另一头涌过来,似乎是受了谁的欺负,气呼呼地叫着,粗鲁地掀起我披着的外衣,把夜色搅得越来越黏稠,仿佛一伸手就能捞起一大把。转眼之间,远处的山峦、楼群、道路被一一抹平,大地终于在这样的黑暗里实现了一马平川的梦想。我在夜色里摸索着往前走,如一只受惊的蝼蚁。灯火和我隔着一条江,它橘黄色的光芒,慷慨地赐予了眼皮底下的流水、草木、素不相识的脚步,单单撇开了我,把我丢在另一条岸上。
这样的夜晚,熟悉又陌生。它如离开我多年的事物,落满了时间的尘埃,它又隔得那么近,时常于雨水淋漓的午夜偷偷潜入我的梦里。以至于有很多时候,我在梦中的呆坐、奔跑、哭泣,遭遇一条人迹罕至的河流,见到那个心仪已久的姑娘,都不得不在这样的背景里进行。我被黑暗吞噬的影子犹疑不定,像一部小说中卑微的角色,接受命运的驱使去往某个地方,即将穿越一段漫长的黑暗。除了对岸那几盏摇曳的灯火,四周黑茫茫的,赖以指示方向的星辰隐藏在云朵深处。我怀疑脚下的路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它像一根长着青苔的老藤爬向遥远的过去,这条路上一无所有,我只能和自己单独相逢。
每个人对故乡的定义都不相同,我把故乡定义为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村庄以外的地方,我都把它们视为异乡。我那个村子,藏匿在深山里,像一个孤独的隐者,几乎可以忽略它的存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我对它的依赖。我离开它将近二十个年头,但隔一段时间我便要回去看看,它不同于任何一个地方,总是用我儿时的情怀,容纳我的欢乐和悲伤。
我的中学是在外乡的一个小镇上念的,每个周末准时回家。仍然记得那些傍晚,一场小雨刚刚收尾,潮湿的泥腥味跟着风拍打着路边的叶子。两边的山脚下,亮着零星的煤油灯火,冷冷落落,像深巷里偶尔响起的一两声犬吠。橘黄色的光在蒙着薄膜的窗户上晕开,淡淡的一圈,幽微、暗哑,仿佛风雨来临之前的花朵,随时有可能凋谢。它不能像太阳一样,把在远处山顶和湖泊嬉戏的光线送到我的脚下,为我划开一道蜿蜒的光明。不过黑暗只能把山、田垄和房子淹没,它奈何不了我。哪里是房子,哪里是稻田,哪里有一条水沟或者一扇篱笆,我都了然于心。我的心里,有一张回家的地图,我利用一个又一个日子,在地图上把这些东西标注得一清二楚。就算黑暗吞噬了一切,我照样能走得顺顺当当,当我最终停下脚步的时候,出现在眼前的,必然是我今夜要回到的那盏灯。
我把脚步放慢,并不是怕摔倒,我觉得只有从容才配得上黑暗,黑暗里的事物,都呈现出一种缓慢的调子,像秋日黄昏的风中飘来的在山寺中唱诵的经文。祖父先前习惯在夜里做茶,将炒熟的茶叶堆在一个簸箕里,坐在靠背椅子上慢慢地揉。灯盏搁在远远的地方,昏暗的光将他和簸箕的轮廓勾勒在土墙上,模糊、冷清,像是一幅被风化了的壁画。他说要把茶揉得紧实,根根如针,就得慢,得静,得耐着性子。他要在留住雨露和阳光的同时,把闲淡、寂静和黑暗揉进每一片茶叶,使它们成为其中非物质的成分,他相信只有在暗淡的灯光里才能把这样一件考验耐心的事情做好。白天,因为光芒的存在,彼此都成为透明的部分,有人忙着奔跑,有人使劲追赶,从早晨到傍晚,像倾泻的流水,哗啦一声就结束了。我曾经多次在星光沉暗的夜晚穿过长长的黑暗,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思想也青睐于从容,只有在慢节奏或者几近停滞的黑暗里,它们才各就各位,长出翅膀,无所顾忌地飞翔。在故乡那些云低雨落的黑夜里,它领着我走出过村庄,看到了城市灯火照耀下的楼群,公园里骄傲的花朵,挽着手走着的男人和女人,在铁轨上沉默的火车。我对此产生过一种病态般的憧憬,它像一个幻影般的女人俯在我耳边温柔地呢喃,加剧了我青春的孤独和悲伤。
我丢下一片结满茶子的油茶林,经过一座独木桥,踩在树皮剥落的松木上,鞋底像搽了油,身子微微地摇晃,再绕开一道牵牛花凋谢的篱笆后,听到了汩汩的水声。那是一条长满杂草的水圳,马齿苋、鹅肠草、鱼腥草、油烛青互相纠缠,试图阻止流水的通过,以便脱离长期置身水中的苦恼,赢得更多的养分和阳光,让自己长得像树一样高大。经过漫长的对抗,从春天到秋天,它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白天在水草里不停蹦跶的小虾已经安静下来,即将进入梦乡。水圳过去那一大片田垄,一直延伸到山脚。绿得发亮的草把田埂裹了起来,风起的时候,像元宵节时农家汉子手中翻滚的草龙,虫子们结束一天的歌唱之后,躲在里面各做各的梦。田里的晚稻正在扬花,被雨水打湿的稻花比白天听话多了,乖乖地躺在稻穗上,一旦早晨到来,接受阳光轮番的抚摸,挣脱雨水的桎梏之后,它们便借着风势,在稻田的上空自由飘洒,像那些又细又轻的雪沫儿,漫不经心地飘在傍晚的天空,还没落地,便消失在风中。这样的时候,我总会很自然地想到唐诗,子规声响在路边的林子里,柳絮没完没了地在眼前飞。稻花的香是克制的,不过土生土长的庄稼人总能敏感地捕捉到,它携带着泥土和叶子的味道,把收获的信息送进每一扇敞开的大门。水稻是村庄的轴心,所有的人所有的日子都围着它们转,它们用一根根秸杆,轻而易举地绑架了一个村庄的命运。
我停下脚步,面对着这片稻田,稻子你拥我挤,像森林一样蓊郁,那里面有父亲的影子、邻居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它们已经嵌进了泥土的深处,就像泥土已经植入了我们的血肉一样。湿润的空气中,飘来一股甜丝丝的味道,让我感受到呼吸的快感。蛙声时断时续,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萤火在眼前轻快地划过。这些向我描述宁静的事物,像谁在琴弦上调校出没有任何杂质的音调,浮现出秋天夕阳中那种淡淡的清冷。这是卸下了伪装的土地,是一个秋天美好的归宿。如果我是入侵者——来自异乡的游客,这样一个夜晚,将沿着我记忆的路径一直通向人生的尽头。但我不是异乡客,是喝着这个村庄里的水长大的,在落地的那一刻,就和村庄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就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植物,脚下的根不停地吸取有限的养分,让生命得以延续,却又因此成为它的羁绊,残忍地剥夺了它的自由。
在前面等我的是一片芭蕉林,还在老远,我就听到了芭蕉叶子互相扭打的声音,透着一股侵骨的凉意。芭蕉林上去是叶三的泥巴屋,叶三是村庄里书读得最多的人,当了两年民办老师,因为养不活一个家,又回到了村里。每年夏天暴雨来临时,倾斜的雨点越过田垄,像银色的箭镞一样射在他家那扇高高的垛墙上,在上面留下了数不清的斑斑点点。垛墙的木窗台上放着几个粘满灰尘的空酒瓶子,吊着一个用来做种的皱皱巴巴的丝瓜,一道驱邪的符歪歪斜斜地贴在旁边。窗户上蒙着厚厚的薄膜,是拆了装尿素的袋子钉上去的,阻断了风和阳光的进入。屋里潮湿幽暗,青苔相中了这间屋子,在长着霉点的墙脚安下身来,开始呼朋引伴。
我时常不无忧伤地看到叶三站在垛墙下抽烟,用废书纸卷成的喇叭筒在他嘴角时明时暗。他抬头望着天空,表情复杂而古怪,目光里充斥着沮丧,他大概想到了天空离他是如此的遥远。几乎与此同时,他那张承受了三十多年风霜的脸上又洋溢着向往,就像一只养足了精神的鸟一样,随时准备展开自己的翅膀飞上天去,找到主宰他幸福的神祗。有几次我以为天上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抬头望了一眼,天空和平时一样,送来刺目的阳光和堆积的浮云,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我的心里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加快脚步走过去,当我走出老远回过头时,看到叶三还保持着那个样子。
真正主宰叶三幸福的不是天上的神灵,是脚下的田垄和他屋边的菜地,还有他那四个年龄相仿好像永远长不大的女儿。这几乎是他生活的总和,他白天黑夜牵挂和愤怒的所在。他那个肥胖的老婆经常跳起来骂他,还说你读过高中,你是个什么男人?就是个没用的东西。刚开始他受不了这样的咒骂,抽过他老婆几个耳光,他老婆摸着脸上的手指印呼天抢地,寻死觅活,后来叶三度过了情绪的襁褓期,适应了那种坦诚的刻薄,再也不回一句话。
叶三的窗前没有灯火,恐怕是灯油已经耗尽了,他的泥巴屋成了一片黑暗的虚无。他有可能蜷缩在荒芜的床角进入了梦中,梦见自己正抬着头站在高高的垛墙下抽烟。阳光纯粹,从嘴里冒出的烟丝历历可数,天空高阔,白云浩荡。
我加快了脚步,走过叶三那栋储存在我记忆中的泥巴屋,一路上仍在想着他抽烟时的样子,我不愿想起这么一个人,就如我不想经过年初屋门口一样。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更改的,譬如一朵花的凋落,并不取决于花朵自身,早在它还是蓓蕾的时候,雨水和阳光就已决定了它的命运。过两座拱桥,一个水坝,我还是被这条狭窄的泥巴路送到了年初的屋门口。他家那条跛了条腿的黑狗叫了起来,隔着那么阔的田垄,我还是从它的叫声中听到了戒备和敌意。过了片刻,它大概认出了我,知道我是它上屋的邻居,作为一条聪明的狗应该知道,对着一个熟悉的邻居狂吠,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还有一点最要紧的,它担心把我惹毛了,拿着棍子对它一顿暴打,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因此叫了几声后便往墙脚那个洞里一钻,陷入了沉默。
夜,重新回到死寂。
年初已经五十多岁了,儿子快三十了还没娶亲。自从他老婆离开后,他便染上了酒瘾。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只有喝酒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只是他并非经常有酒喝,他舍不得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换成了穿肠而过的毒药。他得把钱攒起来给儿子娶妻生子,这是他余生唯一的目标,否则他这条根就断了,那是他到死都无法接受的事实。酒瘾上来的时候,他就在屋里不停地转圈,像一只屁股上着了火的蚂蚁。和酒瘾搏斗,成了他一门不便公开的职业。灯光从他那扇挂着红薯和镰刀的窗口漏了出来,光晕左右摇摆,像风一样拂过墙根高高垒起的柴禾。杉皮屋檐上,几根悬着的南瓜藤正在向着枯萎走去,像即将晒成干的死蛇一样。这个时候还点着灯,以他的俭省,似乎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喝过酒了,叉开手脚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如雷的鼾声像欢乐的鼓棰擂响一面巨鼓。当然更有可能是酒瘾又犯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期待着酒精来慰藉他长夜里孤独的灵魂,他正处在一种煎熬中,无心去吹灭那盏可以省下一笔钱的灯。
小河就在路边,河水在黑暗中哗哗地流淌,它一年四季都是那么清亮,看得见河床上微小的沙粒,鱼虾若无其事地游动。我希望这样一条河流不单单流过村庄,也流过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雪白的流水,日夜不停地欢唱,那是一件多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惜这样带着仪式感的欢乐,我只能到梦中去享受,等我从梦里脱出身来,现实会像子弹一样,再一次击中我的悲伤。村庄里的百多个人,似乎都来自于一个蹩脚的作家脸谱化的虚构。一个人仿佛是另一个人的替身,即使把叶三和年初的名字互换过来,或者把他们的名字和我交换,也无非是年龄和脸不同而已。
走到村窝口的时候,有些累了,我站在一棵驼背茶树下歇息。月光穿破云层,透过茶树的枝丫洒落下来,像一片片巨大的冰冷的鱼鳞。鸡冠鸟在远处的山上一刻不停地咻咻地叫着,似乎有太多的东西要向这个世界倾诉,我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只听懂了其中忧伤的成分,余下的都成了我在这个夜晚无法破解的秘密。身边的树丛里,鸟在扑腾着翅膀,小兽踩断枯枝的声音嘁嘁嚓嚓地传来,这是故乡的山野偏爱的一种表达,带着秋天夜晚的幽暗与岑寂,像一首诗中冷清的词语落在纸上,缓慢而独立。
小路下面有一片梯田,夹在两座山的中间,如同一架用来登山的梯子。可能是紧靠着山的缘故,经常有野猪在黑夜里出没。有一夜一个邻居刚好碰上,巨大的响动让他误以为是老虎来了,吓得他爬到一棵树上大喊救命,等我和大哥打着手电筒赶到时,稻子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到处是野猪留下的乱七八糟的脚印。这时候,野猪没准就潜伏在对面的山沟里,睁大眼睛望着我,和隐身在荒野伺机出击的狼群、豹子、鹰隼一样,只等我离开便一跃而起。再有一个多月,稻子就要熟了,它们得弄清楚,附近是否有陷阱、索套、铁夹子或者一咬就会把它们的嘴巴炸得血肉横飞的“美食”,这些都是足以置它们于死地的东西。这件事情只能在黑夜里偷偷地完成,白天出来,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倒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在这之前,我十分羡慕那些鸟兽,翻山越水,随心所欲,拥有大地和天空的自由。我从未认识到,野猪有野猪的难,那些以凶猛著称的狼群、豹子、鹰隼也一样,活得并不比人容易。
上一段陡坡,过一片竹林,不用看就知道,熟悉的灯光正悬在老屋的窗前,这是母亲为我点的一盏灯,摇曳在半山腰里,像山谷里燃起的一堆篝火,孤独地搏击着黑暗,山水的凄冷和窗口的温暖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怯怯的摇曳的不仅仅是灯火,还是母亲摇摆不定的心。一个女人为了他的儿子,即使日子再难,也可以不计成本,把这样一盏灯一直点到天亮。
当我站在大门口的青石板上时,我看到了母亲映在窗上的影子,她正在一针一线地纳鞋底,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不敢伸手去敲门,我害怕听到母亲迅速答应着起身向我走来,鞋底踢踏踢踏地响着,像一个农夫拖着疲累的脚步归家的回声。
我攥紧了肩上那个黄色的书包,这是我又爱又恨的东西。我隔了两年重新把它背上,又随时有可能失去。我和年初属于同一类人,和一样东西长期暗中搏斗,打发着一个个摇摇晃晃的日子。母亲是一个忧虑的女人,她的忧虑来自于油又没有了,米不够吃了,孩子的衣服破得穿不了了。和父亲的天性乐观不同,她的忧虑时刻写在脸上。每年开学的那几天,我不敢去看母亲的脸,来自于那张脸上的无奈与彷徨,几乎要将我心头那一抹微光淹没,即使是乐观的父亲,这个时候也变得沉默寡言,把头深深地埋在盘绕的烟雾里。
我把书包放下,又背起,如此几个回合,最终败下阵来,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站把自己丢进了一列绿皮火车。彼时已是深夜,车厢里静得让人恐慌,我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脸包围着,这些从未见过的脸逐渐臣服于睡眠的淫威,仿佛正在向着自己的脖子坠去,暗沉沉的呼吸声冲破不同的喉咙和鼻孔,从四周一拨接一拨地传来,回响在同样暗沉沉的车厢里,像是来自地层的深处。他们趴着,仰着,或者靠在同伴的肩上,如洪水肆虐之后沙滩上那些姿势各不相同的死鱼。火车像一条带电的蜈蚣,似乎是被自己的电流灼伤了,满含痛苦与愤怒,沿着冰冷的铁轨向着黑暗一路窜去,即使累得气喘吁吁,也没有停下的征兆。窗外还有灯火,孤零零的几盏,悬在江边、山脚、隧道口、桥头。这些灯光,细细的一粒,像天边即将坠落的星光,把原本近在眼前的事物拉向遥远虚幻,呈倍数地放大了这个夜晚的荒凉,仿佛有一双巨大的手,把这些山水往北挪移了一大截。我望着闪烁的灯火,期待中的种种美好,山水、城市和村庄在眼前一一掠过的惊喜,深夜时分把我丢在异乡的茫然和新奇,那种脱离一种生活即将进入另一种生活的焦灼和憧憬,顷刻之间荡然无存。我只希望火车再跑慢一点,这样我和我的村庄便靠得近一些,仿佛从来不曾走远,胸膛仍然贴着那片土地。另一方面,我又希望火车像风一样狂奔,以便我尽快抵达那盏陌生的灯火,那里是我暂时寄存肉身换来衣食的地方。
大半生的日子,我一直走在一条路上,我独自穿过黑夜的村庄,找到那个破败小镇的一条老巷子,任由绿皮火车带着我穿过层层叠叠的黑暗,以及背着简单的行囊不管不顾地来到这座城市,我不厌其烦地做着这些事情,就是为了找到命运给我准备的那盏灯。我始终相信,这世间有那么多的夜晚,这夜晚有那么多的灯火,总有一盏灯为我亮着,那是属于我的光芒。
就像今夜,我深陷在这陌生的夜色里,终究要脱身而去,回到一盏灯,尽管我看不到那盏灯,它还藏在黑暗的深处。或许这个时候,还有和我一样的人,正在黑暗中摸索着向一盏灯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