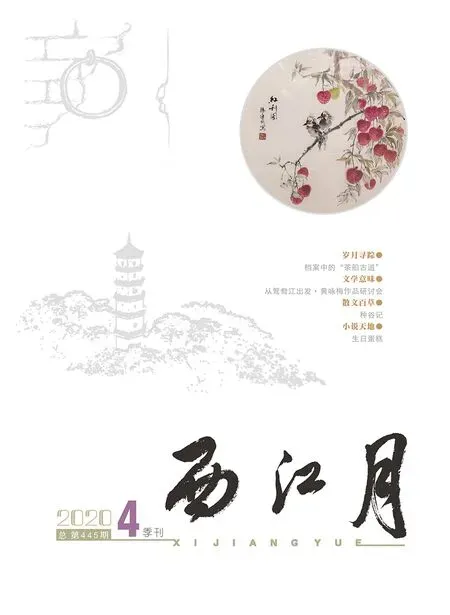种谷记
覃炜明
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种谷,技术比较落后,耕作方式比较原始,谷子的产量也就比较低。一般每亩产量只有四五百斤(好的有六七百斤,差的只有一百来斤),交了公购粮,留下来分配的谷子,必须掺和一些番薯、木薯之类的杂粮,组合着吃,才勉强够一家人糊口。几年下来,种谷的很多画面自然铭刻在年纪小小的我的记忆中了。
种谷,首先是选择谷种。那时候还没有推行杂交水稻,大多数生产队的谷种都是自产自留。在前一年的谷子中,选择产量高、禾杆壮的谷子做谷种。每亩稻田大约要预留十几斤谷种,在专门场地晒干,放专门仓库保管。日子再艰难,谷种都是不能吃的(在我的家乡,如果有人说某人“吃谷种”,就是说他断自己的后路)。当时有一种谷子叫“鸭乸粘”,因为谷粒饱满,适合做谷种。后来才知道,自留谷种的做法,实际很不科学,因为稻谷这样自然留种,会逐年退化的,今年产量好,明年就不一定产量好。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主要原因就是谷种质量得不到保证。
上一年留下的谷种,到第二年春天再播种。播种前,要先将谷种用水浸泡(我们叫浸谷),等待发芽,然后再把发芽的谷种撒到秧田里,精心呵护,等待长出秧苗,方能插秧。
浸谷的时间,一般是在二月初二(社节)以后,那时候天气寒冷,必须将谷种放在竹箩里,淋上十几度的温水,每天淋一两次,等待谷种发芽(在我的家乡,经常需要用井水浇灌谷种,谷种才能发芽)。大约四五天,一粒一粒谷种就会长出弯弯曲曲的白色新芽,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带芽的谷种撒到秧田里。秧田就设在要插秧的稻田一角。如果要插一亩水田,就要准备好大约一分地的秧田。稻田翻耙之前,秧田要先放水,用人力或耕牛把秧田踩成稀泥,然后用锄头刮成微微的拱形(鸡背状)。这时候的秧田,可以映照出干活的人的面容,撒谷种的时候,场面就是一幅非常生动的水墨画。
正常情况下,大约二十多天,谷种在秧田里就长成了秧苗。如果遇上天冷,谷种上边的新芽被冻死了,长不出秧苗,这个时候就要再浸泡谷种,及时补上。如果秧苗刚刚长出,遇上寒冷天气,则要给秧苗盖上薄膜,保持秧苗生长需要的合适温度。小时候看到农民呵护秧苗的艰辛,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
秧苗长到高约二十厘米,就可以进行插秧了。插秧之前,一边要犁田耙地,一边要给秧苗施肥。给秧苗施肥,要先淋上大粪,然后在粪水上撒一层草木灰或草皮泥,这样插下去的秧苗定根快,并且容易生长。我十四岁回家当“准农民”,干得最多的活就是给秧田撒草木灰,或者放草皮泥。我们这些劳动力不强的孩子,由一个叫全家泰的老人(大家叫他五翁,我则叫他五伯爷)带着,专门给刚刚浇了大粪的秧田撒干肥。五伯爷那时候大约七十岁,由于无儿无女,一把年纪还要操劳农活。不过他非常乐观,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有时候还会跟我们说一些笑话。又因为他舌头大,发音特别有趣,经常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都特别喜欢跟着他干活。记得有一年生产队开会,他把衣服穿反了,来到会场上反反复复扣不上布做的扣子,后来大家都发现他衣服穿反了,一起哈哈大笑,他笑呵呵说:“这个老婆子,故意出我洋相。”原来他的衣服是出门时五伯娘帮他套上的,他归咎于老太婆故意开她的玩笑。
在种谷整个过程中,插秧的场面是最热闹的。因为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在插秧的现场,农民各有分工。力气大的男人,一般专职做铲秧。所谓铲秧,就是把秧苗连根带泥,用秧铲铲起来,铲成长长一块。把这些秧泥装在簸箕里,每一个簸箕大约可以装十块。然后由另外一拨负责担秧的人,把这些秧泥挑到田基上。每一个簸箕的秧泥上面,放有一块竹子做的牌子,插秧的人就是靠这些竹牌子计算自己的工作量,多劳动多记工分。
插秧的现场,最活跃的是那些插秧的人,一般都是女人。她们卷起裤脚,扎着头巾,有时候还要把腰间的衣服用带子扎紧。因为插秧的时候,全程弯腰,手上全是泥巴,头发不能够散开,否则会掉到泥水里,衣服不能够太宽松,否则容易走光。开始插秧的时候,只见那些女人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拉着空秧盆,到田基上抽起一簸箕秧苗,“笃”的一声,放到秧盆上,然后拉着有些重量的秧盆,一幅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来到自己认定的位置。她们检查一下头上、腰间,然后把袖口再往手臂上扎实,拿起一块秧泥,轻轻一抛,秧泥下边用手掌托着,秧泥上边几乎要顶到胳膊,一切准备好了,女人弯下腰,另一只手就像小鸡吃米一样,飞快地摘下秧苗,往水田里插下去。每一块秧泥,大约有四五根秧苗,非常均匀。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起插线上,插着插着,有人就插到了后边,越插越远,把手慢的人抛在前边。整个插秧的场面生动的诠释了你追我赶的含义。而这个时候,水田上边,也会流传各种各样的荤段子。当时十六嫂刚刚从一个叫莫冲的地方嫁到我们村,每逢听到这些荤段子,她的脸上都会泛起特别好看的红晕。
插秧时节,一般在清明前后。那时候也是各种作物播种的时候,种花生,种芋头,种豆角……农民们非常忙碌。有时候干完了生产队的活,回家以后还要干自留地的活,天亮出门,天黑才回家吃饭,成为常事。如果遇上寒冷天气,插秧时,一双脚长久泡在冷水里,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家乡有这样的谚语:正月冷牛,二月冷马,三月冷插田妇娘乸。反映的就是插田妇女之苦。在我的家乡,插秧的活虽然大部分是女人干,但是也有男人插秧的速度和女人不相上下的。在中巷生产队,有一个驼背的男子,跛着一只脚,外号“阿蹩”,因为他体力不足,不能够铲秧,也不能够担秧,只好混在女人堆里插秧,据说他插秧的速度完全是“须眉不让巾帼”,很多女人都喜欢和阿蹩一起干活。
如果说,插秧的场面,是种谷过程最热闹的场面,你追我赶,热火朝天,那么耘田的过程,就多多少少有一点写意。一般来说,秧苗插下去以后,过一个月或两个月,要先后进行两次“耘田”。所谓耘田,是用人工把水稻周边的杂草去除,另一方面通过耘田,用脚将禾苗周边的泥浆翻新,再向水稻追加肥料,这样水田容易吸收肥料,增加水稻产量。
耘田的过程,有点像在水田里跳舞。大家不分男女站成一排,对着每一株秧根,运动脚板,不需要过分用力,也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如果遇到野草和杂禾,则要把这些野草和杂禾连根拔起,以免它们和稻子抢肥料。整个耘田的过程,大地满眼碧绿,田野上到处欢声笑语,各种段子也在田间流传。当然,有时候这些段子指向了现场的某一个人,也可能马上演变为口角,乃至几拨人当场破口大骂。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生产队长只好下令:“收工,收工!”一场“战役”,就此得以偃旗息鼓。
一般而言,稻谷的生长过程大约需要几个月。清明插下的秧苗,经历两轮耘田,然后自由生长,大约两个多月,最多三个月,就可以长出谷子,慢慢成熟等待收割了。如果是晚稻,禾苗抽穗扬花的时候,一旦遇上“寒露风”,多半会影响产量。我的家乡有句谚语:禾怕寒露风,人怕老来穷。所以水稻生产,一定要赶季节,过了季节经常影响产量,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颗粒无收。
收割水稻,可能是整个种谷过程中最辛苦的工作。因为水稻成熟(特别是早稻)的时候,是一年中天气最炎热的时候。早稻成熟时,田里的水都没有放干(晚稻是放干的)。这个时候收割水稻,割稻子的人,弯腰一天,满面汗水,再被禾杆扫过来扫过去,扫得奇痒难受。打谷子的人,那时候用的是一个四方的木制的谷桶,用人力一把一把的将谷子甩打到谷桶里。一身的汗水和泥水混合在一起,这个时候谁都没有讲话的兴趣,都在默默地干活。后来生产队购买了几台打谷机,这种打谷机依靠一只脚踩踏,产生动力,再通过齿轮带动中间转动的打谷的中轴,打谷的效率自然提高了。但是这种打谷机很笨重,需要两个人甚至四个人抬起来才能够转移场地。尽管如此,当年也从这样的打谷机身上,体会到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句话的厚重分量。
离开家乡以后,我虽然还干了几年体力活,但是对农活自然是越来越生疏了。现在种谷怎么播种,怎么插秧,包括还要不要耙田、耘田……我已经不知道。而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水稻产量的提高,加上种谷的劳动成本太高,据说很多地方种植水稻的面积都开始缩小了。无论将来科学如何发达,我相信水稻种植一定属于千秋万代的事情。因此,纪录一下我的种谷经历,这也是一段历史,一段人与自然相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