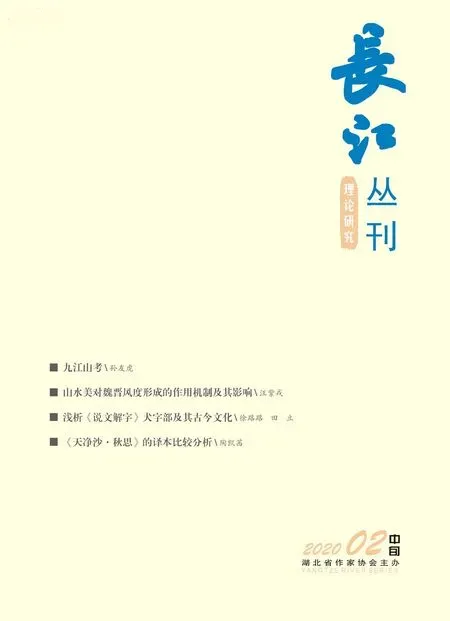“民胞物与”与“浑然与物同体”比较研究
■谭阳伊/湖南科技大学
一、前言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是张载之学的核心,语出《西铭》,这既是张载对人生理想的确定,也是张载对社会理想的描绘。这一思想可分开理解 :“ 民吾同胞”重在人与人的关系,“物吾与也”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者既各有侧重,又具有内在联系。张载作为儒家统绪之一,“民胞物与”思想自然是对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程颢认为《西铭》这篇文章的儒家思想意思极其完备,是仁的本体。他在《识仁篇》中强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一个整体,甚至包括仁者自己也浑然其中,这样天地万物就与自己休戚相关了。在这里程颢和张载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互相诠释,而程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成为仁者,所需做到的修养工夫。
二、“民胞物与”与“浑然与物同体”本体论比较
张载是在气化宇宙观基础上,精心描绘出“民胞物与”的人生理想。张载认为无论是具有具体形态的万物,还是没有具体形态的“太虚”都是由“气”这个最高的物质范畴所构成,“气”聚合到一起就能产生具体有形的事物,“气”散扩分开就会化作没有具体形态的“太虚”。没有具体形状的“太虚”是“气”的本来存在状态,所以“太虚”和“气”是统一的,“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并且,张载认为“气”是一个包含阴阳两端的统一体,“气”的内部是阴阳两方面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因而“气”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生成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既然作为个体的人皆是由“气”构成的,那么在这个“气化”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也就否定了人不是脱离于社会而存在的单个人。在张载“民吾同胞”思想中,他所设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道德秩序的规定:整个世界的人都是一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犹如同胞之间的关系那样亲密,每个人都怀揣博大的胸襟,保持着博爱的情感,认同并融入到这个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便是一个和谐统一的大家庭,每个人的社会理想也就随之实现。
一方面,张载确定个体在宇宙中是渺小的。他在气学的基础上,将人生位置的确定提升至了宇宙这一宏观层次上。时间和空间是个体存在的方式,张载以“气”——在他看来最高的物质范畴,来解说个体的生死是“气”的大化流行。这种形而上的阐释,也就表明个体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渺小的,所以张载说 :“ 予兹藐焉”。另一方面,个体在宇宙之中有着卓越的位置,具有能动的性质。在人生位置的确定上,张载体现出了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并没有将个体视为被动的、消极的个体,而是看作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个体作为主体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并且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能动的性质不是个体已经完全拥有、完全表露,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创化之中。所以张载说 :“ 天地之帅,吾其性。”总之,个体在明确人生位置渺小的同时,也可以能动地追求与他人、他物的友好关系。
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张载推崇他的“太虚即气”的气化宇宙观,而程颐推崇他自己所体悟出来的理学,二者的观点可以说截然不同的。但是,程颐唯独对张载包含“民胞物与”思想的《西铭》一文特别推崇,可以说张载这一思想就是在程颐这里得以抬升,从而对后世的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程颐主张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体就是天理,仁体天理,即明白万物一体的观念,这一思想根本缘于儒家的仁道。在儒家的仁道观中,仁体即绵延的生命本体,其特点在于感通,感通的功能就是生命的层层推扩,推扩的过程没有止境,所以说仁体“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体为万德之本,知道此理又以诚敬保存。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故须反身而诚。
三、“民胞物与”与“浑然与物同体”工夫论比较
张载在气化宇宙观基础上建构了他的道德价值境界。首先,乾坤天地是天地万物的道德价值来源。《西铭》中第一句说 :“ 乾称父,坤称母。”张载借《易传》中的“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合起来“乾坤”也就是天地,亦是“天道”。张载用天地是万事万物的父母这一比喻,说明“天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有价值的根源。其次,“天道”与“人道”是本来内在于一体的。“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藐”就是幼小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天道”面前是如此的渺小,而“天道”是如此高远。人并非与“天道”截然分离没有任何关系,“人道”浑然处于“天道”之中,所以,“天道”不是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恰恰相反“天道”是内在于人的。最后,天地万物和人都是休戚与共,流行运动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也就是说“天道”充满我的身体,而“天道”的统帅便是我的本性,天地万物和人都处在“气”的大化流行之中。最终,个体体认到天地万物是我的同伴,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友好的关系。只有当每个人都觉悟到了这个宇宙层面的人生理想,才会意识到自身所能具有的超道德的自由人格。
张载提出要想上达这一境界需要做到“大心”。我们要想具有这一境界所展现出的博爱精神,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的眼前利害得失,而应该用自己的道德理性,思考感觉之外的事物。从而补充人的感官感知外物所形成的见闻之知,进而完完全全地体认天下万物。圣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尽心知性,在于不被见闻之知束缚自己道德理性思考,从而能通过自己“大其心”的工夫,获得关于天地万物整体的道德体认,具有博大的胸怀。可以看出,张载所说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与孟子所说的“尽心则知性知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上达这一境界需要“变化气质”存养“天地之性”。张载说 :“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这是张载所确定的人性,能够经过后天的努力,使其向善。这里的气质之性可以视为人的感性欲求,天地之性可以视为人的善良本性。古代先哲致力于对自身内在思想道德的修养,追求贤人、仁人、圣人、大丈夫、真人等理想人格。张载将圣人这一理想人格的界定为除去气质之性对自身天地之性的遮蔽,使得天地之性得以彰显。当今的人所能掌握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为什么依旧摆脱不了人对物的依赖?除了社会分工依旧存在等一些客观原因外,实际上还有放滥自己感性欲求等主观原因,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放心”。现今许多人十分关注自己外在的小财小富的得失,但是,对自己良知良能的丢失却不知道找寻回来,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
最后,张载主张做“大人”,亲身参与实现理想社会。尽管人与万物都具有天道,而不是某一个体独自拥有,但是唯有“大人”才能体现这个天道,“大人”想自立必须让他人、他物自立;想成就自己必须让他人、他物成就;想知自己必须知人知物,想爱自己必须爱人爱物。张载提出 :“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正蒙·乾称篇》)可以看出张载倡导要尊重年长的人、慈爱孤弱的人,对那些丧失行动能力残疾的人、失去至亲鳏寡孤独的人、流离颠沛无处诉苦的人,要像对待自己同胞兄弟姐妹那样亲爱他们、保护他们、拯救他们。
程颐称赞《西铭》的观点主张,是极其纯净没有杂质的儒家学说,这是秦朝、汉朝以来的儒家学者所未曾达到的高度。程颐认为《西铭》一文通过由形上推理至形下,求得儒家道德义理,将张载之前的儒家学者未能言及的地方,进行了扩充,确确实实与孟子的性善论和存心养性的论述有着相同的贡献。可见,程颐将张载《西铭》认可度之高,极为推崇其形上和形下的各自说明。
程颢进一步提出为仁首先需要“识仁”。“识仁”,也就是觉悟人自身所本身具有的良知良能。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认同,认同良知良能就是自己所本有的,认同善的道德价值。只有做到了“识仁”才能为后面的工夫打好基础。在做到“识仁”之后,进而要做到“诚敬”的工夫。也就是说当人们确信自身本具的良知良能之心后,又要求人们存习自己的良知良能。在这一点上,基本上与张载的“变化气质”的修养工夫相通,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看作与天地万物血脉相连,从而能够意识到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实实在在地去爱护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可以看出,程颢对张载的继承与发扬更加侧重于“仁之体”方面。